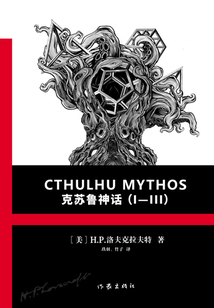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22評論第1章 H.P.洛夫克拉夫特生平
All H. P.Lovecraft's Life
作者:Setarium
1890年8月20日上午九點,霍華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出生在羅得島州首府普羅維登斯城,父母均為早期英國移民的后裔(這一點使重視血統與出身的洛夫克拉夫特在日后十分自豪)。他的父親,溫菲爾德·斯科特·洛夫克拉夫特(Winfield Scott Lovecraft),時任格爾漢姆銀器制品公司[1]的銷售員,時常因生意出行,旅居于美國東海岸。在洛夫克拉夫特三歲時,溫菲爾德因梅毒晚期引發精神失常而住院,直至五年后的1898年在波士頓的巴特勒醫院逝世。據日后洛夫克拉夫特的書信稱,當時他被告知自己的父親是因工作壓力而精神崩潰,所以就醫,而洛夫克拉夫特本人是否得知其父入院與死亡的真正原因,今日已不可知。
父親住院之后,撫養小霍華德的重任便落在了其母莎拉·蘇珊·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Sarah Susan Phillips Lovecraft)與他的兩個姨媽,及其外祖父,惠普爾·范·布倫·菲利普斯(Whipple Van Buren Phillips)——一位在當時頗有名氣的富商身上。當時,洛夫克拉夫特家家境富足,五人均住在其外祖父的大宅里。宅邸中專門設有一間藏書室,作為私人圖書館所用,而洛夫克拉夫特童年的絕大多數時間便是在那里度過。也因此,洛夫克拉夫特在孩童時期展現出驚人的文學天賦——他兩歲便能背誦詩詞,在六七歲時便可寫出完整的詩篇。在外祖父的鼓勵下,他閱讀了諸多文學經典,例如《天方夜譚》、布爾芬奇[2]的《神話時代》與《伊利亞特》《奧德賽》等古典希臘神話,而外祖父也時常給他講述一些哥特式恐怖故事。這成為了他對恐怖與怪奇的興趣的源頭,同時,對神話的閱讀也激發了他對古典文學乃至一切古代文化與事物的愛好。這一愛好最終伴隨了他一生。也是在這時,年輕的洛夫克拉夫特自《天方夜譚》中汲取靈感,創造了“阿卜杜·阿爾哈茲萊德”(Abdul Alhazred)這一人物,日后在其筆下成為了《死靈之書》的作者。
青年與少年時期的洛夫克拉夫特常受身心疾病,特別是心理疾病所困擾。他在八歲入學于斯雷特街公學,之后因健康狀況數次休學。但這并沒有影響洛夫克拉夫特對知識的渴望,并因對科學的愛好首先自學了化學,而后轉向天文學。在興趣的指引下,洛夫克拉夫特開始自己編輯出版了幾期膠版印刷刊物——《科學公報》(The Scientific Gzette)(1899—1907)與《羅得島天文學雜志》(The Rhode Island Journal of Astronomy)(1903—1907)——在社區與好友之間傳閱。之后,洛夫克拉夫特于赫普街高中就讀,并在其中結識了諸多好友。也是在這時,他開始為如《鮑圖基特谷拾穗者》《普羅維登斯論壇報》(1906—1908)與《普羅維登斯晚報》(1914—1918)等當地報刊撰寫天文學或類似的科普專欄。
1904年,惠普爾因中風去世,而家人對其遺產的經管不當使洛夫克拉夫特家很快陷入了財政危機。因此,洛夫克拉夫特與其母不得不搬離外祖父的豪宅,既而入住于安吉爾大街598號的一座小屋。外祖父的去世,外加失去了自己心愛的家園,使洛夫克拉夫特遭受了沉重的打擊,甚至一度令他產生了自殺的念頭,不過這時他的求知欲仍遠勝于這些消極情緒。然而在1908年,洛夫克拉夫特因自己無法學好高等數學,進而無法成為他理想中的職業天文學家引發了精神危機,又在不久之后演變為嚴重的精神崩潰,因此在高中畢業前夕退學。雖然他在日后堅稱自己獲得了高中文憑,但他始終沒能完成高中學業,而未能入讀心儀的布朗大學深造天文學也成了洛夫克拉夫特一生中無法釋懷的遺憾。
在退學后的1908年到1913年里,洛夫克拉夫特變成了一位隱士。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幾乎對外界完全封閉的時光,除了繼續自學天文學與詩歌創作之外毫無建樹——據其高中同窗回憶,當時洛夫克拉夫特很少出門,而當他外出時則會將衣領拉得很高,對任何人,即使是高中時的好友,也會回避有加。他的母親也仍被丈夫的死所困擾,因而歇斯底里患上了抑郁癥,并與洛夫克拉夫特處在一種愛恨交加的關系中——大多數時候她仍會像洛夫克拉夫特小時候那樣疼愛他,但有時又會莫名其妙地對他數落謾罵,稱他相貌丑陋——這也進一步導致了洛夫克拉夫特的自我封閉,也是他在日后近乎自卑自謙的源頭。
將洛夫克拉夫特從避世帶回到現實的事件多少有些偶然。在閱讀了大量當時的通俗雜志后,他對業余雜志《大船》[3]中的一位名叫弗萊德·杰克森(Fred Jackson)的浪漫愛情作品意見甚多,認為它們庸俗不堪,因此寫了一封抨擊其作品的信。這封信于1913年發表后立刻引來了杰克森的支持者一連串的反攻,洛夫克拉夫特不甘示弱,相繼在《大船》和類似業余雜志的來信專欄展開還擊。這場激烈的爭論引起了當時的聯合業余刊物協會(United Amateur Press Association, UAPA)——一個由美國各地的業余作家與雜志出版人構成的組織——會長愛德華·F.達奧斯(Edward F.Daas)的關注,他在不久后邀請洛夫克拉夫特加入了這一組織。洛夫克拉夫特于1914年初應邀入會,并在1915年自創雜志《保守黨人》(The Conservative)(1915—1923)以發表自己的詩作與論文。在后來的歲月中,他又當選為協會會長與首席編輯,也曾在聯合業余刊物協會的競爭對手,全國業余刊物協會(National Amateur Press Association, NAPA)任會長一職。參與業余寫作協會是洛夫克拉夫特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一系列事件不但將他從可能默默無聞的一生中所拯救,他在其中所結識的業余作家也對他多加鼓勵,使他重拾了一度遺棄的小說創作。雖然直至1922年他的作品大多仍是詩篇與論文,但是在這段時間里他還是寫出了如《墳墓》與《達貢》等具有代表性的早期作品。同時,他也通過這些業余作家協會的聯絡網認識了日后眾多志同道合的好友。
洛夫克拉夫特的母親因每況愈下的身體與精神狀況,在1919年的一場精神崩潰后被送入了其夫曾經入住的巴特勒醫院,并于1921年5月24日在一場失敗的膽囊手術后離世。雖然在1908—1913年的五年中,洛夫克拉夫特與母親之間有過些許不和,但他們仍舊保持著親密的關系,即使在她入院之后兩人之間仍有密切的通信來往。毫無疑問,母親的去世是繼外祖父的死以及失去童年家園后,洛夫克拉夫特所再次承受的巨大打擊。這使他又一次短暫地陷入了與世隔絕的狀態,不過幾周后便從中恢復,并在1921年7月前往波士頓參加了一次業余刊物集會。也是在這一場會議中,他遇到了自己未來的妻子,索尼婭·格林(Sonia Greene)——一位比自己年長七歲、居住在紐約的衣帽商人。兩人一見如故,洛夫克拉夫特還特意在1922年前往索尼婭在紐約布魯克林的公寓看望她,最終在兩年后的3月3日成婚。不過,洛夫克拉夫特的姨媽——他僅存的兩名親人——對兩人的交往在一開始便毫不贊同,認為自己的外甥不應被商人的銅臭味所玷污,所以洛夫克拉夫特在婚禮結束之后才向她們傳達了自己婚事的消息。婚后,洛夫克拉夫特搬入了索尼婭在布魯克林的公寓。在這場婚姻的初期,一切看似對兩人都十分有利:洛夫克拉夫特因其早期作品被雜志《詭麗幻譚》[4]所采納,正式開始了職業寫手的生涯,同時索尼婭在紐約第五大道的衣帽店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這段時間可能是洛夫克拉夫特生命中唯一的高潮。在初來紐約時,他在書信中將其描繪為“如同僅在夢里才能一見的城市”;而在索尼婭的陪伴下,他的飲食也改善了很多,開始略微發福。對他來說,未來充滿了希望,同時在這段時間他也接觸了鄧薩尼勛爵的作品,并為其中奇偉瑰麗的夢之幻境而著迷,進而寫出了如《烏撒的貓》《塞勒菲斯》《蕃神》《伊拉農的探求》等鄧薩尼式風格濃厚、奇幻大于恐怖的作品,與之前愛倫·坡式的哥特恐怖風格大相徑庭。夫婦兩人在這一段時間里也合作完成了一篇名為《馬汀海灘的恐怖》的小說。
不過好景不長,兩人不久便遭遇了困境。索尼婭的衣帽店因經濟原因破產,她本人也不堪重負而病倒,不得不在新澤西的一家療養院養病;洛夫克拉夫特因不愿搬去芝加哥而拒絕了《詭麗幻譚》雜志副刊的編輯職位,并試圖在其他領域尋找工作,但他并沒有在其他領域的工作經驗,加之年齡偏高(34歲),所以一籌莫展。1925年1月,索尼婭應聘前去克利夫蘭工作,而洛夫克拉夫特則因廉價的房租搬去了人種雜居的布魯克林雷德胡克(Red Hook)區,落腳于一間單人公寓中。
盡管洛夫克拉夫特在紐約結交了許多朋友——弗蘭克·貝爾科納福·朗、萊恩哈特·克萊納,以及詩人薩繆爾·洛夫曼等——他仍因與日俱增的孤獨感,以及在移民潮中無法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只能靠撰寫毫無文學價值的庸俗文章以及代寫與修訂工作勉強度日,這一切所帶來的挫敗感令他日漸沮喪。洛夫克拉夫特十分看重出身與血統,并因自己對早期殖民時代的認同感,認為盎格魯-撒克遜文明是世界上最為先進的文明。此時,自己作為一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后裔,面對來自東歐、中東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大潮卻幾乎無法維生。這使他對自己眼中的“外國人”逐漸產生了偏見與抵觸,而他作品的主題也由起初對家鄉的懷念(《避畏之屋》,1924年,取材自普羅維登斯)轉向了消沉與厭世(《他》和《雷德胡克的恐怖》均寫作于1924年,前者表達了他對紐約的厭惡,而后者更像是他對外來移民的恐懼與憎恨之情的宣泄)。最終在1926年,他在與朋友的書信中聲明自己正在計劃返回普羅維登斯,隨后下定了回家的決心;雖然洛夫克拉夫特在書信中仍稱對索尼婭愛慕有加,但他的姨媽依然堅決反對兩人的婚事。于是,洛夫克拉夫特與索尼婭的婚姻在維持了七年后(其中兩人相處的時光僅有三年)于1929年終結。離婚后,索尼婭在加利福尼亞定居,并在那里度過了余生。
洛夫克拉夫特在1926年4月17日返回普羅維登斯,入住于布朗大學以北的巴恩斯街10號。這一次他并沒有像在1908年一般使自己在默默無聞中消亡——直到1936年去世為止,這最后的十年是洛夫克拉夫特生命中最為高產的時光,也是在這十年里,他脫離了之前愛倫·坡或鄧薩尼勛爵的風格,明確地在作品中建立了獨屬于自己的筆風。在他的寫作生涯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克蘇魯的呼喚》《瘋狂山脈》《印斯茅斯的陰霾》《敦威治恐怖事件》《查爾斯·德克斯特·沃德事件》與《超越時間之影》均是這十年間的產物。同時,作為堅定的古典愛好者,他也時常沿著北美東海岸旅行,到訪一個又一個古城鎮的博物館與歷史遺跡,最遠曾前往加拿大的魁北克城。也是在這時,他通過數量驚人的書信聯絡,認識了諸多在當時仍處在事業初始階段的年輕作家,如在他死后大力推廣其作品、為保持其作品流傳而功不可沒的奧古斯特·德雷斯與唐納德·汪德雷,20世紀60年代著名科幻與奇幻巨頭弗里茨·雷柏,《驚魂記》(Psycho)小說原作者羅伯特·布洛克等,并鼓勵他們積極創作,同時無償為他們修改文章。洛夫克拉夫特也是在這時結識了大名鼎鼎的羅伯特·E.霍華德——“蠻王柯南”系列的作者。兩人進而成為了好友,在書信之間對如人類文明的發展等主題展開了諸多討論,而兩人的作品也因此相互影響。但洛夫克拉夫特終究心儀于生養自己的土地——新英格蘭地區與普羅維登斯城,于是,它們也成為了他這十年內作品靈感的源泉。同樣也是在這時,他開始對美國以及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產生了興趣:因大蕭條對經濟與政治的影響,他開始支持羅斯福的“新政”并逐漸成為了一位溫和社會主義者,但同時對古典文化以及英國王權的認同又使他對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5]產生了好感(不過他卻鄙視希特勒,認為希特勒不過是效仿墨索里尼,是嘩眾取寵的小丑),并持續了對從哲學到文學,再到歷史與建筑學知識的自學。
不過,洛夫克拉夫特一生中最后的數年間卻充滿了艱辛。1932年,他的一位姨媽,安妮·E.菲利普斯·加姆威爾(Annie E.Phillips Gamwell)病故,洛夫克拉夫特便于1933年再次遷居至學院街66號,與另一位姨媽,母親的姐姐莉莉安·D.克拉克(Lillian D.Clark)同住。而他后期的作品因其長度與詞句之復雜,向雜志社的推銷開始逐漸變得困難。加之洛夫克拉夫特表面上處世態度波瀾不驚,但私下里對其作品受到的批評卻十分敏感,尤其是《瘋狂山脈》在科幻雜志《驚奇故事》(Amazing Stories)中首先慘遭大篇幅修改,進而飽受看慣了浮夸的“太空歌劇”式科幻作品的讀者的猛烈抨擊,這對洛夫克拉夫特的打擊巨大,使他幾乎產生了放棄寫作的念頭。同時,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幾年里,外祖父留下的家產已然消耗殆盡,洛夫克拉夫特被迫又回到了在紐約時期的老本行,以代寫與修訂工作掙取收入,依靠廉價的罐頭食品(有時甚至是過期的罐頭食品)度日。在這段時間里,他唯一的慰藉來自于與自己保持通信的友人們——1935年,居住在美國東海岸的朋友陸續前來拜訪洛夫克拉夫特,而他也在1935年夏季南下至佛羅里達州探望好友羅伯特·巴洛,之后在秋季迎來了巴洛北上的旅行。
1936年,摯友羅伯特·E.霍華德自殺身亡,這使得洛夫克拉夫特在震驚與悲傷之余備感疑惑。但當年冬季的旅行,以及業余出版協會同好威廉姆·L.克勞福德決定將《印斯茅斯的陰霾》以書籍形式出版仍為他帶來了些許驚喜——即使這個版本錯誤連篇且漏洞百出,篇幅與正規書籍相比也只能算是小冊子,但這仍是洛夫克拉夫特在活著時唯一以書籍形式出版的作品。
艱辛的生活,以及長期因財政窘境而養成的糟糕的飲食習慣,終于在1937年初使洛夫克拉夫特一病不起。他的病情在年初開始迅速惡化,僅用了幾個星期便使他因難以忍受的疼痛而無法自由行動。因此他推掉了諸多寫作任務,其中包括一項來自英國出版商、很可能會使其從通俗雜志寫手轉為主流作家的項目。當友人們在2月底拜訪洛夫克拉夫特時,他已經因劇痛而臥床不起,并終于在3月10日入住普羅維登斯的簡·布朗紀念醫院。1937年3月15日早晨7點15分,在入院五天后,霍華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因小腸癌與世長辭,終年四十六歲。
因其生前并不十分出名,在洛夫克拉夫特死后,他的作品面臨著被遺忘的危險。而他那些以通信而結識的朋友在此刻則幫了他的大忙——奧古斯特·德雷斯與唐納德·汪德雷為了使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保持流通,不惜自己出錢成立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使他的作品能夠流傳至今;眾多曾受他鼓勵與指導的作家在日后都為紀念洛夫克拉夫特寫下了回憶錄。不過,洛夫克拉夫特能有今日的影響力,且受世人敬仰,除了友人的不懈努力,與其作品的獨特性,以及其中超越時代的洞察力是有著無法分割的關系的。誠然,他的一些作品的主題在今日看來早已不被時代所接受,而他的筆風也有些許迂腐,但其中對于人類過度探索未知的警示,以及在人類無法企及的未知邊緣所徘徊的恐懼卻是永恒的——無論在史蒂芬·金膾炙人口的小說中,還是在克里夫·巴克筆下光怪陸離的扭曲異界里,抑或在托馬斯·黎哥提對形而上的黑暗的探尋中,我們都能看到洛夫克拉夫特的影子。可能正如洛夫克拉夫特自己在他的著名論文《文學中的超自然恐怖》中所提,黑暗題材終于在今日成為了大眾矚目的焦點。但無論如何,洛夫克拉夫特早已與世長辭,如今只有他的作品留下供眾人品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