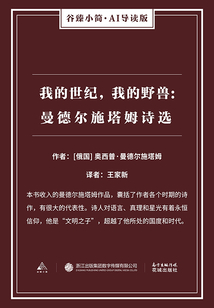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毫無疑問,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歌及其命運多年來一直吸引著中國的詩人和讀者們。第一次將普希金之后俄羅斯詩歌的“白銀時代”展現在中國讀者面前,他所引用的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詩,也像珍貴的種子一樣落在了北島、多多那一代人的心中。正因為這種揮之不去的“情結”,自20世紀90年代起,我開始收集和閱讀曼德爾施塔姆等詩人的英譯本。曼德爾施塔姆已經是一個獨創性的思想者和成熟的詩人。他的詩學中所隱含的東西詩人跨越時間、用新的語言重塑過去經驗的能力在一系列大膽的智力突襲中顯現出來。
正是以這種詩學意識和藝術表現,他既與同時代的“未來主義”先鋒派拉開了距離,也擯棄了象征主義的夢囈及其對超驗世界的迷戀,他使詩歌回到了具體可感的現實中來。正是在這個新的基礎上,如布羅茨基所指出的那樣,他還要運用亞歷山大詩體這種“記憶載體”去呼應和溝通另一種“記憶載體”奧維德的六音步詩體,以把俄國的語言和詩帶回到他所說的“世界文化”之中。
這就是曼氏早期的詩歌抱負。在朝向一種新古典主義詩學的同時,曼氏還愈來愈專注于語言和形式,稱“詩即手藝”。
而這樣一位詩人的命運不能不注定了是悲劇性的。卻不幸生于一個歷史的大災變年代。從那時起,這種洞見就使他成為最具有當代性的詩人,從更深的層次上說,也即俄羅斯最具有政治性的詩人。
這樣的詩,不僅表現了詩人的“奧維德情結”,也令人驚異地預示了他自己的命運,我相信很多中國詩人和讀者都曾為它的悲劇性音調所震撼,并體會到這里面的巨大沖動。當然,詩人對此的反應是同情而并非譴責,正如他對世紀野獸也有幾分哀憐。曼德爾施塔姆拒絕讓詩歌成為任何政治的工具。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詩人心中與時代爭執、抗辯的那個聲音愈來愈強烈了,他對于“悲劇必然性”的體味也愈來愈刻骨。
對于曼氏作為詩人的一生,已有很多研究,讓我們記住布羅茨基的描述:這是一個“為了文明和屬于文明”的詩人,這體現在他那“俄國版本的希臘崇拜”中,同時體現在他對時間主題的處理中。
現在看來,曼德爾施塔姆的選擇,使沃羅涅日從此成為俄羅斯文學地圖上不可磨滅的一個座標。這是直接卷入了與命運的搏斗,而在這個過程中,詩人與他的語言一種幽靈般的語言也建立了更為密切的關系。正是在沃羅涅日的三年期間,在艱難絕境中,曼迎來了自己一生創作的巔峰期。他在這期間的詩有近百首,編有三冊《沃羅涅日詩鈔》,其數量之多,占了他全部詩作的近三分之一。的確,沃羅涅日帶給了詩人藝術上的新生,他在這里所寫的詩,不僅更直接,也更新奇,更富有獨創性,充滿了詞的跳躍性和“句法上的突變”。正是與大地、苦難和死亡的深切接觸,詩人擁有了他的“最后的武器”。而隨著經驗的沉淀和感受力的深化,這片流亡者所“耕耘”的黑土地,也愈來愈令人驚異了。
曼氏在沃羅涅日的日子,曾被阿赫瑪托娃準確地概括為“恐懼與繆斯輪流值守”。既有創作的興奮,大自然的撫慰,也有無望的掙扎,以及焦慮的等待。但是,真正讓一個詩人不朽的,卻是那與死亡的抗爭,那種災難中的語言迸發和閃耀。曼氏流放后詩風的變化,是主題上的、意象和詞語上的,也是句法上的、發音上的、語言姿態上的。這就是說,即使身處逆境,曼氏依然是一個存在意義上的詩人,他要力圖穿過個人的苦難經歷來為事物重新命名,并對世界進行勘探和測量。
從很多意義上,曼德爾施塔姆是幸運的,因為有娜杰日達這樣的女性在陪伴他,有阿赫瑪托娃這樣的偉大對話者在關注他,有那么一種神圣女性的“低部沉重的高揚歌聲”在伴隨他,這就是為什么在他最后的詩中會深深透出那種“知天命”的坦然和超然。詩人最終達成的,仍是對愛、信念和苦難的希望本身的肯定。他最后所做的,仍是要這首詩的接受者和他一起向遠方抬起頭來,因為那即是命運最終的啟示。
曼德爾施塔姆最后的詩,就這樣展現了他與他的時代的劇烈的沖突。但它們不僅僅是犧牲者的文獻,它們是血的凝結,也是語言本身所發出的最后痙攣,是深入到了存在的內核中的具有永恒價值的詩篇。
詩人的悲劇性命運,他的“永久的心跳”和為此付出的全部代價,為這種“真實”提供了永久的保證。前些年,在我翻譯策蘭的時候,我就意識到我也必須去翻譯這位被策蘭視為親人和精神先驅的詩人。在那里,圍繞一個提供形式和真實的中心,圍繞著個人的存在,以其永久的心跳向他自己的和世界的時日發出挑戰。這顯示了從被毀棄的一代的廢墟中升起的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歌,與我們的今天是多么相關。
為此,有時一首詩的翻譯我參照了多種英譯和研究資料,也經過了再三的修改或者說“聚焦”過程。
在本雅明看來,正是通過這種偉大作品才具備的“可譯性”,原作將自己授予譯作,而譯者也有可能以充滿創造性的翻譯,使其本質得到新的綻放。不管怎么說,只有以這樣的“再創造”,才配得上曼德爾施塔姆在語言上的創造力,也只有這樣來譯,才能給我們自己的漢語詩歌帶來一種灼熱的語言上和精神上的沖擊。顯然,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多位英譯者都談到了在英語中再現俄語詩歌特有的音樂性的巨大困難。希尼稱贊了默溫的翻譯,但也委婉地指出在將曼氏的格律詩翻譯成自由詩時弱化了原詩“雕塑般的聲音”。從這個意義上看,曼德爾施塔姆幾乎不可翻譯,但詩的生命就在于翻譯。詩的不可譯性也在召喚著翻譯。而我作為一個漢語譯者,也必須找出其音律、節奏方面有效的替代方案,以這樣的漢語句法來譯,不僅強調了意象本身,也形成了一種節奏和張力。我只是想更深刻、也更有力地傳達出來自漢語世界和我個人生命中的共鳴,只是想通過翻譯刷新和深化人們對這位天才的悲劇性詩人的理解,并盡力把他最閃光的東西揭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