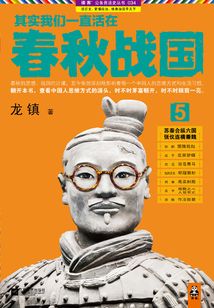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6評論第1章 三家分晉(1)
公元前455年夏天,晉國晉陽的空氣驟然緊張。
晉國亞卿、趙氏宗主趙無恤突然率領大批家臣和族兵,從首都新田返回晉陽。
無恤進城后,即令緊閉城門,加派崗哨,給護城河加注河水。種種跡象表明,一場戰爭即將來臨。
對于上了年紀的晉陽人來說,戰爭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晉陽城也經歷過一場大戰。那是公元前497年,晉國發生內亂,中行氏和范氏討伐趙氏,先主趙鞅退守晉陽,抵擋兩家聯軍達四個月之久。后來因為智、魏、韓三家出手相救,晉陽才得以解圍。
時隔四十二年,晉陽再度面臨戰火的考驗。令人感慨的是,斗轉星移,風流水轉,這一次進攻晉陽的不是別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晉陽的智、魏、韓三家。
在這四十二年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變成今天的敵人?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從那個名叫荀瑤的人說起。美德,獨缺仁義。長得漂亮,武藝高強,能言善辯,才藝出眾,敢于任事,這都是好事,但是如果內心無仁義的話,這些美德只會助長他的暴戾之氣。恕我直言,如果您一定要荀瑤繼承家業,智氏必亡。
荀申考慮再三,還是立了荀瑤為世子。
智果帶著家人跑到晉國太史那里,改了族譜,宣布脫離智氏,自稱輔氏。這就意味著,此后智氏家族不論興廢存亡,都與他沒任何關系了。
直到二十多年后,人們才會拍著大腿,稱贊智果是個聰明人。但在當時,人們對他的行為并不理解,他們看到的是,智氏家族在荀瑤的帶領下越來越強盛,甚至超越了荀躒和荀申的時代。
公元前472年,荀瑤以亞卿的身份率軍討伐齊國,在犁丘與齊軍相遇。戰前,他親駕戰車巡視晉軍,戰馬突然受驚,朝著齊軍陣營狂奔。以荀瑤的駕車技術,要控制住戰馬是輕而易舉的事,但他意識到,如果這樣做,會讓齊國人誤以為自己膽小,于是他放馬疾馳,一直沖到齊軍營壘前才掉頭。此舉極大鼓舞了晉軍士氣。在后來的戰斗中,荀瑤又身先士卒,奮勇殺敵,親手擒獲齊將顏庚,取得了此戰的勝利。
公元前468年,荀瑤伐鄭。齊國權臣陳恒(即田恒,古代陳、田同音,陳氏即田氏)率軍救援鄭國。荀瑤得知消息,主動引兵退去,但是派人給陳恒送去一封信。信上說:“您的祖先是陳國公子,陳國的滅亡(陳國于公元前478年為楚國所滅),鄭國是出了力的(完全是胡說),所以寡君才派我攻打鄭國,是為了替陳國報仇。但是您卻跑來救援鄭國,讓我感到很不理解。難道您一點都不在乎陳國嗎?既然您都不在乎,我又有什么所謂呢?所以我主動撤軍了,恕不奉陪。”這封信東拉西扯,不著邊際,顯然只是為了調戲對方。陳恒閱后大怒,但又想不出什么詞來回罵,只得提筆回信說:“老是欺負別人的人,不得好死!”
不消說,荀瑤很快贏得了晉國人的好感。該有的他都有了:顯赫的家世,尊貴的地位,偉岸的身軀,機智的談吐,一往無前的勇氣,貨真價實的戰功,還有調弄敵人的閑情逸致。他宛如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光芒四射,照耀晉國,連趙鞅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
公元前464年,荀瑤再度伐鄭,趙鞅派世子趙無恤隨行,擔任荀瑤的副手。
趙鞅的本意,一是讓無恤親歷戰場,獲得經驗和名聲;二是向荀瑤表明,晉國日后必定是荀瑤的天下,請他對無恤多多關照。可以說,這既是“知其雄,守其雌”的政治智慧,也是一位垂垂老矣的父親對兒子的關懷與呵護。
但是,荀瑤對趙鞅的拳拳之心并不以為意。
據《左傳》記載,這一戰進行得并不順利。晉軍包圍了鄭國的首都新鄭,卻遭到鄭軍的猛烈反擊,攻勢一度受阻。
戰斗最危急的時刻,荀瑤命令身邊的無恤出戰,帶領敢死隊強攻新鄭的南門。
聽到這道命令,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冷兵器時代,攻城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強攻更是險上加險。守城者可以憑借著城墻和箭垛保護自己,而進攻者則暴露在箭矢檑木之下,還要扛著云梯等攻城器具越過護城河,極易傷亡。如果沒有充分的理由,進攻方一般不會采取這種“殺敵八百,自損三千”的笨辦法。
退一萬步說,即便是強攻,也不該由無恤來擔當。這倒不是說無恤不能冒險,而是沒有讓一支軍隊的副統帥去當敢死隊長的道理。
大伙都將目光集中在無恤身上,看他如何應對。
無恤只說了三個字:“主在此。”
主在此,這三個字看似簡單,實則可軟可硬,大有乾坤——軟一點說,“有主將在,我不敢爭先。”硬一點說,“你是主將,為什么不自己去?”總之就是我不去,你看著辦吧!
荀瑤盯著無恤看了幾秒鐘光景,突然操起案幾上的一個銅酒壺,朝無恤狠狠砸去,發瘋似的罵道:“懦夫!賤人!你這樣的人居然也能當世子,我真替趙氏感到羞愧。”如果不是無恤躲得快,再加上眾將死死勸住,荀瑤非將無恤砸死不可。
無恤灰頭土臉回到自己帳中,家臣都很憤怒,摩拳擦掌,要去和荀瑤拼命。無恤用一句話將大伙都勸住了。
“父親立我為世子,不就是因為我能忍嗎?”
強權之下不屈服,不妥協,但也不亂來,這就是在亂世之中的生存法則。
事情到此,本來應該過去了。但荀瑤顯然不解恨,從鄭國回來后,他專門找趙鞅談了一次,一本正經地建議趙鞅廢掉無恤,另立世子。
趙鞅聽了,一臉錯愕,不明白眼前這個人是過于顢頇(mānhān)還是過于跋扈。要知道選擇繼承人乃是家族內政,豈容他人插手?更何況趙鞅現在是晉國上卿,智氏家族雖然強盛,荀瑤也不過是個亞卿,憑什么對他的家務事指手畫腳?
荀瑤卻沒有關注趙鞅的情緒變化,仍在那里滔滔不絕,極力向趙鞅證明:不廢無恤則趙氏必亡。
可是趙氏亡不亡跟他有什么關系呢?站在競爭者的角度,趙氏的繼承人越是不堪,不是對他越有利嗎?
趙鞅半瞇著眼睛,聽著聽著,終于弄明白了:荀瑤這個人,從骨子里頭有一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氣質,但凡他看不慣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如果是這樣的話,選擇外柔內剛的無恤來對付他,倒是沒錯了。趙鞅睜開眼睛,老練地打了幾個哈哈,說了幾句無關痛癢的話,便將荀瑤打發走了。
新鄭城下的這場沖突,為九年之后的晉陽之戰埋下了伏筆。
外柔內剛的趙氏族長趙無恤
其實趙鞅選擇無恤為繼承人,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趙鞅骨子里頭是個舊式貴族,對一切傳統事物抱有一種溫婉的敬意。他當權的時候,晉國公室已經極度衰落,大權完全把控在四大家族手里,但他以上卿之尊,仍然保持了對公室的尊重(至少表面如此),在那個年代是不多見的。
在選擇繼承人的問題上,一開始他也是嚴格遵守周禮的規定,立了嫡長子伯魯為世子。
那時候,無恤還小,而且是奴婢所生之子,在眾多兄弟中,地位最為低下(是以荀瑤稱之為賤人)。趙鞅即便不立伯魯,恐怕也輪不到無恤。
直到有一天,一位名叫姑布子卿的相士來到趙鞅府上。趙鞅將自己的兒子都叫出來,讓姑布子卿給他們看相。姑布子卿看完之后便搖頭說:“您的兒子不少,但都不是大將之才。”
趙鞅很緊張:“照您那樣說,趙氏豈不是沒希望了?”
姑布子卿說:“我進來的時候,看到一個小孩在院子里玩泥巴,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兒子?”
趙鞅趕緊叫人將那小孩帶進來,拍著腦袋想了半天才說:“這個是我兒子,叫什么來著……對了,無恤。”
姑布子卿站起來說:“這位才是真正的貴人。”
趙鞅說:“您不是開玩笑吧?這孩子的母親,是我從狄人那里買來的奴婢,一點也不貴!”
姑布子卿高深莫測地說:“天命所賜,雖賤必貴。”趙鞅再問時,他便笑而不答,飄然而去。
趙鞅將信將疑,但是從此之后,便開始注意觀察無恤的言談舉止,發現這個小孩確實有與眾不同之處。
有一次,趙鞅將自己總結的一些人生格言書寫在竹片上,發給兒子們學習。過了些日子去檢查,其他人都背不出來,只有無恤倒背如流,還能舉一反三,說出自己的見解。
趙鞅很驚奇,便問無恤為什么學得這么好。無恤從懷里掏出一個錦囊,小心翼翼地打開,從里邊掏出那幾塊竹片,說:“我每天將父親的教導帶在身邊,不時拿出來溫習,自然記得牢。”
這件事無疑大大增加了無恤在趙鞅心目中的分量。
過了一些年后,無恤也成年了。有一天趙鞅將兒子們全召到跟前說,他在常山(即北岳恒山)埋藏了一件寶貝,誰先找到它,就有重賞。
大家趕緊駕車出發去尋找,唯有無恤慢慢吞吞,不緊不慢,最后一個出發。幾天之后,大伙都空手而歸。無恤回來之后,卻對趙鞅說:“我找到了。”
“哦?”趙鞅很高興地說,“在哪?”
無恤說:“您所謂的寶貝,就是我們可以憑借常山之險,吞并代國。”
代國位于今天的山西東北與河北西北交界之處,是白狄人建立的國家。趙鞅為了拉攏代國,將自己的女兒(也就是無恤的姐姐)嫁給代王為妻。但是在他心里,早就盤算著如何吞并代國來擴大趙氏的地盤,同時獲得代地盛產的良馬。
這么多兒子去找寶貝,只有無恤看穿了他的心思。經過這件事后,趙鞅下定決心,廢除伯魯,改立無恤為世子。
公元前458年,趙鞅去世。無恤辦完喪事,還沒脫掉孝服,就帶人跑到夏屋(今山西省代縣),請姐夫代王前來相聚。
代王欣然赴會,他把這次宴請當作無恤上臺后向他示好的表示,沒有想到會有什么陰謀。
席間賓主相談甚歡,從無恤的臉上看不出一絲失去父親的悲痛。如果是中原人,必定能夠看出不對勁的地方——父親去世不久,就算是裝也得裝出悲傷的樣子,怎么能夠談笑風生呢?但是代王顯然不懂中原文化,他毫無防備,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的隨從也喝得東倒西歪。
這個時候上來一隊光膀子的精壯廚子,一人拿著一個長把銅勺,給客人分羹。無恤咳嗽一聲,用寬大的袖子將臉遮住。代王還沒反應過來,腦袋上已經挨了銅勺重重一擊,立馬腦漿迸裂。他帶來的人也被如法炮制,悉數殺死。
無恤迅速興兵北上,輕而易舉拿下代國。
如果要問無恤這一票撈得有多大,其實也不算太大——一百多年后,趙氏的后人趙武靈王在這里設置代郡,下轄區區三十六個縣而已。
無恤的姐姐聽到代王被殺的消息,呼天搶地,悲痛萬分。當無恤派人接她回晉國,她哭泣道:“因為是自己的親弟弟,就忘記殺夫之恨,是不仁;因為自己的丈夫死了,就怨恨弟弟,是不義。”于是跑到一座山上磨笄(jī)自殺。
所謂磨笄,就是將發笄磨得尖尖的。代地的百姓憐憫這位剛烈的女子,將她自殺的地方稱為磨笄之山(今河北省張家口)。而后人以“磨笄”代稱后妃自殺殉國,典故就出于此。
無恤為了姐姐的死,很是內疚。那時候伯魯已死,無恤便將代地封給了伯魯的兒子趙周,稱之為代君。他這樣做,也許是想告訴天下人,趙無恤不是一個無情無義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并非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趙氏。
智伯的致命弱點:貪婪與傲慢
趙鞅死后,荀瑤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晉國上卿,三位亞卿分別是趙無
恤、韓虎(韓不信之孫)和魏駒(魏曼多之子)。
荀瑤一上臺,便雷厲風行地干了幾件大事。
公元前458年,荀瑤謀劃進攻仇由。仇由是狄人建立的山中之國,交通極為不便,戰車無法通行。荀瑤命人鑄造了一口大鐘作為禮物,載在牛車上送給仇由國君。仇由人歡欣鼓舞,在山中開辟道路迎接。道路開好后,晉國大軍隨著那口大鐘一擁而入,消滅了仇由。
公元前457年,荀瑤劍指中山。中山地處今天的河北省中西部,是白狄的一支——鮮虞人建立的國家。據《呂氏春秋》記載,中山軍中有一種“力士”,身穿鐵甲,手持鐵棒,“所擊無不碎,所沖無不陷”,戰斗力極強。但是荀瑤顯然不怕中山力士,一舉攻下了窮魚之丘(今河北省易縣),后來又派人攻占了左人和中人(今河北省唐縣),使中山遭受重創。
公元前456年,荀瑤又命韓虎、魏駒率軍討伐居住在伊水和雒水之間的戎人部落,攻取盧氏城(今河南省西部),將戎人在伊、雒之間建立的大小政權全部摧毀。這一次行動的意義重大,“自是中國無戎寇”,解決了自春秋時期以來就一直困擾中原的戎患。
應該說,荀瑤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燒得很旺,贏得了滿堂喝彩。有人甚至認為,若荀瑤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必能成為晉國中興的名臣。
但是很顯然,荀瑤的志向不在于晉國中興。
他將三位亞卿召集起來開了一個會,討論原來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歸屬問題。
這些土地,自從二氏滅亡后,一直由公室代管。荀瑤提出,現在公室人才凋敝,難以管理這么大片的土地,不如分給四大家族來管理。
三位亞卿都無異議——誰會有異議呢?當然,有一個人很有意見,那就是晉國名義上的統治者晉出公(晉定公于公元前475年去世,晉出公是他兒子)。
晉出公一怒之下,向齊、魯兩國發出密函,請求他們發兵“清君側”,討伐四大家族。這下捅了馬蜂窩,四大家族聯手起來,將晉出公趕出了晉國。
國不可一日無君。晉出公出逃后,一個名叫姬驕的公室子弟被立為國君。
姬驕是晉昭公的曾孫,他的祖父公子雍是晉昭公的小兒子,他的父親公孫忌跟荀瑤的關系很好。因為這層關系,他才被荀瑤選中。姬驕在歷史上是如此不重要,以至于在《史記》的記載中,他一時被稱為晉哀公,一時被稱為晉懿公。而在其他史料中,他又被稱為晉敬公。到底哪個才是他真正的謚號,沒有人花心思去考證。
荀瑤現在成為了晉國的第一人,智氏家族也成為晉國的第一大家族,實力遠在另外三家之上。從公室瓜分來的土地,智氏獲得最多,超過其他三家的總和。他按捺不住興奮的心情,大興土木,給自己蓋了一座宮殿。
宮殿落成之日,家臣都來祝賀。有一位名叫士茁的,一直拖到晚上才來。荀瑤半帶著醉意,不無炫耀地問士茁:“這房子壯觀嗎?”
士茁回答:“壯觀是壯觀,但是下臣總覺得有些擔憂。”
荀瑤說:“你有什么好擔憂的?”
士茁說:“下臣為智氏掌管文書,看到書上說,高山峻嶺,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土質不肥。您這房子造得太壯觀了,我怕它不太適合居住。”
士茁這些話,記載于《國語》。該書還煞有介事地說,荀瑤的宮殿建成后三年,智氏果然滅亡,仿佛兩者之間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系。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荀瑤的致命傷,絕不是他喜愛豪宅。喜愛豪宅有什么錯呢?家大業大了,建所大房子難道不應該嗎?
荀瑤最大的問題,還是在于他目中無人。
有一次荀瑤從衛國出差回來,韓虎和魏駒設宴為他接風。好好的一場宴會,卻因為荀瑤戲弄韓虎并侮辱其家相(家臣之長)段規,最后不歡而散。
事情具體經過,據明人馮夢龍杜撰,是荀瑤喝醉了,對韓虎說:“我曾經查遍史冊,天下與您同名的,只有齊國的高虎和鄭國的罕虎,加上您也就三個人。”
韓虎無言以對,段規在一旁聽了,很不是滋味,站起來說:“君子以禮相待,不直呼其名,請不要拿我家主人的名字開玩笑。”
那段規生得五短身材,站在韓虎身邊,頭頂還不到韓虎的胸部。荀瑤也不生氣,用手拍著段規的頭頂說:“小朋友知道個啥,這不是你玩兒的地方,小心三虎把你給吃了!”說完一陣大笑。
段規氣得渾身發抖,但是不敢發作。韓虎則佯裝喝醉,閉著眼睛說:“智伯說得對啊!”然后告辭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