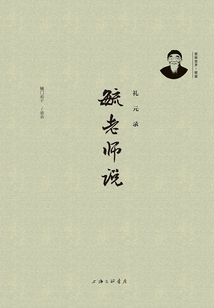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編序
毓老師如是說
毓老師全名“愛新覺羅·毓鋆”,大清開國功臣禮烈親王代善第十一世孫,父親命名“金成”,“毓鋆”為宣統皇帝溥儀御賜嘉名。
毓老師生于清光緒三十二年夏歷丙午年(公元1906年),與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儀同年生,六歲進入毓慶宮成為溥儀伴讀,師事陳寶琛、羅振玉、王國維、鄭孝胥、柯劭忞、康有為等名儒,曾留學日本、德國。
毓老師在“滿洲國”擔任御前行走,參贊機要,銜命訓練“滿洲”兵,負責內政、治安、軍事、外事等工作,曾奉諭見過希特勒、墨索里尼。在紛亂的民國初期,毓老師自言“四十四年間經二帝五朝歷八雄十代”;因為身份特殊,毓老師與國共重要人物、當年政軍界名人均有接觸,也因曾手握“滿洲”軍政實權,足以影響東北政局。國民政府敗戰時,毓老師繼張學良后,于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不久,被國民政府送至臺灣。
毓老師在1947年赴臺東農校當教導主任,1958年左右正式收西方洋博士弟子,開始講學,1967年8月擔任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來年兼系主任。1969年8月離開中國文化學院。毓老師在中國文化學院時,許多教師都到附近的“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吃免費午飯,毓老師不去。歷史系黎東方教授家人是北方人,常請毓老師吃餃子,毓老師回報他,就講些清朝典故,成了黎東方教授名著《細說清朝》的部分數據源。
1970年,毓老師在臺北四維路開始收臺灣的大學生弟子;1971年遷至臥龍街,正式以“天德黌舍”之名對外招收臺灣的大學生,講授經、子、史等典籍。
毓老師小時候受教,十三經全得背熟,初讀經書,經文得念百遍,1971年至2011年的四十年間,開課百余班,以《論語》為例,至少讀過千遍。故而訓勉弟子書讀百遍自通,讀經不要囿于后人批注,要直看原典。
由于讀書百年,教學六十四年,讀經千遍也不厭倦的毓老師,在世時間比孔子長三十多年,治學也比熊十力先生長二十余歲,毓老師講經有令后儒難以企及的高度。
毓老師講《六經》義理,一以貫之,脈絡分明,以“元”為夏學思想之源,以“時”說孔子之學,以“中”發揮中國往圣相承道統。
毓老師認為能留傳至今的中國古書,幾乎都是可用的實學,讀古書要以古人智慧來啟發自己智慧。毓老師教學以古證今,常有讓弟子心神俱醉的新意,像《論語·顏淵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毓老師說:“足食就是搞好財經,足兵就是搞好軍事國防,民信之矣即上頭講話,能讓人民信服。”毓老師這一解讀,讓人覺得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談統御之術蠻前衛的,今人搞政治還不如他呢!
毓老師最令弟子信服的是,遠離摯愛和故土的苦痛,所淬煉出來的睿智,授讀經書時,有時用語體白話比原文更傳神。像《論語·微子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毓老師解讀:“你這有德的鳥啊,為何會缺德呢?”荷蓧丈人說子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毓老師解說:“百無一用是書生,哪個老師教的?”讓聽課弟子哄堂大笑。
也就因為毓老師講經通神,聽課弟子對毓老師述而不作,未免遺憾。不少弟子曾請教老師,老師說得客氣:“不寫書,因講都未講明白,不欺人!”
其實,毓老師六十四年的教學,雖然自己未曾著書,但這不成遺憾的。
《論語》一書中,孔子固然談了《詩》、《書》、《禮》、《樂》等《六經》之文,但占全書比例不大;這就是說,《論語》所收篇章,大抵非孔子論《六經》之語,而是孔子自己的人生之論、體道之語,且非孔子本人親自為文,而由孔門弟子聞道記錄成書。
參照《論語》,毓老師不只有述,也有作:課堂上的訓誨之語,如能集錄成書,即是毓老師之作。
于是,我們十六名毓門弟子,輯錄了“禮元錄”。
公元2000年前后,毓老師在授課時說:“唐宋以后著書盛行語錄體,大儒朱熹著有《近思錄》、王陽明著有《傳習錄》、顧炎武著有《日知錄》,將來要出版我的第一部書叫《禮元錄》。”
毓老師先前在課堂中曾說,有意寫《思痛錄》、《知勉錄》、《用知錄》等書。老師六十整壽,洋博士弟子出版了《無隱錄》祝壽,也用“錄”字為書名。
恭錄弟子覺得毓老師既然“親定”他的第一部書名叫《禮元錄》,又口說想寫幾本語錄,于是參照《傳習錄》,不只書名曰“錄”,篇章亦為“某某錄”。
毓老師先祖是大清禮烈親王代善,毓老師念茲在茲的是“長白世澤,禮烈家聲”、“世間凡事禮為尊”;毓老師又以“元”字為夏學之原,元是體,中國文化是元文化,是夏學的奧質。大易乾元統天,人法天,所以人得“奉元”,而“奉元”必得“禮元”(禮有尊之義),所以毓老師的第一部書自定為《禮元錄》。但是,《禮元錄》的書名有些深奧,毓老師曾說著書要讓大家都能讀能懂,所以恭錄弟子擇選“毓老師說”為“禮元錄”的副題(簡體版改書名為“毓老師說”,“禮元錄”為副題)。“毓老師說”是古語的“毓子曰”(毓門弟子應尊稱毓老師“子毓子”),“說”不只是說經,也是毓老師的立說。
本書集十二個語錄,《思痛錄》、《訓勉錄》、《用知錄》為老師曾經有意撰寫的語錄名,“政事”、“識往”、“司鐸”、“奉元”、“述學”、“問心”、“立本”都是老師常提撕弟子的字詞。
毓老師自言一生對不起太師母、師母,他的兩性相處之道情真意摯,思慕后的心頭點滴令人動容。毓師母寫信給毓老師有“倚門閭而望穿云樹”之句,毓老師聞毓師母亡故,《招魂小詩》有“倚欄未了知心話”之句,我們特別輯錄了《倚欄錄》。在十二個語錄中,《倚欄錄》的分量最少,但老師的感情最真也最深。
《禮元錄》收輯的語錄,最早的一則是庚子年(196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毓老師書勉弟子黃大炯的“學不可緩”,最后語錄則是老師作古前夕,即2011年1月25日,由編者所恭錄的“滿人皇族出皇后,姻親扎紅帶子,有別于宗室的黃帶子”。
毓老師在文化學院任教時,年過六十,毓老師的哲學體系已然建立,爾后的哲學思想鮮有變動,充其量只在智海中起微瀾,所以我們不記載筆錄時間和記錄者,但涉及特殊性,必須作較清楚交代,就以括號作按語簡略說明。
毓老師的思緒圓融一貫,有些文句既可放在《司鐸錄》,也可放在《問心錄》或《用知錄》、《思痛錄》,編者的選擇排序,只能說是方便檢索閱讀而已,準確性當有不足之處。像毓老師談智慧,我們匯集于《用知錄》,但幾則智慧之言觸及了毓老師的傷痛處,我們編入了《思痛錄》;毓老師論說的孔子之學,有關大易、《春秋》部分收錄在《奉元錄》,《論語》義解則集中在《述學錄》,而申明時之用和時之義的文字則編在《用知錄》。
有些讀友或許會將《禮元錄》和《論語》作比較,認為《禮元錄》文字淺顯,不需如《論語》般作注,這個說法需要解釋。毓老師因時因勢而發的感情、言談深刻且幽默,有些話又意在言外。再說,今日讀來頗為不易的《尚書》、《易經》、《論語》,都是當時的語體文本,我們所恭錄的某些語錄文句,像“烏鴉落在豬身上,只見別人黑不見自己黑”、“勘破世情驚破膽”、“萬般不與政事同”、“蝸牛角上校雌雄,石火光中爭長短”、“行家看門道,力巴看熱鬧”……已然分不清是毓老師之說,還是毓老師引自俗諺或其他故實。可預見未來,《禮元錄》可能要如《論語》般詳細加注,所以我們先以括號作了小批注。
毓老師授課六十四年,毓門弟子近兩萬名,每個弟子都有筆錄,若要廣收合集,為數必定可觀,我們只是起了頭。《禮元錄》匯集毓老師言教一八五一則(簡體版有所刪減),恭錄弟子為王鎮華、白培霖、李濟捷、沙平頤、林義正、阮品嘉、吳榮彬、陳文昌、賈秉坤、黃大炯、黃德華、黃忠天、劉君祖、顏銓潁、顏維震、許仁圖等十六人。
毓老師曾慨嘆說,他是滿族旗人,是被孫中山先生所打倒的“韃虜”,他到臺灣六十四年,是臺灣人口中的外省人,而他一輩子講授的是中國文化:“文化大公無私,跨越了國界、種界,為天下人所公有,而非一國人所能獨占私有;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文化屬于愛好者、使用者。”
毓門弟子在毓老師作古后,成立了“中華奉元學會”,由徐泓師兄率眾師弟接下毓老師的棒子,還組成讀書小組,孫鐵剛師兄領眾,進行經文的筆記整理,未來整理出來的文字面世,讀者當可見到毓老師富美的百官廟堂。
黃大炯師兄細細校訂了《禮元錄》,改正了不少文字。黃師兄還有兩個建議,一是周知所有學會師兄姐,請各師兄姐提供所記的老師語錄;二是書中輯錄名稱的差異性不明顯,致使不少語錄匯集無法完整統合,有改進的空間。
黃師兄的建議甚是,但《禮元錄》已確定在老師冥誕日出版,周知所有學會師兄姐提供老師語錄,可能要花很長時間,至于集錄名稱的改進,編者只能盡力了。
《儼然錄》本來就希望收錄各位師兄姐追記老師的初心感動,或對老師的思慕之情,也因時間因素,只能從已發表的相關報道中擇錄,或請周遭師兄姐撥空撰文相助。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禮元錄》的筆記有的遠在三四十年前,又匆促記錄,難免有些未盡信達要求,期盼同門師兄姐提供補正。
《禮元錄》的恭錄,希望能記下毓老師峙立崖岸,天際流云的一二風采而已。
附:恭錄弟子(排名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鎮華 白培霖 劉君祖 許仁圖
阮品嘉 李濟捷 吳榮彬 沙平頤
陳文昌 林義正 賈秉坤 黃大炯
黃忠天 黃德華 顏銓穎 顏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