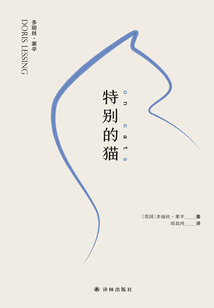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我家坐落在一座小山上,盤旋于樹林上空的鷹隼等鷙禽,大多與我的視線平行或偶爾略低一點兒。經常只要一低頭,便能瞅著一雙寬約六英尺的深褐色大翅膀,平展在金光閃閃的陽光下,貼著彎曲的樹林邊緣飛行。山坡下,田地已經犁過,不妨選一處犁溝躺下,最好是犁頭轉拐處的深凹坑,躺在里面,就等同于藏身在一道由青草和樹葉筑成的屏障之下。雙腿盡管被太陽曬得黝黑,但擱放在紅褐色土壤上,仍顯得蒼白觸目,還是要往腿上撒點兒泥土,不然干脆把雙腿埋進土里。一群飛鳥在數百英尺的高處來回盤旋,眼睛緊緊盯著田野,搜尋老鼠、家禽或鼴鼠的蹤跡。隨便挑一只鳥兒,沒準就是頭頂正上方的那一只。也許就在那么一瞬間,仿佛看見鳥兒與自己對視了片刻,它用冷漠的鳥眼,直勾勾地盯著人類平靜又好奇的雙眸。在它那雙巨翅中間,如子彈般窄小的身體下方,兩只尖爪早已蓄勢待發。大約過了半分鐘,不對,才二十秒,鳥兒突然一個俯沖,撲向選定的小動物,得手后旋即飛起,扇動著巨翅騰空而去,只留下一陣紅色塵煙和一股熱乎乎的氣味。天空又恢復了原貌:遼闊而寧靜的蒼穹下,東一簇西一群旋轉飛翔著鳥兒。然而,就在山頂上方,或許正有一只老鷹盤旋巡視,時刻準備著從側方姿態瀟灑地俯沖而下,撲向選定的獵物——我們家的某只雞。有時它甚至會沿著林中的一條山道逆飛而上,一路上不停地調整翅膀方向,避開身邊懸垂的枝條。這些老鷹為什么寧可違反自己高速飛翔的天性,不從高空飛落地面,反而選擇穿行于林中山路的上空?
我們家的雞圈,就是方圓數英里的老鷹、貓頭鷹和野貓的鮮肉補給站,至少它們的敵人對此堅信不疑。我們家的雞一天到晚都在無屏無障的開闊山頂自由活動,那耀眼的黑、褐、白等各色羽毛,咕咕喔喔的啼鳴聲,腳爪窸窸窣窣的刨地聲,走路時大搖大擺的樣子,都是引起掠奪者發動攻擊的最好標記。
非洲的農場有個做法,愛把煤油燈和汽油罐的蓋頂除掉,往里面放些金屬亮塊,用來反射陽光,據說用此法能夠嚇走鳥兒。但是,我曾經親眼看到一只老鷹,從樹上飛下,無視周遭一大群黑人白人、貓呀狗呀,徑直把一只昏昏欲睡的正在孵蛋的胖母雞擄走。還有一次,我們正在屋外喝茶,一只老鷹突然從空中直撲而下,從十幾個人的眼皮子底下,攫走了一只藏身于灌木下的半大小貓。要是在漫長炎熱的寂靜正午,忽然聽到一陣吱吱喔喔的叫聲或是撲撲的拍翅聲,就只有兩種可能性:不是哪只母雞被公雞踩了腳,就是又有一只雞被老鷹抓走了。好在我們家里的雞多得是。話又說回來,附近的老鷹實在太多,用槍是打不完的。不管什么時候,只要站在山坡上抬頭一望,必然可以在方圓半英里內,找到一只正在空中打轉轉的老鷹,而在它身體下方幾百英尺之處,還有一個細小的黑影正迅速地掠過樹梢,越過田野。我坐在樹下休息時,經常看見地上的小動物們,只要一發現高空巨大鳥翼所投下的不祥陰影落到了自己身上,或遮住了樹叢和草地上的陽光,不是被嚇得動彈不得,就是慌里慌張地找地方躲藏。老鷹從不獨來獨往,向來都是兩只、三只或是四只結伴出行。你可能會納悶:這些老鷹干嗎總在一個地方打轉轉?道理很簡單嘛!因為它們借力的是同一道氣流,只是高度不同而已。就在這幾只鷹的不遠處,還可以看到另一組鷹群。再凝神細看,就會發現天空中到處都是小黑點;若遇上陽光,小黑點就變成小光點,如同窗外一縷陽光下的塵埃。在這片綿延數英里的碧空中,究竟有多少只鷹隼?上百只總有吧?每一只都有能力在短短幾分鐘內擄走我們的家禽。
所以,除非憤怒到極點,我們一般不會射殺老鷹。記得那次,一只在鷹爪下凄厲慘叫的小貓,眼見著就要消失在天空,氣得母親舉起槍朝空中一頓掃射,自然毫無收獲,純粹是在浪費子彈。
如果說白天是鷹群的獵場,那么黎明和黃昏就是貓頭鷹的陣地。太陽一落山,我們就會把雞群趕進雞圈,可是已有貓頭鷹守在樹上伺機而動了;再說,晚睡的貓頭鷹會趁著曙光初現,雞圈再度開門時,下手捕雞。
鷹群總是在陽光下活動,貓頭鷹會在微光中活動,而夜光下活動的,則是貓,野貓。
這時,槍就可以派上用場了。鳥類可以在綿延數千英里的天空中遨游,但貓卻不同,他們有窩、有配偶,還有小貓,再怎么說總有一個貓窩。一旦發現哪只野貓選擇在我家山上安家,我們就格殺勿論。趁著夜色,野貓會從墻上或是鐵絲網上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縫隙鉆進雞圈作案。他們還會跟我們家的貓交配,引誘這些愛好和平的家貓,到樹叢中風餐露宿,而我們堅信,我家的貓并不適合那種危險的生活。野貓的出現,讓我們家這些嬌生慣養的小東西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了質疑。
一天,我家的黑人幫廚說,他在半山腰的樹上看到了一只野貓。當時我哥哥不在家,于是我抄起一把來復槍趕了過去。那個時候恰好是大中午,按道理野貓一般是不會出來活動的。在一棵并不高大的樹上,那只貓趴在一根樹枝上,沖我嗚嗚低吼,一雙綠眼瞪著我。野貓的樣子大多不好看,黃褐色的毛皮丑兮兮的,又硬又糙,身上還帶著股難聞的味兒。她顯然剛剛吃了一只雞,案發時間就在十二小時之內,因為這棵樹下散落著一堆白色羽毛和幾塊已經開始發臭的肉屑。我們討厭野貓,他們一見我們就豎起爪子,嗚嗚低吼,他們也討厭我們。這是一只野貓,我朝她開了一槍,她“咚”的一聲摔下樹枝,跌到我腳邊,在飛舞的羽毛堆中抽搐了幾下,便一動不動了。換作平常,我都是立刻抓起那又臟又臭的貓尾巴,拎起尸體,扔進附近的一口廢井里。但我總覺得這只野貓有點奇怪,于是彎下腰看了看她。她的頭型不太像野貓的,毛發雖然粗糙,但與野貓相比還是偏柔軟了些。我不得不承認,她不是野貓,而是我家養的貓。我們認出,這具丑陋的尸體,就是米妮,那只我家兩年前忽然失蹤的寵貓,當時我們還以為她是被老鷹或是貓頭鷹抓走了呢。米妮有一半波斯貓的血統,身子毛茸茸的,摸著特別舒服。眼前的死貓的確是她,一名偷雞賊。在我擊斃她的那棵樹附近,我們找到了一窩小野貓,但這些小貓崽兒實在太野了,把人類視為天敵,我和仆人四肢上的咬傷和抓痕就是明證。沒有辦法,我們只能把他們消滅。準確地說,是母親找人消滅了他們。由于一些家庭法則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建立,因此,這類討厭的活兒,都是落到她的頭上。
你們想想,家里常年有貓,但距離我們最近的獸醫,也遠在七十英里外的索爾茲伯里[1]。記得,當年沒人愿意給貓治病,母貓的麻煩事兒就更沒人管了。養貓,就會有小貓,而且數量多,生產次數也多。所以說,沒人要的小貓總得有人除掉吧。是家中的非洲幫傭或幫廚下的手嗎?我記得,耳邊常常聽到這個詞兒:bulala yena。(殺了它!)不管是家里的還是農場中的,受了傷的和體弱多病的牲畜家禽,全都逃不了這個命運:bulala yena!
但是,我家里有一桿獵槍和一把左輪手槍,一般是我母親在用。
比方說,蛇通常就是由她處理的。家里有蛇出沒是常事兒,我們就等于與蛇同住,這么說是很恐怖,卻是事實。比起蛇來,我更害怕蜘蛛——那些體龐個大、奇形怪樣、數量繁多的蜘蛛,想想都是噩夢。平日里我們常見的蛇是眼鏡蛇、黑曼巴蛇、吹氣蝰和夜蝰蛇。還有一種極其可惡的蛇,叫非洲樹蛇。這種毒蛇喜歡纏繞在樹枝或者廊柱之類遠離地面的地方,誰驚擾了它,它就朝誰臉上噴毒液。它們通常待在和人類視線平行的地方,所以常常有人被這種蛇毒瞎。但在與蛇同居的二十年里,這種慘事只發生過一次:一條樹蛇將毒液噴進了我哥哥的眼睛里,幸虧一位非洲人用草藥保住了他的視力。
但是,警鐘依然常常響起:廚房里有蛇,陽臺上有蛇,餐廳中有蛇;蛇似乎無處不在。有一次,我差點將一條夜蝰蛇當作一絞毛線給撿起來。幸好它先被我嚇了一跳,發出嘶嘶的叫聲,救了我倆的命:我嚇得落荒而逃,它也趁機溜走。我家的書桌上堆了很多白紙,紙堆間有很多縫隙。有一次,一條蛇竟然溜進了紙縫中,母親和仆人為了將它打死,花了好幾個小時才將它驚出。還有一次,一條曼巴蛇闖入儲藏室的谷物箱底下,母親奈何不了它,只好平躺在地,將近在咫尺的它開槍擊斃。
記得有一次,一條鉆進柴堆里的蛇讓一家人惶恐不安。我告訴家里人,我好像看到那條蛇竄進了兩根木柴中。這句話卻斷送了一只我最心愛的貓咪的性命,因為我看見的其實是她的尾巴。母親朝著一個移動的灰影開了一槍,隨即響起一聲凄厲的慘叫,貓的肚子被打破了一個大洞,血肉模糊。她在木堆中掙扎滾動,不停哀叫著,碎裂的肋骨下露出血流不止的小心臟。母親一邊流淚一邊撫摸她,她終于斷氣了。而作為罪魁禍首的眼鏡蛇呢,此刻正盤在幾英尺外柴堆高處的一根木頭上,安然無恙。
另有一次,家中突然一片喧嘩,人人驚恐。原來是在一條布滿木槿和荊棘的亂石小道上,一只貓正在和一條舞動著的小細黑蛇對決。小蛇倏地一下鉆進一簇三英尺寬的荊棘叢中,躲在里面,用亮晶晶的眼睛盯著那只無法接近荊棘叢的貓。貓守了一個下午,繞著蛇藏身的荊棘叢一直打轉,沖著對手又是齜牙咧嘴又是喵嗚喵嗚地怒吼,可是當夜幕降臨時,小蛇便趁著夜色溜之大吉了。
許多故事沒頭沒尾地在記憶中閃現。記得曾有一只貓,眼睛被蛇毒所傷腫得老大,躺在母親床上喵嗚哀嚎,后來怎么樣了?還有那一只貓,腹部因漲奶都耷拉到了地上,一路哀哀叫著走進屋子,后來她又怎么樣了呢?我們去工具房看她那窩躺在舊盒子里的小貓崽兒,卻發現他們全都不見了。仆人看了看盒子周圍塵土上的痕跡,說:“Nyoka。”是條蛇干的。
小時候,對人呀、動物呀、事情呀,遇見什么就接受什么,消失了就消失了,沒有人告訴理由,自己也不會張口詢問。
但現在想起貓,總是有貓,想起那樁樁件件與貓相關的事情,想起與貓相伴的歲歲年年,不由得為養貓帶來的繁重工作而震驚。如今我在倫敦只養了兩只貓,都常常叨叨,若是有人敢說,養兩只小動物能有多麻煩,能操多少心,這個人肯定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那些年里,所有跟貓有關的活計都是母親的事兒。男人主外干農活,女人主內打理家務,乃天經地義。即便鄉下的家事要比城里所謂的家務活繁雜千百倍,她也得接手。因為單從性情上而言,那些活兒也非她莫屬。母親仁愛明理,善持家,尤其務實,極少感情用事。不僅如此,她還是那種懂得如何做事、也肯親力親為的女子。總之,她是一個厲害角色。
對那些事兒,父親心里其實是清楚的,畢竟他是鄉下人,但他的態度卻不以為然。每當有事情必須解決,必須拿出對策,必須采取最后的非常手段——而執行任務者總是母親,父親卻說:“所以說就這么決定了!隨便你了!”語氣酸溜溜的,有幾分不滿,卻也不無欽佩。但到最后他總會服軟:“大自然嘛,如果都能安分守己,不也挺好的。”
對母親來說,能與自然相安無事自當竭力為之。的確,此事既是她的職責,亦是她的心頭之痛,但她向來不會在多愁善感的問題上浪費時間。“你倒是挺好的,對不對?”她幽默地回答,其實心里是惱父親的,因此母親的幽默中略帶怨憤,因為像淹死小貓,開槍射蛇,殺死生病的家禽,或者用硫黃熏白蟻窩這類事兒父親一律不管不問,相反,他還喜歡白蟻來著,常常看它們忙乎,一看就入迷。
所以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在那個可怕的周末,母親會拋下我不管,把我丟給父親,讓我們與四十多只貓待在家里。
我思來想去,對她的行為,只有一種解釋:“她這個人太心軟了,連一只小貓崽兒都舍不得淹死。”
說這話的人是我,我當時正窩著火,說話的口氣很不耐煩,也很沖。那會兒我正在跟母親進行著一場“戰爭”,一場生死搏斗,或者說一場生存之戰。母親的離家是不是跟我倆的戰爭有關,我不得而知。如今想來不禁納悶:究竟是什么原因讓母親突然勇氣盡失?還是她是想以此來抗議什么?她的心里到底承受著怎樣的痛苦?當年她突然開口說,淹死小貓崽兒,殺死病貓的事兒,今后別再找她,她說這話的真正用意又是什么?最后,她明明知道在我們家養貓成患已是事實,心里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事情,為什么依然拋下我們獨自離去?
自從母親拒絕擔任監管者與仲裁者之職,不再參與維持自然界的合理繁殖和不合理增生之間的平衡事務,不到一年時間,我家屋里、周圍庫房以及農場四周的灌木叢,全都貓滿為患。小貓、老貓、半大不小的貓;家貓、野貓、半馴半野的貓;患上疥癬的貓、受傷腫眼的貓、跛腿的殘疾貓,各種貓一應俱全。更糟糕的是,還有六只懷孕的母貓。照這樣看來,如果不趕緊采取措施,數周之后,我們家勢必淪為百貓相爭的戰場。
是得采取行動了。父親這么說,我這么說,仆人們也這么說,母親卻抿緊嘴唇,一言不發地離開家門。她離家之前去和她最喜歡的貓道了別。那是一只很老的虎斑貓,我家的貓全都是她的子孫。母親一邊溫柔地撫摸貓頭,一邊哭泣。我仍記得自己當時的想法,覺得母親是在自尋煩惱,并不懂得她哭泣是因為無助。
母親前腳才離開家門,父親就念叨了好幾遍:“這么說,非做不可了,是不是?”是的,的確到了非做不可的時候。于是父親給城里的獸醫打了一通電話。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兒。我們家是跟其他二十家農戶共用一條電話線,得等到別人聊完八卦或農場見聞后才輪得上,然后打電話到話務局,向他們申請一條可以跟城里通話的線路,等到有線路可以用的時候,他們再打電話通知你。這一等說不定就是一個小時,甚至兩個小時。坐在一旁干等,望著群貓,巴望著這等齷齪事兒能速速了結,這樣的等待簡直就是一種折磨。我與父親并排坐在餐廳的餐桌邊,等待電話鈴聲響起。最后我們總算聯系上了獸醫,可獸醫卻說,讓成年貓死去的最人道的方法,就是用氯仿。距離我們最近的藥店在二十英里外的錫諾亞[2]。于是,我們開車去錫諾亞,沒想到藥店那周不營業。我們在錫諾亞打電話去索爾茲伯里,拜托那兒的一位藥師,請他第二天托火車捎一大瓶氯仿過來。他答應幫忙看看。平時沒下雨,我們晚上都會待在屋前乘涼。那天夜晚,我們坐在屋前的星空下,心里既難過又憤怒,還滿腹愧疚。為了盡快熬過這段折磨人的時光,我們早早就上床睡覺了。第二天是周六,我們開車去車站,可火車上并沒有氯仿。周日,一只母貓產下了六只小貓,可是沒有一只健全的貓,每一只都有一些地方出了問題。父親說,這是近親繁殖的后果。如此說來,只要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可以讓幾只健康的貓,變出一支殘疾貓大軍,簡直匪夷所思。仆人將新生的小貓崽兒處理掉,而我們又度過了一個痛苦的日子。周一我們開車到火車站,等到替我們捎帶貨物的火車,帶著氯仿返回家中。母親預定這晚回家。我們拿了一個密封的大餅干罐,往里面放了一塊浸滿氯仿的棉球,然后把一只生病的可憐老貓關進去。我不推薦這種方式。獸醫說這個辦法能立竿見影,可事實并未如他所言。
最后,我們把貓統統趕進一個房間。父親帶著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使用的左輪手槍走進房間,說什么手槍比獵槍好使。槍聲接二連三地響起。那些還沒被捉住的貓預感到自己的命運,在灌木叢里四處亂竄、尖叫,躲避人的追捕。父親從房間里走出來過一次,只見他臉色發白,雙唇緊閉,眼眶濕潤,看起來很不舒服。他嘰里咕嚕地罵了好一陣子,又進到房間,隨之槍聲再次響起。最終他走出了房門。仆人進去,把貓尸體運出來,扔進廢井里。
但還是有幾只貓逃過了此次大劫,一共三只,他們再也沒有回到這所兇宅,最后肯定是變成了野貓,生死未卜。母親回到了家里,等到接她回家的鄰居離開之后,她便輕手輕腳、一言不發地穿過這棟只剩下一只貓的房子,她心愛的老貓正窩在她的床上睡覺。母親并沒有要求我們放她一馬,因為她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太好。但是母親一回家就在找她,她在她身邊坐了很久,一邊撫摸她,一邊和她說著話。然后,她走到陽臺上。父親和我就坐在那里,感覺自己像殺人犯似的。母親坐下來。父親正在卷一支煙,手仍在顫抖。他抬起頭看著母親,說:“絕對不能讓這種事情再發生了。”
我想,這樣的事情以后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這場屠貓行動,讓我異常憤怒,因為它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在我的記憶中,我并未因此而悲傷。我十一歲那年,一只貓的死亡,讓我傷心欲絕,從此我硬起心腸不再為貓難過了。當時,望著那具冰冷沉重的尸體,我實在無法相信,她就是昨天那只輕盈似羽毛的小貓。我告訴自己:這種痛苦我絕對不再承受第二次。但我心里很清楚,這樣的誓言我曾經發過。父母告訴我,我三歲時,有一次和保姆外出散步,當時是在德黑蘭,我不顧保姆的反對,在街上撿了一只餓得奄奄一息的小貓,把她抱回了家。他們說,我一直嚷嚷著說,她是我的小貓。家人一開始是堅決不同意收養的,但我為了小貓對他們死纏爛打,決不放棄。小貓身上很臟,家人用高錳酸鉀給她洗澡消毒,從此她就和我同睡一鋪。我不允許別人把她帶走,但她卻一定得離開我,因為不久之后我們舉家搬離波斯,只能將她留下。又或許是她死了,或許——我怎么知道?不管怎樣,在遙遠的過去,一個小女孩為自己贏取了一只日夜相伴的小貓,可惜小女孩最終還是失去了她。
過了某個特定的年紀——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是在年紀很小的時候——生活中便不會再有新人、新動物、新夢想、新面孔以及新事情出現了,因為一切均已發生過,所有人物以前全都露過面,只是戴著不同的面具,穿著不同的服裝,擁有不同的國籍和膚色而已,而實際上卻是一樣的,一模一樣,全都是陳年往事的回聲和重復;甚至所有的哀傷,也都是許久以前封存于記憶中的傷心過往的重現。譬如我吧,記憶中那撕心裂肺的悲痛,以淚洗面的日子,深入骨髓的孤獨,遭受背叛的絕望,全都跟一只瘦瘦小小、行將死亡的貓有關。
那年冬天,我生了一場病。當時,我的大房間準備重新粉刷,不方便住人,我便搬到了最靠邊的小屋里去住。我們家的位置靠近但并非立于山頂,而是坐落在旁邊的坡道上,所以給人的感覺好像它隨時會滑到山腳的玉米地里似的。我的這間屋子,非常狹小,卻有門有窗,常年開著。七月里,天空一碧如洗,寒風陣陣,但我這間小屋依然門戶洞開。天空中陽光燦爛,田野里灑滿陽光,天氣卻很冷,冷得不行。那只藍灰色波斯貓,咕嚕咕嚕地爬到我的床上,待在那里分擔我的病痛,分享我的食物、枕頭和美夢。每當我清晨醒來,臉頰貼著冰塊似的亞麻被單,毛毯外側冰冷無比,從隔壁房間飄過來的墻漆味兒寒氣襲人,夾雜著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屋外寒風刺骨,塵土輕揚。但是在我的臂彎里,總是蜷著一個暖乎乎、輕輕發出咕嚕聲響的小家伙,我的愛貓,我的朋友。
屋后,浴室外面的地下,埋了一個大木桶,用來接洗澡水。我們的農場里沒有自來水設備,需要用水時得趕著牛車去幾英里外的井里汲水。在長達數月的干旱季節里,我們只能用臟洗澡水來澆花。寒風凜冽的一天,我的貓不小心掉進裝滿熱水的木桶里,驚恐地大聲尖叫,被我們撈出。木桶里很臟,除了落葉、塵土,還有肥皂水,我們用高錳酸鉀給她洗澡,擦干后放進我的被子里取暖。她不停地打噴嚏,呼呼喘著粗氣,接著就發起了高燒。她得了肺炎。我們用家里一切可用的藥物治療她,但是那時還沒有抗生素,所以她還是離我而去了。她在我的臂彎里躺了一周,用一種顫抖、沙啞的細弱嗓音,艱難地打著咕嚕,但她的聲音一日弱似一日,最后聽不見了。她舔我的手;聽見我大聲呼喚她的名字,懇求她活下去時,她睜了睜綠色的大眼睛,然后永遠合上了雙眼,接著被扔進了那口一百英尺深的枯井里。一年前,這里的地下水突然改道,使得這口我們家十分仰賴的水井,變成了一個干枯、破裂、石塊密布的豎坑,里面很快就積了不少垃圾、鐵罐和動物尸體。
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不能讓這種悲劇再次上演。多年來,我總是拿朋友家的貓、店里的貓、農場里的貓、街道上的貓、墻頭的貓,以及記憶中的貓,與那只溫柔的、愛咕嚕咕嚕叫的藍灰色生靈相比,而唯有她才是我心目中獨一無二的貓,任何貓都無法替代她在我心中的地位。
此外,有一段日子,我的生活中沒有一樣多余的、不必要的裝飾品。貓在一個總是四處漂泊、不停搬家的人那里是找不到容身之所的。對貓而言,他不僅需要一個屬于自己的人,還需要一個屬于自己的地方。
我在兜兜轉轉了二十五年之后,才擁有了養貓的條件。
注釋
[1]索爾茲伯里(Salisbury),是津巴布韋的首都,現名為哈拉雷。
[2]錫諾亞(Sinoia),津巴布韋一地名,位于首都哈拉雷(原索爾茲伯里)西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