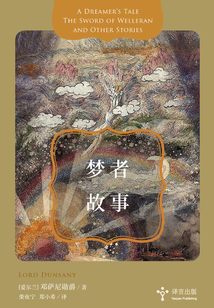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27章 魏樂蘭之劍及其他故事(12)
- 第26章 魏樂蘭之劍及其他故事(11)
- 第25章 魏樂蘭之劍及其他故事(10)
- 第24章 魏樂蘭之劍及其他故事(9)
- 第23章 魏樂蘭之劍及其他故事(8)
- 第22章 魏樂蘭之劍及其他故事(7)
第1章 他方無凈土——《夢者故事》譯者序
在某個陽光稀薄的下午偶遇此書。冥冥中,“夢者”二字恰巧與腦中回旋多年的某段旋律踩在同一節奏上。彼時因緣聚首,傳來瓜熟落地之音。從著筆至定稿,歷經初稿、審訂、修改、互審,共一年有余。待書成面世,再歷一年有余。期間際遇變幻,至撰譯序時刻,重讀此稿,其中體會也仿佛書稿付梓,只等破繭成蝶的一瞬。
心中曾有一方人間凈土如詩中所述:“白晝幽闃窈窕如夜,夜比白晝更綺麗、豐實、光燦”,“過去佇足不去,未來不來”[1]。彼國天地萬物靜默渾莽,有種凝滯之美;反觀此岸人間,生命誕生、意識混沌初開,追逐,卻儼然譜寫了大地子民的生命之歌——獵食、求偶、競爭、逃離、挑戰、改變……在追逐與被追逐之間,靜默被撕開,沖突拉開了帷幕。生而為人,未曾停歇的是追逐的本能。興許是造物者預見了人間的疲憊生活,心生憐憫,便賜予白天與黑夜、現實與夢境,世人白日追逐,黑夜做夢,日間無法兌現的愿望,或可在夢里推倒重來,或自我彌補與告慰,一如弗洛伊德所言:“夢是愿望的達成。”某種意義上,每當世人感到現實無處棲居,普天之下沒有凈土,人間仍有一處地方可去,仍有一處彼岸可玄想寄托,即“夢境世界”。
筆譯《夢者故事》以前,此番解讀是為“夢”之囈語;譯文以后,“夢境”仿佛踏足了了新的他方凈土。
《夢者故事》之“造夢人”鄧薩尼勛爵(Lord Dunsany,1878-1957),20世紀奇幻小說的開山始祖之一,生于愛爾蘭世襲貴族家庭,普倫基特家族第十八代男爵,其人生歷程可謂精彩紛呈:年輕時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曾于非洲大陸上捕獵獅子,在雅典大學擔任英文教授,甚至空閑之余還發明了鄧薩尼象棋。本書的兩卷選集(《夢者故事》、《魏樂蘭之劍》)完稿于20世紀初,歐洲大陸正值新舊時代交替之際,戰火紛飛,暗潮洶涌。28則故事串聯起的“他方夢境”如鄧薩尼勛爵所言,正是一片“在我們了解的天地之外”(beyond the fields we know)的“第二世界”。他方世界的萬事萬物超越了本時空的一切規則與常理,然而,在看似荒誕不經、縹緲哀愁的一場場夢里,我偶爾恍悟,似乎依稀窺見這般種種意象的隱喻。
彼時的西方社會正志得意滿,在世界版圖上閃著昌盛光芒,隱約透著故事中少年得志的凱莫拉克[2]的影子,似有萬鈞蠻力,任光陰與大地都不得奈其何。在鄧薩尼的筆下,每一場夢的序幕未必驚艷,甚至于夢中人與現實世界里的凡夫俗子相差無幾。昂恩之王凱莫拉克也不能免俗。為了證偽一個預言,他率領戰無不勝的軍隊連夜啟程——預言家斷定,凱莫拉克永遠也不可能抵達卡爾卡松,那座傳說百年卻無人親睹的城池。遠征軍馬不停蹄,朝著一個不可名狀的遠方奔赴而去,一隊斗志昂揚、熱血澎湃的年輕人要往哪兒去呢?比遠方更遠的卡爾卡松究竟在哪兒?若這場夢止于軍隊啟程,則不足以為夢;若止于斗士們遭遇挫折,理想幻滅,亦不足以為夢。鄧薩尼的魔力恰在于此:他不急不緩地道盡一場夢誕生到幻滅的歷程,既不刻意雕琢夢生的豐實,也不避諱細描夢滅的殘酷,在清醒刺骨的回轉與起伏中,讀夢人恍惚間產生一種錯位的真實感。夢里,凱莫拉克的軍隊追逐遠方,走走停停,懈怠后再次奮起,多年后獨留兩位老者殘存于世,孤獨面對宿命成真、理想幻滅的真相;夢外,不肯輕易折服于現狀的自由公民們懷揣各式各樣的前程藍圖,追逐明天與未來……
身為譯者,我幾度沉湎于夢中人哀而不傷的敘述難以自拔,透過鄧薩尼的筆調,隱約瞥見“夢”的另一層解讀:彼方夢界并非一片美滿圓融的“凈土”,“夢”未必是“愿望的達成”,亦非某種偽裝的補償。恰恰相反,每一場夢如同浮沉不定的清醒夢,與現世生活一樣,愿望似乎永遠無法被填滿,夢中人在恍惚之中幾番掙扎,不斷被推向現實中避而不談的情結與缺憾。
本書落成至今,晃眼已過百年,滄海未平,桑田變幻。那代代難逃大海召喚的年輕人,是否返回了原鄉?那些宿命的挑戰者,是否仍在征途?那初嘗人間滋味的精靈,是否獲得了內心的平靜?夢之所以為夢,正因夢中人千百回流轉于夢中情節而不自知,即便反客為主,操縱夢土眾生,夢醒又如何?此岸無凈土,他方亦無凈土,何處有凈土?——對此,無數作家已提問了千百年。
而讀者——每一個讀夢之人——會有不一樣的答案。
以上,本人拙見,是為序。
柴夜寧
2017年10月
廣州
注釋:
[1]摘自臺灣詩人周夢蝶之詩《孤獨國》。(注)
[2]本書《夢者故事》第12則《卡爾卡松》中的人物。(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