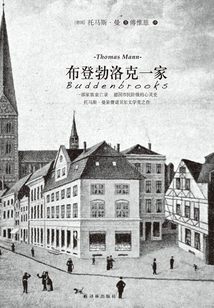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譯序(1)
黃燎宇
1.
1897年5月,出版商薩繆爾·費舍爾致信旅居意大利羅馬的托馬斯·曼:“如果您肯給我機會出版一部大型散文作品,哪怕是一本篇幅不那么大的長篇小說,我將非常地高興。”這位年僅二十二歲、只發表過幾個短篇的文學青年欣然允諾。在隨后的三年里,他從羅馬寫到慕尼黑,完成了一部以他的故鄉——瀕臨波羅的海的呂貝克——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取名《布登勃洛克一家》[1]。小說于1901年出版,出版不久便顯露崢嶸,反響甚大,[2]銷量隨之出現戲劇性攀升[3]。從馬賽到哥本哈根,從阿姆斯特丹到柏林,都有讀者發出驚嘆:“和我們這里的情況一模一樣。”1929年11月,瑞典文學院宣布托馬斯·曼獲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但保守的評委們對《魔山》這樣的長篇杰作和《死于威尼斯》等優秀中篇視而不見,特別強調托馬斯·曼獲獎是因為他寫出一本《布登勃洛克一家》。[4]時至今日,《布登勃洛克一家》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百年文學經典……初出茅廬便寫出不朽的長篇,文學史上仿佛又增添了一個一不留神搞出偉大作品的奇跡。然而,托馬斯·曼不相信奇跡。他在驚喜之余開始思考一個問題:起點不高、期望不大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憑什么打動世人?他冥思苦想,終于在年近半百之時豁然開朗:《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部“市民階級的心靈史”,他的一生,其實只講述了一個故事,那就是“市民變化的故事”。
為概括《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中心思想”而絞盡腦汁的外國讀者,十有八九不會因為讀到托馬斯·曼這一高屋建瓴的自我總結而茅塞頓開,因為“市民”恰恰是一道阻礙外國讀者進入托馬斯·曼藝術世界的概念屏障。我們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德文詞Bürger。Bürger源自Burg(城堡),字面意思是“保護城堡的人”,也就是“城堡居民”或者“城市居民”,即“市民”。在西歐,市民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階級,就存在對立面。一部歐洲近代史,就是市民階級反對貴族階級的歷史,就是前者高舉著自由、平等、知識以及勞動光榮的旗幟,與固守政權、固守舊有社會觀念和社會秩序的后者對壘的歷史。這場斗爭在18、19世紀才塵埃落定,西歐各國的市民階級相繼登上歷史的寶座,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引領時代。然而,盡管有著相似的歷史經歷,德國市民階級的自我意識卻和他們的近鄰有所不同。Bürger一詞便是例證。Bürger的內涵意義不同于英語的burgher(家道殷實,思想保守的中產階級市民)或者citizen(公民)或者二者之和,也不同于法語的bourgeois(資產者)或者citoyen(公民)或者二者之和,讓英文和法文譯者不勝煩惱。[5]與德國人同文同種同歷史的英國人和法國人尚且如此,中國讀者的處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我們因為閱讀托馬斯·曼的作品查閱一本合格的現代德漢詞典,我們有可能被Bürger詞條搞得頭暈目眩:市民,公民,市儈,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我們習慣把“市民”看成“城市居民”或者“市井俗民”的縮寫,既不理解德國“市民”的關系為何如此復雜,也不明白德漢詞典中的解釋怎么就沒有一個百分之百地適合托馬斯·曼的語境。[6]撞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翻譯家,這個詞恐怕只好音譯為“畢爾格”。Bürger的隱含意義如此豐富,如此駁雜,多少反映出社會意識的歷史變遷。這中間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從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的德國市民階級(das Bürgertum),實際上是一個精英階層,是由醫生、律師、工廠主、大商人、高級公務員、作家、牧師、教授以及高級文科中學教員組成的中上層。相同或者相似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是聯系形形色色的階級成員的紐帶。據考證,德國市民階級在19世紀——歷史學家們稱之為das bürgerliche Zeitalter(市民時代)——中葉僅占總人口的5%,如果把匠人、小商人、小店主這類小市民也計算在內,也不超過15%。盡管德國市民階級都是殷實之家,我們所熟悉的政治話語也一直把他們統稱為資產階級,使人聯想到這個階級的本質特征是占有并崇拜財富,但是德國市民階級很難接受單純的資產階級稱號。個中原因在于,他們引以為豪的恰恰是財富和文化的水乳交融。約翰·沃爾夫岡·封·歌德(雖然他的姓名之間添了一個代表貴族身份的“封”字,他仍然被視為德國市民階級的偉大代表)的一句箴言便充分表達出他們的文化精英意識:“若非市民家,何處有文化。”[7]第二,從19世紀開始,Bürger這一概念便不斷受到貶義化浪潮的沖擊。德國浪漫派對市民階級的社會理想和道德理想進行了諷刺和批判,把市民統統描繪成手持長矛的形象,使Bürger 和Spieβbürger(市儈,小市民)[8]結下不解之緣;掀起“波希米亞革命”的藝術浪子們紛紛向吉普卜人看齊[9],浪跡天涯、無牽無掛的“波希米亞”讓穩定而體面的“布爾喬亞”遭到嚴重的審美挫折;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和1848——1849年的民主革命的失敗,使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認清了德國市民階級的本質,Bürger不僅成為保守、軟弱、缺乏革命性的化身,而且和來自法國的Bourgeois(資產者)融為一體;20世紀60年代,隨著學生運動和新左派思潮的興起,“市民”和“市民性”再次成為批判對象,市民階級的文化優勢也淪為笑柄,左派人士故意畫蛇添足,張嘴就是Bildungsbürger(文化市民)[10]。就這樣,Bürger從一個原本褒義的概念逐漸演變成為一個中性的、見仁見智的概念。
托馬斯·曼有著根深蒂固的階級意識和階級感情。和許多藝術家不同,他年紀輕輕就表現出強烈的階級歸屬感。人們也許會因為中篇小說《托尼奧·克呂格爾》(1903)感人至深地刻畫了市民的靈魂和藝術家的靈魂如何在他心中對峙和爭吵而疑心他的階級立場發生了動搖,但是這一顧慮被他隨后發表的《閣樓預言家》(1904)打消。在這篇小說中,他不僅把自己塑造成一個頭戴禮帽、蓄著英式小胡子的中篇小說家(這是19世紀德國市民的標準形象),而且帶著譏諷和憐憫描寫了在閣樓上面折騰的“波希米亞”。對于他,“市民”是一個值得驕傲的稱號,市民階級是一片孕育哲學、藝術和人道主義花朵的沃土,歌德和尼采都是在這塊土壤上成長起來的文化巨人,所以他托馬斯·曼要保持市民階級的特色,要捍衛市民階級的尊嚴;所以他強調,“市民變化的故事”講的只是市民如何變成藝術家,而非如何變成資產階級或者馬克思主義者。他也如愿以償地被視為20世紀的歌德[11],被視為德國傳統市民文化的集大成者。
必須指出的是,1900年前后的托馬斯·曼還沒有系統地反思市民問題,也沒有以市民階級的總代表自居,所以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本能地把市民階級劃分為三六九等(這在第四部第三章描寫的市民代表大會上可謂一覽無余),代表曼家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以下簡稱布家)屬于高等市民。這不足為怪。這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又一例證。我們知道,托馬斯·曼生在呂貝克的一個城市貴族家庭。誕生于1226年的呂貝克,其實是一個高度自治的城市共和國,德意志民族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所賜予它的“帝國直轄市”地位,甚至保持到1937年。呂貝克是一個擁有輝煌歷史的商業城市,在14世紀曾為盛極一時的漢莎同盟的總部所在地(現在的德國航空公司就取名為“空中漢莎”)。但是,在工業化和技術化浪潮席卷德意志大地的19世紀中后期,呂貝克的社會經濟發展卻沒有完全跟上時代的步伐,商業和商人仍然是社會生活的主宰和核心。曼家的崛起就很說明問題:曾祖父獲得呂貝克的市民權并創辦糧食商行,祖父和父親先后子承父業,其名望卻超過了父輩。前者兼任荷蘭駐呂貝克領事,后者則當選為市府參議,成為這個袖珍國的部長級人物。到托馬斯·曼這一輩,曼家已成為無可爭議的城市貴族。所謂城市貴族,也就是貴族化的市民,是那些雖然沒有放棄本階級的政治和道德理念,但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方面向貴族階級看齊的上層富裕市民。市民貴族化,符合倉廩實而知禮儀的社會發展規律,所以這種現象并非19世紀或者晚期市民階級所獨有,而是貫穿于市民階級的發展史。城市貴族的標志,則是考究的飲食和穿著,含蓄而得體的言談舉止,還有高雅的審美趣味。可是,當市民階級進化到城市貴族的時候,也許麻煩就出來了。這正是《布登勃洛克一家》所觸及的問題。
2.
注意到《布登勃洛克一家》副標題“一個家庭的沒落”的讀者,將驚喜地發現,這本講述家族沒落的小說,竟見不著多少感傷情調,反倒通篇幽默,笑聲不斷。透過這笑聲,我們首先望見了橫亙在城市貴族與中下層大眾之間那條階級鴻溝,望見了高高在上、嘲笑一切的城市貴族。不言而喻,離貴族生活相距十萬八千里的窮人或者說無產者是要受到嘲笑的。他們對不起貴族的聽覺,因為他們一張嘴就是土話(在德國,不會說高地德語即德國普通話,是要遭人歧視的),就在鬧笑話(參加共和革命的工人斯摩爾特,他在被告知呂貝克本來就是一個共和國后,便說“那么我們就再要一個”),就會說出讓人難堪的話(前來祝賀漢諾洗禮的格羅勃雷本大談墳墓和棺材);他們也對不起貴族的嗅覺,因為他們身上散發著汗味(而非香水味)、燒酒味(而非葡萄酒或者白蘭地味道)、煙草味(而非雪茄味);他們更對不起貴族的視覺,因為他們在參加布家的喪葬或者慶典活動時,走路像狗熊,說話之前總要咽口水或者吐口水,然后再提提褲子。格羅勃雷本的鼻尖上一年四季都搖晃著一條亮晶晶的鼻涕。嚴格講,小說里所有的窮人都應取名格羅勃雷本——這是Grobleben的音譯,意為“粗糙的生活”。令人寬慰的是,格羅勃雷本們并非《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主要嘲笑對象,因為高高在上的托馬斯·曼對他們沒有什么興趣(除了《布登勃洛克一家》,他那卷帙浩繁的作品里幾乎見不著格羅勃雷本們的蹤影)。社會地位與布家相同或者相近的人受到了更多而且更尖刻的嘲笑,如布商本狄恩,酒商科本,裁縫史篤特,以及漢諾的教師。和布家聯姻的佩爾曼內德和威恩申克,更是布家的大笑料。布家人不但要挑剔發音和穿著,挑剔坐相、站相、吃相,他們也看重知識和教養。誰要把《羅密歐和朱麗葉》說成席勒的劇本,或者只會欣賞靜物畫和裸體畫,或者碰到蓋爾達就問“您的小提琴好嗎”,誰就會遭受無言的蔑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