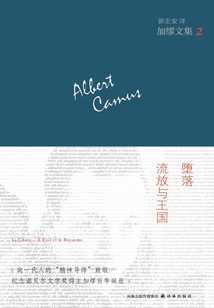
加繆文集2:墮落·流放與王國
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墮落(1)
先生,我可以不揣冒昧,為您效勞嗎?我怕您不知道如何讓掌管這家企業的大猩猩明白您的意思。事實上,他只講荷蘭話。除非您允許我為您辦這一案子,否則,他是猜不出您要刺柏子酒的。看,我敢說他聽懂了我的話:他這一點頭,該是表示他對我的論據是折服了。果然,他去了,以一種適度的遲緩來加快腳步。您真運氣,他沒有嘟囔。當他拒絕服務的時候,嘟囔一聲就行了:沒有人再堅持。縱情使性,這是大型動物的特權。我告退了,先生,為您效勞,我感到榮幸。謝謝,若是果真不惹人生厭的話,我就接受您的邀請。您太好了。我就把我的杯子放在您的杯子旁邊吧。
您說得對,他的沉默轟然震耳。這是種原始森林的寂靜,籠罩一切,包括嘴巴。我們的寡言朋友對文明語言表示不滿,其頑固程度有時令我吃驚。他的職業是在這家阿姆斯特丹的酒吧間里接待各國海員,不知何故,他稱這間酒吧為墨西哥城。對如此尊敬這間酒吧的人來說,您不認為他們要為他的無知會使人不快而擔心嗎?請想象一下那個住在巴別塔[1]里的克羅——馬尼翁人[2]吧!至少,他會感到離鄉背井之苦。啊不,此人并無流落之感,他走他的路,什么也加害不了他。我從他嘴里聽到的為數不多的話里有一句是“要就要,不要就拉倒”。該要什么不要什么呢?無疑,指的是我們這位朋友自己。我承認,這些鐵板一塊似的生靈吸引著我。當人們或是出于職業需要,或是出于天性,就人這類生靈沉思良久之時,往往會懷念起靈長類來。它們是不打小算盤的。
不過,說真的,我們的主人卻是有一點小算盤的,盡管相當模糊。由于聽不懂人們當他面說的話,他就養成了一種多疑的性格。由此而產生這副滿腹狐疑的莊嚴氣派,至少他好像對人和人之間有什么事不對勁起了疑心。這種態度使那些與他的職業無關的談話不太容易進行。您看,比方說,在他背后墻上,他頭頂上方的那塊長方形的空白,那是一幅被摘掉的畫的位置。事實上,那里原有的一幅畫特別引人注目,是一幅真正的杰作。您猜怎么著,主人收到它,又把它讓出的時候,我都在場。兩次都是同樣的疑慮重重,反復思考了幾個星期。從這一點看,社會也是有些,應該承認,多少有些敗壞了他率直淳樸的天性。
請注意,我并不在審判他。我認為他的疑心有根據,而且,如您所見,如果我的喜怒形于色的天性對此不加反對的話,我將樂于贊同他的疑心。我愛說話,唉!但也隨和。盡管我知道要保持適當的距離,但是,一有機會,我就要交換看法。我在法國時,每逢遇見有才智的人,我就不能不立即與之結交。啊!我看見您在對虛擬式未完成過去時[3]皺眉頭。我承認我對這種語態有癖好,一般地說,我對高貴的語言有癖好。請相信,我自己也責備這種癖好。我知道愛好精致的襪子并不一定意味著有一雙骯臟的腳。盡管如此,風度卻和常常掩蓋著濕疹的府綢襯衣相似。我對自己說,無論如何,聊以自慰的是,說話結結巴巴的人也并非純潔無瑕。對,還是喝酒吧。
您在阿姆斯特丹逗留許久嗎?一座美麗的城市,是不是?迷人?這個形容詞我很久沒聽到了。我離開巴黎已經有好幾年了。然而,記憶猶新,對我們美麗的首都,還有它的濱河路,我什么也沒有忘記啊。巴黎是個真正的假象,是個壯麗的舞臺,住著四百萬具人形的生靈。據最近一次調查,接近五百萬了?當然,他們該生下小的了。這不足為怪。我總覺得我們的同胞有兩大狂熱:思想和通奸。亂七八糟,姑且這樣說吧。不過,我們不要譴責他們;不獨他們如此,整個歐洲也這樣。我有時夢想著未來的歷史學家將如何評說我們。對于現代人,一句話足矣:通奸和讀報。我敢說,下了這個有力的斷語之后,文章就做盡了。
荷蘭人,啊不,他們遠非那么現代化。您看看他們,優哉游哉。他們干什么?這些先生靠那些婦人工作為生。這是些公的和母的,非常資產階級化的家伙,他們來這兒,像平時一樣,或是出于說謊癖,或是出于愚昧。總之,是由于想象力過于豐富或缺乏想象力。這些先生們不時地玩刀弄槍,然而,別以為他們認為有必要。角色要求這樣,如此而已,他們放出最后幾發子彈,害怕得要死。除此而外,我覺得他們比其他人更有道德,后者是慢慢地整家整戶地殺人。您沒有注意到我們的社會就是為了這種滅絕而組織起來的嗎?您自然是聽說過巴西河流中那些極小的魚,它們成千上萬地一齊攻擊粗心大意的游泳者,小口小口地,飛快地清掃他,一會兒工夫,就只剩下一具完整干凈的骨架。您看,這就是它們的組織。“您想過一種干凈的生活?像大家一樣嗎?”您自然回答說是。怎么能夠說不呢?“同意。人家于是就來清掃您。這是一門職業,一個家庭,一種有組織的娛樂。”小小的牙攻擊肉體,直至骨頭。我不公正了。不應該說這是它們的組織。這是我們的:爭先恐后地清掃別人。
終于給我們拿來了刺柏子酒。祝您健康。是的,大猩猩張嘴叫我博士。在這個國家里,人人都是博士或教授。他們喜歡尊敬,這是出于好意或是出于謙遜。在他們這里,至少惡毒的言行不是一種國家制度。無論如何,我不是醫生[4]。您若想知道的話,我來到此地之前是律師。現在,我是法官——懺悔者。
請允許我介紹一下我自己:讓——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為您效勞。很高興認識您。您大概經商吧?差不多?回答得妙!也很確切:我們什么事情都是差不多。這樣吧,允許我扮演偵探。您差不多同我一般年紀,有著差不多是飽經世故的四十歲人的深明底細的眼神,您差不多是衣著講究,也就是說,像我們那里的人一樣,而且,您有一雙光滑的手。因此,您是個資產者,差不多!是一個講究的資產者。對虛擬式未完成過去時皺眉頭,事實上就證明了您的文化程度,首先是因為您知道它,然后是因為它又使您厭惡。最后,我使您開心,不是自夸,這說明您的腦筋在某種程度上是開通的。因此,您差不多……但這又有什么關系?職業不如宗派那樣令我感興趣。請允許我向您提兩個問題,您只需在不覺得唐突的情況下再回答我。您擁有財產嗎?有一些?好。您與窮人分享嗎?不。那么,您是我稱之為保守的猶太人的那種人。我認為,如果您未曾奉行過《圣經》的教導,您是不會晉升得更快的。這使您晉升?那您知曉《圣經》嘍?您真使我感興趣。
至于我……還是您自己來判斷吧。從身材、肩膀、人家常說是兇惡的臉來看,我更像個橄欖球員,是不是?但是,如果從談吐看,應該說我還有些高雅之處。向我的大衣提供毛的駱駝肯定是長了疥;然而,我的指甲修剪得干干凈凈。我也很世故,但現在卻不加提防地,只根據您的模樣就講了心里話。最后,盡管我舉止得體,談吐優雅,我卻是濱海區海員酒吧間的常客。算了,別打聽了。一句話,我的職業是雙重的,和人這類生靈一樣。我已對您說過,我是法官——懺悔者。在我身上只有一件事很簡單,即我一無所有。是的,我曾經富有過,不,我從未與人分享過什么。這證明了什么?證明了我也曾是一個保守的猶太人……啊!您聽見港口的汽笛了嗎?今夜,須德海上要起霧了。
您要走?原諒我拖住了您。如果您允許,我來付賬。您在墨西哥城,就是在我家里,我在這兒接待您感到非常高興。我明天晚上一如既往,肯定在這兒,我感激地接受您的邀請。您的路……那么……最簡單的是,我陪您一直到港口,您認為有所不便嗎?從那兒,繞過猶太區,您就會找到那些漂亮的大街,街上駛過擺滿鮮花、音樂聲震耳欲聾的電車。您的旅館就在其中的一條街上,當拉克街。您先走,請。我嘛,我住在猶太區,直到我們的希特勒兄弟們打掃地盤的時候一直這樣叫法。什么樣的大清洗啊!七萬五千猶太人被關進集中營或被屠殺,這是真空清掃。我欣賞這種專心致志,這種有條不紊的耐心!如果沒有魄力,就該有方法。這兒,這種方法其效如神,沒說的,我住在發生了歷史上最大的罪行之一的地方。也許正是這個幫助我理解大猩猩和他的戒心。這樣我就可以同我的天性作斗爭,它使我身不由主地滑向同情。當我看見一張陌生的面孔時,我身上的某一個我就在敲警鐘。“減速。危險。”甚至在同情心最為強烈的時候,我還是保持警惕。
您知道嗎?在我小小的故鄉,有一次在鎮壓時,一個德國軍官彬彬有禮地請一位老太太在兩個兒子中選擇一個作為人質槍斃。選擇,您想象一下吧。那個?不,這個。眼睜睜地看著他走了。您別堅持,相信我,先生,任何意想不到的事都是可能發生的。我認識一個心地純良的人,他不愿意懷疑。他是個和平主義者,絕對自由主義者,他以同樣的感情愛全人類和所有的動物。一個優秀的靈魂,是的,這是肯定的。在歐洲的最后幾次宗教戰爭中,他歸隱田園了。他在門檻上寫道:“不管您來自何方,請進,歡迎您。”您說,誰答復了這盛情的邀請呢?民兵[5],他們如同進了自己的家,開膛掏了他的內臟。
噢!對不起,太太!原來她什么也沒懂。這么多人,嗯,這么晚了,還下著雨,幾天都沒有停!幸好,有刺柏子酒,黑暗中唯一的光明。您感到了投在您身上的金色的、紫銅色的光亮嗎?我喜歡趁著刺柏子酒的熱力,在晚上穿過城市。我整夜整夜地走著,冥想著,無休止地自言自語著。像今天晚上一樣,是的,我怕有些使您厭煩了吧,謝謝,您真是彬彬有禮。然而,話真是太多了,我一張嘴就要說。何況,這個國家激發起我的靈感。我愛這里的人民,他們擠滿了街道,夾在房屋和水之間的狹小空間里,被霧、冰冷的土地以及像洗衣盆一樣冒著氣的大海包圍著。我愛他們,因為他們是雙重的,他們在這里,同時又在別處。
真的,聽著他們沉重的、走在油膩的路上的腳步聲,看見他們在店鋪中間笨重地走過,那里面擺滿了金色的鯡魚和枯葉色的首飾,您一定以為他們今天晚上會在這里吧?您像眾人一樣,把這些老實人當成一些顧問和商人,懷著長生不老的希望去數他們的錢,而他們唯一的雅興就在于有時戴著寬大的帽子聽講解剖學?您錯了。的確,他們在我們身邊走著,但是,看看他們的腦袋在哪兒吧:在那紅綠招牌下由霓虹、刺柏子酒和薄荷酒組成的迷霧中。荷蘭是個夢,先生,一個黃金和煙霧的夢,白天煙霧迷漫,夜晚金光閃爍,日日夜夜相繼如斯,這夢里充塞著洛漢格林[6],如同那些心不在焉地騎著車把高高的黑色自行車的人一樣,像一群陰郁的天鵝,不停地盤旋在全國各地、大海周圍、運河兩岸。他們想入非非,頭裹在紫銅色的云中,在迷霧的金色的香煙中打著旋兒,高高飛起,睡眼惺忪,他們不在這里了。他們向幾千公里外進發,去爪哇,遙遠的島嶼。他們向印度尼西亞的那些做鬼臉的神祇祈禱,用它們裝點所有的窗戶。它們此時正在我們頭頂徘徊,然后作為莊嚴的表征,附在招牌和梯形的屋頂上,提醒這些思鄉的移民,荷蘭不僅僅是商人的歐洲,而且是大海,通向扶桑國[7]的大海,在那些島嶼上,人們死的時候瘋狂而幸福。
我信口說下去,我在辯護啊!對不起。這是習慣,先生,是天賦,也是我想讓您了解這座城市,事物的心臟!因為我們正處在事物的中心。您注意到阿姆斯特丹的同心的運河好像地獄之圈?資產階級的地獄,自然是糾纏著噩夢。當人們從外圈開始,一圈深似一圈,生活,亦即罪惡,變得越來越濃厚,越來越陰暗。這兒,我們正處在最后一圈。是……啊!您知道?見鬼,您變得更難于確定等級了。然而,您因此而明白為什么我能說事物的中心正在這里,盡管我們處在大陸的邊緣。敏感的人理解這些怪事。無論如何,看報的人和通奸的人不能走得更遠了。他們來自歐洲各地,在內海周圍黯然無色的沙灘上停下。他們聽著汽笛,徒然在迷霧中尋覓船舶的輪廓,然后,再越過運河,冒雨返回。他們在這里中轉,用各種語言到墨西哥城要刺柏子酒喝。我在那兒等著他們。
明天見吧,先生,親愛的同胞。不,您現在找得到路了,我在這座橋邊同您告別。我夜里從來不過橋。這是許了一次愿的結果。反正,您設想某人投水吧。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您跟著跳下去救起他,在嚴寒的季節,您將冒最大的危險!或者您丟下他,逃回家去,有時會感到莫名其妙的酸疼。晚安!怎么?玻璃窗后面的那些女人?夢,先生,廉價的夢,神游印度!這些人涂抹著香料。您進去,她們拉上窗簾,航行于是開始。裸體之上,有神降臨,島嶼癲狂,隨波逐流,棕櫚覆蓋,如臨風之亂發。不妨一試。
什么是法官——懺悔者?啊!您對我的這個稱呼感到奇怪。請相信,其中并無任何戲謔,我可以解釋得更清楚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甚至是我的職務的一部分。但是,我應該首先擺出一定數量的事實,這有助于您更好地理解我的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