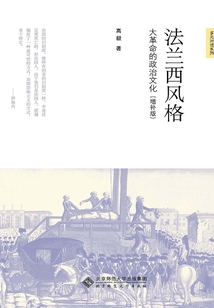
法蘭西風(fēng)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增補(bǔ)版)
最新章節(jié)
- 第17章 增補(bǔ)版跋
- 第16章 后記
- 第15章 附錄二:法國(guó)式革命暴力與現(xiàn)代中國(guó)政治文化[1]
- 第14章 附錄一:中法文化在法國(guó)大革命問(wèn)題上的歷史性互動(dòng)[1]
- 第13章 參考書(shū)目
- 第12章 結(jié)語(yǔ):群眾現(xiàn)象與法蘭西內(nèi)戰(zhàn)式政治風(fēng)格的形成
第1章 序
十年浩劫把歷史研究引入死胡同,十年改革開(kāi)放給歷史科學(xué)帶來(lái)了新生。本書(shū)的出版就是一個(gè)生動(dòng)的實(shí)例。
從1977年起我得以重操舊業(yè),講授西方史學(xué)史,評(píng)介西方史學(xué)流派,招收研究生;同時(shí)邀請(qǐng)外國(guó)知名歷史學(xué)家來(lái)校講學(xué),選拔優(yōu)秀中青年學(xué)者到國(guó)外進(jìn)修。
本書(shū)作者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考入北京大學(xué)世界史專(zhuān)業(yè)的高材生。他于1977—1981年讀完本科,1981—1984年作為碩士研究生,碩士論文是對(duì)丹東的研究,接著又在我的指導(dǎo)下寫(xiě)博士論文。正如高毅在《后記》中所述,他有幸在選擇論文題目時(shí),先后受到法國(guó)巴黎大學(xué)法國(guó)革命史講座教授米歇爾·伏維爾和美國(guó)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法國(guó)史教授林·亨特女士講課的啟發(fā)。這兩位學(xué)者代表法國(guó)革命史研究中的新學(xué)派,前者從社會(huì)史轉(zhuǎn)向心態(tài)史的研究,后者著重民族政治文化的考察。從1985年到1987年,高毅有機(jī)會(huì)到瑞士日內(nèi)瓦大學(xué)進(jìn)修,又受到該校歷史學(xué)教授、原籍波蘭的布羅尼斯洛·巴茨柯的影響。回國(guó)后他用了一年時(shí)間完成了博士論文《熱月反動(dòng)與法國(guó)革命的政治文化》,在答辯中博得專(zhuān)家們的好評(píng)。
兩年前,高毅曾考慮要把這篇博士論文修改出版。最近他把書(shū)稿拿給我看,要求我在書(shū)前寫(xiě)幾句話。我驚異地發(fā)現(xiàn),這是一部嶄新的著作,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論文原來(lái)的范圍,面目煥然一新,在論點(diǎn)和論據(jù)上更加充實(shí)和成熟,更有說(shuō)服力,堪稱為近年來(lái)外國(guó)史研究領(lǐng)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可喜可賀!
我國(guó)歷史學(xué)界經(jīng)過(guò)“文化大革命”后的“撥亂反正”和關(guān)于真理標(biāo)準(zhǔn)的辯論,認(rèn)識(shí)到必須運(yùn)用新方法,掌握新材料,研究新問(wèn)題,才能進(jìn)一步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xué)。一時(shí)出現(xiàn)“方法論”熱,各國(guó)各派的史學(xué)方法先后被引進(jìn),不少都冠以“新”字——新經(jīng)濟(jì)史、新政治史、新社會(huì)史……遺憾的是,介紹多,評(píng)論少;宣揚(yáng)多,應(yīng)用少;即使有個(gè)別人嘗試用某種“新方法”來(lái)重新說(shuō)明歷史,也往往牽強(qiáng)附會(huì),缺乏說(shuō)服力,失敗的多,成功的少。除了難度大之外,其中還帶有幾分政治風(fēng)險(xiǎn),使嘗試者望而卻步。
高毅此書(shū)也是一種大膽嘗試,在我看來(lái)是一次相當(dāng)成功的嘗試。它的主題是1789年的法國(guó)大革命,這是一個(gè)被成百上千位中外歷史學(xué)家重復(fù)闡述過(guò)的老題目,特別是為了紀(jì)念法國(guó)大革命200周年,法國(guó)和世界各地又出版了數(shù)百種新著。一個(gè)中國(guó)歷史工作者,怎樣才能用自己的觀點(diǎn)分析總結(jié)法國(guó)大革命的經(jīng)驗(yàn)而不落窠臼?不僅做到不落窠臼,而且開(kāi)辟研究和思考的新徑呢?
我們過(guò)去在法國(guó)革命史學(xué)中,常常滿足于說(shuō)明這場(chǎng)革命的資產(chǎn)階級(jí)性質(zhì),革命群眾的先鋒推動(dòng)作用,革命領(lǐng)導(dǎo)者的更替和革命的階段性,雅各賓專(zhuān)政的必要性、徹底性、局限性及其失敗的必然性,等等。這些論述都是對(duì)的,但是總感到有所不足,或者說(shuō)有點(diǎn)一般化、簡(jiǎn)單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沒(méi)有抓住這場(chǎng)革命的民族特點(diǎn),即法國(guó)政治文化的特點(diǎn);第二,沒(méi)有分層次地對(duì)各種革命現(xiàn)象與行為進(jìn)行剖析,區(qū)別精英文化與群眾文化,并揭示它們的分合規(guī)律;第三,沒(méi)有把影響革命進(jìn)展的各種因素,特別是那些中介因素,全都挖掘出來(lái),從而更細(xì)致、具體地說(shuō)明革命成敗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高毅此書(shū)之所以成功,可能正是由于他注意到我們過(guò)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而努力加以改進(jìn)。他善于借鑒國(guó)外史學(xué)方法與成果,把年鑒史學(xué)、心態(tài)史學(xué)、政治文化史學(xué)的一些基本概念引進(jìn)歷史研究,從而強(qiáng)化了我們的闡釋武器,加深了對(duì)歷史現(xiàn)象的認(rèn)識(shí)。年鑒史學(xué)引導(dǎo)我們注意在歷史長(zhǎng)河中起長(zhǎng)期作用的那些結(jié)構(gòu)因素;心態(tài)史學(xué)著重考察群眾意識(shí)與無(wú)意識(shí)的作用;政治文化史學(xué)強(qiáng)調(diào)民族的政治傳統(tǒng)、習(xí)慣、觀念、行為、象征物對(duì)群眾特別是革命運(yùn)動(dòng)的影響。讀者在此書(shū)中自會(huì)發(fā)現(xiàn)這些不同的史學(xué)流派方法的反映和痕跡。
可貴的是作者并不是亦步亦趨地效顰某種流派,更沒(méi)有片刻放棄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chǎng)和觀點(diǎn)。他在法國(guó)革命史研究中“始終以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必然歷史進(jìn)程作為認(rèn)識(shí)的基本前提”。他贊同林·亨特教授的許多看法,但不同意她孤立地對(duì)待法國(guó)的民族政治文化,把它同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割裂開(kāi)來(lái)的傾向。他在分析法國(guó)革命的激烈性和徹底性時(shí),牢牢抓住革命資產(chǎn)階級(jí)與群眾結(jié)成聯(lián)盟這條主線,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以精英為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jí)亞文化與革命群眾亞文化之間的區(qū)別與對(duì)立。
但是作者也反對(duì)把一切歷史現(xiàn)象都同經(jīng)濟(jì)生活直接掛鉤,也不擬用階級(jí)劃分來(lái)說(shuō)明全部政治行為,因?yàn)樗J(rèn)識(shí)到在歷史表象和“終極原因”之間存在著無(wú)數(shù)“中介因素”,同時(shí)在驅(qū)使人們參與政治活動(dòng)的無(wú)數(shù)動(dòng)力中,不僅有各階級(jí)的經(jīng)濟(jì)利益,還有各種看不見(jiàn)、摸不著的精神、思想、感情、心理因素。例如,法國(guó)革命為什么比早在150年前爆發(fā)的英國(guó)革命更激烈、更徹底?除了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思想條件更成熟這一根本原因外,法國(guó)革命者從一開(kāi)始就具有“與傳統(tǒng)徹底決裂”的信念。這種決裂感一度支配著革命群眾去砸爛舊制度的一切。隨著革命的開(kāi)展,國(guó)內(nèi)外反動(dòng)勢(shì)力總是處處企圖抵抗和反撲,于是社會(huì)上滋生一種無(wú)與倫比的緊張氣氛,人們終日在這種氣氛中生活,自然而然地產(chǎn)生一種危機(jī)意識(shí),把敵對(duì)勢(shì)力的一切活動(dòng)都看成是“陰謀”,因而產(chǎn)生一種“陰謀憂患”,群眾輕信任何謠言。這樣,決裂感、危機(jī)意識(shí)、陰謀憂患與謠言輕信癥結(jié)合在一起,推動(dòng)著法國(guó)革命群眾一步一步地向最激烈的方向前進(jìn)。這樣的分析豈不比一般地談?wù)摗案锩纳仙A段”更生動(dòng)、更具體、更有說(shuō)服力嗎?
與此同時(shí),法國(guó)革命也需要正面的象征物來(lái)鼓舞自己:三色徽、小紅帽、自由樹(shù)、瑪麗安娜、赫居利斯等都有其特殊功能。人們以更換人名、地名來(lái)表示對(duì)革命的支持,連語(yǔ)言、日歷和服裝也革命化了。為了法國(guó)的再生,需要培養(yǎng)與舊社會(huì)迥異的“新人”——對(duì)革命者的崇拜代替了舊的偶像崇拜。“聯(lián)盟節(jié)”成為象征革命群眾團(tuán)結(jié)的最盛大的節(jié)日。這些都是我國(guó)史學(xué)界忽略的重要側(cè)面,高毅則在本書(shū)中加以充分闡述。
為了建立新的政體,在革命者中間展開(kāi)了一系列政治辯論,涉及重權(quán)輕法與重法輕權(quán)之爭(zhēng),公意高于王權(quán)與王權(quán)高于公意之爭(zhēng),一院制與兩院制之爭(zhēng),強(qiáng)制委托制與代議制之爭(zhēng),代議制與直接民主制之爭(zhēng),等等。但是爭(zhēng)來(lái)爭(zhēng)去,一直到拿破侖三世1870年在色當(dāng)投降,才最后擺脫君主制,這只能說(shuō)明法國(guó)專(zhuān)制主義傳統(tǒng)的根深蒂固和徹底決裂信念的不現(xiàn)實(shí)性。如果僅用法國(guó)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的普遍性來(lái)直接解釋這種政治保守現(xiàn)象,不顧政治文化的作用,恐怕是又犯了簡(jiǎn)單化的毛病。
諸如此類(lèi)的革命政治文化的特點(diǎn)還有不少。例如,雅各賓專(zhuān)政強(qiáng)調(diào)政治的公開(kāi)性、透明性和反黨派性(顯然不是不要黨派,而是不要?jiǎng)e人的黨派),并且以此為借口來(lái)消滅政敵。細(xì)讀此書(shū),自會(huì)發(fā)現(xiàn)更多真知灼見(jiàn)。我順便提醒初學(xué)者,這不是一本易讀的書(shū),決非瀏覽一下就能抓住要點(diǎn);而一旦進(jìn)入“角色”,你會(huì)獲得雙倍的收益。
在本書(shū)的結(jié)尾,作者指出:法國(guó)革命留下了豐富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并創(chuàng)造了一種“內(nèi)戰(zhàn)式的政治風(fēng)格”,它在革命后近百年甚至更長(zhǎng)時(shí)期內(nèi)影響著法國(guó)的政治生活。這種政治文化的某種表現(xiàn)對(duì)我們而言也并不陌生。高毅的勞動(dòng)果實(shí)不僅有益于世界史工作者,也有助于中國(guó)史研究的另辟蹊徑。祝愿高毅在歷史教學(xué)和科研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張芝聯(lián)
1991年4月于北大朗潤(rùn)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