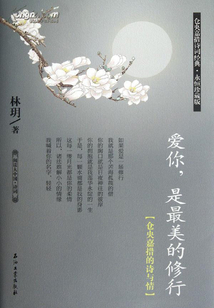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7評論第1章 序 那一日 那一世
魂斷青海湖
他說,他見到過那片湖的。
像仙子的一顆眼淚穿越蒼茫的天空,淌過一路的星河,碎在如茵的草地上。他撲進了青海湖的巨大的畫卷里。這是倉央嘉措夢中的世界:席芨草瘋狂的席卷了湖畔,接葉連天。有大顆大顆的露水鑲嵌在這一片綠色中,星星點點,匯成一地的銀河。高原的風張開它巨大的翅膀,撲在青海湖的懷抱里,油菜花在風的臂彎里梨渦淺笑。
那像藍寶石一樣晶瑩的一片海,就是他魂牽夢繞的青海湖吧。
藍錦緞一樣的湖面,被風揉碎了,一層一層的泛著金色的粼粼光波。像少女寬寬的裙擺,飄在風中。這是一個溫柔的湖,恬雅的湖。寧靜而寬廣,碧泄千里、袤邃無垠。
為了這盛大的遙遠的相見,他奔赴而來,是期望已久的約會。
他說,這樣美麗的湖,在夢中,他一定見過的。
他說,是瑪吉阿米的魂魄牽引他來到這里的。
他說,你看,這片湖是瑪吉阿米的眼睛。
他喃喃著,瑪吉阿米,我來了……
白色的仙鶴,
請把你的雙翅借我,
我不遠飛,
只到理塘就回。
公元1706年,藏歷第十二饒迥火狗年。青海湖畔。
解送倉央嘉措的大隊人馬,噠噠而來。這是一支由漢、藏、滿、蒙等各色人等組成的隊伍。奉康熙皇帝的命令,將倉央嘉措解送回京。
穿過茫茫的戈壁,踏過青翠的草原,翻越了唐古拉山脈。在青海湖畔,他們停下了匆匆的腳步。
青海湖,藏語叫措溫波,意思是青色的湖。十一月的青海湖,沒有綠地和花朵的點綴,冷冷清清。在一片枯黃的天地里,青海湖像少女的一汪眼淚,躺在日月山的懷抱里。這里,是倉央嘉措的埋骨之地。
炊煙伴著暮色裊裊飄起,月亮也拉開了她米色的圍裙,飄在空中。風吹在臉上,落在倉央嘉措的眼睛里、睫毛上。有白色仙鶴在水面上滑翔,它的紅掌輕輕的撥動湖面的漣漪,折彎了光潔的湖水。它們的長頸糾結在一起向天悲鳴。
押送倉央嘉措的兵丁,大多是黃教弟子,對活佛的虔誠和敬畏,讓他們對難中的倉央嘉措更添了一絲虔敬和尊重。一路上悉心照顧,恭恭敬敬。
篝火燃起來,噼里啪啦的響。蒙古兵丁在帳篷外大口的喝酒吃肉,吵鬧聲在遙遠的山谷回蕩。有兵丁送來了新做好的飯菜。
他說,佛爺,該吃飯了。
倉央嘉措閉目不語。
他說,他不是佛。
碧海青天夜夜心。寶藍色的湖水在風中起舞,敲打著湖畔,唱著不知名的曲子。倉央嘉措站起來,走出大帳。是瑪吉阿米來了嗎?你聽,那清脆的歌聲是她對我的深沉的呼喚。
寂靜的風張開它寬大的翅膀,撲向空寂的草原,落在倉央嘉措的懷抱里,把他的蕃衣吹成了一面旗子。閉上眼睛,有歌聲在耳畔飄蕩,似離人在哀傷的哭泣。
在看得見你的地方,我的眼睛和你在一起。
在看不見你的地方,我的心和你在一起。
青海湖靜謐著,似乎在等待著一場盛大的死亡。
水的鱗波在藍色的湖面上蔓延,星星碎在青海湖的眼波里,汪著的全是淚水。黑夜在寶藍色的星空上蒙了一層黑紗,青海湖更加神秘和朦朧,一如倉央嘉措的那顆躍動的心。在青海湖柔軟的湖畔邊,他立在湖邊,顧影自憐。
瑪吉阿米的滿月似得臉龐浮在青海湖面上,那么清晰。他伸手,觸到的卻是水的冰涼,那冷是一條冰冷的蟲,吞噬了他的骨髓,他禁不住打了一個哆嗦。他忽然明白,瑪吉阿米,成為一個夢一樣的傳說了。
那些濃烈的愛,那些熾熱的恨,還有那些蒼涼的故事,落在時間的尾巴上,成了落幕的帷帳。他說,這結局,他要自己做決定。
在青海湖的柔波里,化作一尾魚,來生,會不會多一些自由?湖水甩動著裙角,在風的懷抱里翻騰,一層接著一層。它調笑著,打濕了倉央嘉措的衣袖。
這剩下的路,他要靠自己來走了。
一步、兩步、三四步。在踏進湖水的一剎那,他的心是歡愉的。在星海中,在藍色的天鵝絨被里,靈魂綻開它自由的翅膀,在湖心里飛翔,像遠離,又像是命途的回歸。
瑪吉阿米,我來了。
三生石畔,我愿與你同行。
青海湖的余波
桑杰嘉措曾說,青海湖是文成公主的眼淚匯成的。
一千年以前,一場雨淋濕了長安。繁華的長安街頭,有人在送行。灞橋邊有人折柳,有人揮手,有人遙望,有人淚水流。唐蕃的和親隊伍穿過長安的磚瓦,一步一步走出了長安的視線。坐在皇家鸞轎里的是唐太宗的宗室女文成公主。
貞觀十五年,24歲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持節護送下遠嫁“吐蕃”王松贊干布。西去的腳步,是一個王朝的鐵定。長安街頭的胭脂,散淡在蒼涼的西風里,飄向不知名的遠方。
山水,一程又一程;風雨,一更又一更。長安在歲月里,漸行漸遠漸無窮。文成公主,這個美麗溫婉的女子,她知道,此一去萬水千山,此一走離別經年。那一樹緋紅的桃花,還會出現在長安的夢里嗎?那些飛在風中的紙鳶,還會流連長安的天空嗎?
翻過日月山,前面,就是吐蕃的領地了。草原在眼前鋪開一片翠綠,把田疇和阡陌拋在身后。松贊干布的迎親隊伍在山的另一邊守候,大唐的使者要返唐了。有那么一刻,她心里的私心越出水面,她希望這條路可以再長一點再長一點,護送的隊伍可以再慢一點再慢一點。或許這樣,她可以再看一眼大唐的風月,可以再睹一次東土的花雪。
琵琶幽怨的聲音一次次嗚咽,唱一首離別曲,留一地相思,給長安。再回首一遍,把大明宮刻在心里,把文宗皇帝的叮囑刻在心里,把父母的白發刻在心里。
勸爹娘,莫把兒思念。
日月神鏡一直握在手中,緊緊的。母親說,思念的時候,可以在銅鏡里回望長安。
金色的鏡子在日中的沐浴里有著斑駁的光線。對著銅鏡再理一次青絲,那如云的鬢發,母親一次次挽起又放下,眼淚落下來,在青絲間流轉,宛若明珠。
父親說,這是我們李家最大的冠冕。可是,父親,這是榮耀,你又為何在月下默然長嘆?為何在揮手間讓淚水濕了雙眼?
眼淚落在銅鏡里,氤氳了如花的容顏。長安,請你走慢一點……
一揮手,銅鏡落地。一半如日,一半如月。
人們說,日月山是日月神鏡的碎片隆起的。日月山是文成公主的守護神,忠誠地守護她西去的陽關,忠誠地守護她的愛與痛,一個女子的和平的守望,融化了西風中的劍戟刀槍。青藏高原的風塵,在她回望的眼睛里,溫柔的收斂了翅膀。
她知道,以后陪伴她的,就是這蒼茫的草原了。
眼淚不自主的落下來,在日月山間匯成一泓細流。讓思念伴著淚水前行,流向長安吧。青海湖懂得,她的所有的相思。
日光城的陽光明晃晃的,落在眼睛上,是溫暖的感覺。拉薩天空里的云,懶懶的睡在藍湛湛的天空的懷抱里。文成公主——這個大唐美麗的女人帶著“和邊”的使命,不辭積年累月的長途跋涉之苦,要去雪域高原傳播友誼,傳播文化,走向這離天最近的地方。
溫柔的淚水熄滅了燃燒的戰火,遠去了青色的硝煙。因為這個女子,挺拔的高原里開出和平的芬芳。
《舊唐書·吐蕃傳》中記載,松贊干布“率其部兵次栢海,親迎于河源,見道宗執子婿之禮甚恭。既而嘆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見到文成公主端莊賢淑,與高原女子的質樸純真大不相同,更仰慕有加。既而“漸慕華風”,在文成公主的協助下,在藏區移風易俗,推進了社會文明。
文成公主入藏時,隨行的隊伍非常龐大,唐太宗的陪嫁十分豐厚。《吐蕃王朝世襲明鑒》記載,有“釋迦佛像,珍寶,金玉書櫥,360卷經典,各種金玉飾物”數不勝數。文成公主善良賢淑,深受藏族同胞的熱愛,在她的影響下,漢族的碾磨、紡織、陶器、造紙、釀酒等工藝陸續傳到吐蕃;她帶來的詩文、農書、佛經、史書、醫典、歷法等典籍,促進了吐蕃經濟、文化的發展,加強了漢藏人民的友好關系。
文成公主攜帶入吐蕃的佛主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被供奉在布達拉宮大昭寺圣殿。
這些,都是第巴桑杰嘉措告訴他的。
桑杰嘉措說,青海,是鑲著一顆翡翠玉盤的神奇的土地,這是一片和著眼淚和寂寞的土地。這也是藏傳佛教信徒靈魂皈依的故土。這里是弘揚佛法的圣地,蒙古人在寧靜祥和的梵音中,放下嗜血的屠刀,文明的光輝在青海復蘇。
他懂得,青海湖的包容和愛。
1706年的冬天,蒼涼的西風席卷青海湖畔,青翠的綠毯擱淺成黃色的斑點,有枯樹在風中哀哀的哭泣。就在這一年,倉央嘉措的故事停留在青海湖邊,化作一則傳奇。
傳奇終究還是傳奇。人們不愿意相信,這個六世活佛的傳奇人生就此戛然而止。有人猜測,有人考證,有人記錄,有人傳唱。他的死因在歲月里顛簸,最終成了一個劃不上的句點。
關于倉央嘉措的歷史蹤跡,至今未成為定格。在《清史稿》中也有,倉央嘉措“行至青海湖,亡逝于此”。這是官方留給后人的最后的憑證。
關于倉央嘉措死亡的說法,有人說,他病逝于青海湖畔。這也是大家最認可的一種說法。《清圣祖實錄》中有:“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庚戌,理藩院題:“駐扎西寧喇嘛商南多爾濟報稱:拉藏送來假達賴喇嘛,行至西寧口外病故。假達賴喇嘛行事悖亂,今既在途病故,應行文將其尸骸拋棄。”從之。”天寒地凍的時節,再加上長途跋涉,倉央嘉措體力不支,染病身亡。這或許是歷史給人們的最好的說法,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平息這一場政治紛爭。可是,歷史也會留下疑點待人們來垂詢。在《清史稿》的列傳中,關于倉央嘉措的史料只是只言片語,這不得不讓人們費疑。所以,有些學者提出了謀殺之說。
一場謀殺的蓄謀,要從最根本的利益說起。死亡的直接矛頭指向了拉藏漢。他也是最希望倉央嘉措死的一個人。不可否置,拉藏漢和倉央嘉措的死有重大關聯。他的一句“假活佛”,將倉央嘉措推進死亡的邊緣。這也是人們愿意將死因歸咎于他的緣由。倉央嘉措對拉藏漢來說,已經構不成任何威脅。在押解的路上行刺倉央嘉措,對拉藏漢來說,是件沒有必要的事情。
民間更多的人相信倉央嘉措并沒有死。《西藏民族政教史》:“行至青海地界時,皇上降旨責欽使辦理不善,欽使進退維艱之時,大師乃舍棄名位,決然遁去。周游印度、尼泊爾、康、藏、甘、青、蒙古等處。弘法利生,事業無邊。爾時欽差只好呈報圓寂,一場公案,乃告結束”。人們說,押送倉央嘉措的兵丁,不忍看他顛沛流離,苦苦哀求他離去,路過青海湖時,將他放生。世人憐惜這位活佛,更愿意他遠走他鄉,用漂泊來成就一段風流。《倉央嘉措秘傳》中說,倉央嘉措自青海湖遁去后,云游四川、尼泊爾、印度、返回到西藏,最后在內蒙古圓寂。這或許是對他生命的最好的詮釋。一個活佛,最好的光環,是讓自己解脫,還眾生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