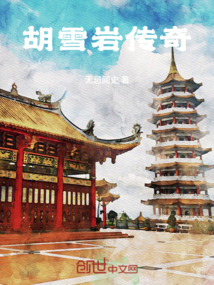
胡雪巖傳奇:權財雙修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
杭州梅花碑茶館,午后的人聲像鍋里的湯,翻滾著熱氣,也翻滾著閑話。
破口青瓷蓋碗里兩片龍井葉子浮浮沉沉,淡得快成白水。王有齡攥著蓋碗,喉頭滾動,卻像吞下了一口“窮味兒”。他三十整,青布長衫洗得發白,肘上補丁又薄又亮,鞋面開了線,用黑線縫死,走一步便露出半截腳趾。茶店伙計瞧他眼熟——天天來,天天坐角落,像孵一顆遲遲不肯破殼的蛋,江湖人給他取了個綽號:“孵茶王。”
“喲,王老三,今日又來‘孵龍井’?”鄰桌有人半笑半嘲。
王有齡裝沒聽見,抬眼一瞬又低下去。不是沒脾氣,是沒本錢。做生意要本錢,做官也要本錢——這世道就這么直白。
門口忽地一陣光。一個少年踏進來,細白夏布長衫漿得筆挺,里面紡綢小褂褲,腳上玄色貢緞雙梁鞋,白竹布襪口露出一線,整個人像剛從水里撈上來那般清亮。他笑起來有梨渦,眼睛卻能照顧四面八方,一掃店里,就在王有齡桌旁坐下。
“王兄,拼個桌?”少年落座自來熟,手里還捏著一塊折得方方正正的手巾包。
“坐。”王有齡淡淡,聲音里沒什么起伏。
少年轉身對掌柜打個響指:“一壺黃酒,兩碟小菜——花生、油焙馀,再給王兄續一碗滾水,別再拿白開水糊弄人。”
掌柜“噯”了一聲,眉眼彎起來。少年回身,又笑著道:“稍等,我把這邊棋盤收拾一下,賺兩口酒錢。”
他挽袖去下棋。茶店里“撞車”、“爭炮”的吆喝聲起起落落。少年開局用“雙車錯”,第二盤“馬后炮”連殺,第三盤更狠,小卒一路逼宮,把對手的帥殺得走投無路。三盤畢,他拎回那手巾包,在桌上一抖——二兩碎銀叮叮當當地滾出來,亮得叫人心口一跳。
“王兄,走,擺一碗。”他笑意像春風,“棋友們請客。”
擺一碗,是杭州話,去小酒店對酌。
王有齡下意識擺手:“不必破費。”
“誰破費?他們破費。”少年用下巴點點那幾位輸棋的茶客,輕松得很。旁桌有人嘟囔:“這小子的棋,邪氣。”也有人艷羨地嘖嘖:“這手氣,真闊。”
盛情難卻,再坐下去只能繼續讓人嚼舌根。王有齡站起身,跟少年出門。兩人沿著青石板路一路上吳山,風自山隙里來,帶著熱氣與桂花殘香。山脊上“立馬吳山第一峰”的碑影在晚照下拉長,腳下燈火次第點亮,杭州城像一盤展開的棋,黑白分明。
他們選了處風口不大的空地席地而坐,小酒店掌柜熟門熟路送來酒菜。黃酒溫得正好,油焙馀熱氣騰騰,花生米脆得響。少年舉杯:“先干為敬。”
酒到半酣,少年收了笑,眼神忽地正了:“王兄,我憋了好幾回,總覺得該問問你。”
“問。”
“我略懂麻衣相法。”少年瞇起眼,像在衡量他眉眼間的棱角,“你是大貴之相,不該困在茶館角落孵茶。為何整日消磨在此?”
王有齡指尖一緊,把杯口碰在唇邊,酒沒入口,他先笑了:笑少年天真,更笑自己心里被“貴相”兩字磕出的一點火星。他伸手取了塊油餅,咬得極慢,像嚼一段咽不下去的日子。
“你要我說什么?”他望向山下燈海,喉間壓著悶氣,“做生意要本錢,做官也要本錢。我一文不名,拿什么翻身?”
“做官?”少年挑眉,“你我都沒進過學,是白丁。哪來的官做?”
“不能捐嗎?”王有齡抬眼,聲音不高卻直直落下。
山風帶著燈油味兒吹過。少年笑意一斂,杯子輕輕一扣:“捐,可以是紙門神,也可以是梯子。你想當門神,還是想爬?”
王有齡沉默。
“先說膽子,再說法子。”少年伸手在空中一劃,像落子,“明日城南恒生糧行鬧賬,掌柜的指伙計偷銀,伙計嚷掌柜使黑心,里正左右為難。你去替里正理賬,三件事:一刻三分內點明誰做了手腳;讓雙方心服;拿回屬于你的銀子。”
“屬于我的銀子?”
“破了局,自有人替你擺酒。”少年笑,笑意里卻有鋒,“你不是沒本事,是沒人給你一個讓你發聲的戲臺。戲臺我搭,你敢不敢唱?”
風從衣襟里鉆進去,帶走了酒意留下一身清醒。王有齡盯著少年,良久,像是咬碎了牙里那股不甘:“敢。”
“好。”少年舉杯相碰,“明日辰時見。”
他收起手巾包,碎銀叮哐一聲合在一起,像把一個承諾封死。
次日辰時,城南恒生糧行門口圍了半城人。米袋像小山,塵灰撲面,掌柜金某油光滿面,嘴皮子利得像涂了桐油;被指為賊的伙計阿貴眼睛紅腫,嗓子喊啞:“我沒偷!”
里正叉腰站在堂前,臉憋得通紅:“都別吵!”
人群讓出一條縫,一個穿舊長衫的人從縫里進來,神情冷靜。里正一愣:“你是——”
“王有齡。”他拱手,聲音不緊不慢,“借老爺威名一用,此處賬目,可否讓我過一過?”
金掌柜冷哼:“你懂賬?”
王有齡沒搭理,袖口一挽,翻開賬冊。紙張泛黃,字跡龍飛鳳舞,他先看每日入出,再看短平長欠,最后把“米耗”另外一冊抽出來,單獨翻。指尖在算盤梁上輕輕一敲,眼神已把整個糧行從里到外走了一遍。
“先借秤一用。”他淡淡開口。
伙計搬秤來。王有齡并不立刻稱,先抓兩把米請三個人分別憑手感分成五份,又讓在場老米行掌秤。秤星一動,針尾總在刻度前半分跳。
“舊秤一斤十六兩,新秤十六兩半?”他問。
阿貴忙不迭點頭:“前些日子掌柜換的,說舊秤不準。”
“舊秤不準,換新秤也要打招呼,‘耗’該記在公賬。”王有齡指尖點在賬冊上,“六月初八,入庫五十擔,出庫四十八,按理余兩擔,你只記一擔半。半擔去了哪兒?”
“米蟲吃了。”金掌柜翻白眼。
“蟲要吃半擔,這糧行早該關門。”王有齡不客氣,“再看六月初十,出庫四十五擔,收銀三十六兩八錢。按今日米價,一擔八錢,你這帳打給誰看?”
人群笑聲四起。金掌柜臉漲成豬肝色:“你胡說!”
“胡說的是你。”王有齡拇指輕擦算盤,“你兩頭吃——換秤多出的半兩,壓在伙計頭上記‘短斤’;又把進出價差記‘暗耗’,銀子半路截留。別急,我還沒問庫房的‘水耗’怎么算呢?這幾天杭州潮大,你泡米的水加多了,行,但你把那部分記進阿貴名下,是個什么意思?”
阿貴眼圈通紅,嘴唇哆嗦著:“我……我真沒拿一文。”
里正板起臉,轉向金掌柜:“金老金,你解釋。”
金掌柜支支吾吾,滿頭汗,忽地往后一坐,拍腿:“我認錯!我認錯!都是下頭小管事搞的鬼……我……我疏于管教。”
“你疏于的是良心。”王有齡把賬冊啪地合上,“今日里正在此,第一,把阿貴名下的‘短斤’污名去掉;第二,把這三個月暗耗補足——銀子補到公賬,不許拿阿貴當替死鬼;第三,把換秤的事寫告示貼門口,以后秤星半分不準,米價少半分,別讓鄰里吃虧。”
人群里先是靜,隨即炸成一片“好——!”“說得好!”掌柜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卻又不敢公然對著眾人耍橫。里正撫須,連連點頭:“就這么辦。”
不多時,小柜里端出一碗銀子,十兩。金掌柜硬著頭皮送到王有齡手邊:“兄臺破局之功,理當謝禮。”
王有齡看都沒看:“兩兩就夠。”
里正愣住:“其余八兩——”
“恒生拿去,把米價往下放半分,算今天鬧賬的補償。”王有齡語氣平靜,“別又記到伙計頭上。”
里正先是一怔,隨即拍案大笑:“痛快!王兄,硬氣!”
人群的視線換了味兒。昨日他們還笑他“孵茶”,今日已有人悄悄問他姓甚名誰、住在何處。掌柜訕笑著把告示寫好貼門口,墨跡未干,風一吹,紙貼在門上“呼啦”作響。
散場時,門柱旁靠著一個熟悉的身影,扇骨輕敲手心,笑意微微。
“小胡。”王有齡走過去。
“嗯。”少年朝他豎了個大拇指,“唱得不錯。”
“還差點火候。”王有齡淡淡,卻難掩眉間那絲舒展。
“走——擺一大碗。”小胡輕笑,“今日換我埋單。”
夜來吳山,燈火比昨夜更盛。兩人又回到那塊風口不大的空地。小胡把酒一推:“你今天做了三件事——翻了賬,立了名,收了心。”
“收心?”
“對。”小胡眼睛透亮,“你拒掉八兩,是拿聲名做本錢。這東西比銀子升得快。你若只拿銀子,明天就被人罵成‘借鬧賬撈錢的’;你讓恒生降價,鄰里記你情;里正看你順眼,官面上有了臺階。捐,說白了是把門票拿在手里,但爬不爬得上去,看的是人心。”
王有齡沉默片刻,忽然笑了,很淡,卻像把一塊壓胸口的石頭挪開:“你看得真透。”
“別急著夸我。”小胡再次把折紙攤開,是一張絲價行情,“明后兩日,城西石橋碼頭有一票貨,外包絲。四和洋行放風壓到八錢一斤,鄉下蠶戶哭了半條街。我已經打招呼讓貨主暫時壓貨。你去找兩個舊識——里正,和三塘橋姚掌柜。明天你帶他們去見貨主,開一個‘公議價’——我們不跟洋行對賭,我們跟鄉人站一起,價升到九錢,不貪天之功,只拿轉運的水腳與信息錢。”
“洋行肯?”王有齡皺眉。
“他們當然不肯。”小胡笑得溫柔又鋒利,“他們會放話,說你擾亂市價,說你今日鬧恒生另有居心。甚至,今晚就會有人來敲你的門——試試你的膽色。”
風忽然涼了一寸。吳山燈火在風里輕輕顫。
“所以我才問你。”小胡端起杯,低聲,“你真想捐?真想往上走?真想讓這城里再沒人敢拿‘孵茶’三個字堵你?”
王有齡握住酒杯,一仰而盡,熱辣從喉嚨一直燒到胸口:“想。”
“好。”小胡伸出手,掌心沉穩有力,“明晚子時,石橋碼頭不見不散。”
兩人掌心一合,像落下一枚最關鍵的棋。
夜更深了。王有齡回到住處,破木門、紙窗、半截油燈,屋里能叫得出名的只有一張塌塌米。他把今日所得兩兩銀子塞進枕頭底下,剛要吹燈,巷子里傳來腳步聲,細細碎碎,像一窩螞蟻在鐵皮上爬——先三道影,又一道人影,慢慢投到窗上。
“是不是這間?”外頭有人用極輕的杭州話問。
“王爺——”另一個人的笑,像蛇吐信,“聽說你今天在恒生,很能耐啊。”
一聲輕響,刀鞘碰在門框上。紙窗隨風一顫,油燈的火苗也抖了一下。
王有齡沒退,順手抄起床腳的竹竿,橫在門后。心跳很快,卻不慌。他忽然明白,這不是來談理的,是來試膽的——若這一步都邁不過,談什么捐、談什么往上走,都是笑話。
門被輕輕一壓,木栓“咔”的一聲裂開一道縫。王有齡眼一冷,竹竿前探,借著門縫直捅出去——
“哎喲!”一聲叫。門外的人顯然沒料他先手。幾乎同時,院墻上黑影一閃,一顆小石子“叮”的一聲打在門楣上。
那是暗號。
“各位,”一道帶笑的聲音從墻頭落下,“深夜造訪,不如改天擺一碗?”
小胡。
他手里沒有刀,只有一把紙扇。扇骨一合,敲在其中一人的手腕,那人“哎呦”一聲,刀落地。另兩人對視一眼,硬著頭皮放出狠話:“明晚,石橋碼頭見!”
腳步聲漸遠。屋里又只剩油燈的光。王有齡把門栓再頂上,額頭汗珠滾落,回身看向小胡。
“累不累?”小胡問。
“累。”王有齡笑了笑,眼睛卻亮,“但痛快。”
“痛快就好。”小胡拍拍他肩,“明晚燈底下說亮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