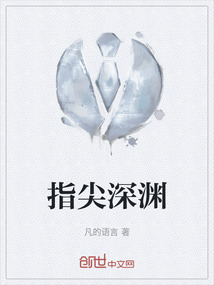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虛擬薔薇開——誘餌篇
第1回:數據樓深夜敲代碼,聊天窗突現俏佳人
夜深得像潑翻的墨,金融中心A座的第23層,只剩幾扇窗還亮著慘白的光,像懸在半空的孤眼。崔浩按了按發脹的太陽穴,指尖在鍵盤上敲出最后一個分號,屏幕上那串纏纏繞繞的AI量化交易模型代碼,終于停了滾動。空氣里飄著冷美式的酸苦味,混著中央空調吹出來的風——那風總帶著點金屬的涼,刮在臉上像沒磨過的刀片。辦公區早空了,只有他工位的電腦還亮著藍光,把眼底的紅血絲照得一清二楚。
三十五歲的崔浩,在這家中型券商的金融科技部待了八年。當年揣著代碼理想來的毛頭小子,如今成了AI模型調試小組的組長。說是組長,手下就倆剛出校門的應屆生,真要啃硬骨頭,還得他自己上。妻子總打趣他“跟數據過日子”,可她哪知道,行情一波動,老板拍著桌子要“立刻優化模型抓趨勢”時,他盯著屏幕熬的那些夜,每一秒都像在油鍋里煎。
今晚又是這樣。為了優化那個追蹤主力資金流向的算法,他已經連熬了三個通宵。屏幕右下角的時間跳成凌晨一點十七分,他擰開保溫杯,空的。苦笑一聲剛要起身去茶水間,桌角的手機突然震了下,屏幕亮起來——微信新好友請求。
這時候?崔浩皺了眉。他微信里多是同事家人,老同學都沒幾個,從不加生人。拿起手機,那頭像卻讓他愣了愣:一張側臉照,光線軟乎乎地裹著鼻梁,長發被風掀起幾縷,背景是虛掉的城市夜景。不算清楚,甚至有點模糊,可不知怎的,透著股安安靜靜的氣質。
驗證消息就一行字:“崔浩先生您好,冒昧添加。同頻的金融科技人,或許能聊聊AI在量化中的困境?”
“同頻的金融科技人”?崔浩的手指在屏幕上頓了頓。這話像根細針,輕輕扎在他心里那塊早就發僵的地方。在這棟樓里,他天天應付的是KPI、老板的指令、客戶的要求,誰會真坐下來,聊聊技術本身的“困境”?尤其此刻,他對著跑不通的算法獨自較勁,這“同頻”兩個字,竟讓他覺得有點暖。
猶豫幾秒,他還是點了“通過”。
幾乎是秒回,對話框里跳出一行字:“感謝通過!我是林婉如,現在在港交所做數據分析師,偶爾會關注內地的AI應用場景。看您朋友圈分享的技術文章,感覺您對深度學習在量化交易中的落地很有研究?”
港交所?崔浩挑了挑眉。那可是金融圈的圣地。他飛快掃了眼對方朋友圈,設了三天可見,就一條動態:咖啡杯擱在筆記本旁,配文“凌晨三點的機房,數據不會說謊”。照片拍得挺講究,光影搭得舒服,電腦屏幕上隱約能看見些數據圖表。
“林小姐客氣了,就做點基礎工作,談不上研究。”他回,“您在港交所做分析,接觸的該是前沿項目吧?”
“前沿談不上,麻煩倒不少。”林婉如回得快,語氣里帶點恰到好處的無奈,“就說我們最近做的項目,想用NLP技術解析港股公告,提取隱含的風險因子,可語義歧義這關總過不了。尤其碰著金融衍生品,模型誤判率高得嚇人。崔哥您做量化模型,遇見過類似的‘語義陷阱’嗎?”
NLP解析公告?語義歧義?崔浩眼睛一亮。這正是他最近的頭疼事!他們小組也在試自然語言處理分析研報,想抽關鍵信息輔助決策,可就栽在“語義陷阱”上——一個術語多幾層意思,模型就能給出完全反的信號。
他頓時來了精神,指尖在屏幕上飛快敲:“太有同感了!我們做的主力資金追蹤模型,也得結合研報和公告數據。單一個‘增持’,語境不同意思天差地別,有的是真看好,有的說不定是機構出貨前放的煙幕彈……”
“對!就是這樣!”林婉如的回復帶了驚嘆號,“我們試過用知識圖譜搭金融術語的上下文關系,可訓練數據量太大,算力燒得厲害,老板天天盯著成本念叨,說我們這是在扔錢。崔哥你們怎么處理的?有什么‘土辦法’能救急?”
一來二去,兩人從NLP的語義歧義,聊到量化模型的過擬合,又扯到AI抓不住市場非理性波動的局限。林婉如的話專業又精準,時不時拋些港交所的實操案例,既顯了她的背景,又總能剛好勾出崔浩的共鳴。她說“我們機房空調開得跟冰窖似的,敲代碼得裹外套”,也抱怨“數據清洗碰著臟數據,能讓人想把鍵盤砸了”——這些細碎的話,讓她的樣子在他心里活了起來,像個真真切切和他一樣,在深夜里跟代碼死磕的同行。
崔浩徹底沉進去了。忘了時間,忘了冷透的咖啡,甚至忘了明天一早還有會。他像在沙漠里走了太久,突然撞見個能分他半壺水的人。這種被懂、被認的感覺,在日常工作里太稀罕了。
他忍不住點開林婉如的頭像,想看得再清些。照片還是模糊,屏幕光晃了晃,才看清耳垂上那枚銀杏葉耳釘,銀亮亮的,像沾了點月光。這細節讓他覺得莫名熟悉,可想破頭也記不起在哪兒見過。搖搖頭,許是錯覺吧。
“崔哥,”對話框里的字突然軟了些,“跟你聊得真投緣。好久沒遇著能這么深聊技術的人了。平時同事間,不是聊KPI就是說業績,誰愿意沉下心說這些‘吃力不討好’的技術細節啊。”
崔浩心里一暖,回:“我也是,跟你聊完像開了竅。多謝你肯分享港交所的經驗。”
“互相學習嘛。”林婉如發來個微笑表情,“說起來,崔哥這么晚還在公司,是模型卡殼了?”
這話又準準戳中他的現狀。他嘆口氣,把正在優化的主力資金追蹤模型的難處簡單說了說——尤其識別“偽裝成散戶的機構資金”時,模型準確率總上不去。
“嗯……這問題確實棘手。”林婉如回得慢了,像是在認真琢磨,“我們之前做類似項目,試過摻點行為金融學的理論,分析資金流的‘異常模式’,或許能給你點思路?比如機構建倉,就算拆成小單,時間分布和成交量上,說不定還是能看出點規律……”
她的思路挺新,從行為金融學切入,跳出了純技術的框框。崔浩越聽越覺得在理,忍不住跟她掰扯具體怎么實現,你一言我一語,竟把困擾他好幾天的難題理出了點頭緒。
窗外的天不知何時泛了白,遠處的高樓慢慢顯露出輪廓。崔浩這才驚覺,天快亮了。揉了揉發脹的太陽穴,身子累得發沉,腦子卻興奮得很。
“崔哥,”林婉如的消息突然帶了點感性,“你有沒有覺得,數字世界里找個懂行的太難了?代碼是冷的,數據是硬的,可真能聊透這些冰冷硬邦邦背后的門道,其實挺不容易的。”
這話像顆石子投進心湖,蕩開一圈圈漣漪。崔浩盯著屏幕上的字,一時不知該回什么。他想起辦公室里那些客套的寒暄,想起回家后妻子抱怨他“眼里只有工作”的眼神,突然覺得林婉如這話,說到了他心坎里。
還沒等他組織好語言,聊天框顯示“對方正在輸入”,可過了會兒,只發來一句:“時間不早了,崔哥趕緊休息吧,別熬壞了。今天聊得很開心,下次再請教你~”
之后,那個“正在輸入”的省略號就消失了,再沒新消息來。崔浩盯著屏幕,“數字世界里找個懂行的太難了”那行字還在,像句帶著溫度的嘆息。他拿起手機,想再說點什么,又覺得多余。
緩緩放下手機,靠在椅背上長長舒了口氣。辦公室還是空蕩蕩的,只有他自己的呼吸聲。可奇怪的是,剛才那種鉆進骨頭縫的孤獨,好像淡了點。
起身走到窗邊,推開條縫。清晨的風灌進來,帶著點涼意,他打了個激靈。遠處的天徹底亮了,第一縷陽光刺破云層,照在密密麻麻的高樓上,反射出晃眼的光。
崔浩摸出煙盒,點了支煙,深深吸了一口。煙霧繚繞里,林婉如那句話總在腦子里轉:“數字世界里找個懂行的太難了。”
是啊,太難了。
他掏出手機,又點開那個對話框,看著林婉如的頭像和名字,心里生出點說不清的感覺。或許,這個突然冒出來的“同頻的金融科技人”,真能給這日子添點不一樣的東西?
他不知道的是,城市另一頭的出租屋里,窗簾拉得密不透風,一個穿皺巴巴T恤的年輕男人正關電腦,揉了揉熬紅的眼睛。屏幕光映著他下巴上沒刮的胡茬,關掉聊天窗口時,指尖在“林婉如”的頭像上頓了頓,忽然嗤笑一聲。他手機相冊里,那張側臉照下面,標著行小字:“網圖37號,已用在第12個目標。”
陽光越來越烈,照亮了崔浩桌上那杯冷透的咖啡,也照亮了屏幕上那句沒回復的、帶著溫度的話。而數字世界的另一頭,一張無形的網,已經悄悄張開。崔浩深吸口煙,把煙頭摁滅在煙灰缸里,眼里有疲憊,卻也藏著點說不清的期待。他沒察覺,自己已經朝著那陷阱,邁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