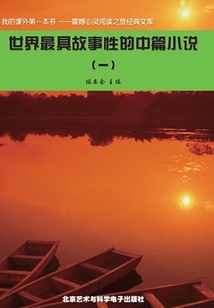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過去(1)
——郁達(dá)夫
空中起了涼風(fēng),樹葉煞煞的同雹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gè)小港市里,然而也象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吃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shí)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后三四點(diǎn)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云,把太陽遮住,接著就刮起風(fēng)來了。
這時(shí)候,我為療養(yǎng)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里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恰巧遇著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wěn),所以就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后來又因?yàn)镠港的生活費(fèi)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yīng)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gè),所以這港市的建筑,還帶著些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性,很有一點(diǎn)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座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里,建筑著許多顏色很沉郁的洋房。商務(wù)已經(jīng)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很大的榕樹排列在那里。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著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服的態(tài)度。正因?yàn)樯虅?wù)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于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沉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哪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里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后不再遷徙了,以后就在此地住下去吧”。誰知住不上幾天,卻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shí)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xì)雨蒙蒙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nèi)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去吃晚飯去。經(jīng)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shí)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棚門口,忽而從里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gè)女人來。她身上穿著灰色的雨衣,上面張著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不見。大約是在棚門內(nèi),她已經(jīng)看見了我了——因?yàn)檫@一天我并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shí)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仿佛是很熟,但記不起是哪一個(gè)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zhuǎn)頭來一看,只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jīng)是夜色朦朧的時(shí)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只大眼睛,卻閃爍得厲害,并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yán)滹L(fēng)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dòng)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rèn)不清了吧!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唉!你是老三么?你何以會(huì)到這里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zhuǎn)過身來逼進(jìn)了一步,并且伸出手來把她那只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么地方去?幾時(shí)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么地方去?”
她經(jīng)我一問,一時(shí)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顎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shí)候的她的那種怪脾氣,所以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并肩默走了幾分鐘,她才幽幽的告訴我說: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huì)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么樣?也完全變過了吧?”
“你倒沒什么,唉,老三,我嚇,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diǎn)。有的時(shí)候,在報(bào)紙上就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蹤。不過李先生,你怎么會(huì)到此地來的呢?這真太奇怪了。”
“那么你呢?你何以會(huì)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著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yīng)該也是應(yīng)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嗯,……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真好!”
“他現(xiàn)在怎么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么?”
“他已經(jīng)死了!”
“這……這么說起來,你現(xiàn)在只剩了一個(gè)人了啦?”
“可不是么!”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yuǎn)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么地方,打算明天午后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卻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里去。”
出了P街以后,街上的燈火已經(jīng)很多,并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gè)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笑的機(jī)會(huì)。到了分別的時(shí)候,她只約略點(diǎn)了一點(diǎn)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jìn)去。
經(jīng)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wěn)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里,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jīng)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shí)候她的年紀(jì)還沒有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我在寄寓著的對(duì)門的一間洋房里。這一間洋房里,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gè)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在住。當(dāng)時(shí)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gè)姐妹的生計(jì)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他們的老二認(rèn)識(shí)以后,約有兩個(gè)月的時(shí)候,我在他們的廂房里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著很闊綽的中老紳士,她們?yōu)槲医榻B,說這一位是他們的大姐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duì)面的廂房里去和他攀談去了,于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姐夫的故鄉(xiāng)卻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姐的結(jié)合,是當(dāng)他在九江當(dāng)行長的時(shí)候。
我當(dāng)時(shí)剛從鄉(xiāng)下出來,在一家報(bào)館里當(dāng)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bào)館總經(jīng)理友人陳君的住宅。當(dāng)時(shí)因?yàn)槲疑虾G樾尾皇欤荒芰硗馊プ夥孔幼。跃图淖≡陉惥募依铩j惣液退齻儗?duì)門而居,時(shí)常往來,因此我也于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rèn)識(shí)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仿佛是那一位銀行經(jīng)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fèi),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xué)費(fèi),都由這位銀行經(jīng)理負(fù)擔(dān)的。”
她們姐妹四個(gè),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yàn)樯锰赖脑颍岳隙韵拢齻兘忝萌齻€(gè),全已到了結(jié)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gè)適當(dāng)?shù)呐渑颊摺?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jīng)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商店的門口了。在這一個(gè)黃昏細(xì)雨里,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dú)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zhuǎn),右手矗立著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里的帆檣,是我到M港后去得次數(shù)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diǎn)著煙卷,朝電燈光呆看的時(shí)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她們姐妹中間,當(dāng)時(shí)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jīng)有了主顧,對(duì)她當(dāng)然更不能生出什么邪念來,老三有點(diǎn)陰郁,不象一個(gè)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jì)和我相差太遠(yuǎn)——她當(dāng)時(shí)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fā)生相互的情感,所以當(dāng)時(shí)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梁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xì)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卻相差得很遠(yuǎn)。老大和藹,老二活潑,老三陰郁,老四——說不出什么,因?yàn)楫?dāng)時(shí)我并沒有對(duì)老四注意過。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dòng),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xiàn)。凡當(dāng)時(shí)在民德里住的年紀(jì)在二十七八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總沒一個(gè)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著高底鞋的時(shí)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
說話不顧什么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xué)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shí)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白細(xì)牙齒,彎腰捧肚,笑個(gè)不了,有時(shí)候竟會(huì)把身體側(cè)倒,撲倚上你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qǐng)客,我因?yàn)槭芩倪@一種態(tài)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bào)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卻為我取了一個(gè)別號(hào),叫我作老二的雞娘。因?yàn)槔隙笠恢恍垭u,有什么可笑的事情發(fā)生的時(shí)候,總要我做她的倚柱,撲上身來笑個(gè)痛快。并且平時(shí)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眾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dòng)作和我說錯(cuò)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象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dāng)時(shí)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并且還時(shí)以為榮耀,快樂。我當(dāng)一個(gè)人在默想的時(shí)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里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后來甚至于打牌的時(shí)候,她要什么牌,我就非打什么牌給她不可。
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shí)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只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zé)之后,心里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shí)候因?yàn)橄胧芩@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只尖長的皮鞋腳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夠!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氣地,再舉起手來或腳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shí)候,才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象這樣的時(shí)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喝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zé)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飯;我正在她們家里坐著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姐姐房里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diǎn),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只。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只的時(shí)候,脖子上已經(jīng)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duì)她微笑著,問她“穿得怎么樣”的時(shí)候,她說:“右腳尖有點(diǎn)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jīng)地對(duì)她說:“踢兩腳吧!踢得寬一點(diǎn),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腳,實(shí)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jīng)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腳,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腳一樣。我也曾為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皙白,腳尖很細(xì),后跟很厚的肉腳,時(shí)常要作我的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腳,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shí)候,我一見了粉白糯潤的香稻米飯,就會(huì)聯(lián)想到她那雙腳上去。“萬一這碗里,”我想,“萬一這碗里盛著的,是她那雙嫩腳,那么我這樣的在這里咀吮,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著身體,把這一雙肉腳伸出來任我咀吮的時(shí)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唇線里,必要發(fā)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zhuǎn)起身來,也許狠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
象這樣活潑放達(dá)的老二,象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guān)系,在半年里發(fā)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guān)系,當(dāng)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dāng)時(shí),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娶親,對(duì)于將來的希望,也還很有自負(fù)心哩!
當(dāng)在陳家起坐室里說笑話的時(shí)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著襪,并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的踢打,豈不很好么?”老二聽到這些話,總老是笑著,對(duì)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huì)侍候人。我倒很愿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之后,我心里總滿感著憂郁,要一個(gè)人跑到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郁悶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姐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yán)滹L(fēng)。這時(shí)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晚秋的時(shí)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著說:“老二,我們上去吃一點(diǎn)熱的東西再回去吧!”她也笑了一笑說:“去吃點(diǎn)熱酒吧!”我在酒樓上吃了兩杯熱酒之后,把平時(shí)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tài)度除掉了,向前后左右看了一看,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gè)人也沒有,就挨近了她的身邊對(duì)她媚視著,一邊發(fā)著顫聲,一句一逗的對(duì)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著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么啦?”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gè)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gè)嘴巴。樓下的伙計(jì),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么酒菜?”我忍著眼淚,還是微微地笑著對(duì)伙計(jì)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jì)下去的時(shí)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tài)的對(duì)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干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把這事當(dāng)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