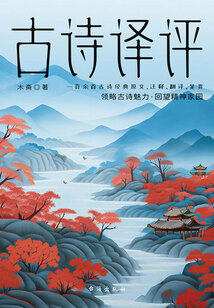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自序
如果一個人立志成為偉大的學者,那他一定先要花十年左右來打好基礎,而不是急于寫著作。這是我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四十年的經驗所得,也是我學術之路的切身體驗和肺腑之言。
20世紀80年代,我確定要寫一部有關中國文學源流史的著作。這不是一般的文學史著作,而是一個宏大的計劃。
正如我在即將出版的《中國文學源流史》的“總序”中所描述的:“此書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史,而是一部重在探索中國文學源流演變關系的專著,一部以論文作為分章形式的特殊的文學史。”而要寫出這樣的一部大源流史,勢必先要將文學史上的一系列瓶頸性難題一一解決,才有可能探索出文學源流演變的歷史真相。
目標如此遠大,理想的實現如此艱難。我充分認識到自身能力與遠大理想之間的巨大差距。“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我學術之旅的第一步是從翻譯古詩開始的。為了打基礎,當時我的計劃是,把唐宋之前的古詩重點作品都先翻譯一遍、評點一遍、鑒賞一遍,然后在這個基礎之上研究一遍、寫作一遍,來重寫中國文學源流史。為何要翻譯、評點和鑒賞后才進入研究和寫作階段?
因為我常常感受到,古代文學原作常常被似是而非地解讀,只有翻譯一遍才能將對原作每一個字的解讀落到實處;只有評點一遍才能在翻譯的基礎之上,將原作的靈魂融入內心;只有在前兩者的基礎之上鑒賞一遍,才能將原作的審美表達成自我的文字。
除了翻譯原典作品,我還寫作鑒賞文章。在20世紀90年代相當長的時間里,每天寫作兩篇鑒賞文章成了我有規律的課程。鑒賞辭典的編輯及親歷親為的寫作奠定了我分析原材料的基本功,后來的許多新發現也都得益于鑒賞寫作。這是學者深入解讀原典材料的最好練習。
此外,我還有一段時間專門從事工具書的編寫工作,這同樣是為實現遠大目標而打基礎。我在20世紀90年代主編和出版了包括《唐宋詞百科大辭典》在內的一個百科辭典系列,就正是我的打基礎工程中的部分成果。
編書階段結束后,我開始用筆名“木齋”(意思是告別編書的故我而開始寫書的真我)進入到寫書階段,先后有《古詩評譯》《唐詩評譯》《宋詩評譯》《唐宋詞評譯》等書出版問世。當下,擺在各位讀者面前的這本《古詩譯評》,就是在當年《古詩評譯》的基礎之上加以增補修訂而成的。之所以將書名從“評譯”改為“譯評”,大概是由于出版方認為此書的主要特點在翻譯,評點倒在其次。這倒也合于實際情況。
本書所選的詩歌作品,上起于詩騷,下迄于唐前。為何采用“古詩”而非“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作為書名?眾所周知,狹義的古詩指的是失去作者姓名的一批漢魏時期作品,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被稱為“漢魏古詩”;廣義的古詩可以指中國古代文學從“詩三百”到明清時代的古代詩歌,以此區別“五四”之后的新體詩。本書采用“古詩”作為書名中的時代界限,借指先唐的古代詩歌,大概由于不喜歡冗長的題目作為書名的緣故——在當時我主編的辭典中,也將唐前部分簡稱為《古詩百科大辭典》,與《唐詩百科大辭典》《唐宋詞百科大辭典》并行。
這一本《古詩譯評》主要由兩個方面構成:其一,這是一本以新體詩翻譯先唐古詩的文學作品,力圖以美的詩歌境界來打通古今兩個世界,讓當下讀者充分解讀古人詩歌作品的境界;其二,此書是在一定學術研究的基礎之上來解讀古代文學作品,這主要表現在本書的“漢魏古詩”部分。
如果讓我回憶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哪一首詩作的翻譯最為值得提及,那就是《離騷》全首的翻譯。《離騷》篇幅之長、難度之大,眾所熟知。時過境遷,我仍舊記得翻譯這一首長篇詩作時的艱難。
從《古詩評譯》到《古詩譯評》,兩個版本之間跨越了二十五年的時光(原版《古詩評譯》問世于1999年,京華出版社出版)。我的學術研究應該說早已經超越了如此漫長歲月之前的認知,對于先唐古詩的評點和翻譯,顯然會有一定的飛躍。不過,這一些新的解讀,不一定適合年輕學者的閱讀習慣和審美接受;因此,這一次再版,只做了兩個部分的增補和調整:
其一,在“詩經”部分,從拙作《先秦文學演變史》中增補了若干首詩作,其中部分詩作的注釋部分,由門下弟子劉夢瑤同學幫助完成,深銘謝意!其二,在“古詩十九首”部分,從拙作《曹植甄后傳》中,增補了若干首詩作的評點,但仍將原作的評點保留。此外,全書多數還是保留了原版原貌。本書的主要參考文獻如下:
《詩集傳》朱熹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楚辭集注》朱熹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注,中華書局1978年版
《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注中華書局1978年版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注中華書局1978年版
《先秦文學演變史》木齋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唐前文學源流史》木齋著世界漢學書局2022年版
《曹植甄后傳》木齋著世界漢學書局2022年版
《詩經譯注》周振甫譯注中華書局2010年版
如此漫長歲月之前的舊作,被編輯從歲月的風塵之中,從無數“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出版物之中甄選出來,加以出版。這既是我的榮幸,也是我的慚愧——二十五年之前的“作業”,不知道能否通過當下各位讀者的考察,并受到各位讀者朋友的喜愛?
寫完以上文字,我忽然想到此書重新出版的由來始末——大概一年之前接到了一位陌生編輯的信息,不妨節選如下:
前些日子,我有幸看到您幾本作品——《宋詩流變》《唐宋詞流變》《古代詩歌流變》《古詩評譯》——印象很深,翻遍舊書網和網上圖書館,有幸讀到全貌,很是喜歡!這幾本書深入淺出,適合詩詞愛好者及大中學生閱讀和學習。只是這幾本書已絕版多年,繼續塵封十分可惜。冒昧給您來信是想詢問,您對上述幾本書是否有再版的想法?如有此想法,可否授權我方進行出版?
我在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一些作品,在時間的車輪駛過二十余年之后,仍被有心人搜尋出來重新出版,這是對我學術研究的高度評價和最好鼓勵。
找到約稿函之后,查看一下發函信息,竟然與筆者作此序的時間為同一日,只不過早了一年而已。真是巧合!莫非冥冥之中,一切都由天定?
木齋2023年12月6日 三亞木齋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