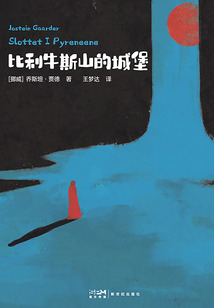
比利牛斯山的城堡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我在這兒,斯泰因。再次見到你,宛如夢一般,而且恰巧還是在那兒!你自己也慌張得不知所措,腳步趔趄了一下,差點跌倒。但那絕不是什么“意外重逢”,而是某種力量發揮了作用,知道嗎,那是力量的作用!
我們為自己爭取到了四個小時。可爭取到了又能怎樣呢?況且事后尼爾斯·佩特一直悶悶不樂,直到我們的車開到弗勒[1]的時候,他才肯開口說話。
那天,我們只顧著在山谷中向上攀爬。半小時后,我們又一次站在那片白樺樹林前……
整段旅途之中,我們兩個人一句都沒多說。我指的是,關于那件事。其他能聊的,我們都聊到了,唯獨沒提那件事。和從前一樣,我們依然無法共同坦然面對曾經發生的一切。我們簡直是從根里爛起,無可救藥。究其原因,或許并不在于以個體出現的你或我,而是以戀人身份出現的我們。回想當初,我們甚至沒有勇氣互道晚安。我記得,最后一個晚上,自己是睡在沙發上的。我還記得,你坐在另一個房間里抽煙的時候飄來的煙味。我的目光仿佛能穿透墻壁和緊閉的房門,看見你耷拉著的腦袋。而你只是微微駝著背,坐在書桌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第二天我就搬了出去,從那以后,我們再也沒見過面。時間一晃已經過去三十多年,簡直匪夷所思。
如今我倆仿佛從睡美人般的沉睡魔咒中蘇醒過來——受到同一只奇幻鬧鐘的召喚!于是我倆不約而同地奔赴同一個目的地。喂,斯泰因,那可是三十多年后,新的千年,新的世界的同一天。
你可別告訴我,那只不過是巧合。別以為那一切完全不受外力的指引!
最出乎意料的,莫過于旅館女主人突然出現在露臺上的那一幕。當年,她還只是旅館老板的年輕女兒而已。對她來說,一切也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我相信,她一定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你還記得她說了什么嗎?她說,你倆還在一起,真好。她的話語多少透著打趣的意味,但在我聽來未免有些刺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一個早晨,我們曾幫她照看過三個小女兒,此后我和你就再沒見過面。而我們幫她那個忙,是為了感謝她借給我們自行車和晶體管收音機。
他們在叫我了。現在是七月的傍晚,要知道,這兒的海濱夏日簡直和度假一樣。想來,他們應該已經把鱒魚放上了烤架,尼爾斯·佩特正好給我端了杯杜松子酒過來。他給我十分鐘的時間完成郵件。而我也的確需要這十分鐘,因為有件重要的事情,我想拜托你幫忙。
我們能否向彼此鄭重承諾,在閱讀完畢之后將互發的郵件一律刪除?我的意思是,毫不猶豫地、立刻刪得干干凈凈,當然也絕對不打印出任何紙質版。
在我看來,這種新建立的聯絡,是涌動于兩個心靈之間的思緒激流,而非必然持續下去的相互書信往來。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放心地暢所欲言。
更何況,我們都已經分別組建家庭,有了各自的孩子。我可不想把這些郵件留在電腦里。
我們不知道何時會告別。如果這一切是一場盛大的嘉年華,總有一天,我們都會摘掉面具,從角色中抽離出來,只留下散落一地的道具,最終黯然收場。
我們將會走出時間,離開我們所謂的“現實”。
時光飛逝。可一想到那些與陳年往事相關的種種會再次浮現,我的內心總是難以平靜。那感覺就好像,身后有人緊緊尾隨,或是猝不及防在我脖頸邊呵出一口暖氣。
我一直無法忘卻萊康厄爾[2]閃爍的藍色燈光。而且時至今日,在路上駕駛的時候,只要后面突然出現警車,我仍然會抓狂。幾年前的某一天,一位穿制服的警察按響了我家的門鈴,我的驚慌失措無處遁形。而他不過是想打聽附近的一個地址而已。
你肯定覺得我純屬杞人憂天,不管怎么說,就算是刑事犯罪,法律追訴時效也早已過期。
可是罪惡感不會過期……
所以請答應我,你會刪除所有郵件!
重逢那天,直到我倆找到山間已經坍塌的牧羊人小屋,坐在廢墟里時,你才告訴我拜訪此地的原因。你試著把過去三十多年里自己所做的事情闡述清楚,并且介紹了你在進行的氣候研究,之后,你才試探地提到,我們在旅館露臺重逢的前一晚,你做了一個特別的夢。你說,那是一個關于宇宙的夢。但關于夢的討論戛然而止,因為有幾頭小牛突然沖我們跑過來,攆著我們一直退回到山谷腳下。后來,你就再也沒有重提這個話題。
但對于你關于宇宙的夢境,我其實并不感到意外……當年出事后,我們曾設法睡上幾小時,可兩個人的情緒都太過激動——想不激動也難——于是我們干脆閉上眼睛躺著,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關于星辰、銀河系之類的。反正就是這類遙不可及、龐大恢宏的東西……
如今回想起來,這事未免有些蹊蹺。那時我還是個無神論者,但之后不久,我就找到了自己的信仰。
他們又在叫我了。我把最后一點想法寫完,就把郵件發出去。當初我倆經過的那個湖泊名叫埃爾德勒湖[3]。對于一個遠離塵世的高山湖泊來說,起這個名字是不是挺可笑的?我是說,相比于歷史悠久的峽灣和高山,究竟誰才算“比較古老”呢?
最近的這次,我和尼爾斯·佩特開車從埃爾德勒湖經過的時候,我的目光就沒離開過地圖。自從那件事情以后,我再也沒有到過那片區域,特別是駛過湖邊的時候,我根本就不敢抬頭看。幾分鐘后,車子轉彎繞過另一個關鍵地點——我指的是懸崖邊的那個發卡彎——那簡直是整段旅途中最讓我崩潰的地方。
我記得,車子一直駛抵下面的山谷,我才終于將目光從地圖上移開。那一路,我通過鉆研地圖知道了不少新的地名,然后逐一念給尼爾斯·佩特聽。我總得找些事做。否則我擔心自己會精神崩潰,被迫向他坦陳過去發生的一切。
接著我們駛過新開鑿的隧道。我堅持從隧道穿過去,放棄傳統的路線:先經過木板教堂,然后沿河畔的老路一直開下去。為此,我編了個特別拙劣的借口:天色晚了,要趕時間。
都是因為埃爾德勒湖。
那位越橘女倒是的確比較“老”,至少當時我們都這么覺得。我們的原話是,“那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婦人”。一位披著玫紅色披肩的上了年紀的婦人。我們必須反復確認,我和你看到的是同一幅場景。當時我倆尚且能互相交流。
事實上,那時的她和現在的我差不多大,算是同齡人,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中年婦女”……
當你走到旅館露臺上的時候,我感覺就好像遇見了另一個自己。我們已有三十多年未曾見面,但我倆之間的糾葛又遠不止這么簡單。我清清楚楚地感覺到,我居然能從外部審視自己,我是說,從你的視角,通過你的目光看見我自己。在那一瞬間,我仿佛成了越橘女。這種錯覺讓我的心頭籠罩上一層不安的陰影。
他們又在叫我過去了。這已經是第三次了。要么我現在就按下發送鍵,發出后立即刪除郵件。致以親切的問候,索爾倫。
我必須思忖再三,才不至于寫下“你的索爾倫”幾個字,畢竟我們之間從未真正分手。三十多年前的那天,我隨便拿了幾樣屬于自己的東西,然后決然地走出了房門,再也沒有回來。直到將近一年后,我才從卑爾根[4]寫信過去,拜托你把其余的物品打包寄給我。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覺得那算正式的分手,只不過我住在山的另一邊,和你相隔遙遠,那種做法純粹是出于實際考慮。后來又過了幾年,我才遇到尼爾斯·佩特。而你要等到十幾年后,才決定和貝麗特在一起。
說真的,你的確很有耐心。你從未真正放棄過我們之間的感情。有的時候,我會恍惚覺得自己過著重婚一般的生活。
對于在那條山間道路上發生的事,我永遠也忘不掉。我總有一種感覺,自己其實無時無刻不被那件事牽絆著。
可那件事還有后續,不僅神奇,而且頗為鼓舞人心。如今想來,我會覺得那是上天饋贈的一份禮物。
如果我們坦然接受了這份饋贈,那結局會是怎樣?可惜當時的我們魂飛魄散,你先是被嚇得痛哭流涕、手足無措,只能由我來照顧,后來你突然跳起來,開始一路狂奔。
過了沒幾天,我們之間就出現了裂痕。我們無法直視對方的眼睛,既不愿意,也做不到。
那可是我和你啊,斯泰因。簡直不敢相信。
索爾倫!索爾倫!你是那么美!你一身紅色長裙,背對著峽灣、花園和白色欄桿,簡直讓人目眩!
毫無疑問,我一眼就認出了你。又或者,是我的幻覺嗎?可那真的是你——仿佛從另一個時空突然冒出來一樣。
而且我現在就要告訴你的是:我根本沒把你和什么越橘女聯系到一起。
你居然真的給我寫了郵件!說真的,我盼了好幾個星期。雖然當初是我提議,我們可以給對方發電子郵件,但最后你說,你會等到合適的時機再聯系我。所以其實是你掌握了主動權。
我之所以那么不知所措,是因為我從沒想過,我們竟然能像從前那樣,在一個偏僻的地方相遇。那感覺就好像我們遵循著一個古老的約定,在某時某刻某地再度重逢。然而根本不存在什么約定,一切都是巧合罷了。
重逢的那一刻,我剛好端著放在碟子上的咖啡杯走出餐廳,手忙腳亂間,咖啡潑了出來,燙傷了我的手腕。你說得沒錯,我的腳步的確趔趄了一下,差點跌倒——我好容易穩住了咖啡杯,才沒把它摔在地上。
我和你的先生簡單打了個招呼。他突然急著要去車上拿東西,給我們留下了交談的機會。后來旅館女主人就走了出來。我從前臺走過去的時候,她肯定看到我了,而且還記得我以前的樣子——三十多年前,那時旅館的主人還是她的母親。
你和我就這么面對面站著,旅館女主人顯然把我們當成了一對中年夫婦。她大概以為,三十多年前,我們深入峽灣支流開展過一段甜蜜的戀愛之旅后,便下定決心長相廝守——我曾經也這么憧憬過。而現在,或許是因為戀舊,我們決定故地重游,回到年輕時冒險的地方。更何況,吃完早餐后,我倆本就應該走到外面的露臺上透透氣,就算我們都已經戒了煙,出門散個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再說,我們還可以遠眺歐洲山毛櫸林、峽灣以及高山。畢竟,我們當初就是這么做的。
旅館重新裝修了前臺,還新開了一家咖啡館,供過路人小憩。但是樹林、峽灣和高山依然保持著原貌。大堂里的家具和裝飾畫也沒變,就連臺球桌也還在原來的位置。但我猜,那架有年頭的鋼琴應該調過音。當初你曾用它彈奏德彪西的曲子,還演奏了肖邦的《夜曲》。而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其他住店客人聚在鋼琴周圍專注地聆聽,然后爆發出雷鳴般掌聲的場景。
三十多年的光陰轉瞬即逝,可時間仿佛凝固在了這一刻。
提到改變,我差點忘了,就只有一點:隧道是新開鑿的!我們當初是乘坐渡輪進去的,之后也是乘坐渡輪離開的。當時水路是唯一的交通方式。
你還記得嗎,得知最后一班渡輪終于啟程時,我們總算松了口氣,暫時緩解了內心的不安。那座村落變成了與世隔絕的所在,我們擁有了整個黃昏、夜晚和第二天早晨的平靜時光,直到次日中午時分,內斯號載著新的乘客返回。我們當時說,那是上天寬恕我們的寬限期。換作今天,我們恐怕必須整晚坐在露臺上,密切關注從隧道口駛出的汽車,留心它們是繼續西行,還是在冰川博物館那里轉個彎,然后直奔旅館來接走我們——我是說,抓捕我們。
對了,關于幫旅館女主人照顧女兒的事,我早忘得一干二凈了,可見我不是什么都記得。
我同意你的提議,閱讀完郵件之后立即刪除,回復郵件后也在發件箱內刪除郵件。我不喜歡在硬盤里儲存太多東西。能夠即興抒發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倒是一種不錯的放松方式。現在這個時代,互聯網也好,優盤和移動硬盤也罷,被存儲的言論已經泛濫成災了。
所以,我已經刪除了你發來的郵件,然后才踏踏實實地回復。不過我必須承認,刪除郵件的做法也有弊端,就好比我現在坐在電腦前,已經不可能再查閱你郵件中所寫的文字,這讓我有些沮喪。我只能憑借自己的記憶力進行回復,而且以后的郵件往來也都將如此。
你說,或許是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在發揮作用,從而促使我們奇跡般地在露臺上重逢。就這方面而言,我還是會和從前一樣,毫無保留地坦陳自己的想法,所以打從一開始,我就只能懇求你的諒解。總之,在我看來,這種意外重逢完全是偶然事件,并不以任何意志為主導,更談不上某種力量的“指引”。就事論事,我們的重逢的確是一個巨大的巧合,絕非輕描淡寫的小事。但你應該想想,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不會遇到類似的事件。
我這么說可能會讓你對神秘學產生興趣,但我還是決定冒險坦白自己的心路歷程:當我搭乘的巴士,駛出貝里霍爾登的山頂隧道的時候,整個峽灣籠罩在濃霧之中,下面的景色成為朦朧的一團。我能看得見山頂,然而峽灣和山谷卻仿佛猝然消失了一般。緊接著又是一條隧道,當駛出隧道口的時候,我已經在云霧之下。這時,我已經能看得見峽灣和三個山谷的谷底,山頂卻再也尋不到了。
我當時就在想:她也在這兒嗎?她會來嗎?
然后你就出現了。第二天早晨,當我端著快要漫出來的咖啡杯,小心翼翼地走出餐廳時,你就站在露臺上,穿著一襲充滿少女氣息的夏日長裙。
恍惚中我有種感覺,就好像你是我創造出來的詩篇一樣,被我寫進了那天的古老木結構旅館。你之所以會出現在外面的露臺上,完全孕育于我的記憶和思念。
如今我再次回到曾被我們戲稱為“情欲角落”的地方,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我腦海中對你的思念會如此強烈。我們的重逢固然美好,但除了“純屬巧合”使然,我實在找不出別的解釋。
我坐在早餐桌邊,一邊喝著橙汁、敲開水煮蛋的殼,一邊想著你。那天,我完全沉浸在前一晚的宏大幻夢之中,稀里糊涂地端著咖啡杯走到了露臺。然后一抬眼——天哪,你就站在那兒!
我對你的先生深感抱歉。一小時后,我倆轉過身,背對著他踏上山路時,我真心實意地對他表示同情。
如果說年輕時那場戀愛之旅留有余味,那么我們走路的方式,還有相互交談的語氣,就是一種享受和品嘗。山谷依然如舊,而我由衷地感慨:你看起來還是那么年輕。
但我不相信命運,索爾倫。我真的不信。
你再次提起了越橘女,讓我想起這輩子我所經歷的最離奇的遭遇。我并沒有忘記她,也不會否認她的存在。關于她的話題,我等一下再講。因為我想告訴你,回家途中,我還看到了其他東西。
你們踏上返程后,我繼續留宿在旅館,準備第二天一早參加新舉辦的氣候大會的開幕式。我告訴過你,在午餐時間,我還將配合活動做一個簡短的致辭,所以我一直等到星期五早上才搭乘高速渡輪,從巴勒斯特蘭駛抵弗洛姆。在弗洛姆等了幾小時后,我坐火車前往米達爾站,從那里坐上卑爾根線回到奧斯陸。
在駛往米達爾的途中,弗洛姆線的觀光列車在名為肖斯瀑布[5]的大瀑布前停了下來。游客們幾乎是蜂擁著涌向火車外面,抓住機會拍攝照片,或是目睹雪白的飛瀑。
我們站在站臺上的時候,瀑布右側的山坡上突然冒出了一位美艷的森林精靈,就好像從虛空中幻化出來的一樣。接著她又突然消失不見了,但僅僅幾秒后,她出現在三五十米之外。她就這么神出鬼沒地來來回回了好幾次。
你怎么看?或許這種北歐神話里的人物,是不需要屈服于自然規律的。
別急,我們先別妄下結論。會不會是我眼前出現了幻覺?可當時有二三百人在場,目睹了一樣的場景。難道,我們見證了所謂的“超自然現象”?所謂“超自然”,我指的是一個真正的精靈,或是魔幻人物?不,當然不。這一切顯然是為游客特地安排的,而我唯一無法弄清楚的,就是女演員表演的時薪。
還有什么是我忘了說的嗎?對了——總而言之吧,那位少女在風景中顯得很突兀,而且她簡直是以閃電般的速度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這種移動的方式也實在算不上自然。不過反正是演戲嘛!我不知道那天下午到底有幾位“森林精靈”在肖斯瀑布輪班。我猜兩三個就夠了,她們應該也拿一樣的薪水。
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是因為我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當時我們或許從未考慮過另一種可能。而且在我看來,就算現在重新納入考慮也為時不晚。有沒有可能,越橘女也是以某種方式被安排出現在那里的?或許她扮演了某種角色,說不定她和我們玩了個惡作劇,而且,因為越橘女這個角色上當受騙的絕對不止我們兩個。只要是遠離塵囂的荒郊野外,幾乎到處都有這種怪人。
等等,我是不是還遺漏了什么細節?對了!有一點,越橘女和森林精靈很像——她憑空突然冒出來,又憑空消失得無影無蹤。感覺就好像她演完了自己的戲份,就嗖的一聲鉆到地底下去了。沒準兒她就是那么做的。也說不定她喜歡開開玩笑,趁人不注意跳進一個廢棄的陷阱,或者躲到石頭堆后面去了,我哪兒知道!當時我們又沒仔細查看附近的地形,就好像被魔鬼盯上了一樣,在山谷中落荒而逃。
我們常喜歡說一個詞:眼見為實。但這并不意味著,只要是見到的任何事物,我們都要相信它具有真實性。在極少數情況下,我們必須先擦亮眼睛,才能決定相信與否。我們必須捫心自問:為何我們會任由某件事或某個人的擺布,被耍得團團轉?然而那一次,我們并未質疑。我們被嚇得驚魂未定。況且因為幾天之前發生的事情,我們都還沒緩過勁兒來。如果我們其中一個瀕臨崩潰,另一個也必然情緒失控。
你千萬別覺得我這是在指責或駁斥。再見到你,我簡直欣喜若狂,無論走到哪兒,我的臉上都不自覺地掛著微笑。在我看來,這類巧合絕不能用毫無意義或無關痛癢來定義。巧合的深遠意義在于,它們會將我們牢牢掌控,在我們身上留下深刻烙印,甚至,對未來走向還會起決定性作用。
挪威有著那么多的城市和鄉村,而我們偏偏就在那里重逢。然后又一次攀上山間的牧羊人小屋。誰能想到會發生這種事呢!
對于定期聯絡見面,比如說每年聚個一兩次的人來說,四小時的時間的確不算長。但我們已經有幾十年沒見面了,相比之下,四小時已經相當漫長了。畢竟,再次重逢和杳無音信之間,隔著巨大的鴻溝。
好吧,斯泰因。很高興收到你的回信。不過與此同時,這也讓我回憶起當初分手的原因。其中一個就是,當年的你我就和現在一樣,對我們共同經歷的事情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讀。至于另外一個原因,是你始終以居高臨下的口吻,對我的解讀進行評判。
不過話說回來,收到你的回信確實挺開心的。我也很想你。請給我多一點時間,等我心情好一些的時候給你回信。
首先,我并沒有居高臨下的意思,可我的原話究竟是怎么說的,我自己也記不清了。我都寫了些什么?我有沒有告訴過你,自從再見到你之后,我總是滿面春風地在家里走來走去?
除此之外,我也有更多事情要和你說。我所搭乘的渡輪,是根據峽灣分支的名字來命名的。渡輪第一站停靠在海拉,當時我們正是在那里丟棄了撞得稀爛的汽車。如今站在甲板上遙望渡輪碼頭,總覺得怪怪的。然后,渡輪朝著旺斯內斯的方向橫渡峽灣,接著掉轉方向,駛向巴勒斯特蘭。抵達巴勒斯特蘭后,我在歷史酒店旁邊的岬角兜來轉去,等候著從卑爾根開來的高速渡輪。渡輪晚點了應該有半個小時吧。等我上船的時候,赫然發現船舷上居然印著“索倫蒂號”!
我整個人一怔,立刻想到了你。自從兩天前,我們在舊輪船碼頭揮手道別后,我幾乎滿腦子都是你。哪怕在我回復郵件的此時此刻,我還在忍不住回想,那年夏天我們前往索倫一帶的群島探望你外婆的事。她是不是叫蘭蒂?蘭蒂·約訥沃格?
我并不只是深陷回憶而已,更準確地說,這應該是一種百感交集的狀態。過去的種種經歷仿佛潮水般突然涌上心頭,那些畫面和印象仍然栩栩如生。當時我倆都才二十出頭,站在海邊的一幕幕仿佛電影般的場景,雖然我已經不記得自己拍過,但我能肯定,那絕不是一部默片,因為我仿佛能聽見你的聲音,聽見你帶著笑意和我竊竊私語。等等,是不是還有風聲,以及海鷗的叫聲?莫非我還能嗅到你深色長發的氣味?你的發絲滲透出大海和海藻的氣息。這已經超出了平常思想活動的范疇,仿佛間歇泉一般,驟然噴涌出壓抑已久的幸福感,又或像電影閃回那樣,迅速切換到曾經屬于我們的美好時光。
首先,我在那家頗有年頭的木結構旅館里和你不期而遇,那里也是三十多年前我們攜手同游的地方;等踏上歸途的時候,我所搭乘的高速渡輪又得名于你母親故鄉的島嶼。你不是也和我說過嗎,你名字的靈感就源于索倫一帶的群島。當時,我倆討論的話題主要集中在外敘拉[6],就是你外婆住的最西端的那座小島。索爾倫和索倫蒂!這也太巧了吧!
不過,我們最好還是別被這類偶然的巧合事件所誤導,得出什么關于神秘學的結論。這艘渡輪只是和某座擁有常住居民的海濱城市恰好同名而已,沒什么可大驚小怪的。于是我的心情平復下來。但我仍然久久佇立在甲板上,嘴角不自覺地泛起微笑。
你呢,你怎么看?
我正在外面。我的意思是,我不在卑爾根,而是在索倫。我就坐在科爾格羅夫[7]的老房子里,眺望著窗外大大小小的島嶼和礁石。從我的方向看出去,唯一有點煞風景的就是一雙男人的腿。尼爾斯·佩特正站在鋁梯上,忙著粉刷我正上方的閣樓窗框。
那個星期三,你和我從牧羊人小屋回來后,我先生就催促著盡早往回趕。他說,一定要在晚間新聞播出前回到卑爾根的家里。
下午三點左右的時候,我們開車穿過博雅山谷,駛入冰川旁邊的隧道。鉆出隧道后,我們沿著狹長的約爾斯特湖[8]往前開,蒙蒙霧氣逐漸消散,太陽重新露出了臉。一直到經過弗勒之前,天氣似乎是尼爾斯·佩特唯一肯發表評論的話題。他當時咕噥了一句,“總算放晴了”。說這話的時候,我們已經沿著約爾斯特湖繞了大半圈,差不多開到謝伊。我好幾次試著打開話題,可他怎么都不肯開口。后來我才恍然大悟,他唯一的那句臺詞,恐怕不僅僅是針對天氣的評論,還暗示了他的心情。
等我們經過弗勒,向南行駛的時候,他突然扭過頭看著我,表示這一天開的路程實在有點長,不如去我外婆的房子過夜,用現在的流行說法,就是那里算是夏天的“度假屋”。本來我們是打算直接開回家的,主要也是因為他第二天還有安排。不過他臨時起意的提議也算是打破僵局的一種妥協,一方面,因為我堅持和你散步,去了那么久,他氣得暴跳如雷——可我們都三十多年沒見了,斯泰因。另一方面,他一路上賭氣地沉默不語。于是我們臨時改變了計劃。我們搭乘了往返呂謝爾道斯維卡和呂特勒達爾兩地的渡輪,橫渡峽灣,然后繼續前往索倫的群島。就在你出席氣候大會開幕式的同時,我們在海濱度過了陽光燦爛的一天。當然,我通過意念向你傳遞了消息——我指的是我們曾經共同擁有的美好回憶和片段,而且之后的幾天,我源源不斷地向你進行隔空投遞。看來還是有一定效果的嘛,你不記得自己曾經拍過的“電影場景”,但有一些的確出現在了你的腦海之中……
我們是星期四晚上回到卑爾根的家里的。星期五一大早,我就步行來到海濱碼頭,目送索倫蒂號起錨離港。按照計劃,它應該八點從卑爾根出發。因為你之前提到過,所以我知道你那天上午會從巴勒斯特蘭登上這艘渡輪。反正我起得早,干脆來個晨練。從斯康森的住宅區一路向南,穿過魚市,抵達海濱碼頭,遙祝你旅途平安的同時,也和你再次道別。再見,斯泰因。這種做法實在不夠理性,可我還是執意如此。你可別告訴我,我的問候沒有送達。一想到你要搭乘索倫蒂號,我就忍不住覺得有趣。而且我能想象得到,你一定會聯想到我,還有我們在那里度過的美好夏日。
那艘渡輪當然不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正如你所說,它是因為松恩峽灣[9]入海口的一處定居點而得名的。上次我在那兒逗留了幾乎一整天,而現在我又坐在了這里,一邊眺望大海,一邊寫郵件。幸好那兩條腿已經不見了,不然總在眼前晃來晃去,有礙觀瞻不說,還影響思考……
索倫一帶有大大小小數百座群島,而索倫蒂(Solundir)純粹是古北歐語索倫(Solund)的復數形式。“索”(Sól)的意思是“溝壑,切口”,而“倫”(-und)則有“滿是,遍布”的意思。索倫的群島上的確布滿了溝壑,所以這個地名相當精準地描述出這里的地質景觀。一如歌里唱的那樣:當她聳入云霄,溝壑縱橫,在海上經歷風雨……
你肯定還記得,那些五顏六色、夢幻般的礁石,當年我們在其中追逐嬉戲,玩捉迷藏的游戲。你也一定沒有忘記,我們花了好幾個鐘頭,在雕塑般的風景中挑揀零散的石頭。你專門挑大理石,而我則撿了好多紅色石塊。我用它們砌了花壇,所以你和我撿來的那些石頭,如今仍然在這里熠熠閃爍。
沒錯,我的外婆是叫蘭蒂。不過我真的挺失望的,你差點就忘了她的名字。當初你們倆可是很投緣的。我還記得,你說外婆是你見過的最溫暖可親的人,至于外婆,她會站在小花園的一側,喃喃自語說:“對,就是那個斯泰因!”在外婆心目中,“那個斯泰因”顯然很特別,其他小伙子可沒有他那么體貼細心。
你知道,我媽媽也是在那兒長大的,那里如今是挪威最西端的定居點。你一定還記得,我媽媽的婚前姓是約訥沃格,而父母之所以給我起名索爾倫,也絕非憑空想象或是心血來潮。我名字的靈感,多多少少受到了這種家庭背景的影響。
如今,我們一家四口回到這里。英格麗都已經上大學了。趁著學校開學前,享受難得的休閑時光。幾天之后,我們就要回歸瑣碎的日常生活。昨天很難得,雖然面向開闊的大海,卻沒什么風,所以我們難得能坐在花園里吃燒烤。
世界并不是由一系列巧合拼湊而成的馬賽克圖案,斯泰因。世間萬物之間都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
收到你的回信真好。你說過要等心情好一點才會回信,我很慶幸沒等太久。
你現在居然在那兒啊。恐怕是因為通信的原因吧,我感覺自己好像也在那兒。就算隔著相當遙遠的物理距離,兩個人也能彼此靠近,這一點好像是我先提出來的吧。你說世間萬物之間都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這點我是贊同的。
我實在太感動了,你一大清早趕到海濱碼頭,就為了讓高速渡輪為我捎去問候。我眼前完全可以浮現那個畫面:你走出斯康森的家門,順著臺階一路小跑下去,那場景讓我聯想到一部西班牙電影。倘若說之前我還有些猶豫,現在我已經能夠篤定地說:“你的問候已經順利抵達。”
可是,在我們穿過蒙達爾山谷向上攀登的途中,你曾說過,你否認一切超自然現象的存在。你強調說,你不相信心靈感應,以及任何形式的第六感或超感視覺能力。就在你說這話之前,我剛剛舉出幾個活生生的事例,證明超自然現象的存在。對你而言,或許你拒絕使用天生擁有的感知天線,寧愿蒙上眼睛自欺欺人。有些時候,恐怕連你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那些突然涌現的靈感,不過是你“接收”到的信息罷了。
但你并不是個例,斯泰因。在我們這個時代,充斥著太多心靈上的盲目以及精神上的貧瘠。
而我自己是多么天真和幼稚啊,對于我們在旅館露臺上的重逢,我實在無法歸因于單純的巧合。我相信冥冥中自有安排,至于如何安排、為什么安排,我真的不知道。但不知道并不意味著緊閉雙眼。俄狄浦斯王并不知道自己注定受到命運的擺布,當真相大白時,他在百感交集中刺瞎了自己的雙眼,自我放逐。因為就注定的命運而言,他始終都是盲目的。
郵件這么一來一回的,感覺就像在打乒乓。說不定一整個下午,我們就這么坐在電腦前收郵件、發郵件。如此一來,我也算跟著你云游了索倫。對吧?
嗯,我們想到一起去了。一來我在休假,二來度假屋里有條不成文的規矩:休假的時候,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有一點比較苛刻,就是我們必須一起吃飯。當然早餐除外,每個人起床后都可以自行解決早飯。現在我們剛吃完午飯不久,直到晚飯前,我都沒有陪伴的義務。不刮風的話,說不定今晚還能來頓烤肉大餐。
你呢?我是說,今天下午,我會跟你云游何方呢?
說來慚愧,我的日程安排,其有趣程度完全無法和你周圍的環境相提并論。我正坐在奧斯陸大學布林登校區一間乏善可陳的辦公室內,一直要待到七點左右,然后再趕到少校宮區[10]和貝麗特碰面。然后我們一起前往貝魯姆探望她父親。她父親雖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鑠,思維敏捷。不過那是后話了。在此之前,我們還有好幾個小時可以聊。
你可別忘了,我可是在布林登校區上了五年大學。那些年啊,斯泰因……對我而言已經足夠夢回故里了。
我猜,你自己應該也沒想到,你會成為奧斯陸大學的教授。你的目標不是當一名高中老師嗎?
自打你離開后,我一下子空出了好多時間。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同時,我還申請到一筆科研經費。要么我們先等等再回憶“過去”,我好奇的是,你現在變成了怎樣的人。
說起來,結果是我成了一名高中老師,這一點我應該已經告訴過你。我從未后悔過自己的選擇。每天花上幾個小時和積極熱情的年輕人相處,教授我所感興趣的學科,況且還能以此謀生,對我而言是種莫大的榮幸。另外,我并不認為教學相長這一觀念屬于陳詞濫調。對了,我教過的幾乎每一個班里,都會有一位金色鬈發少年,讓我回憶起曾經的你,還有曾經的我們。其中一個長得和你像極了,就連說話聲音都很像。
現在談談你的看法吧。我已經明確表態,我倆再次出現在旅館露臺上,絕對不是簡單的巧合……
我們的確同時出現在了旅館露臺上。但“不期而遇”或是“意外巧合”這類的字眼,從統計學上看,恰恰說明了這些都屬于小概率事件。我曾經計算過,同一枚骰子連續十二次擲出六點的概率,甚至還不到二十幾億分之一。當然這并不表示一定不會有人湊巧連續十二次擲出同樣的點數。道理很簡單,這顆星球上居住著幾十億人,每時每刻都會有人在擲骰子。不過我們虛構的這個情況,有點像挪威著名的博彩游戲“概率轟炸”——連續押中賭注的概率,實在是渺茫到微乎其微的地步。如果真的發生那種情況,當事人恐怕要笑到聲嘶力竭。因為從統計學上講,要想實現同樣點數的十二連中,一個人必須不休不眠地擲骰子,一連擲上幾千年才有可能實現。要真是一試就中,那簡直神了。這么一想是不是挺有趣的?
不管怎么說,這件事應該在你內心投下了一枚炸彈,帶給你相當大的震撼。你要問我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稱之為“撞大運”,但它絕對不是什么超自然現象。
你真能百分之百確定嗎?
對,我幾乎可以確定。另外我很肯定的一點是,任何命運、神旨或念力都無法影響事情的發展結果。就拿擲骰子來說吧,擲骰子當然能通過耍花招或者耍賴皮來作弊,也就是大家說的“出老千”,況且還有記憶出錯、報道失實的情況。即便如此,物理事件是不會受到天意或命運的操控的,更不可能受到偽科學的影響——比如所謂的“念力”。
你聽說過有誰能夠通過念力來控制輪盤,準確預測珠子會落在哪個格子里,從而大發橫財的?我們只需要提前幾秒預見未來,便能輕輕松松地成為百萬富翁。可沒人具備這種能力。任誰都不行!所以,你也不會看到哪家賭場掛出牌子,禁止具備超能力或讀心術的人員入內。這種擔心完全是多余的嘛。
無論是對于博彩游戲還是日常生活來說,我們都必須將另一種情況納入考慮。世界上最驚人的巧合都具有共同的內在傾向:很容易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以至于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中,流傳著大量聳人聽聞的奇聞異事。不知情的人往往以此作為證據,認為神秘力量在控制著人們的生活。
在我看來,理解這種機制是絕對必要的。這種“選擇性”的記憶和流傳,讓人聯想到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理論。二者的區別在于,我們所談論的并非自然選擇,而是人為選擇。遺憾的是,這種人為的選擇方式,很容易產生人為的誤解和曲解。
對于原本毫不相干的事情,我們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聯系到一起。在我看來,這是人類典型的通性。不同于其他動物,我們會設法尋找潛在的理由,比如命運、天意,或其他的操控力量,即使在完全看不出外力因素的情況下,我們仍會陷入執念。
所以我認為,發生在那個美好夏日的重逢,是一場純粹的偶發事件。誠然,這件事發生的可能性低到不能再低——這三十多年以來,我們兩個都不曾故地重游——但就算只有微乎其微的概率也不足以說明,除了驚人的巧合之外還存在其他解釋。
假如我們擴大調查范圍,將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重大巧合,包括所謂“中大獎”名單,都一一記錄成冊的話,恐怕要有數千億卷之多。退一萬步說,就算能找到足夠多的藏書館陳列,也要有足夠多的木材制成用來印刷的紙漿。在我們這顆星球上,恐怕既沒有那么大空間,也沒有那么多樹木。
那么我換一種問法好了:如果縮小關注范圍,單就某個博彩事例而言,在你讀過的長篇采訪報道中,有任何一篇的主角,是未中大獎的人嗎?
看來你沒怎么變啊,斯泰因。其實這樣也挺好的。你的固執透著孩子氣,充滿了生機勃勃的活力。
或許,你未免有些盲目了。說不定你只是思想偏執、目光短淺罷了。
你還記得馬格里特的那幅畫作嗎?畫面正中是一塊懸浮于地表之上的巨石,巨石頂上矗立著一座小小的城堡[11]。你總不至于忘了吧。
如果今天目睹到類似的現象,你一定會千方百計地予以否認。可能你會說,一切都是精心安排好的,石頭是中空的,里面充滿了氦氣。沒準兒人們使用了一套隱形的滑輪和繩索裝置,把石頭吊了起來。
我這個人的想法比較單純。如果真的看見巨石的話,我只會張開雙臂,高呼“哈利路亞”或是“阿門”。
你在第一封郵件中寫道:“我們常喜歡說一個詞:眼見為實。但這并不意味著,只要是見到的任何事物,我們都要相信它具有真實性……”
我必須承認,你的說法讓我陷入了沉思。在我看來,這句話完全和經驗主義背道而馳,全盤否定了一個人的感官印象。老實說,甚至還有點中世紀的味道……
如果體驗到感官印象不符合亞里士多德的理論,那么出錯的一定是感官;如果觀察到的天體軌道違反了地心說,那么就引入一套所謂“本輪”[12]的宇宙結構學說,解釋人們所看到的天文現象。教會和宗教裁判所的教徒們,奉行著刻板的自我審查制度,拒絕使用伽利略的天文望遠鏡。當然,這些不用我說你也懂……
你想過這樣一個問題嗎:我們曾目睹的現象,宛如懸浮在苔蘚和石楠之上的巨石。一個奇跡,一個超脫世界之外的奇跡!而且我還要多說一句:我們見證了同樣的一幕,這是我和你當時達成的一致意見。
是嗎?
對,肯定是的。不過,我們能不能把命中注定這些討論暫擱一旁,回到重逢的話題上來?
什么意思?
或許那次“巧合”僅僅源于一次再平凡不過的心靈感應。當然,你已經決意不再“相信”任何心念交流,所以對你而言大概沒有差別。
但你相信重力的存在。你能對它做出解釋嗎?
你是不是應該也給我一個機會,至少通過我的伽利略望遠鏡看上一眼?
我無法對重力做出解釋。反正重力就是客觀存在的。我當然很樂意通過你的伽利略望遠鏡一窺究竟。哪怕你有一打這樣的望遠鏡,我也會耐心逐一看過。現在,請把第一副望遠鏡遞給我吧。
對于尼爾斯·佩特和我而言,和你重逢的那次完全是一趟臨時起意的旅程,而且我很確定,是我主動提出前往菲耶蘭[13]來個一日游,參觀當地的書市和冰川博物館。當時我們已經離開東挪威,正在開車返回卑爾根的途中,我突然想,時隔那么多年,或許應該繞道去那里看看,當然了,難過是不可避免的。那個念頭就好像一直扎根在我心里,突然在那個時候冒出來了一樣。
既然你的行程是早就規劃好的,那么你顯然是信號的發送方,而我是接收的一方。多年前,我們在那家古老的木結構旅館小住過幾天后,這還是你第一次故地重游,這么想來,你給我隔空發送信號倒也不足為奇。關鍵在于,發送和接收信號的時候,人們往往是渾然不覺的。我們在思考的時候,自己其實也意識不到。就算想到特別激烈、特別悲傷,甚至極富戲劇性的情節,我們也感覺不到大腦發出嗡鳴或是嘎吱作響。究其原因,大概在于,我們的思想和身體或生理過程之間往往并沒有關系。
我和你之所以會同時出現在那個讓人既甜蜜又痛苦的地方,最簡單的解釋就是,一切源于心靈感應。而你的解釋或托詞則復雜得多,在我看來,就是一堆冰冷生硬的統計數字的堆砌。
如果純粹從發生概率的角度來看,我們在那個老舊露臺上不期而遇的可能性,大概可以打這么一個比方來形容:我們兩個面對面站在峽灣的兩端,手持步槍,各自射出一枚子彈,兩枚子彈必須恰好在峽灣的正中相撞,然后融為一體落入水中。那大概屬于超自然現象,或者至少,可以定義為“奇跡般的精準”。對于我來說,更簡單的解讀應該是:兩個曾經親密無間的靈魂,隔著遙遠的距離,對魂牽夢縈的過往進行心靈交流。你向我發送信號,告知了你的行程,而我在接收到信號后,欣然前往。
這就是心靈感應。如今已有大量文獻證明心靈感應現象的存在,我提出的這一合情合理的解釋,在你看來只是“巨大的巧合”而已。圍繞心靈感應這一課題,世界上許多大學都開展過實驗性研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卡羅來納州杜克大學的萊因博士夫婦開創了名為超心理學的學科,并成為該研究領域的先驅人物。我這里有完整的文獻目錄,你愿意的話,我可以寄一些參考資料給你。
量子力學不是也已經證實,宇宙中的一切都息息相關,哪怕最小的粒子也是如此嗎?
最近,在一些同事的幫助下,我也粗淺研究了一下量子力學。去年一整年,我們學校利用晚上的時間,定期舉辦了若干場跨學科研討會。我們將這個小俱樂部命名為“紅酒中的真理”,由此不難看出,這種社交方式非常輕松隨意。我和幾位物理老師還有自然科學老師聊過幾個晚上,感覺相比于柏拉圖時代,如今這個世界的神秘感,并未因現代物理學而有所遜色。斯泰因,如果有任何不妥的話,你盡管糾正我就是了。
兩個具有共同起源或起點的粒子(比如兩個光子)被分離開來,哪怕以極快的速度遠離彼此,仍然可以構成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即使它們沿截然相反的方向被送入太空之中,相隔若干光年之遙,它們仍會出現量子糾纏的現象。每個粒子都攜帶著蘊含另一個粒子屬性的信息,“孿生粒子”中的一個有所改變,另一個也會隨之受到影響。然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并非通信或交流,而是一種關聯性,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非局域性”。事實上,在量子層面上,世界是不存在局域限制的。這或許就像重力一樣蹊蹺,讓人費解。在愛因斯坦看來,這是對理性的挑釁,因此他否認了這一現象。但在愛因斯坦去世后,這一現象已經通過實驗得到證實。
現在我們所談的已非心靈感應,而是物理感應。在我看來,遠距離的心靈溝通對人類所產生的意義遠大于量子力學——道理很簡單,我們都具有靈魂。抬頭仰望夜空,你會看見星辰、星系,還有倏忽劃過蒼穹的彗星和小行星,說不定你會露出會心的笑容。這些天體縱然壯觀,可我們才是這個宇宙中鮮活的靈魂。彗星和小行星知道什么呢?它們能夠感知喜怒哀樂嗎?它們擁有自我意識嗎?
對于迷信的人來說,光子應該具有意識吧,它們或許能夠隔空傳遞思想,進行遠距離溝通。可我并不這么認為。我相信我們人類占據著獨特的地位,我們才是整座宇宙劇場里的靈魂!
斯泰因,就在你閱讀這些文字的時候,幾十億粒中微子正在穿過你的大腦,它們來自太陽,來自銀河系內的其他行星,來自宇宙的其他星系。它們以自己的方式,體現出宇宙的非局域性。
另一個矛盾之處在于,量子力學中的粒子不僅可以部分地以粒子的術語來描述,也可以部分地用波的術語來描述。粒子既具有波動性,也具有粒子性,也就是所謂的波粒二象性。實驗已經證明,一個電子——也就是小型的點粒子或點狀物——能夠同時通過兩條狹縫。這種現象有多不可思議呢,你不妨設想一下,就好像揮拍發出一只網球,讓它同時穿過網球場圍欄上的兩個洞。
至于粒子是如何能夠同時具有波和粒子的雙重性質的,你無須明白,也不必向我解釋。我只不過懇請你,尊重并接受宇宙本來的樣子。物理規律之所以在我們眼中顯得神秘,是因為它們本身就很神秘。對于天地間的萬物,我們可能因為無法一一做出解釋而感到遺憾,于是這種遺憾成為某些詩人的靈感來源——我們身處這個極度神秘的宇宙,卻對它知之甚少,難免讓人搖頭嘆息。不過就目前而言,這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事實。
你能夠發送一個念頭給我,而我或多或少能夠有意識地進行接收,這種情況用今天的數學或物理知識顯然解釋不通。不過,它總不至于比量子力學更難讓人信服吧?
你說呢?
英國數學家、物理學家詹姆斯·金斯曾說過這么一句話:“宇宙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宏大的思想,而非一部龐大的機器。”
我剛接到一份最新的氣候報告,情況比我們預想的更讓人憂心。有幾名記者急著要在見報前發表評論,已經給我打了無數通電話要求采訪。隨著氣候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如今一些媒體的態度也開始變得歇斯底里。所以現在,我不得不暫時中斷我們的對談,不過下午稍晚些時候我就會回來。我向你保證,絕對尊重你的信念。還有,無論你我如今支持的是哪種主義,我對你個人始終是尊重且在乎的。因此,請原諒我無法相信“超感官現象”。
好吧。不過你這家伙啊,內心其實有很多面。曾經我也算對你比較了解,所以現在我也打算就越橘女的話題寫點什么。我能感覺到你的抵觸和抗拒,就像那一晚,我的目光能穿透房門和墻壁,看見你抽煙的模樣。但現在,你一定要沉下心來聽我說。
那次出事之后,你哭了,像個孩子似的號啕大哭,我只能將你抱在懷里。三十多年后,我們再一次回到山上時,又發生了什么?
你在郵件里寫道,你不相信任何未知力量能夠操控我們的生活。可當我們再次站在那片白樺樹林前的時候,你整個人不住地顫抖。身體是不會說謊的。
靠近那里的時候,你突然緊緊抓住我的手。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常常手拉手出門散步,可現在,你突如其來的動作幾乎嚇了我一跳。好在我立刻就反應過來,應該是我們靠近當年事發地點的緣故,而你迫切地需要我的慰藉。你害怕了!反正在山里的那片白樺樹林前,你的情緒可不怎么穩定。對于不屬于這個世界的東西,你感到恐懼而焦慮。
斯泰因,你的手厚實而有力,卻在顫抖個不停!
那一瞬間氣氛的凝固,多多少少也影響了我的心情。但我要比你冷靜,內心也更有安全感。究其原因,或許是我對所謂“來世”已經產生了確定性。在我看來,超自然現象其實再自然不過。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越橘女會以實體化的形式再次出現。當然,實體化是一個容易產生誤導的說法,畢竟她不是物質。或許,她是一個“幻影”,所以攝影器材根本無法捕捉到她的影像。關于這類現象,歷史學和超心理學領域充斥大量的記載和報道:盡管兩個人在物質世界中可能相距數千千米之遙,一個人可能立即出現在另一個人的身上,并以對方的肉身形式出現。不少文學作品中也描述過,有些人并未真正死亡,而且在復活后不久,還能發出旨意和信息,傳達給接收的信眾。然而,我們如今所推崇的文化由于高度物質化,幾乎阻隔了和精神層面的接觸,更遑論來世了。但你不妨讀一讀莎士比亞,讀一讀冰島的薩迦[14],或是翻一翻《圣經》《荷馬史詩》。或者,你也可以聽一聽不同文化對薩滿和祖先的看法。
你知道嗎,我相信那一次,她之所以會現身,主要是出于安慰的目的。自從發生了你所謂“戲劇性的一幕”后,我曾無數次地反思和回想。她當時注視我們的眼神,并沒有任何責備或怨恨的意味,而是充滿了溫柔。她露出了微笑。她已經穿越到了彼岸,一個沒有恨的地方。因為彼岸并非物質世界,自然也就沒有恨。
對我們兩個來說,那一次的經歷算是相當震撼。不僅僅是你,就連我也被嚇得魂飛魄散——而且之前,我們已經擔驚受怕了一個星期。如果她再度現身的話,我一定會張開雙臂迎接這一切。
只不過這一次,她沒有出現……
死亡并不存在,斯泰因。既然沒有死亡,也就沒有死者。
注釋
[1]松恩—菲尤拉訥郡的一座市鎮。2020年,挪威將原有的20個郡(含首都奧斯陸市)縮減到11個。2022年,挪威議會決定,郡數量將在2024年恢復到15個。本書中出現次數較多的松恩—菲尤拉訥郡于2022年與霍達蘭郡合并為韋斯特蘭郡;阿克什胡斯郡、東福爾郡、布斯克呂郡合并為維肯郡。本書原作出版于2008年,故本書腳注中出現的郡名均采用2020年改革前的命名方法。——編者注。
[2]松恩—菲尤拉訥郡的一座市鎮,是該郡首府,位于松恩峽灣畔。(除特殊注明外,本書腳注均為譯者所加)
[3]松恩—菲尤拉訥郡的一座湖泊。“埃爾德勒”在挪威語中的意思是“比較古老的”。
[4]僅次于首都奧斯陸的挪威第二大城市,是霍達蘭郡首府。——編者注。
[5]位于松恩—菲尤拉訥郡的一座瀑布,海拔約669米,總落差約為225米,是挪威一處著名的旅游景點。
[6]索倫的一座島嶼,也是索倫三座主要島嶼中最西端的一座。
[7]索倫的一個村莊,位于外敘拉島的西海岸,是島上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
[8]松恩—菲尤拉訥郡的一座湖泊,面積約40平方千米。
[9]挪威最長、最知名的峽灣,全長約205千米。
[10]挪威奧斯陸市中心的一個高檔社區,因維格蘭雕塑公園聞名。
[11]比利時畫家馬格里特創作于1959年的《比利牛斯山的城堡》。
[12]指周轉圈,即一個小圓的圓心繞著一固定的大圓圈而轉。
[13]松恩—菲尤拉訥郡的一個村莊,位于菲耶蘭峽灣盡頭。菲耶蘭峽灣是松恩峽灣向北延伸的一個分支。盡管菲耶蘭只是一個有著三百余名居民的村莊,這里卻有十幾家書店,每年的五月至九月還會舉辦書市。
[14]薩迦,是誕生于北歐的一種文學體裁,源于代代相傳的口述故事。原意為“話語”,是人們用散文體將敘述祖先功績的口頭文學記錄下來。薩迦后來逐漸成為北歐地區一種獨特的文學體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