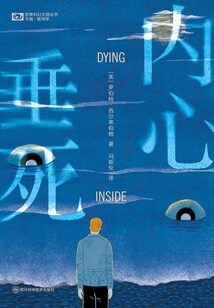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是時候再進城一趟了,去大學里搞點兒錢。我的日常開銷并不大,一個月兩百美元足以維持生計,只不過最近手頭比較緊,我也不敢再去找妹妹借錢了。很快,這些學生就得寫本學期的第一篇論文了。這門生意一直比較穩定,戴維·塞利格疲憊不堪、日漸衰敗的大腦即將再次派上用場。今天應該能接到七十五美元的活兒。十月份的清晨很美妙,陽光燦爛,空氣干爽。一股高氣壓籠罩著紐約市,吹走了濕氣和薄霧。在這樣的好天氣里,連我那逐漸衰弱的能力也活躍起來。那么我們走吧,你我兩個人,正當天空慢慢鋪展著清晨。[1]目標百老匯地鐵站,請準備好地鐵代幣。
你我兩個人,我在對誰說話?畢竟我正獨自一人前往曼哈頓下城。你我兩個人。
為什么是兩個?當然指的是我和住在我腦子里的那個生物。它蟄伏在海綿般的巢穴里,窺視著毫無戒心的凡人們。那個狡猾的東西,生病的怪物,正在比我更迅速地走向死亡。葉芝曾寫過一首詩——《自我與靈魂的對話》,而塞利格的自我分裂是葉芝這個可憐的傻瓜永遠無法理解的。既然如此,那塞利格為何不能也聊一聊自己這項獨特卻易逝的天賦,將其比作一個強行寄宿于他頭骨之中的不速之客呢?有何不可呢?那么我們走吧,你我兩個人。穿過走廊,按下按鈕,進入電梯。一股大蒜的臭味。這些鄉巴佬,烏泱泱的波多黎各人,走到哪里都能留下強烈的氣味。我的鄰居們,我愛他們。向下,向下。
現在是東部夏令時[2]上午10點43分,中央公園的溫度是57華氏度[3],濕度為28%,氣壓表讀數為30.30英寸汞柱[4],且氣壓呈下降趨勢。東北風,風速每小時11英里[5]。天氣預報顯示,今天和明天都是晴天,陽光明媚,最高溫度在60至65華氏度。今天的降水概率為零,明天為10%,空氣質量良好。戴維·塞利格時年四十一歲,呈老化趨勢。他的身高略高于中等水平,身材是一個習慣自己胡亂對付一頓的單身漢特有的瘦削。平時,他總是一副微微皺眉、略帶疑惑的神情,還經常眨眼。他身著褪色的藍色牛仔夾克、1969年的復古條紋闊腿褲和結實的厚底靴。從外形看,他很年輕,至少脖子以下如此;但事實上,他整體看上去活像一個從某間非法實驗室里跑出來的實驗品:一個日漸禿頂、滿是皺紋、一臉愁容的中年男子的腦袋被嫁接到了一個不情愿的青春期男孩的身體上。這事是如何發生在他身上的?他的臉和頭皮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衰老的?電梯從十二層(他那兩室一廳的避難所所在的樓層)慢慢下行時,纜繩發出一陣尖利刺耳的嘲笑。他懷疑這些生銹的纜繩比他的年紀還大,而他自己可是生于1935年的老古董了。這片房屋可能建于1933年或1934年,當時的紐約市市長還是菲奧雷洛·亨利·拉瓜迪亞[6],也許還要更早一點——可能建于二戰前。(你還記得1940年嗎,戴戴?那一年我們帶你參觀了世界博覽會。這是尖角塔,那個是圓球[7]。)不管怎么說,這些建筑都在變老。但話又說回來,世間萬物不都是如此嗎?
電梯吱吱呀呀地停在了七層。斑駁的電梯門尚未開啟,我卻早已感知到一束通過電梯橫梁傳來的思維顫動,源頭是一名拉美裔女性。門外站著的很有可能是一個年輕的波多黎各妻子——畢竟大樓里到處都是這種人,她們的丈夫在這個時間段都已外出工作。然而,我堅信自己讀出了她的靈場,而不是全憑瞎猜。果不其然。她身材矮小,皮膚黝黑,二十三歲左右,挺著大肚子。我可以清楚地捕捉到來自她的雙重思維輸出:她自己淺薄、感性的跳躍式思維,以及從她堅硬隆起的腹部里傳出的毛茸茸的模糊躍動。胎兒大概六個月。她面部平坦,臀部寬大,一雙小眼睛具有光澤,薄薄的嘴唇抿得很緊。她的另一個孩子大約兩歲,是個臟兮兮的女孩,此刻正緊緊地抓著母親的拇指。她們進入電梯時,這個孩子沖我咯咯直笑。女人懷疑地看了我一眼,也淺淺地微笑了一下。
她們背對我站著。一陣壓抑的沉默。日安,女士[8]。天氣不錯,對不對,女士?多么可愛的孩子啊。但我選擇沉默不語。我不認識她,而她看起來和這棟樓里的其他住戶沒什么不同,甚至連輸出的思維也十分平常,毫無個性:她正模糊地盤算著買點芭蕉和大米,還惦記著這周的彩票結果和今晚的電視節目集錦。是個無趣的娘們兒,但她是人類,我愛她。她叫什么名字?也許是阿爾塔格雷西亞·莫拉萊斯夫人,或是阿曼蒂娜·菲格羅亞夫人,抑或菲洛梅娜·梅爾卡多夫人。我喜歡她們的名字,像詩歌一樣動聽。那些和我一起長大的豐滿結實的女孩兒,她們的名字都是桑德拉·維納、貝弗利·施瓦茨、希拉·威斯巴德這類。女士,您是伊諾森西亞·費爾南德斯夫人嗎?或者克洛多米拉·埃斯皮諾薩夫人?還是博尼法西婭·科隆夫人?也許是埃斯佩蘭薩·多明格斯夫人。埃斯佩蘭薩。埃斯佩蘭薩。我愛你,埃斯佩蘭薩。埃斯佩蘭薩永駐人們心中[9]。(去年圣誕節,我去新墨西哥州的埃斯佩蘭薩參加了斗牛比賽,住在假日酒店。好吧,開玩笑的,我沒去過。)一樓到了,我敏捷地上前把電梯門打開。可愛但冷漠的孕婦走出了電梯,沒有對我微笑。
好嘞,現在出發去坐地鐵。需要穿過一個長街區才能到達地鐵站。市郊這段軌道位于地上。我沿著油漆開裂剝落的樓梯一路沖刺,到達站臺層時幾乎沒怎么氣喘,戒癮生活初見成效。最近我的飲食樸素,不抽煙,適度飲酒,不碰迷幻藥和致幻劑,還戒掉了快速丸。這個時間段的車站幾乎空無一人,但沒過多久,我的耳邊就傳來了車輪飛馳而來的尖嘯,夾雜著金屬相撞的聲音。幾乎在同一時刻,一團緊緊擠壓在一起的思維山呼海嘯般涌入我的大腦。北邊迎面駛來五六節車廂,里面擠滿了乘客。他們的靈魂形成了一個混沌的整體,不斷沖擊著我。這些思緒微微震顫著,如同一堆被海洋學家打撈上來的膠質浮游生物,粗暴地擠在漁網中,構成一團復雜的有機體,所有個體的身份特征都消失不見了。列車慢慢滑行進站,我捕捉到了許多獨立個體突然萌生的念頭:針刺般的欲念,粗啞的恨意,痛苦的懊悔,一小段下定決心的喃喃自語。它們從混亂的背景音中驀然浮現,就像陰郁的馬勒交響樂中突然出現的幾小節不和諧的古怪旋律。今天,能力似乎非常強大,我讀到了很多人的思緒。這是過去幾周以來最強烈的一次感應,當然,今天的低濕度也幫了忙,但我并沒有傻到誤以為能力已經停止消逝、開始慢慢回歸了。還記得最開始有脫發跡象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發現發際線似乎不再后退了,而且還發生了逆轉,本來瀕臨禿頂的額頭竟然開始長出幾小塊細碎的黑發,這可把我高興壞了。但從最初的歡欣鼓舞冷靜下來后,我決定接受一個更現實的觀點:這不過是激素的短暫作用罷了,不可能出現重新造林的奇跡。不要抱太大期望,衰退只是暫時中止了。不出我所料,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發際線又恢復了不斷后退的趨勢。如今在車站發生的情況大概也是如此,當你知道自己體內有東西在走向死亡,你就會學會不再相信這種轉瞬即逝的活躍了,因為它很可能只是隨機出現的回光返照。雖然今天的能力還很強大,但明天也許就只能隱隱接收到一些模糊的雜音,讓我干著急。
我在第二節車廂的角落找到一個座位,翻開書,等待列車開往下城區。我在重讀貝克特的《馬龍之死》,它很符合我目前的心境:如你所見,我正在自憐自嘆。
我的時間正在倒計時。某一天,當一切在陽光下熠熠生輝的時候,大片厚重的烏云會突然襲來,將藍天永遠奪走。我的境地確實很微妙。我將失去生命中多少美好和重要的東西啊。我害怕,害怕重蹈覆轍,害怕不能及時完滿,害怕此生最后一次攪動內心愁苦、仇恨的死水,以及最后的狂歡。萬物的形態變化多端,而永恒則立于無形之上。[10]
啊,不愧是老熟人薩繆爾,總能給予讀者一些凄涼的慰藉。
此刻地鐵行駛到了180街的某處,我抬起頭,發現斜對面的一個女孩正仔細地打量著我。她二十歲出頭,面色略顯憔悴,但仍很吸引人,長腿,胸部豐滿,有一頭紅褐色的秀發。她也有一本書,但只把它攤在腿上,并沒有翻開。我認出了封面,是一本平裝本的《尤利西斯》。她是對我有興趣嗎?我沒有讀她的思想。進入車廂后,我就自動把思維攝入調至最低,這是我小時候就學會的一個技巧。為了集中注意力,我必須把自己與車廂或其他封閉公共場所里嘈雜散亂的人群噪聲隔離開來。我決定先不去探測她的思維信號,盲猜一下她對我的想法,這也是我經常玩的一個游戲。他看上去非常聰明……他的臉比身體要老得多,一定受了不少苦吧……他的眼睛充滿柔情……看起來那么悲傷……他是個詩人,或者是學者……我猜他一定滿懷激情……把所有壓抑的愛都傾注在肉體上,傾注在做愛上……他在讀什么?貝克特?沒錯,他一定是個詩人,小說家……也許還很出名……我可不能太主動,他一定討厭咄咄逼人的女孩……一個羞怯的微笑,肯定能吸引他……接下來就水到渠成了……我會邀請他共進午餐……
為了驗證我的直覺是否準確,我接入了她的思維頻道。起初,沒有任何信號,真該死,我那越來越弱的能力又一次背叛了我!等等,信號開始出現了——先是一陣靜電噪聲,因為我同時接收到了身邊所有乘客的思想活動,但都是一些低水平的含混雜音。過了一會兒,一個甜美清晰的聲音浮現了,是來自她靈魂的絮語,憧憬著今天上午在96街的空手道課。她在與她的空手道教練戀愛,一個強壯、臉上有痘的日本人,今晚他們還要約會。她的腦海中隱隱飄來了日本酒的味道,還有他強壯的身體把她壓在身下的畫面。原來她的腦子里壓根兒就沒有任何關于我的事情啊,我不過是背景的一部分,和頭頂掛著的那幅地鐵路線圖同一個待遇。塞利格啊塞利格,你這種自作多情的性格每次都能整死你。我發現此刻她的臉上確實掛著一抹羞怯的微笑,但對象并不是我;更糟的是,當她意識到我在盯著她看的時候,笑容就立刻消失了。我只好把注意力重新轉回書上。
地鐵毫無征兆地停在了137街以北兩站之間的隧道里,過了好一陣才重新開動,搞得我汗流浹背。116街—哥倫比亞大學站終于到了,我爬上樓梯,感受著迎面灑下的陽光。猶記得,整整二十五年前的1951年9月,我第一次爬上了這些樓梯,那時的我還只是一個來自布魯克林的高中生,剃著平頭,臉上有青春痘,驚慌失措地去參加大學入學面試。在禮堂明亮的燈光下,面試官鎮定自若,舉止成熟——他是怎么做到的?當時他也才二十四五歲的樣子。不管怎么說,他們同意接收我入學了。此后,從1952年9月開始,這里就成了我的必經之地,一直到我后來離開家,搬進了校園附近的公寓。當時,地鐵站的入口是馬路上的一個舊鑄鐵亭子,正好位于兩條車道之間。哥大的學生們過街時滿腦子都是克爾凱郭爾[11]、索福克勒斯[12]和菲茨杰拉德[13],總是會心不在焉地走到汽車前,還發生了好幾起致命的車禍。如今,這個亭子已經不見了,地鐵入口改到了人行道上,更為合理。
我沿著116街繼續向前走去,右手邊是寬闊的南草坪,左手邊是通往洛氏紀念圖書館的低矮臺階。我對當年的南草坪還有印象,那時它還是校園中央的一個運動場,滿是棕色的泥土、壘道和圍欄,大一的我在那里打過壘球。我們會先去禮堂的儲物柜,換上運動鞋、馬球衫和臟兮兮的灰短褲。當我們走在西裝革履或身著預備軍官訓練團制服的同學之中時,總是有種赤身裸體的感覺。之后我們會沖下長長的臺階,狂奔到南運動場,進行一個小時的戶外運動。我很擅長壘球,雖然肌肉不發達,但我反應快、眼神好,而且我還有個優勢:知道投手的心思。他站在那里想,這家伙太瘦了,肯定打不中,我要發一個上升快球。然而,我早已做好準備,猛地把球擊打到左外野。在所有人反應過來之前,我已經繞各壘跑了一周,輕松得分。有時對方會嘗試打帶跑這類笨拙的策略,而我則輕松地走上前,撿起滾地球,順手打一個雙殺。當然,這只是區區壘球罷了,更何況我的同學們大多是些矮胖墩,他們跑步都費勁,更不用說讀心了,不過我還是很享受成為一名優秀運動員的滋味,這感覺實在不常有。我還一度沉浸在當選道奇隊游擊手的幻想中。布魯克林道奇隊,還記得嗎?在我大二的時候,為了紀念建校200周年,他們把南運動場整個鏟掉,改造成了一個草坪,還用鋪磚的過道把它隔成兩半。這事發生在1954年,天哪,都過去那么久了。呵,我變老了……我變老了……我將要卷起我的長褲的褲腳。我聽見了女水妖彼此對唱著歌,我不認為她們會為我而唱歌。[14]
我邁上臺階,在智慧女神銅像左側約十五英尺[15]的地方坐了下來。無論天氣好壞,這里都是我的“辦公室”,學生們知道要來這里找我。我坐定后,消息也會很快傳開。與我提供相同服務的還有五六個人,多數是一些貧窮的研究生,但我速度最快,也最可靠。此外,我還有一群熱情的粉絲。不過,今天業務開張得比較慢,我煩躁不安地坐了二十分鐘,時不時翻幾頁貝克特,一會兒又抬頭盯著銅像看一陣。幾年前,一個激進的炸彈襲擊者在她的側面炸了一個洞;但現在,雕像已然不見絲毫受損的痕跡。我仍記得,當時聽說這個消息后,我先是感到十分震驚,接著又對自己的震驚感到震驚——我為什么要在乎一座象征一所蠢學校的蠢雕像呢?那件事差不多發生在1969年,簡直像新石器時代一樣遙遠。
“塞利格先生?”
一個大塊頭運動員出現在我面前,投下的影子籠罩了我。他長著寬寬的肩膀和一張胖乎乎的天真面孔。他非常窘迫:自己選了比較文學這門課,需要趕快寫出一篇關于卡夫卡小說的論文,可他連書都還沒來得及讀。(到橄欖球賽季了,他是首發中衛,訓練非常忙。)我告訴他價錢,他趕忙答應了。趁他站在那兒的工夫,我暗中對他的思維進行了解讀,大致了解了他的智力水平、詞匯量和寫作風格。他其實比外表看上去更聰明,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如此。如果時間充足的話,他們自己其實也能把論文寫得足夠好。我記下了對他的一些第一印象,他興高采烈地離開了。中衛走之后,生意變得異常火爆:他推薦了一個兄弟會的成員,這個兄弟又介紹了一個朋友來,朋友又介紹了自己兄弟會的成員……介紹鏈不斷延長。到了下午,我發現已經接夠了力所能及的活兒。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所以一切都很順利。在接下來的兩到三周里,我不會再吃了上頓沒下頓,也不用再去懇求妹妹給予經濟支援。沒有來自我的消息,朱迪絲該高興吧。現在,準備回家,開始我的槍手任務。我很棒,能言善辯,態度懇切,在表達深刻思想的同時又能流露出一股不自知的幼稚淺薄,令人信服——我還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文風。文學、心理學、人類學、哲學等所有人文學科的知識,我都信手拈來。感謝上帝,我還留著大學時期寫的學期論文。就算過去二十多年,它們依舊可以派上用場。我的收費是每頁紙三塊五,如果在讀心后發現客戶很有錢,就多收點。保證論文的最低成績為B+,達不到不收費。這些年來,我還從來沒有退過錢。
注釋
[1]此句為作者化用T.S.艾略特的長詩《J.阿爾弗瑞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中的詩句。——本書注釋均為譯者注。
[2]美國東部時間以位于西五區的紐約、華盛頓等城市為代表,區分夏令時(從每年的三月份的第二個周日開始)和冬令時(從十一月份第一個周日開始)。美東夏令時=北京時間-12小時。
[3]美制溫度單位,華氏度=32+攝氏度×1.8。
[4]美制壓力單位,指0℃時已知高度的汞柱產生的壓力,1英寸汞柱≈3.3864千帕。
[5]英美制長度單位,1英里≈1.61公里。
[6]菲奧雷洛·亨利·拉瓜迪亞(Fiorello Henry La Guardia,1882—1947),美國意大利裔政治家,美國共和黨成員,第99任紐約市市長(1934—1945)。
[7]尖角塔和圓球(Trylon and Perisphere)是1939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標志性建筑。
[8]該句原文為西班牙語。
[9]此處化用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蒲柏《人論》中的詩句“希望永駐人們心中”。在西班牙語中,“埃斯佩蘭薩”既可充當人名,又有“希望”之意。
[10]節選自愛爾蘭作家薩繆爾·貝克特的作品《馬龍之死》。
[11]索倫·奧貝·克爾凱郭爾(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麥神學家、哲學家及作家。
[12]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前1496—前406),古希臘劇作家。
[13]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美國作家。
[14]摘自T.S.艾略特的長詩《J.阿爾弗瑞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此處采用查良錚譯文。
[15]英美制長度單位,1英尺=30.48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