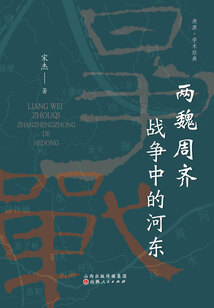
兩魏周齊戰爭中的河東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河東”地望及其歷史演變
一、戰國秦漢時期的“河東”
“河東”這一地理名詞,在隋朝以后,所指的范圍大致相當于今山西省全境,如唐之河東道、宋之河東路。而在此之前,它卻有著不同的內涵,隨著各歷史階段的發展而有所變化。“河東”一詞,最早出現于戰國時的著作,其含義有二:
(一)黃河以東某地
此概念往往是一種泛指,不論某地,只要其位置在黃河以東,就可以稱為“河東”。例如《戰國策·趙策三》載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仇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于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鮑彪對文中的“河東”“河北”注道:“此二非郡。”即表示這兩個名稱不是具體的地名,僅代表其位置在黃河以東、以北。又見《戰國策·秦策四》:“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鮑彪注:“大河之東,非地名。”
(二)今山西西南部
“河東”在當時的另一個概念,是專指戰國前期魏國都城安邑所在的統治重心區域,即今山西西南部運城地區。見《孟子·梁惠王上》載魏惠王曰:“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趙岐注:“魏國在河東,后為強國,兼得河內也。”按三家分晉時,趙據晉陽(今太原盆地),韓都平陽(今臨汾盆地),魏都安邑(今山西夏縣),以今運城盆地為主體,西及南境面臨黃河河曲,東至垣曲與韓相鄰,北接晉君保有的領地——故都新田、絳、曲沃(今山西聞喜、絳縣、翼城、曲沃等縣;后三家滅絕晉祀,其地多入于魏),西北越過汾水,沿黃河東岸而上,又有北屈、蒲陽、彘(今山西吉縣、隰縣、蒲縣、大寧及霍州等地),與趙、韓領土接壤[1]。
秦兼并六國領土后,“河東”這一地理名詞有了第三種概念,即郡名。
(三)郡名
即被正式作為國家行政區域的名稱,秦朝及兩漢設置河東郡,治安邑,轄境仍以運城盆地為主體,還包括原韓國故都平陽所在的臨汾盆地及晉西高原的南部,東括太岳山脈及王屋山,北至今靈石、石樓縣南境,西、南兩面瀕臨黃河。《漢書》卷28《地理志上》載河東郡為秦置,有24縣(《漢書》卷76《尹翁歸傳》載為28縣),包括安邑、大陽、猗氏、解、蒲反、河北、左邑、汾陰、聞喜、濩澤、端氏、臨汾、垣、皮氏、長修、平陽、襄陵、彘、楊、北屈、蒲子、絳、狐□、騏;它所包含的地域范圍比起戰國魏之河東擴大了許多。西漢時期,朝廷為了強干弱枝,增加自己直接控制的領土和人力、財賦,繼續擴展中央直轄的司隸校尉所屬之河東郡境,將其向東延伸到王屋山以北的沁河流域,把原上黨郡西南部的濩澤、端氏等地(包括今沁水縣、陽城縣的大部分地區)劃歸過來,借以鞏固和加強集權統治。[2]
二、魏晉南北朝的“河東”
(一)魏晉時期河東郡境的縮小
漢末以來,中國長期處于分裂割據的政治狀態,地方勢力強橫,而朝廷的力量有限,難以有效地控制它們,故采取了縮小地方行政區域的做法,試圖以此減弱它們對中央政權所構成的威脅。像曹魏時期,河東郡轄境開始縮小,《三國志》卷4《魏書·齊王芳紀》載正始八年“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曹魏之河東郡的轄境西、南兩面不變,北邊則退至汾河下游河道及澮水以南一線,大致上僅包括秦漢河東郡在汾河以南的轄區,即今運城地區,將汾北劃為平陽郡管轄。
西晉時期,河東郡的轄境進一步縮小,又把王屋山以東沁水流域的濩澤、端氏兩縣劃歸平陽郡。據《晉書》卷14《地理志上》所載,司州平陽郡“故屬河東,魏分立。統縣十二,戶四萬二千”;有平陽、楊、端氏、永安、蒲子、狐□、襄陵、絳邑、濩澤、臨汾、北屈、皮氏諸縣。河東郡統縣九,戶四萬二千五百,有安邑、聞喜、垣、汾陰、大陽、猗氏、解、蒲坂、河北諸縣。
(二)北朝“河東”的三種含義
經過十六國的長期戰亂,北魏統一中原后,建立新的行政區劃,地方政權的轄境再度縮小。根據《魏書》卷106《地形志》的記載,拓跋氏將原晉朝河東郡境分屬三州管轄:
泰州 轄河東郡(治蒲坂,今山西永濟西南),有蒲坂、安定、南解(今山西永濟東)、北解(今山西臨猗西南)、猗氏(今山西臨猗南)五縣。北鄉郡(治汾陰),有汾陰(今萬榮榮河鎮)、北猗氏(今臨猗)二縣。
陜州河北郡(治大陽) 有大陽(今山西平陸縣)、南安邑(今山西運城安邑鎮)、北安邑(今山西夏縣北)、河北(今山西芮城)四縣。河北郡所屬之陜州又歸京畿所在的司州管轄。
東雍州 轄邵郡(治白水,今山西垣曲),轄白水、萇平(今河南濟源西)、清廉(今山西垣曲西)、西太平(今山西絳縣)四縣。高涼郡(治高涼,今山西稷山),轄高涼、龍門(今山西河津市)二縣。正平郡(治正平郡城,今山西新絳),轄聞喜、曲沃二縣。
東西魏分裂時,河東地區被東魏高歡占據,沿襲了過去的行政區劃。這樣,河東郡的轄境進一步縮小,在北魏、東魏統治時期只有中條山以北、涑水中下游的安定、蒲坂、南解、北解、猗氏五縣之地,西魏北周統治時期又加以合并,省為蒲坂、虞鄉二縣。
由于上述原因,“河東”這一地理概念,到了北朝后期,又發生了新的變化。王仲犖先生《北周地理志》卷9《河北上》認為,當時的“河東”有兩種含義:一是泛指黃河以東;二是僅指退至蒲坂周圍數縣之河東郡。“當周齊之世,亦有舉河東者,按其實,如《周書·稽胡傳》:‘沒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此河東、河西,皆指黃河東西兩岸言之。又《周書·薛善傳》《敬珍附傳》載李弼軍至河東,珍率猗氏等六縣戶十余萬歸附。太祖執其手曰:‘國家有河東之地,卿兄弟之力。’此河東蓋指河東郡言之。由此以知,周之河東,或指河東郡,或指黃河東岸,而非唐河東道之含義。”
但需要補充的是,兩魏周齊時代所稱的“河東”,還有第三種含義。
(三)魏晉時期的河東郡轄境
如裴寬、裴果、裴文舉,《周書》卷34、卷36、卷37本傳中皆稱其為“河東聞喜人也”。另,薛端、薛澄、薛修義,《周書》卷35、卷38,《北齊書》卷20本傳中皆稱其為“河東汾陰人也”。按聞喜在北朝屬正平郡,汾陰在北魏、西魏時屬北鄉郡,北周改稱汾陰郡;皆與當時的河東郡無涉。可見上述史籍所言之“河東”者,自有另外一種含義,即指聞喜、汾陰兩縣在魏晉時所屬的河東郡(今山西運城地區)。
前文已述,戰國時期,“河東”一詞所表示的范圍較廣,除了涑水河流域,還包括汾河以北的部分區域,因此“汾北”包含在“河東”這一較大的地理概念之中。見《戰國策·魏策三》載客謂樗里子曰:
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于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為合于齊外于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翟強以為佐,何故不能有地于河東乎!
秦漢時期,河東郡境則明確地劃為汾北、汾南兩個轄區,見《漢書》卷76《尹翁歸傳》:“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而北朝時期汾北久已劃歸平陽郡,“河東”僅有汾南之地。因此當時人們改為以“汾北”與“河東”對稱。例如,西魏、北周政權曾一度占有今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河道南北的領土,齊人即習慣將其轄境分為兩個區域,稱為“汾北”“河東”。見《北齊書》卷16《段榮附子韶傳》:“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這也表示他們使用的是“河東”的第三種含義,即魏晉之河東郡的轄境,而這時的汾北已分離出去,“河東”的這一概念僅包括汾南,故以兩者并舉。
本書使用的“河東”一詞,基本上屬于上述第三種含義,其地域范圍大致相當于西晉的河東郡,即以今山西運城地區(包括鹽湖、永濟、河津三區市,及芮城、臨猗、萬榮、新絳、稷山、聞喜、夏縣、絳縣、垣曲、平陸十縣)為主體,這是西魏、北周與高氏對抗時在黃河以東長期占有的區域(汾河以北的領土時得時喪),其西境有滔滔大河自北而來,至風陵折向東行;蒲坂(今山西永濟)之東又有中條山脈向東北方向延伸。北境的汾河與澮河相交后,橫流匯入黃河;汾、澮兩河之南是峨嵋臺地,自東而西分布有絳山(紫金山)、峨嵋嶺、稷王山、介山諸峰,迤邐而至大河之濱。這一地區的平面呈三角形,在自然地理方面接近一個完整的區域單位。它古屬冀州,春秋屬晉,戰國屬魏,秦漢魏晉屬河東郡地,故史稱“河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