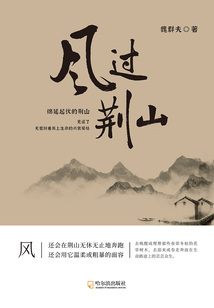
風過荊山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序 生活的歌者
群夫先生的散文集《風過荊山》即將出版,囑我作序,甚是惶恐,以我的資歷和成就,是擔不起這個重任的,但群夫先生言辭懇切,恐卻之不恭,于是,寫下些我的閱讀感想,權且為序。
跟大多數作家一樣,群夫先生飽含深情地書寫他的故鄉,在他的筆下,故鄉美麗、可愛,是一篇雋永的散文,是一幅值得永遠珍藏的畫。
作者寫荊山的春風:這時的風,還有些冷,也還有些硬,涼涼地掠過桃枝。這些凜冽的山風時而左沖右突,時而游蕩往復。桃花無處可逃,又似乎并無逃的意思,反倒像較了勁兒,風越挑釁,桃花開得越是艷麗、妖冶、放蕩。他寫夏日背柴遇到風:山風徐徐吹來,勞餓頓消,一時愜意無比,干脆解開衣襟,袒胸露膀,涼個痛快。穿行在夏日的山風里,身子格外清爽。總之,這荊山的風,總是可愛,不論哪個季節,不論哪面山坡。風吹在故鄉,雨落在故鄉,都是一首詩,都是令人心旌搖曳的風景。
故鄉值得落筆的實在是太多了,“魏家院子”是作者著力描繪的一個點。作者在這里出生,在這里度過了少年時光。一個家族在大院繁衍,幾代人好幾個家庭幾十號人同在一個大院生活,大家家境不同,命運不同,各有各的欣喜,各有各的憂愁,卻能夠和睦相處,休戚與共。在這里,我們體會到道德光芒之下的溫暖與快樂,體會到親情燭光的相互照射。雖然作者盡量不動聲色地敘述,盡量客觀地呈現,我們依然可以領略到作者富有激情的心跳,我們仿佛看到了作者滿臉的笑容。客觀的敘述中有著深藏的贊許,有著依依不舍的留戀,有著逝者不可追的惋惜。他贊許、留戀、惋惜的不單單是一座院子,更重要的是一種家族文化。
故鄉是卡夫卡的布拉格,故鄉是木心的烏鎮,故鄉是群夫的保康。他愛故鄉,他匍匐在這片土地之上,聆聽它的呼吸,傾聽它的心跳,感受它的溫度,然后用文字把它展示給世人,讓更多的人多了一份相思。
親情的描寫和展示是群夫先生散文寫作的重要內容。
在群夫的散文中,有著大量書寫親情的篇什,讀來令人動容。
《老院兒》寫了幾世同堂的一個家族共同居住在一個院子里,上孝下悌,左右和睦,親情的春風吹拂,分外溫暖。五奶奶是一個尤重親情的人,他和五爺沒有生育,過繼了一個侄子,這在那個時代倒也常見,除此之外,還養育了爺爺和第一個奶奶生育的被稱為“九姑”的一個女兒,這就不一般了。九姑不僅享受到了五奶奶的養育之恩,院里所有人都待她很好,文中寫道:“九姑每次來,我記得家家排著隊接她們母女吃飯。五奶奶和我奶奶都把她當親閨女待,她回娘屋受到的禮遇,我印象中沒有第二人。”
五奶奶待人寬厚,親情垂顧。有一年,家里進了土匪,過繼來的兒子受不了酷刑,招了藏寶的地方,土匪們將其洗劫一空,五爺一病不起,不久辭世。“五奶奶是個心胸開闊之人,她從沒向任何人提起金銀首飾被劫這事兒,好像從來就沒發生過一樣。”五奶奶深情待人,自然也贏得了別人的尊重和愛戴。五奶奶一家后來繁衍成為一大家人,“始終沒有分過家,五奶奶的起居、飲食并沒因五爺過世而有什么變化,她被兒媳、孫媳照顧得很周到,吃穿用度從不為難她。這在那個年代,已算不容易了。這樣看,五奶奶的晚年算得上享清福的人”。
整個老院,大家都在維護著親情的參天大樹,又在這棵大樹下享受著親情的蔭涼,那是怎樣的一種美好,我們只能從群夫先生文章的字里行間去領略那溫暖的氤氳,因為這樣的老院已經在時光的流逝中坍塌,正在被一天天壯大起來的利己主義消解。
群夫跟母親的感情很深,在很多文章中寫到母親都寫得感人至深。我印象最深的是《半坡蕎麥花》。
祖母愛吃苦蕎,母親就常種蕎麥。“祖母過世后,母親就不大愛種蕎麥了。老種蕎麥的那塊地,用來插紅薯。收的紅薯,用來喂豬,可能吃豬肉比吃蕎麥面合算。”“前幾年,哥哥查出高血糖,聽人說吃苦蕎好。母親進城來玩,哥哥在她面前念叨過一回,一家人聽到都沒往心里去,母親也沒搭腔兒。不想,回老家后,母親用糧食換了兩升苦蕎種子,把已租給別人種的那塊地又要了回來,全部種上了苦蕎麥”,而且年年種。患了癌癥后的“今年”,“瞞著我們兄妹,母親悄悄在那塊地里,種上了今年的苦蕎麥”。等“我們”知道,是安頓好母親的喪事后。因為“我們”兄妹商量把老家的那塊坡地再次租給別人種時,那人說:“那塊地,你媽種了苦蕎麥!”
讀到這里,我忍不住淚水潸然。
散文是語言的藝術,群夫的散文語言生動、形象,表現手法運用自然純熟,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語言風格。
《橫沖白霧》是一篇寫景的文章,好的描寫句子比比皆是,用了很多比喻句,把虛幻縹緲的霧寫得可知可感。霧如驚恐之馬,一“涌”而入,讓讀者感受霧涌進門扉的迅疾快捷。霧如潮水,如白馬群,如天上云,如縷縷輕煙,如千丈白練,一系列的比喻描寫了霧的濕度、形態、顏色,奔涌的態勢,那一場大霧如在我們眼前。
《泥下消息》的開頭:“北風呼嘯,秋聲遠去。清晨,空寂寥落的田野里,麥苗上凝結著一層薄霜,在凜冽的寒風中瑟瑟抖動。”這幾句描寫,交代了時令,告訴人們已經進入了收獲季節,引出沉潛在泥下的果實正在等待農人將它們挑揀回家。
在《蓋房記》中,寫風水先生勘測宅地時的動作是這樣寫的:
風水先生打開布袋,蹲下身子,將羅盤輕輕觸地,神情專注地盯看指針忽左忽右地搖擺,細心捕捉來自山脈、地脈的絲絲氣息。就像一位老中醫,伸出一只溫潤的手,搭在病人的脈搏之上,感知病人脈搏跳動傳遞出來的縷縷信號。
風水先生的七分專注、三分故弄玄虛寫得生動傳神。
群夫的散文較少那種大段的集中描寫,他往往是寥寥幾句,以少勝多,正是這不多的描寫,很好地渲染了環境,營造了意境。比如《半坡蕎麥花》中的句子:
蕎麥花小,色白,細細碎碎的,極為繁密,一簇挨一簇,密密匝匝。半坡地的蕎麥花,開得白茫茫一片。
“花小,色白,細細碎碎的,極為繁密,一簇挨一簇,密密匝匝。”這是寫實,跟母親平凡的一生極為相似,二者在美學趨向上的高度一致使這句話具有了一種象征意義。“半坡地的蕎麥花,開得白茫茫一片。”很好地營造了一種意境。花盛開,人不在,花開得越是茂密、越是繁盛,作者內心的孤寂越是強烈。
群夫的散文語言除了準確、生動、形象、流暢以外,還富有自己的個性,因而,他的散文有自己的味道。
比如《徐徐墜落》中:“困苦日子里留下的烙印,總是讓時光已經走了很遠,而當事人還刻骨銘心,在記憶的深處揮之不去。”只有對生活有了深刻感悟,才能寫出這樣的句子。他是想告訴讀者,困苦日子留下的烙印,永遠不會忘記,但如果這樣寫,就太一般了,跟一個初中生的作文沒有太大差異。文貴曲而忌直,把句子寫得曲折一點兒,俏皮一點兒,是每位散文作家應該努力的方向。群夫的散文還有一些機智幽默的句子,比如《風過荊山》中的“風把桃花惹急了”“風雨相互勾結,狼狽為奸”,這些有個性的句子,凸顯了作者的語言風格。
還有一些副詞、連詞,比如“越發”“況且”的恰當運用,讓文章增加了一種味道,具備了五四時期散文的某些行文特點,讓文章更加耐讀。
群夫先生是一位生活的歌者,他用手中的筆歌唱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歌唱我們每天都在經歷的世俗而又超然的生活,歌唱藏之于心底的關于未來生活的圖畫。他的這種歌詠已經刻錄在很多大刊大報,在讀者中已產生了廣泛的共鳴。我們相信他會把《風過荊山》的出版作為新的起點,不斷學習,不斷反思自省,把自己的審美趣味和文學境界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讓明天的歌詠更加美妙動聽,為湖北散文界的合唱增添動聽的音符!
我們期待著!
溫新階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湖北省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副主任、宜昌市散文學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