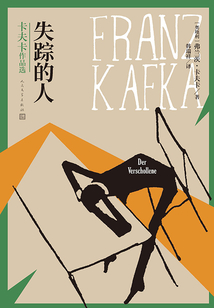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譯者前言
弗蘭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在西方現代文學中有著特殊地位。他生前在德語文壇上鮮為人知,死后卻引起世人廣泛關注,被譽為西方現代派文學主要奠基人之一。
論年齡和創作年代,卡夫卡屬于表現主義一代,但他并沒有認同于表現主義。在布拉格特殊的文學氛圍里,卡夫卡不斷吸收,不斷融合,形成了獨特的“卡夫卡風格”。他作品中別具一格甚至捉摸不透的東西就是那深深地蘊含于簡單平淡的語言之中的、多層交織的藝術結構。他的一生、他的環境和他的文學偏愛全都網織進那“永恒的謎”里。他幾乎用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眼睛去看世界,在觀察自我,在懷疑自身的價值,因此他的現實觀和藝術觀顯得更加復雜,更加深邃,甚至神秘莫測。
布拉格是卡夫卡的誕生地,他在這里幾乎度過了一生。在這個融匯著捷克、德意志、奧地利和猶太文化的布拉格,卡夫卡發現了他終身無法脫身的迷宮,同時也造就了他永遠無法擺脫的命運。
卡夫卡的一生是平淡無奇的。他出生在奧匈帝國統治的布拉格,猶太血統,父親是一個百貨批發商。卡夫卡從小受德語文化教育,1901年入布拉格大學攻讀德國文學,后迫于父親的意志轉修法學,1906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大學畢業后,先后在法律事務所和法院見習,1908年以后一直在一家半官方的工傷事故保險公司供職。1924年肺病惡化,死于維也納近郊的基爾林療養院。
卡夫卡自幼酷愛文學。早在中學時代,他就開始大量閱讀世界文學名著,尤其對歌德的作品、福樓拜的小說和易卜生的戲劇鉆研頗深。與此同時,他還涉獵斯賓諾莎和達爾文的學說。大學時期就開始創作發表一些短小作品。供職以后,文學成為他惟一的業余愛好。1908年發表了題為《觀察》的七篇速寫,此后又陸續出版了《司爐》(長篇小說《失蹤的人》第一章,1913),以及《變形記》(1915)、《在流放地》(1919)、《鄉村醫生》(1919)和《饑餓藝術家》(1924)四部中短篇小說集。此外,他還寫了三部長篇小說:《失蹤的人》(1912—1914)、《審判》(1914—1918)和《城堡》(1921—1922),但生前均未出版。對于自己的作品,卡夫卡很少表示滿意,認為大都是涂鴉之作,因此在給布羅德的遺言中,要求將其“毫無例外地付之一炬”。但是,布羅德違背了作者的遺愿,從1935年起陸續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全部著作。這些作品發表后,在世界文壇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從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現代文學史上形成了特有的一章:“卡夫卡學”。
無論對卡夫卡的接受模式多么千差萬別,無論有多少現代主義文學流派和卡夫卡攀親結緣,但卡夫卡不是一個思想家,也不是一個哲學家,更不是一個宗教寓言家,他只是一個風格獨特的奧地利作家,一個開拓創新的小說家。在卡夫卡的藝術世界里沒有了傳統的和諧,貫穿始終的美學模式是悖謬。首先,卡夫卡的作品著意描寫的不是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景,而是平淡無奇的現象:在他的筆下,神秘怪誕的世界更多是精心觀察體驗來的生活細節的組合;那樸實無華、深層隱喻的表現所產生的震撼作用則來自那近乎無詩意的,然而卻扣人心弦的冷靜。卡夫卡敘述的素材幾乎毫無例外地取自普普通通的生存經歷,但這些經歷的一點一滴卻匯聚成與常理相悖的藝術整體,既催人尋味,也令人費解。卡夫卡對他的朋友雅魯赫說過:“那平淡無奇的東西本身就是不可思議的。我不過是把它寫下來而已。”其次,卡夫卡的小說以其新穎別致的形式開拓了藝術表現的新視角,以陌生化的手段,表現了具體的生活情景。他所敘述的故事既無貫穿始終的發展主線,也無個性沖突的發展和升華,傳統的時空概念解體,描寫景物、安排故事的束縛被打破。強烈的社會情緒、深深的內心體驗和復雜的變態心理蘊含于矛盾層面的表現中。卡夫卡正是以這種離經叛道的悖謬法和多層含義的隱喻表現了那夢幻般的內心生活——無法逃脫的精神苦痛和所面臨的困惑。卡夫卡所表現的世界是荒誕的、非理性的;困惑于矛盾危機中的人物,是人的生存中普遍存在的陌生、孤獨、苦悶、分裂、異化或者絕望的象征。他的全部作品所描寫的真正對象就是人性的不協調,生活的不協調,現實的不協調。卡夫卡獨辟蹊徑的悖謬美學就是獨創性和不可模仿性的完美結合。
未竟之作《失蹤的人》寫于1912年至1914年間,它是卡夫卡的長篇小說處女作。作者生前發表了其中的第一章,也就是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司爐》(1913)。1927年,卡夫卡的摯友馬克斯,布羅德編輯出版這部小說時取名“美國”。根據卡夫卡的日記和書信記載,德國費舍爾出版社后來出版的校勘本則采用了作者在其中多次提到的“失蹤的人”這個名稱。這也是卡夫卡研究界迄今普遍所認可的。
小說《失蹤的人》敘述的是一個名叫卡爾·羅斯曼的少年的故事,他十六歲時因被一個女仆引誘而被父母趕出家門,孑然一身流落到異鄉美國。羅斯曼天真、善良、富有同情心,愿意幫助一切人。由于形形色色的利己主義者和陰險的騙子利用卡爾的輕信,他常常上當,被牽連進一些討厭的冒險勾當里。羅斯曼要尋找賴以生存之地,同時又想得到自由,他與那個社會格格不入。從主人公的坎坷行蹤里,可以讓人看到一個比較具體可感的社會現實;美國是故事情節的發生地,但卡夫卡卻從未到過那里。因此,他筆下的美國無疑是其對自身生存現實感知的鏡像。
與卡夫卡后來創作的兩部小說《審判》和《城堡》相比,《失蹤的人》在敘事風格上比較接近傳統的敘事,讀者從頭到尾可以追蹤到一個連續不斷的情節鏈條。評論界向來認為這部小說的創作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狄更斯的影響,卡夫卡甚至在他的日記里也表白了羅斯曼與狄更斯的小說《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主人公的因緣關系。盡管如此,無論從人物命運的表現,還是從敘事方式來看,卡夫卡在這里已經開始了獨辟蹊徑的嘗試,尤其是采用了主人公的心理視角和敘述者的直敘交替結合的方式,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展露出現代小說多姿多彩的敘述層面,形成分明而渾然的敘述結構,為其后來的小說創作奠定了基礎。
小說的主人公羅斯曼從一開始就是其生存環境的犧牲品,不斷地陷入了一個又一個卡夫卡式的迷宮里而無所適從。小說第一章“司爐”就已經為羅斯曼的卡夫卡式的命運做了必然的鋪墊:受到家庭女傭的引誘,他被父母親毫不留情地發配到美國,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這樣的命運。他懷著一顆天真的公平正義之心踏上了那個以自由女神著稱的國度。他在輪船上遇到了那個遭受種種不公正的司爐,為其境遇憤憤不平。在這個陌生的環境里,他義憤填膺地扮演起了一個律師角色,挺身為司爐主張公正。可面對以船長為代表的權力世界,他徒勞無望的所作所為顯得幼稚、荒唐和可笑。實際上,這個呈現在“司爐”一節的主題貫穿于小說表現的始終。羅斯曼試圖在美國找到一種公正的生存,但卻處處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令他心灰意冷,甚至絕望。剛一抵達美國,從天而降的幸運讓他莫名其妙,因為他在船上與素未謀面的富翁舅舅邂逅相遇,初來乍到就進入了美國的上層社會。然而,他生活在上層社會那錯綜復雜的關系網中卻一籌莫展,無所適從,森嚴的等級觀念讓他難以適應,他很快就莫名其妙地被舅舅趕走了。
不言而喻,舅舅在這里是一個權力的象征,絲毫也不能容忍任何違背他的意志的行為。無家可歸的羅斯曼不得不繼續去尋找自己的生存。他在一個現代化的大酒店里當了電梯工,但似乎又陷入了一個任人擺布的迷宮里,他時時處處受到監視,生存如履薄冰,無妄之災隨時都有可能降臨。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操作現代技術顯然成為一個非人的工作,它迫使人像機器一樣運轉,使人成為被操縱的工具;羅斯曼在此的命運便可想而知:他僅僅離開了工作崗位兩分鐘,便又莫名其妙地被解雇了,這無疑是卡夫卡筆下所有的人物始終要面對的慘無人道的嚴酷。這個酒店因此看上去就如同《審判》和《城堡》中的權力機構。雖然它是實實在在的存在,是羅斯曼工作的地方,不像那些權力機構那樣似真似幻,難以捉摸,而且其權力承載者都是些活生生的人,但羅斯曼生活在其中所感受的壓抑和困惑則更加顯而易見,更為直接,更為刻骨銘心。
在這個陌生的美國,無論是上層社會的達官貴人,還是現代化酒店上上下下的人,或者與羅斯曼同命相連的流浪者,他們的行為無不受到統治欲望和邪惡的驅使,真正的仁愛在這個爾虞我詐的社會不復存在。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斷裂的。最終羅斯曼甚至成了他曾經幫助過的兩個流浪者的犧牲品,被迫淪為必須俯首聽命的仆人,遭受著種種難以擺脫的折磨。世態炎涼的生存環境使得羅斯曼失去了任何行動的自由,他無力應對生存,只有聽從命運的擺布,充當任人肆意蹂躪的對象。實際上,羅斯曼的命運與卡夫卡其他人物的命運如出一轍。
小說《失蹤的人》是卡夫卡整個文學創作不可分割的部分,體現了“卡夫卡風格”形成的端倪,為全面研究和認識卡夫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見證。這部小說問世近百年來始終是評論界爭論不休的對象,但時至今日依然是卡夫卡研究者十分關注的焦點之一,同樣也是廣大讀者很喜愛的卡夫卡作品之一。值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失蹤的人》單行本之際,譯者對收錄在《卡夫卡小說全集》中的譯文進行了全面修訂。作為喜歡卡夫卡的讀者,譯者在此愿與所有對卡夫卡感興趣的同仁繼續共勉。
韓瑞祥
2019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