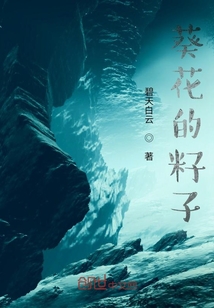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shū)友吧第1章 前言:在時(shí)間的縫隙中尋找自我
一、循環(huán)的牢籠與覺(jué)醒的可能
我第一次構(gòu)思《葵花的籽子》這個(gè)故事時(shí),窗外正下著那年冬天的第一場(chǎng)雪。電腦屏幕的光照在結(jié)了霜的玻璃上,反射出無(wú)數(shù)個(gè)嵌套的發(fā)光矩形,像極了一個(gè)個(gè)相互映照的平行時(shí)空。這種視覺(jué)錯(cuò)覺(jué)突然讓我想起初中時(shí)反復(fù)做過(guò)的那個(gè)夢(mèng)——在夢(mèng)里,我總是拼命奔跑著去趕一班永遠(yuǎn)差三十秒就能趕上的公交車(chē),每次醒來(lái)時(shí),枕頭上都浸滿了冰涼的汗水。
這種被困在時(shí)間循環(huán)中的焦慮,成為了古藤這個(gè)角色的精神底色。在傳統(tǒng)的時(shí)間旅行敘事中,主人公往往擁有改變命運(yùn)的能力,但我想探討的恰恰是它的反面:當(dāng)一個(gè)人發(fā)現(xiàn)自己不過(guò)是命運(yùn)的提線木偶時(shí),該如何保持作為人的尊嚴(yán)?葵花每次墜落前說(shuō)的“第七次了“,既是對(duì)古藤的提醒,也是對(duì)我們每個(gè)活在固定模式中的人的詰問(wèn)。
日本導(dǎo)演今敏在《紅辣椒》中展現(xiàn)的夢(mèng)境嵌套,給了我重要的結(jié)構(gòu)啟發(fā)。但與動(dòng)畫(huà)中絢麗的視覺(jué)奇觀不同,我選擇用最樸素的校園場(chǎng)景來(lái)承載這個(gè)奇幻故事——掉漆的課桌、永遠(yuǎn)擦不干凈的黑板、操場(chǎng)邊散發(fā)淡淡霉味的儲(chǔ)物柜。這些日常細(xì)節(jié)構(gòu)成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背景,反而讓時(shí)間循環(huán)的異常感顯得更加尖銳。當(dāng)古藤數(shù)著課桌上的劃痕時(shí),那些細(xì)微的計(jì)數(shù)差異就成了撼動(dòng)現(xiàn)實(shí)基座的裂縫。
二、縣域青春的生存樣本
故事發(fā)生的縣城高中,是我特意選擇的文化坐標(biāo)。在中國(guó)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這樣的縣城處于都市與鄉(xiāng)村的夾縫中,既失去了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血脈,又尚未獲得真正的現(xiàn)代性品格。古藤對(duì)自己姓氏來(lái)源的困惑,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文化懸浮狀態(tài)的隱喻。
我采訪過(guò)七個(gè)不同省份的縣城中學(xué)生,他們的生活呈現(xiàn)出驚人的相似性:早晨六點(diǎn)二十分的早讀課,永遠(yuǎn)油墨未干的試卷,父母在沿海工廠發(fā)來(lái)的節(jié)日紅包。這種高度程式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個(gè)宏觀意義上的時(shí)間循環(huán)。有個(gè)女生告訴我:“我覺(jué)得自己像被裝在同一天的罐頭里,生產(chǎn)日期和保質(zhì)期都是別人定的。”這句話直接演化成了小說(shuō)中葵花關(guān)于“罐頭人生”的獨(dú)白。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現(xiàn)代媒介對(duì)這種生活的影響。在初稿中,我原本設(shè)計(jì)了大量手機(jī)使用的場(chǎng)景,但在實(shí)地考察時(shí)發(fā)現(xiàn),這些學(xué)生最常使用的APP不是社交軟件而是各類(lèi)計(jì)時(shí)工具——“倒計(jì)時(shí)182天“、“距離高考還有4374小時(shí)“。這種將生命量化為數(shù)字的行為,與古藤用課桌劃痕記錄循環(huán)次數(shù)的舉動(dòng)形成了有趣的互文。最終我刪除了所有智能設(shè)備的描寫(xiě),讓時(shí)間以更原始的方式顯現(xiàn):日光在教室地面的移動(dòng)、葵花籽在口袋里的重量變化、懸崖上影子長(zhǎng)度的增減。
三、植物性存在的啟示
葵花這個(gè)角色從雛形到定型經(jīng)歷了七次重大修改。最初的設(shè)定里她是個(gè)來(lái)自未來(lái)的時(shí)空警察,后來(lái)變成了患有預(yù)知能力的精神病患者,最終才確定為現(xiàn)在這個(gè)帶著葵花籽的謎樣少女。這個(gè)演化過(guò)程本身就像一次次的敘事循環(huán),每次修改都在接近某個(gè)更本質(zhì)的真相。
植物意象的系統(tǒng)構(gòu)建是這部小說(shuō)的重要嘗試。葵花不僅是角色名字,更是一種生存態(tài)度的象征。在植物學(xué)家看來(lái),向日葵的向日性并非浪漫的追隨,而是生存必需的調(diào)節(jié)——其莖部含有怕光生長(zhǎng)素,陽(yáng)光照射時(shí)背光面生長(zhǎng)更快,導(dǎo)致花盤(pán)轉(zhuǎn)向。這種精妙的生存機(jī)制,暗示了角色們看似被動(dòng)的選擇背后隱藏的生命智慧。
古藤在懸崖邊抓住的那把葵花籽,是我埋設(shè)的最重要的意象密碼。在農(nóng)業(yè)文明中,種子同時(shí)是死亡的終點(diǎn)與新生的起點(diǎn),這種悖論性恰好契合時(shí)間循環(huán)的本質(zhì)。有心的讀者會(huì)發(fā)現(xiàn),每次循環(huán)后種子的數(shù)量都遵循斐波那契數(shù)列增長(zhǎng),這個(gè)數(shù)學(xué)規(guī)律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于向日葵的花序排列。這種隱秘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是我對(duì)“命運(yùn)是否存在更高秩序“這個(gè)問(wèn)題的詩(shī)意回應(yīng)。
四、致即將開(kāi)始閱讀的你
建議你在深夜臺(tái)燈下開(kāi)始這段閱讀,讓書(shū)頁(yè)翻動(dòng)的聲音成為打破寂靜的唯一聲響。當(dāng)讀到葵花第一次說(shuō)出“第七次了“時(shí),不妨合上書(shū)頁(yè),回想自己生命中那些似曾相識(shí)的瞬間——某個(gè)走廊轉(zhuǎn)角的光影,某種突然涌上心頭的無(wú)端悲傷,某次毫無(wú)理由的篤定選擇。這些記憶的碎片,或許正是你自己的“葵花籽“,藏著突破生活循環(huán)的密碼。
這部小說(shuō)沒(méi)有提供標(biāo)準(zhǔn)答案,就像古藤始終沒(méi)能確定那些葵花籽是否真的存在過(guò)。但我希望它能喚起某種“驚異感“,那種柏拉圖所說(shuō)的哲學(xué)起源的震顫。當(dāng)你最終跟隨古藤站在懸崖邊緣,面對(duì)即將第N次墜落的葵花時(shí),或許會(huì)和我一樣意識(shí)到:真正可怕的不是循環(huán)本身,而是我們漸漸不再為重復(fù)感到驚訝的麻木。
在所有的修改版本中,我始終堅(jiān)持保留開(kāi)頭那句:“只要不認(rèn)為是夢(mèng),那發(fā)生的一切就不會(huì)是夢(mèng)。”這既是少年古藤的生活哲學(xué),也是我想送給每個(gè)讀者的生存策略。在時(shí)間的洪流里,我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數(shù)著課桌上的劃痕,而真正的救贖,可能就藏在第三十八道與第四十道之間那個(gè)未被刻下的空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