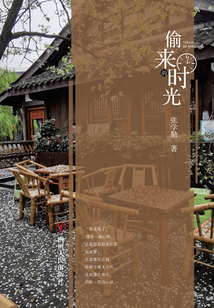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自序
人間四月芳菲盡,水街通錦橋頭,那幾棵李子樹枝頭,青青李子點綴在翠色的樹葉之中,一顆顆錯落有致,迎著早晨的太陽,朝氣四溢。
那青色的果子,時常會被往來蹦跳的黃鸝和周邊的孩童惦記,惦記著這些果子,不多時就長得更大,顏色也變成誘人的胭脂紅,念起酸酸甜甜的味道,仰頭看著,就已經心動不已。
幾棵李子樹下面,是一排排的傘棚和桌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時候,水街基本上是靜止的,除了鳥兒和貓咪會出來覓食,喝茶的傘棚和桌椅都是收起來的。李子樹開花的時節,肖家河的綠水悠悠,一樹李花一溪月,一杯蓋碗一樹影,那特有的情形,今春是不敢奢望了。其實,這個春天,比起往年,還算是長的,但疫情來襲,從冬入春,沒來得及賞,沒來得及游,真應了那句唐詩:“芳樹無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鳥空啼。”
能于青青李子樹下,在四月天,坐一坐,頓覺有點不一般,趕緊把心舒緩,打開書包,寫一寫最近的感念:
我們所經歷的這一場疫情,讓我們懂得更多的難得與珍惜,那些平常日子中的平常,那原本輕易的相聚是多么的不易。2003年非典暴發的時候,我還在北京讀書,當時從外地返京,同學專門給我留了兩袋中草藥,我在《月白風清醉流光》一書中寫道:“至今,都讓我覺得如同武俠小說中摯友千辛萬苦拿來的解藥一般。”那份患難情意,歷久彌新。
這一次疫情來襲,千里萬里,地北天南,城市之間,親朋好友在家隔離,也只能云問候,在線聯系,相互鼓勵,彼此常常叮囑的就是“要運動,要注意休息,增強免疫力”。
若是往年的春天,我一定會去山里茶園,體驗春茶采摘,尤其是川茶多在峨眉等高山地帶,那里空氣清新,不僅僅可以洗肺,遠離城市喧囂,貼近山水自然,也是靜心之行。
采春茶是一項技術活,尤其是上等的雀舌,講究“一旗一槍”,記得讀汪曾祺的書,他講喝茶:“在虎跑喝的一杯龍井。真正的獅峰龍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槍,泡在玻璃杯里,茶葉皆直立不倒,載浮載沉,茶色頗淡,但入口香濃,直透肺腑,真是好茶!”
摘那嫩芽,可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半天的工夫,也不見得能摘多少,“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煙。綠嫩難盈籠,清和易晚天。”唐詩中的摘春茶,也是這么費勁,茶雖好,卻來之不易。可是,古人依然會把這一份春意分享給鄰居老友,“且招鄰院客,試煮落花泉”。
疫情期間,自然無法如愿,幸虧有朋友尋著機會快遞春茶過來。打開春茶的簡易包裝,清新之氣撲面而來,迫不及待地煮上礦泉水,沖泡之后,用小瓷杯,一杯一杯咂摸其中的春意盎然,回味甘甜,那一份獨特的體驗,總是有一種淡然的歡欣。
好茶是要分享的,我會寄給八十多歲的老師,告訴他,北京的自來水太硬,不適合泡茶,要用礦泉水。他在電話的那頭,樂呵呵地聽著我的提醒,這情景,就像十多年前,每一次他在電話中提醒我讀書的方法一樣。我會捎給愛茶的老友,一如寒冬時分他捎過來紅茶的暖意,相互記掛的,總能體現在那一份你來我往中。
如今,交通便捷,來往半天,即可相見,可是和師友平時見面并不多,說好的去北京來四川,逛一逛、轉一轉,卻總是無法兌現。疫情來了,幾個月過去,今年又翻過了半年的篇,寄茶,算是換一種形式的相見,“地遠勞相寄,無來又隔年”。只有過了青年,人才知道時間的有限,大把大把揮霍時光的階段,早已一笑而遠,遠得沒有云煙。
前幾日,蜀地已經降低風險,出差宜賓江安,乘船到了橙花島。長江環繞,群山隱隱,島上的人家不多,竹子做的柵欄,菜蔬圍著小院,江石鋪的小路,野花爬滿了門簾,毛茸茸憨萌萌的小鴨和小鵝,蹣跚晃著覓食,甚至會擠在一起抱團取暖。
主人從樹上摘下青見,說是四月的水果不多,青見才最受待見。我也從書包中取出自己帶的春茶,讓大家泡上,朋友笑著說:“你現在也養成了帶茶的習慣,果真是入川多年,竟然是一副老茶客的習慣。不過,你來江安,不用帶茶,江安茶館多,歷史上就有名,國立劇專留下很多關于喝茶的故事呢。”
江安是一個多竹、多江、多山的小城,“北望青青四面山”,兩三年前我就已經多次來到江安,且不說是有緣,僅這一片好山水,沉淀了國立劇專的往事遺跡,就已經讓人留戀,前些年的散文集《人生忽如寄》中,專門載了江安的一篇。只是,曹禺、吳祖光、謝晉那些曾經的江安青年,風風雨雨,都成了墻上的黑白照片,后人看的時候,無限感嘆。
我與好友聊起這些感慨,朋友舉起手中的茶杯說道:“一杯春茶的滋味是今春的生機盎然,若是幾世修得住江安,這島上的時光,就不能在你的感慨中算,應該是多出來的半天一天,算你賺。”
于是,趕緊記下來,陡然間覺得,這本書中,古巷酒旗,梨花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