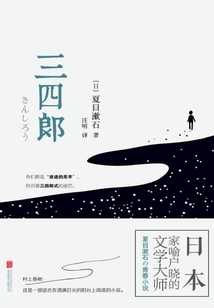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青春的滋味
村上春樹
需要說明的是:夏目漱石的作品,我是在成年后才逐漸產生真正的興趣的。大學畢業至結婚那段時間,我幾乎對他的作品一無所聞(現在想來,這樣的表述并不準確,因為我在大學畢業前便已結婚),那時,我的人生主題是貧窮。
如此忽視漱石的真正原因,我已記不真切了。主因或許是我從十幾歲就沉迷于外國小說,對日本小說抱著某種輕視的態度。次要原因,可能是少年時期讀過的漱石小說從未打動過我(也許是選讀的小說不對)。其三,在動蕩的60年代,即我的少年時期,閱讀漱石的作品并非時尚:既不會讓人敬佩也不會受到表揚。那是一個革命和反主流文化的年代,是切·格瓦拉和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時代。當然,夏目漱石如今已經是現代日本小說的代表,而在那個年代,他的作品遠未受到如此熱切的追捧——至少未受到年輕一代的追捧。
1972年,我與大學同學結了婚(她現在仍是我的妻子),她早于我畢業,以合同工的身份在一家出版社從事校對工作。我每周會去學校上幾天課以修完畢業所需的學分,同時還要打幾份工——音像店職員或者餐館服務生之類。我會利用空閑時間做做家務——洗衣、燒飯、打掃房間、采購、照看貓,十足的家庭婦男樣兒。生活不易,但我十分樂觀,唯一的瑕疵就是沒有足夠的錢買書。
正像我先前所說,那時的生活極為拮據,或者可以說我們竭盡所能把開支降到最低。我們當時正籌劃著開一家小型的爵士樂酒——在一家體面的公司找份體面工作過安穩日子,顯然非吾類所求,對此也不感興趣——正是抱著這樣的生活態度,我們努力工作,積極存錢。買不起暖器,就和貓咪抱團取暖,以度過寒夜。值得慶幸的是,那時的我們年輕、健康、朝氣蓬勃,并且有著明確的生活目標。
但買不起書確實令人難受。現實是:我們不僅買不起書,還要把自己已有的書賣掉以維持家用。那時的我如饑似渴地讀書(這種情景不會重現了),爭分奪秒地讀完一本又一本。這似乎成了支撐著我活下去的唯一辦法。所以,對于這樣的我而言,不能買新書就如同不能呼吸新鮮空氣般痛苦難耐。
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不得不重讀手頭上的書;當身邊沒有書可供重讀時,就開始考慮讀妻子書架上剩余的書。她在大學主修日本文學專業,有許多我未曾讀過的書,其中有兩套“全集”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一套是詩人宮則賢治(1896—1933)全集,另一套就是夏目漱石全集。妻子最初打算以宮則賢治作為畢業論文的主題,所以存錢買了套全集,但后來放棄宮則賢治(我不知為何)而轉向了夏目漱石。當她的一位朋友利用夏目漱石全集完成了畢業論文之后,她便以低廉的價格將這套全集收為己有。妻子還收有小說家谷崎潤一郎(1886—1965)的好幾部作品,以及11世紀的經典名著《源氏物語》和出版家巖波譯的《男孩和女孩的世界文學》。這迥異于我的閱讀品位,我們沒有交集——一點兒也沒有。
當我實在無書可讀時,才會極不情愿地于空閑時開始翻妻子的書。我必須得說,宮則賢治不是我的菜,那時我也沒理由對《源氏物語》產生興趣。夏目漱石和谷崎潤一郎倒令我耳目一新,以至于后來讀他們的小說,還常常將我帶回22歲新婚不久、掙扎在貧困線上的歲月。我們居住的室內異常寒冷,水槽里的水在冬日的早晨通常是結冰的。鬧鐘是壞的,如果想知道時間,我得伸頭張望山腳下煙草店前的那面鐘(那時我還抽煙)。我們有一面朝南的大窗,這樣至少還有充足的陽光曬進來,但是國鐵中央線正好從窗下通過,異常嘈鬧(類似電影《布魯斯兄弟》(The Blues Brother)里靠近鐵路邊的丹·阿克羅伊德(Dan Aykroyd)的公寓)。如果發生罷工,國鐵會停運24小時,雖然這將給大多數人造成極大不便,但對我們卻絕對是個安慰。除此之外,還不時有長長的貨運列車通宵經過。
以上正是我閱讀漱石作品時的“背景板”。正因為如此,閱讀漱石的作品對我來說,總是一段陽光和煦與火車轟鳴相摻雜的回憶。當然,并非每次閱讀時都會有和煦陽光的相伴,此處所述只是我最深刻的印象罷了。而貓們喜歡在我身邊睡覺。那時的我并沒有閱讀漱石的全部作品,而是挑選了其中最重要的幾部,我喜歡其中的一些甚于另一些。我最喜歡的作品,是所謂的“前三部曲”:《三四郎》《從此以后》和《門》。對《門》的深切認同,我至今仍記憶猶新。它講述了一對年輕夫妻遠不理想的生活困境。
漱石最受歡迎的小說《心》對我倒是缺乏吸引力,雖然我也喜歡他因細致入微的心理描寫而贏得廣泛贊譽的晚期作品,卻不能完全認同那些對現代知識分子苦悶的刻畫,我不時會冒出“如此描寫究竟為何”的想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或許只算是漱石的“非主流粉絲”。但無論如何,那段些許遲來的“漱石體驗”,到現在都牢牢扎根于我的內心,而且每當我有機會重讀漱石的作品,都會被其高超的寫作技巧所震撼。當我被問起自己最喜愛的日本作家是哪位時,“夏目漱石”這一名字總是第一個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在我的“漱石體驗”時期,學運已經步入衰退期,人們的情緒迅速回歸平靜。雖然校園各處依舊寫滿了政治標語的巨大布告牌,但是革命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當然,這種可能性一開始就不存在)。改革意愿也在迅速消失,各種理想主義的橫幅已基本燒毀。詹尼斯·喬普林(Janis Joplin),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已亡。在這種毫無方向,深具末世氛圍的環境里,像漱石、宮崎潤一郎這樣的作家的世界,或許再次有了新的意義,我們對此感同身受。至少從我現在功成名就的立場來看就是如此。不管如何,這是我與漱石的第一次真正邂逅。
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三四郎》正是那種適合在灑滿日光的陽臺上閱讀的小說。小說主人公也許處于迷茫中,但還算是積極樂觀的態度。他的面部略微向上傾斜,無盡的蒼穹盡收眼底。以上就是這本書給人的大體印象。事實上,小說里的各式人物也總是不停地望向天空,這些描寫在《三四郎》中占有重要位置。
此種類型的作品在漱石的小說中實屬罕見。他創作的大多數主人公都面臨著現實生活的各種矛盾。他們對“如何生活是好”煩惱不堪,并對在生活中必須做出各種抉擇深感壓力。在充滿矛盾的前現代和現代,如何在愛和道德、西方和日本之間找到自己人生的平衡點,是小說主人公最大的關懷。他們似乎沒有多余的時間用來“仰望天空”。實際上,漱石其他小說里的人物,似乎總是在“低頭走路”。尤其是晚期小說里的主人公,似乎如同作者本人一樣,一直在經受著劇烈的胃痛(但令人奇怪的是,漱石的描寫從未因此喪失自然的幽默感)。
而《三四郎》里的主人公卻不同。他在紛雜異位的環境中同樣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他從未把這異常的環境視為自身內在的問題,他以年輕人特有的坦然,相對自然地接受了這種環境,并把它當作純粹的外部存在。“哦,事情就是這樣啊!”他似乎如此說道。我想《三四郎》之所以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品,其原因就是作者以極為流暢的風格,刻畫出主人公心理的自然變化。三四郎認為自己被生活輕輕拂過,就如同白云從空中飄過一般。在我們清醒之前,就幾乎已經被他的“自由仰望天空”所吸引,甚至忘了以批判審視的眼光來觀察他。
當然,這種無憂無慮的超然生活的態度不能長久。一個人可以退后一步,宣布“我沒有做出任何決定”,但這只能存在于一段短暫的——同時可能也是快樂的——人生階段。最終,不管你是否愿意,都必須負起責任的重擔,一旦決定承擔責任,那么“仰望天空”也將隨即終結。這一切就發生在代助身上,他是漱石下部小說《從此以后》的主人公。這將以更深刻的程度發生在宗助身上,即漱石的下下部小說《門》的主人公。這三部小說一起構成了漱石的“三部曲”——作者在短短三年的時間內完成的報紙連載小說,并以絕對高超的手筆,描寫了明治時代青年知識分子的青春以及青春末期。我們或許可以將這三部小說稱為“成長三部曲”。漱石作為一名作家,在這三年中的成長速度可謂驚人,如同一部快進的電影。
現在,讓我再回到《三四郎》這部小說。小說主人公三四郎尚處于黎明前的人生階段,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最終將承受的人生重擔。正是這種意識的缺乏,成就了三四郎:一個還有閑暇張望天空和凝視云朵的天真青年。我們沒有看到苦惱,看到的只是苦惱的萌芽,以及痛苦的萌芽。漱石在這部小說中顯得從容恬淡。他沒有在背后推動三四郎,沒有強迫他前進,或者在時機成熟之前就強迫主人公面對苦惱與挫折。漱石對他無褒無貶,他只是讓三四郎成為三四郎,并以無拘無束、自得其樂的方式描繪出三四郎,這正是漱石的偉大之處。
我第一次讀《三四郎》時才22歲,對即將迎面而來的重任鮮有認識。那時我剛結婚,還只是一個學生。不管現實生活如何貧困,呼嘯而過的列車如何嘈雜,我依舊在陽光下慵懶地坐著,身邊睡著兩只柔軟而溫暖的貓。
我在神戶附近的恬靜郊區長大,18歲時去東京的早稻田大學讀書。最開始我去東京的欲望不是很強,而是更傾向于進入本地大學過輕松的生活。但在抉擇的最后一刻,我開始覺得自己傾向于離開家鄉,歷練自己——進行人生中第一次獨自生活的嘗試。我打點行李,與女友告別,將大號的行李提前寄到學校宿舍。當我在大阪登上新建的新干線“子彈頭”列車時,隨身只帶了一個手提包。在我口袋里的是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音樂學校》(The Music School)平裝本。作為那段特殊時光的一部分,那本書的封面至今還殘留在我的腦海中。
我和小說開頭的三四郎做著同樣的事情:從外省去東京上大學。當然細節差異較大。《三四郎》寫于1908年,而我去東京是1968年,正好是60年之后。從神戶到東京,坐蒸汽火車需要15~20個小時。對我來說,坐上電力新干線只需4個小時。從僻遠的九州到東京,三四郎花了兩天時間。可以說,我們成長的環境極為不同,這種不同也表現在大學生的社會地位上。在三四郎的年代,任何進入大學的人都會受到尊重,但在我的年代,上大學已是稀松平常之事。學校教育系統也有了很大變化。三四郎剛從“高等學校”畢業,相當于現在的文理學院。他升入大學,開始更有針對性地學習時已經22歲(按西方計齡法),而我只有18歲。但是,對于前往一個陌生大城市,開始新生活所產生的興奮感,我們之間并無太大的區別。
不必說,三四郎在前往東京旅途中的艷遇,并沒有發生在乘坐新干線的我的身上。他畢竟還在旅館過了一夜,而我只是在子彈頭火車上坐了4個小時。坦白說,在我身上確實發生了有點類似三四郎的經歷。為了節省車票錢,我乘坐的是比較慢的子彈頭回音號(Kodama),它要比普通的光速號(Hikari)多停幾站。記得是在靜岡那一站,一個年輕女子上車,坐在了我的身邊。列車其實很空,她完全可以獨占一個兩人座的位子,但她卻選擇坐在我身邊。她是個年輕的漂亮姑娘——不會超過25歲,不是標致美人,但足以吸引人。不必驚訝,她坐在我身邊令我相當緊張。
她坐定后,帶著友善的微笑開始和我交談。你從哪里來?去哪里?她的言談直接而開放,而我盡可能誠實地回答她的問題。我告訴她我從神戶來,去東京上大學,主修文學,喜歡看書,會住在目白站附近的學生宿舍,我還是獨生子,如此種種。我并不真正記得細節。其實那時我懵懵懂懂,我的回答像是自個兒蹦出來的。
總之,在去東京的火車上,這個略長于我的女子一直坐在我的身邊。我們一路交談,記得她還給我買了飲料。火車到達東京時,我們走下站臺。“祝你好運,好好學習。”她一面說一面對我揮手,然后就離開了。這就是我的“艷遇”故事。我至今不清楚,她為什么會在幾近空車的列車里選擇坐在我身邊。或許她只希望有個聊天兒的對象,像我這樣的小孩子不會產生威脅(我比較肯定就是這個原因);又或者她有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弟弟。不管她的理由是什么,留在她身后的我站在東京站的站臺上有著一種奇怪的、近乎飄飄然的感覺。這就是我東京新生活的開始,一開始便微染著某種女性的曖昧氣息,一個年輕女子的美妙香氣,像是會有故事發生的一個信號。毫無疑問,從那一刻開始,這些氣味將有助于決定我的人生歷程。
我到目前為止已將《三四郎》讀過多遍了,每次閱讀都會令我想起那段生活。這本書常常喚起我當時前往東京時體會到的奇妙感受,并意識到自己與家鄉的街道、典型鄉下少年的生活、父母給予的安穩、留在家鄉的女友,以及那時形成的人生觀等事物,正在緩慢而確定地分離。而我收獲了什么——或者將要收獲什么——來取代它們的位置?關于這些,我并不確定。事實上,我甚至并不確定是否存在現實的事物能取代它們。我感受著自由的興奮和寂寞的恐懼,像一個高空秋千的雜技演員,在并不確定是否可以把握住下一輪的繩索前,就已經飛身了。
對我來說,《三四郎》如此出彩,或許正是因為主人公從未公開展示他內心中興奮和恐懼的沖突。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沖突沒有展示在小說表面——并未以現代小說“心理并發癥”的形式呈現。在他的故事里,三四郎始終是個旁觀者。他接受一切并體會一切。確實,他時常會對好或壞、喜歡或不喜歡做出判斷,而且他有時還以相當的口才發表自己對某些事物的看法,但始終是以“初步裁決”的形式出現。他判斷事物的方式,往往不是通過收集材料再做決定。實際上,他的步伐遠非輕盈,甚至可以說是笨拙的,但也不是步履蹣跚。漱石異常成功地塑造了這位天真的、又不失知識分子氣質的知識分子,同時也是充滿了自由開放觀點的外省青年。
這種自由和開放性配合,背景里暗伏的某種危險,不自覺地成就了三四郎作為個體的少年心性,或許同時也是日本作為國家所具有的少年心性——在那段著名的“明治中后期”的世紀之交期間。在年輕三四郎的步伐和凝視里,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正在快速成長的年輕國家與之享有的某些共性:在擺脫舊式封建體制后加速的脈動,大口呼吸著剛剛引進的西方文化的空氣,同時對未來的方向和目標提出質問。但無論是在它的步伐還是眼神里,我們都找不到強烈的一致性。事態在這一刻還保持著平衡,但沒人可以預測其將來的發展。
然而小說里的某個人物似乎意識到了即將到來的危險。廣田教授,三四郎在前往東京火車上偶遇、并在后來成為其導師的古怪家伙,對日本未來的命運做了一番苛刻的評論。在日俄戰爭獲勝后(1905年,小說寫成的3年前),日本或許將如一流強國那樣闊步前進,但他表示,日本從國家層面來說依舊是“腳輕根底淺”。日本對外有何可以自夸的呢?富士山嗎?那就是一個自然景觀而已,并為日本人創造的景觀。教授認為日本也許給人以現代化國家的印象,但這一切都只是表象。而在心理層面上,這個國家的另一只腳依舊深深陷在前開化社會的泥潭之中。
三四郎并非激進的愛國主義者,但這個古怪男人的話激怒了他,他盡力為自己的國家辯解:“日本也在慢慢地發展呀!”那個男人對此的回答非常簡短:“終歸要亡國的。”三四郎震驚了,同時,他也不由自主地欣賞起這個男人。還真是,他想到,東京人就是不一樣。在家鄉九州島上(這是一個尤其保守的地區),沒人敢講這樣肆無忌憚的話——終歸要亡國的。但三四郎從未想過要問:“為什么?”
你需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待世界,教授如此告誡三四郎,更為重要的是,你必須認真審視自己。或許他是在故意挑釁,但是他的話成了貫穿整個故事的一個預言——一個警告——一個關于日本的潛在脆弱性,同時也是對一個名叫三四郎的、明治時代的年輕知識分子思想狹隘性的警告。
三四郎還得到了另一個更為直接的關于男女之情方面的預言。這個預言來自三四郎在火車上碰到的一位女子。他們在名古屋合租旅館的同一房間,兩人翌日清晨告別時,女子投給他會意的眼神,說道:“你真是一個膽小的人啊!”這是對他昨夜沒有采取任何“行動”的譏諷與責備。當三四郎聽到這話時,他感到“自己被人推上月臺似的”。他滿臉通紅到耳根,久久不退;他明白昨晚阻止他“行動”的原因并非道德,僅僅是膽怯。女人的直覺使得她直奔三四郎的要害。
當三四郎全身心地投入到東京新生活時,他將這兩個預言或者警告視為神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九州到東京的火車旅途,即是三四郎需要通過的一系列儀式的第一步。以神話而論的話,這兩個預言蘊含著純真王子進入森林的最重要的兩個動機。在通往成熟的道路上,三四郎是否能成功通過這兩個預言或者警告的考驗?成長紀事神話中的少年英雄,能否以一己之力開辟出一條通往幽深、未知森林深處的道路,與自己的陰暗面做斗爭,并取得奮斗之后所應收獲的部分智慧寶藏呢?
由于這部小說所含有的神話元素如此“蒼白”,對讀者來說無法得到簡單的答案。小說主人公幾乎沒有給出要與人搏斗,或者要對某事負責的任何信號。事實上,他對自己可能得到的一切毫無認識。讓這樣一個人成為神話里的英雄幾乎不可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三四郎》迥異于典型歐洲現代成長小說。在那種小說中,某個年輕人——通常是跟三四郎一樣來自外省、性情淳樸的年輕男子或女子——遭遇諸多阻礙,忍受種種傷害和挫折,內化出嶄新的心理和情感價值,進而成為成熟的個體,躍過“龍門”進入更為廣闊的社會,最終成為一名成熟老練的“公民”,就如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約翰·克里斯多夫》(Jean-Christophe),或者福樓拜(Flaubert)的《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
與這樣的小說相比,三四郎的成長過程相對缺少直線的延續性。他確實經歷了顛簸,各種期望也被大打折扣,但當事情未能如他所愿時,小說中從不明確表示這樣的經歷對他來說是否屬于挫折;或者,對于“挫折”,三四郎自己就沒有明確的定義。直面不利的局面,體會其中的懊惱,并從中找出答案:這不是主人公三四郎能做到的事情。如果有意外事情發生,三四郎只會感到或驚訝,或感動,或困惑,或留下深刻印象。
在東京,三四郎再次邂逅廣田教授。這次他把教授視作自己的人生導師。小說中并未暗示三四郎下定決心,要從這位(看起來)處于人生高段位的長者身上學習重要知識。他只是像觀察壯麗的云朵飄過蒼穹那樣觀察這位教授。他甚至以同樣的態度觀察自己所在的人際圈子,把他們當作美麗的或者有趣的云朵。他多多少少被教授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但是他從未想過把教授作為自己的榜樣。在人際圈子里,他愛戀上一個與自己年紀相仿的女孩:美麗而聰慧的里子(她似乎也被三四郎的純真質樸所吸引)。但他并沒有主動出擊以博取芳心。在心理和情感方面,他都讓自己處于一個舒適的安全地帶。他從不使用邏輯的方法讓自己陷入困境。
也許三四郎對作為一個成熟的年輕人沒有多大興趣,又或許他對何為“公民”壓根兒沒有認識。從西方社會的觀點看,不管是個人角度還是社會角度,他的所作所為既不是成熟的也不是負責任的。他已經22周歲(按日本算法為23歲),作為明治時期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他屬于上層精英的一員,在未來將成為國家棟梁的一員。這樣的角色怎可如此模樣?叉著雙臂,吊兒郎當,無法選擇人生的道路。如果某位外國讀者如此問我,我只能回答:“您或許是對的。”但老實說,這位叉起雙臂,把邏輯和道德困境一股腦兒地裹進盡可能柔軟的感性罩衣的三四郎,他不慍不火的人生姿態,對于我,或對大多數日本讀者來說居然是非常舒服的。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把《三四郎》定義為一本“成長不成熟”的小說。天真的三四郎進入新世界,遇見很多人,有了很多新體驗,并借此邁向成人行列。但值得懷疑的是,最終他是否會以歐洲觀念上的“成熟公民”姿態進入社會?對此,他周圍的社會并未抱有強烈期待,因為日本社會從封建制度橫向發展到皇權制統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未曾改變,并且從未經歷過中產階級公民性的成熟。我對這點有著深刻的認識。
從上述層面而言,西方“現代性”并未在明治時期的日本扎根,或許在今天的日本也尚未深入人心。而無論好壞(沒人能說出這到底是好是壞),現在的日本社會并不十分看重“成熟公民”這個概念。或許正因為如此,《三四郎》對日本人來說是永恒的經典,并且常年吸引著感同身受的讀者。當我閱讀這部小說時,這樣的想法不可避免地出現。
作為英國文化的擁躉和杰出學者,漱石對西方成長小說可謂了如指掌,而且他的敘述方式明顯受到簡·奧斯汀(Jane Austen)的影響。他很樂意將這些西方小說形式作為范本,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改編。事實上,他對兩種文化都有著深刻了解,并且是一位取得了高等成就的最優秀作家:漱石在英國文學方面造詣高超,夏目漱石全集中的多篇文章都展示了他深厚的英文功底。他成年后的整個人生都在創作俳句,而且他在中國古典文學上也同樣學識淵博。
綜上所述,《三四郎》盡管有著西方小說的框架,但是因果關系往往錯亂,思想與物質糾纏不清,肯定和否認時時含混。這一切都是作者有意識的選擇。當然,漱石平緩地推動情節前進,同時通過高超的幽默技巧、無拘無束的行文風格、直白的描寫,以及主人公質樸的性格來支持故事中基礎的模糊性。
許久以來,漱石一直被視作日本“國民作家”,我對此沒有任何異議。在現代西方小說的框架里,他將自己觀察到的日本人心理的不同形態及功能,平穩而準確地移植到小說中。這一點,我們現在仍然可以很容易地認識到。他用極大的真誠來創作這一切,而結果,無疑是巨大的成功。
《三四郎》是漱石唯一一部關于年輕男子成長的長篇小說。一生寫就這樣一部小說,對他來說或許足矣,但他必須至少寫一部。所以這部小說在漱石的作品中占有特殊位置。事實上,所有小說家都會有這樣一部小說。就我自己來說,這部小說就是《挪威的森林》(1987)。我并不特別想重讀這本書,我也沒有欲望再寫一本類似的書,但我感覺到通過完成這樣一本小說,使我有了一種巨大的進步,這本書的“出產”為我后來的寫作提供了堅實的支持。這個感受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并且我想象(就我自己的經歷來說),漱石對《三四郎》也有著類似的感受。
我期待著海外讀者對夏目漱石的反應——尤其是對《三四郎》的反應。如果你們喜歡這本書,我會很開心。這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本書,我猜想,不管你在世界的何處,不管你現在處于青春期的何種狀態、哪個方向,那個重要人生階段的特殊芳香,對我們而言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