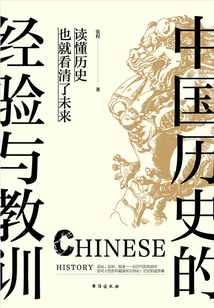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士人春秋 管仲的舞臺
春秋時期,王室實力的衰退,為各諸侯國做大做強提供了機會。“血而優則仕”漸漸地被“學而優則仕”所沖擊、取代,有才能的人,迅速脫穎而出、大展宏圖。這讓人想起了一句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春秋的爭霸,也正是因為有了人才觀的變革,才得以如火如荼地展開。
“管仲射小白”是一個經典的故事,說的是公元前685年,齊襄公的兩個弟弟公子糾與姜小白搶奪王位時發生的事。為了阻止小白趕回齊都臨淄,管仲帶兵堵截,并趁眾人不注意,突然射箭,命中小白胸部。當然這一箭只射中了小白的帶鉤,小白急中生智,咬破舌尖裝死倒地,騙過眾人,然后日夜趕路,搶先到達臨淄。
津津樂道之余,人們往往不會注意這樣一個細節。
我們說到管仲的時候,眼前浮現出的一定是一個氣宇軒昂的文士形象,可是,他的箭法居然如此之好,一箭射去,竟能正中公子小白胸口,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從一個敵人到他的宰相
我們來看看管仲的身世。
管仲,周王同族姬姓之后。但到了管仲這一系,早已喪失了貴族身份,家道中落。等到管仲出生的時候,管家只是齊國一戶貧困商人家庭。但管仲命好,生逢其時。恰遇從西周到東周的社會根本性轉變的良機。
夏商周時代,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即向司徒之官學習。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于是便形成了貴族子弟才有資格入學、當官這樣一種定規。所謂“血而優則仕”,也就是一種世襲制。
然而,公元前770年,新即位的周平王遷都洛陽,即史書所說的“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為了謀生,只能私自教學,于是“學在官府”局面被打破,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學生入學條件較西周時大為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就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脩”(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人”。
春秋以前,貴族子弟學習的課程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禮有大射、鄉射,樂有軍樂,射、御除田獵外,也都是作戰技術,這四科皆為軍事課目,只有書、數才為數學、文字、典章等民政知識。由于國家教育體制的推薦,全社會也崇尚六藝之學,管仲的出身有點類似八百多年后的劉備——知道自己出身卑微,只能通過能力和努力來博取功名富貴,因此管仲自幼刻苦自學,通詩書,懂禮儀,武藝高超也就不足為奇了。
齊桓公姜小白的“新政府”成立的時候,小白的師傅鮑叔牙是最有競爭力的主政大臣人選。鮑叔牙不僅教育、擁立小白有功,而且能力出眾,群臣對由他出任新政府的“總理”基本上沒有意見。齊桓公在任命前例行征詢鮑叔牙的意見,誰料到鮑叔牙固辭不受,反而極力建議國君將國家大權都托付給好友管仲。當年他們曾一塊做生意,走南闖北,鮑叔牙對他十分了解,也十分欣賞。
齊桓公一聽,立刻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一樣。
齊桓公對管仲的排斥,除了射向胸前的利箭和難以忘卻的仇恨外,更是出于維護齊國政治傳統和宗法制度的考慮。
管仲出生于商人家庭。在世卿世祿的貴族政治風氣還很濃的春秋早期,任命一個商人擔任主政大臣匪夷所思,勢必遭到巨大的人力和制度障礙。
此外,管仲的人品也有些問題。齊桓公對鮑叔牙說:“我聽說從前管仲和你一起作戰的時候,總是躲在陣后,或者搶先逃跑;管仲和你一起做生意的時候,出力少卻總是拿得最多;管仲的仕途非常不順,三次被國君排斥。你為什么向我推薦這樣的人呢?”
鮑叔牙回答道:“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夷吾即管仲,鮑叔牙此番話的意思是,如果您只是想讓齊國成為強國,那么任命我或者高傒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想讓齊國成為春秋霸國,那就非把國事托付給管仲不可。“管仲做生意時的確很在意錢財,那是因為他家境窮困,需要養家;管仲在戰場上不敢沖鋒在前,那是因為他家里有老母親。”
鮑叔牙重本質輕小節的一番話,最終打動了齊桓公。不唯身份論英雄,管仲就這樣鯉魚躍龍門,從齊桓公的敵人,變成他的宰相。
非常之識,用非常手段
新官上任前,管仲和齊桓公有過一次長談。
管仲微笑著對齊桓公說:“臣雖蒙受主公恩寵信任,但賤不能臨貴,臣爵位卑下,恐難施政。”管仲這個要求,真有點匪夷所思。齊桓公轉念一想,卻是實情,既然國家要托付于他,他要實權就該給他。于是齊桓公答應了這第一個要求,封國相管仲為“執政之卿”,位在高、國二卿之上。
“謝主公恩賞。臣雖已貴為上卿,然貧不能使富。”原來是要錢,管仲還真是“貪得無厭”啊!
“臨淄各市,有司所得稅賦十分之三歸國相所有,國相富可敵國了。”齊桓公說,然后得意地看著管仲。
“臣蒙主公賜以富、貴,然疏不能治親。”管仲謝恩后又提出了第三個要求。
齊桓公一聽,愣住了。齊國姜姓,高、國二氏及其他大夫,要么出自公族,要么有聯姻之親,雖齊國任人用政不像魯國那般強調親貴,但以管仲貧寒世族出身,族中又無近親與權貴聯姻——在宗法關系尚存的時代,起用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外人來主管事務,周圍這些沾親帶故的大臣們會怎么想?
齊桓公沉吟了一下,突然想到齊國開國之君太公姜尚的故事,當年太公為周文王師,后又輔佐武王,一個外姓人,后來被武王尊稱為“尚父”,可依此例吧。“這樣吧,寡人敢稱國相為‘仲父’,寡人執晚輩子侄之禮,命國人不得稱國相之名,皆稱字,國相以為如何?”
霎時間,一股從心底最深處涌動的熱血,在管仲胸膈之間開闔鼓蕩,以致言語艱難:“昔日罪臣,辱蒙主公托付國事,逾格恩寵,粉身難報。”
當時間過去兩百多年后,孔子如此評價這個歷史片段:“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伯。”——即便如管仲之賢,如果不能得到這三大權力,也不能使齊國面南稱霸。
稱霸是前無古人之事,當用非常手段。管仲這么想,可以理解。齊桓公能答應這三個“離譜”的要求,就很令人深思了。不僅是他個人性格使然,當時,天子式微,禮崩樂壞,宗法制度受到巨大沖擊,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齊桓公才敢于開先河,做前人從未做過之事。歷史上,齊國曾是一個多災的國度,齊襄公亂政更使齊國幾近崩潰。當齊桓公登上了高高的君主寶座,照理講他應該感到高興才對,然而恰恰相反,直面齊襄公留下來的一片殘山剩水,齊桓公產生了深深的憂患意識。對此,《管子·小匡》載齊桓公語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不聽國政。……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正是這種憂患意識,賦予了齊桓公敢為天下先的氣勢。
多少政治人物夢想著擁有施展拳腳的權力和平臺,管仲奇跡般地得到了。
朝秦暮楚,飛黃騰達
其實,不僅是管仲脫穎而出,當時無數有賢才的士人,在春秋爭霸的土壤里,也得到了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而不必非得是波斯貓。
“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這是管仲關于稱霸的語錄。按今天的話來理解,就是一個國家要想做大做強,首先必須爭奪人才。齊桓公不計前嫌,重用管仲就是最好的例子。此舉也開了春秋時期的“養士”之風。一批有志之士,紛紛成為王侯公卿競相招攬的對象,他們朝為布衣,夕為卿相,成為春秋時期各國謀取霸主政治地位的有力援助。
后來,養士甚至成為當時上層社會競相標榜的一種時髦風氣。戰國時,養士之風愈演愈烈,達到高潮,只要是有實力的國君或權臣都盡可能多地收養門客,像魏國的信陵君、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就是以養“士”眾多而著稱的“戰國四公子”。
春秋時期,都有哪些三教九流飛黃騰達?我們還是從管仲身邊說起吧。
主管齊國經濟工作的甯戚被發現和任用,比管仲的任命更具有傳奇色彩。
甯戚(生卒年不詳),姬姓,甯氏,名戚。春秋時期萊棠邑(今青島平度)人,一說衛國(今河南境內)人,早年懷經世濟民之才而不得志。齊桓公六年(公元前680年)拜為大夫。后長期任齊國大司田,為齊桓公主要輔佐者之一。
甯戚雖然也是姬姓,但他的出身還不如管仲,是地道的平民。
不過平民有了知識,有了才能,就成了士人。甯戚便是士人中的佼佼者,所以還未得志之時,已名聲在外,引得管仲慕名而來。
管仲的車隊尋到了甯戚的安身之處——一處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管仲親自上前叩門,門開了。“請問貴人有何事?”甯戚探出腦袋。
“先生就是甯戚吧?”管仲問道。
“是的,小人就是甯戚。”春秋時禮法尚嚴,甯戚在衛國是“庶民”,所以要自稱為“小人”。
“管夷吾冒昧登門,想與先生交個朋友。”
甯戚長揖作禮,管仲見其不卑不亢,舉止有度,更相信自己的判斷。命隨從將飲食酒肴搬入,就在甯戚家中邊吃邊談。屋內極狹窄,眾隨從只得在門外休息,惹來一眾村夫圍觀。門外人聲鼎沸,甯戚卻充耳不聞,意態安詳。
管仲有心而來,于是開門見山,問道:“正要請教先生,齊國百廢待興,應從哪一方面入手呢?”
“治國綱略,仲父恐怕已早有籌謀,甯戚不敢忝言,只從一些末技來談吧。”甯戚本有統籌全局的宏論,卻怕時間倉促,難以細談,而且他要用一些時務實用之學,來回答管仲的“考核”。
“甯戚一入齊國,就聽聞百姓交口稱贊仲父的新政,尤其是不侵奪農時,改公田為賦租,實在是安國富民之策,這些想必已在仲父意料之中。只需區區數年,齊國將粟米滿倉,民眾繁衍。但粟雖為固國之本,但還不足以使民眾安居樂業。”甯戚稍微停一下,再說,“百年之前,農夫使用的農具是木、石所制的耒、耜之類。農夫一戶只能耕種百畝(約合今三十畝),畝收四斛。后為鑄鐵發明,價廉物美,用于農具后,農夫一戶可耕種兩百畝(約合今六十畝),畝收十斛。人口繁殖后,自然又有了余力開墾荒地。今仲父新政,更使農夫不遺余力,外民遷入。可數十年后,齊國已無可開墾之地,民多地狹,豈非亂之源?仲父不可不慮。”
“哦?請先生暢言。”管仲仔細聆聽著。
“此時應獎勵農夫不離鄉土,謀求副業。近海之濱的蓬萊一帶,漁獲豐盛,可使民入海捕魚而向國庫納海租。而在營邱之帶,夏秋高熱少雨,可煮海為鹽。故近海之男,可為魚鹽之業,內陸之處,應使之育養六畜。我觀齊國六畜之種,不如關中、河北之帶的肥壯,可遣商賈前往引入種群,逐步改良。”
原來甯戚的觀點是在農業之外,另開辟副業生產。
管仲發現甯戚在經濟方面很有見地,有心向齊桓公舉薦,于是問起甯戚的身世。甯戚苦笑一下說:“先祖亦曾位列大夫,然國破之后,人為藏獲(即戰俘奴隸),沒入衛國野鄙,世為庶民。先父在日,家道尚為小康,親授圣王治道。后變賣家產,作為旅資,命甯戚行游各地,留意山川形勢,民生風俗,期待日后為明主所用,光復家聲。前年甯戚遠游回家,方知先父已經貧困病逝,家徒四壁,棲遑孤獨。后聞齊國禮賢下士,今日得見仲父,可見此言不虛。”
試問千百年來,天下多少君子賢才,有大智慧而無小機運,徒然埋沒鄉間,而身在高位,識見不能謀其政者,則誤國誤民。甯戚出身貧賤而志存高遠,比照自己曾為桎梏之囚,管仲感同身受,更能體會個中滋味,于是修書一封,讓他去找齊桓公。
次日一早,甯戚依舊穿著短褐單衣,駕著牛車,懷端管仲的薦書直入齊都臨淄。他邊走邊想:自己出身低微,雖獲管仲賞識,卻不知齊桓公是個怎樣之人,若以薦書入稟,即使能獲官職,他日豈不被人譏諷攀援富貴?于是打定主意,直奔宮門外,放開嗓門唱道:“南山燦,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短褐單衣才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歌詞傳到齊桓公耳中,他心想:奇怪啊,一個車夫也感嘆懷才不遇,就將他召入。經過交談,齊桓公確信自己淘到了一塊真金,于是任命甯戚為大司田,掌管農業生產。當時的齊國雖地廣、資源豐富,但人少,土地需要整治,農業既是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又是極有潛力的領域。在甯戚的努力下,數十年后,齊國農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形成了成熟的農業生產管理經驗,為國家的崛起打下了扎實的經濟基礎。管仲死后,甯戚接任相國。
這就是甯戚的才能,這就是士人的才能。和天子諸侯大夫相比,他們可以一無所有,但他們只要有一條就足夠了,那就是:本事。
甯戚可以說代表了春秋時期一大部分士人的特點:有能力,沒負擔,有自由。當時尚未形成民族的概念,這決定了他們可以東奔西走,在自由寬松的氛圍中,齊人去魏,魏人入秦,燕人南下,楚人北上,人才頻繁流動。有才能的士人擇主而事。誰賞識他們的才干,誰給的報酬待遇高,他們就為誰效力。合則留,不合則去。士為知己者死而不是為國死,成為很平常的事情,也并不被看作是道德上的缺陷。至于家庭出身、個人品行,自然也被淡化了。
從春秋到戰國,士人作為一個特殊的階層而崛起,成為當時社會的中堅力量,尤其是那些重量級的士,投身到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會興旺發達;離開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內外交困。正所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釁魏魏傷。”(《論衡·效力》)
一個有西周遺風的人
齊桓公執政集團的另一位重臣是鮑叔牙。鮑叔牙可以說是最富有西周遺風的士人,在他的身上,體現出的是道德至上的上古風格,也可以說是貴族氣質。這也許同鮑叔牙出身較好,家境殷實有關吧。
鮑叔牙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與人“抬杠”,以性情耿直,犯顏直諫著稱。他對齊國的許多政策和人事提出了中肯、尖銳的批評。齊桓公在霸業已成后,常常顯露驕矜之色,甚至覺得自己功勛可比堯舜。齊桓公曾經計劃鑄造大鐘,用以銘記自己的功德。鮑叔牙知道后,主動去和齊桓公談大鐘銘文的事情,一件一件地述說齊桓公的過錯,結果說得齊桓公恨不得找個地洞鉆進去,鑄造大鐘的事情也就無從談起了。
還有一次,齊桓公和管仲、甯戚、鮑叔牙四人同飲。酒酣耳熱的時候,齊桓公責問鮑叔牙:“大家都向我祝酒了,為什么就你坐著不動呢?”鮑叔牙捧杯起身說:“那我也來向國君祝酒,希望國君不要忘記當年流亡莒國的貧困擔憂,希望管仲牢記曾在魯國的囚徒生活,希望甯戚記得夜里車下喂牛的時候。”一席話說得大家都感嘆不已。齊桓公離席,向鮑叔牙鄭重行禮說:“我和兩位大夫若不忘你的話,國家就一定沒有危險了。”
“管鮑之交”,意為至交的朋友關系,這一成語便出自鮑叔牙的知人和自知。
管仲病重后,齊桓公考慮他將不久于人世,便問,可否讓鮑叔牙接替他為相?管仲說,鮑叔牙善惡過于分明,以善待善尚可,以惡對惡誰能忍受得了?“他是位君子,但不可以委以國政。”有人將管仲這些話告訴了奸臣易牙,易牙以為這正是離間管仲與鮑叔牙的好機會,遂到鮑叔牙面前挑撥離間。沒想到鮑叔牙聽了非但沒有生氣,反而笑道:“這正是我推薦仲父為相的原因。仲父忠于國家,沒有私心。若讓我為相,我豈能容忍你們這些小人?”
從鮑叔牙的身上,人們看到了春秋時期士人思想上的變化和沖突,那就是“道”和“德”的交鋒。周武王、周公等用“以德配天”“天以德擇主”來解釋夏、商、周的歷史之變,“德”一直是為政治服務的一個標準價值觀,無論是君主還是大臣,“德”是第一位的。鮑叔牙有這樣的思想,因為他有西周貴族的氣質。與此同時,鮑叔牙應該也認識到了所謂“道高于君”的“道”,作為一個出現于西周初期的政治概念,“道”在春秋時期得到了大發展,也成為后來百家爭鳴的核心思想。這和春秋的社會劇變是分不開的,人們認識到單純以德治國是行不通的,而“道”正符合了這樣的需求,成為為政治服務的另一把利劍。
“道高于君”,這恐怕也是鮑叔牙舉薦管仲而管仲并不舉薦鮑叔牙的根本原因。在管仲的思想里,“法”是“道”的體現,是人類的“公”,因此要尚公崇法,依法治國。這樣的思想,深深體現在管仲的治國措施中,首先就是人才選拔的“公”。
為一位農夫點燃一百根火燭
管仲知道,齊國霸業絕非一木之材可以撐起的,頭一項要務,必是要廣求賢達而用。已經有齊桓公的首肯,新上任的宰相雖然人事不廣,但施行起來也得心應手。很快,八十位辯才無礙、聰慧敏捷的游士離開臨淄城,滿載財帛,向各國奔去。帶著齊國求賢若渴的信息,也負有暗中打探各國情報的秘密任務,如果用現代的話來說,這是一批“外交情報人員”。由于管、鮑二人早已在各國交通要隘,設立了秘密情報點,或混跡于酒肆旅館,或托身于商行作坊。這么多年過去,早對各國政局了如指掌,這些又為八十位游士任務的完成,提供了重要的幫助。可想而知,此后從各個地方涌來齊國的,不僅是人才,還有許許多多情報資料。
另一項求賢的政令,便是選薦“秀民”。以往各國施行的多是世官制,如齊國的上卿高、國二氏,便世代承襲、主持國政。當然同時也有任官制并行其中,比如原來鮑叔牙等人被國君任命為少傅便是例子。但被任命之人僅限于“國人”中的“士”,近十倍于“國人”的“野人”(即野鄙農夫),卻因血緣出身而永遠被阻擋在仕途和從軍之路以外。
管仲開始撕開這張網,雖然“秀民”的人數有限,但畢竟是一個開始。這就是管仲心目中與世官制背道而馳的“賢人政治”,這開啟了戰國以后任人唯賢的濫觴,恐怕也是以后兩千年來科舉取士的源頭吧。
然而在當時,這是一個不易之舉,貴族就首先反對。但由于高、國二氏在之前的改革中,已獲得巨大的利益。遂投桃報李,給予支持。領袖世族的二氏,贊成選薦人數區區的“秀民”,于是這項政策才得以實施。為了顯示這個政策的威嚴,管仲選擇在太廟舉行朝會,要求五屬大夫及其僚屬,“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當然,這也要托先王舊制的“合群叟,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集合各方老人,比較民眾中有道的人,樹立典范作為百姓的綱紀。有了這堂堂之言,地方官員便開始積極為齊桓公的霸業搜羅各種人才。
為了政策的持之以恒,管仲規定每年正月,五屬大夫及鄉長在述職時,要向國君報告舉薦賢人的成效。如發現有而不報,將定為“蔽明”“蔽賢”之罪,屬五刑重罪了。
以上兩項都要假手于人,但庭燎取士之舉,卻是由管仲和齊桓公親自執行的。
齊桓公專門設立了一個招攬人才的機構,起名“庭燎”。西周時,重視等級禮儀,如果要迎接四方之士,就要用高規格的接待禮儀。古代邦國在朝覲、祭祀和商議軍國大事時,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也就是“庭燎”。
本來庭燎的數量按爵位高低是有所規定的:天子為一百,公侯為五十或三十不等。為招徠人才,齊桓公便僭用了天子的庭燎一百之數。但出乎意料的是,時間一天天過去,八十游士和地方臣工都陸續報來佳績,但自己這一邊,卻連一點動靜都沒有。齊桓公實在想不明白,終于有一天,衛士報告有一個自稱“賢才”的人求見。
齊桓公心中一喜,兩月余不見動靜,今番終于有戲了。“舉庭燎迎接,不可怠慢,另外派人請仲父來商議。”
衛士遵令而行,燃起一百把庭燎大燭,煙火沖天。可是到了一看,是一個村野農夫。齊桓公很失望,但人都來了也不能立刻叫人走,只好敷衍地問:“你有什么本事啊?”農夫回答說:“我只會九九術算。”齊桓公一聽急了:“什么,你只會九九術算?那你求見寡人,所為何來?”
只見那農夫恭恭敬敬地行過禮,慢慢地說道:“小人也不覺得會九九術算是什么本事,但卻想為主公排解一件大煩惱。”
“什么大煩惱?”
“主公可曾想過,為何設如此隆重的庭燎之禮,以待賢才,卻無人應召?”
此話正中齊桓公所想:“你說,這是為何?”
農夫憨憨一笑,道:“賢才之所以不來,是因為齊國是名聞天下的大國,主公又是聲名遠播的國君,四方之士自認為比不上主公,所以才不敢來。九九術算,本就是微不足道之技,而小人又是一個村野之夫,然主公卻以庭燎之禮,厚待于我,那些真正的人才,還會擔心自己不受重用嗎?”
齊桓公聽罷,連聲贊嘆:“說得好,說得好。”
管仲趕來后,一聽經過,對齊桓公能從善如流大加贊揚:“泰山不拒壤石,才能成就其高;江海不拒細流,才能成就其大。主公此事處置明哲,天下賢士定會魚貫而入。”
果然,齊桓公厚待一個只會區區九九術算的農夫的故事,如插上翅膀,傳遍遠近。四方前來投靠的能人賢士,紛至沓來。
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短短四五年工夫,齊國就兵強馬壯,蓄勢待發。首都臨淄城的人口超過了四萬戶,有二十多萬人口。在這樣規模宏大的城市中,屹立著巨大的宮殿,里巷縱橫,屋宇鱗次櫛比,肆市林立,男女熙熙攘攘,商賈游人往來其間,是當時我國東方最大的經濟中心。
管仲確立的廣求賢達的制度,效果如此之好,以至被后世的齊國政府牢牢繼承。《史記》載:“齊國遵其政,常強于諸侯。”一個人,一套制度,就保住了齊國的大國地位。若這項制度與用人理念被時代所接受會怎樣呢?這套制度奠定了春秋戰國改革的基礎。在一系列改革的推動下,列國集權程度加強了,官僚政治確立了,地主封建制形成了,小生產發展了,百家爭鳴出現了,并孕育出了為即將到來的大一統專制主義集權統治服務的系統理論。中國由分權割據走向集權統一的歷史條件已日趨成熟。
擴展思考:君臣相得
1.管仲和齊桓公相互信任,共同成就了春秋首霸。他們這樣的關系,史稱“君臣相得”。你還知道中國歷史上有哪些君臣相得、創造輝煌成績的例子?給個小提示:諸葛亮和劉備。
2.管仲算是知識分子。古代知識分子總是主動向公權力靠攏,“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像管仲那樣演繹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話,是多少讀書人的夢想,似乎只有那樣才能實現個人價值。試問,除了從政,古代讀書人還有其他“職業選擇”嗎?如有,其他職業能像當官那樣實現讀書人的抱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