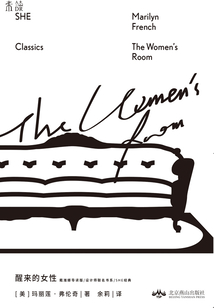
醒來的女性:戴濰娜導讀版(SHE經典)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推薦序
“她者”的醒來
戴濰娜/文
娜拉的覺醒,始自一個懷疑的時刻。從全權的信任、依賴、委托,到帶著質問,懷疑地睜開眼。這是一個驚恐的時刻,一番前所未有的勝利,同時也是一出悲劇性的大戲。從此,命運不在天神或夫君的庇護之下;她自己的命,須一分一厘地掙。文明隨之出現一種迷人而危險的轉折,女人走入了沒有窮盡的革命旅程。
早在奴隸制和私有制產生之前,女人就已被歸為私有財產和美麗的奴隸。她們既不能像公民一樣行使公共權利,也不能如一個完整的人一樣,擁有哪怕是對自己身體的私人權利。男權社會通過摧毀女性的自信、人格,漠視其創造力價值,從而實現控制和奴役。不同的性別和多元的關系,被強制性地壓縮在單一的權力模式里。這一人類史上最古老的壓迫形式,壓迫著男權結構中的每一個女人和男人。我們的整套文明,建立在一半人沉默的歷史上。
女人的聲音沉入海底,女人無法聆聽自己。
維系這種天然的剝削與沉默,需要不間斷的催眠。如果誰不幸提前醒來,那么,從女性意識蘇醒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社會結構中需要被清除的異己。她們或是被安上“歇斯底里癥”的瘋女人(據說這類病癥多發于天賦極高,卻不能適應其社會角色和社會責任的女性),因為過早覺察到世界的瘋狂,而給當成瘋子被瘋狂對待;或是成為被埋沒的女作家、女藝術家、女科學家,是羅丹的情人、艾略特的太太、莎士比亞的妹妹[1]……或者干脆變成女妖、女巫、女怪……抑或她們誰都不是,只是不安分的太太、不開心的母親。從某一天起,她們開始擁有共同的罵名——一群無可救藥的女權主義者。
時至今日,女權主義者依然被很多人視作恐怖分子一樣的可怕存在[2],她們是最富有革新精神,然而卻最不受待見的那類人。女人一做回自己,就讓社會打哆嗦:的確,她們往往是比男性更激進的革命者,只因“她者”的歷史,更值得被清算。如果一部小說野心勃勃地想挑戰這段沉默史,試圖揭穿女人成長過程中積累的甚至連自己都尚未察覺的不公、恐懼、焦慮與幻滅,它大概需要擁有像《醒來的女性》這樣的恢宏體量。這部小說采集了各種女人的聲音,觸碰了整整一代女性的困境。
《醒來的女性》講述了書呆子米拉和她周遭那些不同背景、不同階層、不同性格的繽紛各異的女性,她們一個個如何醒來,又如何一個個被毀掉的故事。
每一個人物,都是“一個呼嘯的戰場”。作者弗倫奇從每個女人內心深處挖出了反叛者的影子,邀請大家一起來思考女性從出生起就接受的種種規訓、引導和暗示。筆尖深入至人性、情感關系、權力結構中的盲點和痛點。這些反叛者,這些覺醒中的女人,充滿矛盾、反復和不確定性。她們處于多重的撕裂之中,內心不斷冒出錯愕、驚恐和羞恥感。米拉、瓦爾、伊索、凱拉、莉莉……女人們成長為自覺或不自覺的女權主義者,可總有一些時刻,她們努力把這個陌生的女權主義者與自己進行切割,試圖找回所謂的正常和快樂。然而,她們已經覺醒,就無法繼續昏睡。
女人們認識到,必須進行一場“情感革命”,挑戰“丈夫”所代表的那個外部世界對她們天然擁有的權力。這部包羅萬象的小說,肥皂劇般展演了多對男女的婚姻真相,描摹出那個年代婚戀關系中的眾生百態——親密關系中的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獨特的、相互攻擊的方式。這些傷害幾乎無從避免,即便是兩個品性高貴的人,哪怕他們擁有優良的階級出身,抑或志同道合默契如一人,都無法消解其中隱藏的精神暴力、被巧妙掩飾的剝削和以幸福之名被奪走的一切——那是男權社會所教習的唯一愛的方式。小說近乎絕望地披露出,在父權體制下,愛之不可能與愛之幸存。
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女人的階層上升通道已不局限于“結婚”這一條獨木橋,她們擁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主人公米拉在經歷了一系列性恐懼、處女危機和失敗戀愛后,嫁給了門當戶對的醫學院學生諾姆。不同于那些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成長小說”,總以女主角的結婚為圓滿結局(那的確常常意味著女性自我“成長”的終點),米拉步入婚姻,故事才剛剛開始。學霸米拉婚后就輟學在家相夫教子,隨著醫生丈夫收入漸漲,二人穩步邁入中產階級,搬到有錢人聚居的郊區。米拉順理成章當起了“順義媽媽”,每天圍繞著丈夫、孩子和八卦。直至看似完滿的婚姻一樁接一樁地破裂,媽媽們曾經無話不談的下午茶風光不再。她們的正義,最終轉為抱歉。她們的吶喊,漸漸沉默。突如其來的婚變之后,米拉選擇去哈佛深造,在劍橋鎮結識了以瓦爾為首的思想獨立的高知女性,組成了小小的精神共同體。她們彼此支撐,見識高明,卻也不能阻擋女人們奔赴各自悲劇的命運。
隨著技術發展急速磨滅男女在生產過程中的體力差距,恩格斯論述中性別壓迫的起源和基石日漸瓦解。此書出版前十三年,林登·約翰遜總統簽署頒布了美國女權運動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民權法案》,其中第七章正式引入了“性別”概念,提出男女“就業機會平等”。然而法案頒布之初,許多人對此不以為然,甚至視法案為“僥幸出生的私生子”[3],距離女性在職場上大施拳腳還有漫長的旅途,社會上多是一些“絕望的主婦”。“要毀掉一個女人……你只需要把她娶回家”。盡管此前的大半個世紀,她們接連贏得了選舉權、遺囑權,以及在不需要丈夫許可的情況下提出訴訟的權利,但是70年代絕大多數美國婦女的生活依然圍繞著烤面包、四季豆展開。即便有洗衣機、烘干機和電冰箱這類“小小的解脫”,仍不能改變她們在婚姻里失去自我的“腐敗的狀態”和充斥她們全部生活的“骯臟的細節”。彼時,避孕工具剛剛得到大規模推廣,女性由生育不受控制的自然狀態向社會化過渡。她們開始享有避孕帶來的身體解放和閑暇時光。在逼死人的空虛之中,主婦們開始檢視自己的感受,日漸覺察到不對勁的地方,全身涌動著實現自我價值的渴求。這份渴求與她們既定的社會角色、性別分工產生了激烈的沖突。反抗者由此認識到,所有這些“他們”的規則和真理,都在講述同一個謊言——女人是天生的受害者。而這顯然是餿掉的隔夜菜,在第二次女權運動浪潮斗志昂揚之際,尤難下咽。
這一波由貝蒂·弗里登、凱特·米勒、朱迪斯·菲特利等掀動的女權浪潮中,性暴力、性別歧視、女性參政議政、同工同酬、女性文學傳統等都處于議題中心。隨著時間的推移,女權主義改變著世界,也改變著女性自己。醒來的女性們,面對著不一樣的風景。當米拉們還停留在半輩子對性一知半解,精打細算欲望和風險的比例的時候,女權主義已迎來了轟轟烈烈的“性解放”。波德里亞曾批評女權運動中的某種近視,認為“性解放”磨滅了界限,導致參照原則的喪失,最終使得誘惑缺席。而這些模糊了的界限,需待四十年后席卷全球的“Me Too”運動再次予以厘清。從大鳴大放的性解放,到精耕細作的改良性文化,女權運動道阻且長。90年代以后,女權主義陣營內部興起大混戰。不同種族、階級、性向的女性群體,攜帶著各自不同的訴求,參與到后現代女權主義論戰之中。事實上,對女權主義最激烈、最戳中要害的批評都來自其內部。女權主義者們從一開始就抵制“完美”——經由男人定義的完美妻子、完美母親;女權主義理論也同樣擯棄了“完美”,它在分裂和批判中成長。如同一個足夠健康的有機體,它沒有極權政治的整齊劃一,也沒有絕對的領袖和中心,它甚至不需要合法的繼承,參與者更多是從個體經驗出發作出判斷和選擇,這些判斷也絕不是非此即彼。而這些恰是有別于男權秩序的女性政治的特征。當伊瑞葛來發問:“在男性專擅的秩序之內,能否出現女性政治?若其為有,在此政治過程中需要什么樣的變革來配合?”[4]弗倫奇似乎在一個小小的精神共同體中預見到這種女性政治的可能性——它以傾聽為核心機制,如同子宮般滋養個體多元化的需求和選擇,待到一定時刻即與母體分離,發展新生。主人公米拉所在哈佛的小團體,一個微型精神共和國,最終優雅地走向分裂和分別。即便彼此堅持己見,她們依舊一次次表示理解。“那晚的分別,像芭蕾一樣優雅又正式……只有適度的端莊舉止、彬彬有禮,才能表達她們到底有多親密,她們之間的距離有多么不可逾越。”
及至千禧年,互聯網時代的女性聲音集體爆發。曾有一個有趣的全球問卷調查:“如果互聯網有性別,那么它是男還是女?”絕大多數網民投票相信,互聯網是女性。互聯網讓人們可以友好地跨越各種不同的界限,它非常多元,又不具備直接暴力,這些都更接近女性氣質。事實上,我們如今的整個文明都開始女性化,這可能是互聯網和城市化進程共同作用的結果。“她者”的回歸,毋庸置疑是這一時刻的歷史需求。當瓦爾憤怒地斥責“一個充斥著‘你們’——滿是男人的世界”,女權主義者們在一代又一代人中添加進“我們”的聲音。
娜拉們當然可以,也應當保持她們的憤怒。
《醒來的女性》出版四十多年之后,女人們一覺醒來,依舊無處可逃。弗倫奇對此大約不會太過驚訝,“我無法想象,哪一種社會結構能容納這種安排,卻不用改變所謂的人性”。人性之中,豎著古老的高墻——人對于他人缺乏同理心,“這一群人對另一群人也是一無所知”,男人和女人之間更是欲望遠超理解。伊瑞葛來這樣的理論家很早就意識到,女權的吶喊不應以男性作為比照而存在,更多是要通過回歸女性生命本質的內在體驗,來思考性別差異、自身與他者的關系。弗吉尼亞·伍爾夫也有這方面的自覺,她在《奧蘭多》中虛構了伊麗莎白時代的男性貴族奧蘭多,在經歷一系列對愛情的失望之后,有一天他突然變成女性,重新以女性的身份體會這個世界,才意識到原來作為女人生活在這世上竟有那么多的麻煩。女性解放運動,絕非一個性別打倒另一個性別——那只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男權。其真正訴求是一場結構性的逆轉,將女性和男性從封閉且唯一的權力結構及認知模式中解放出來。女性權益的爭取,僅是其表層;更幽微的部分,是讓男性與女性都能跨越自身去體會沉默的另一半世界。這種超越自身性別的體察,帶來的將是人性的拓展和成長。
這終究是一個無法與他人徹底切割的世界。女人和男人面對共同的罪孽,承擔同樣的未來。“她者”們千辛萬苦地醒來,她們的憤怒,是一種凈化,是從悲劇經歷中萃取出的精華,它深刻積極地改變著人們原本看待事物的方式,幫助我們對抗普遍的麻木、愚蠢、不公,對成長的扼殺,對生命熱情的怠慢。“希臘語中,遺忘的反義詞是真相”,真相炙烤著醒來的女性。
她們最終站出來代表她們自己。
2020年春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