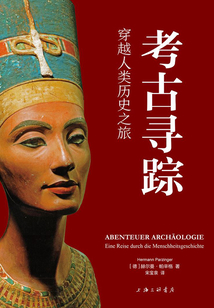
考古尋蹤:穿越人類歷史之旅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考古學入門——學術辯論、研究方法和政治含義
有關考古的神話傳說、著名人物與研究方法
好萊塢將人們對于考古探險的各種神奇想象大加藝術渲染:有時是頭戴軟木遮陽盔、身著卡其色便裝、手握毛刷、鼻梁上架著鎳邊眼鏡的學者,有時是頭戴寬邊軟呢帽、身穿皮夾克、手持馬鞭、腿腳健壯的探險家。他們在探尋失蹤的金銀財寶,揭示古代神秘事件。近些年來,這些人物出現時,他們的膝蓋上還總是想當然地托著筆記本電腦。在當代媒體中,印第安納·瓊斯的身影似乎隨處可見。自從電影《侏羅紀公園》上映以來,有人甚至誤認為恐龍的發掘研究也屬于考古工作者的職業工作范疇。而實際上,這是古生物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早期人類起源問題主要是古人類學家從事的工作。稍了解情況的人則認為,考古就是破解古埃及秘密的。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早已過時的說辭,當然與今天的現實相去甚遠。
考古學在當今眾多的科研領域中,可以說是屬于那種最具魅力的、最引人入勝的學科之一。很少有其他專業能像考古學這樣活躍在國際上、涉獵多種學科并對各個民族發揮著凝聚作用。公眾對某種話題的濃厚興趣往往會引發很多添枝加葉的不實之詞。但是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幾乎每個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渴望知道,他和他的祖先是從哪里來的?我們當今五花八門的文化生活,又是怎樣從無到有、逐漸發展起來的呢?考古學的學科吸引力在于它能見微知著,通過一些不被常人留意的跡象來回答上述這些問題。考古學甚至能夠根據古代廢棄的垃圾堆,破解人類最早的、有文字記載以前的歷史奧秘。當然,今天我們對人類早期歷史的認識遠未達到終點:我們時常從廣播中聽到或在報刊上讀到有關考古新發現和出土文物引起廣泛轟動的消息。這些新的考古發現在不斷地更新和填補我們所復原的遠古時代的畫卷,因為這幅畫卷迄今為止仍然建立在各種支離破碎的殘留遺跡和一些偶然發現之上,還不夠完整。還有其他比考古學更引人入勝的學科嗎?我本人對此深信不疑:考古之所以有著強大的魅力,是因為任何一個微不足道的細節和任何一次默默無聞的發掘工作都完全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甚至徹底顛覆我們對歷史的一些看法。比方說,在內布拉的星象銅盤(Himmelsscheibe von Nebra)被發現之前,我們何曾想過,生活在今天德國中部地區的先民能比古代埃及人更早地將觀察到的天象用圖形記錄下來呢?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智慧結晶!
但這一切又是怎樣開始的呢?考古學是怎樣逐步發展成一門現代科學的呢?考古學(Archologie)這個詞的字面意思就是研究古物的學問。“古物”,即古代物質文化的遺物和遺跡,必須從文化、歷史、地理或人文地理等各種不同角度進行觀察研究。德國各大學沒有設立考古學這個專業或考古系,但設有古典考古學 [1]、西南亞考古學、圣經考古學、基督教考古學、拜占庭考古學、古羅馬行省考古學、伊斯蘭教考古學、中國考古學、古代美洲考古學以及自然科學考古學,還有新近出現的中世紀和近代考古學等。這些考古學分支的專業科研人員作為各個學科領域的代表,一直致力于研究一定的歷史時期、一定的文化區域或特殊的原始資料。
最具普遍意義的是史前考古學(Prhistorische Archologie),或稱史前史(Ur-und Fr ühgeschichte [2])。盡管這個專業主要從事研究歐洲早期歷史,但它不受空間的限制。史前史學者在全球范圍內研究自人類最早制造工具以來,大約始于迄今270萬年的歷史。對原始時代的研究,主要涉及人類早期還沒有發明文字,因而其各種活動尚且沉默在黑暗的、成千上萬年的歷史歲月中的漫長歷史時期。當考古工作有了最早的文字資料作為參考時,人類原始時代就過渡到了歷史時期的早期。與此相關的兩個方面的思考在此尤為重要,值得注意:第一,這個時期的文字資料還非常零散稀少,尚不能以此恢復當時歷史的全貌,因而這個時期的研究仍需要考古工作。第二,一些文化的早期歷史時期特征是,有關其歷史記載往往都是其他外族人撰寫的,如希臘人記載了凱爾特人,或羅馬人記載了日耳曼人,而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這個時期還未能寫下有關自己的文字資料。這些民族只有開始用文字記錄自己的歷史時,他們的早期歷史時期才真正結束。在地中海地區,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古典文化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脫離了早期歷史階段。而在中歐的大部分地區,歷史記載不早于中世紀早期,而北歐和東歐甚至還要推遲到中世紀盛期。
當初主要從藝術史研究起源的考古科學,其奠基人是德國學者約翰·約阿希姆·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在大學讀完神學、歷史、醫學、語言學以及哲學以后,溫克爾曼去意大利各地漫游,并開始在羅馬和龐貝城收集古典時期的遺物。最終,教皇克雷芒十三世(Clemens XIII)于1763年任命他為梵蒂岡教皇國的古物監管人。溫克爾曼認為藝術最崇高的使命是對美的表現。他創造了非常著名的“尊貴的簡樸和寧靜的偉大”的審美公式。他對古代男性英雄和諸神雕塑的高度熱情也是對他本人同性戀的一種反映,這一點可以從他的往來書信中清楚地看到。在他看來,希臘各項藝術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與此同時,他認為羅馬藝術只扮演了一個模仿希臘藝術的角色。這就同他認為希臘的民主優勝于羅馬的專制一樣。在他的研究過程中,他很早就看到通過系統的考古發掘來接近古代遺物這條路的重要性。故而,舉例而言,他當時要求用這種方法對希臘重要的古代遺址奧林匹亞進行研究。在那里,德國考古工作者確實從1874年就開始了他們的田野工作,而這項工作迄今一直在持續進行。
溫克爾曼之后不到幾年的時間,丹麥哥本哈根國家博物館館長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湯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1788—1865)開創性地將當地的古物分別劃分到石器、青銅器和鐵器時代,這就是所謂的“三期論”。因為在湯姆森的故鄉沒有能同希臘和羅馬相媲美的“偉大”藝術,所以當時他的著眼點首先落在古代遺留至今的全部物質文化遺存上,諸如一些因不顯眼而未能引人注意的日常器具和首飾。
幾乎與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進化論(自1858年起)逐漸廣泛傳播的同時,人們在杜塞爾多夫附近的尼安德特峽谷(Neandertal)發現了奇特的、“頭骨扁平人種”的人骨化石(1856年)。然而,就連魯道夫·菲爾紹(Rudolf Virchow,1821—1902)這樣一位德國著名的、受到普遍公認的人類學家,當時卻肯定這些遺骨的年代不會十分久遠,并認為這些異常的骨骼是一個現代人由于疾病而造成的畸形。僅僅由于菲爾紹有崇高的聲譽,所以在學術界幾乎半個世紀沒人敢站出來糾正他的錯誤推斷,而事實上這一錯誤在不久之后就非常明顯了。
重大考古發現和激烈的學術辯論
許多學科在其發展初期都存在很多謬論和錯誤。值得慶幸的是,考古學很快就能將它們其中的一些擺脫掉,但最終往往還是剛糾正了舊的謬誤,接著又犯下了新的謬誤。受荷馬史詩的啟迪,自學成才的德國學者海因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就曾經步入過一個不小的誤區。1872年,他在特洛伊從事考古發掘時,發現了一批珍寶,并以為可以確認這批寶藏屬于傳說中的特洛伊國王普里阿摩斯(Priamos)。誠然,我們在這里必須公正地指出,以當時的考古研究水平,施利曼不可能知道這批寶藏的年代比他的推論實際上還要早近2000年。盡管如此,施利曼在發展考古地層學方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特洛伊,他首次揭開了各個不同時期相互疊壓的文化層。而且,施利曼使作為“鐵鍬科學”的考古學最終得到了大眾的廣泛認可。他在考古研究中,追求從整體出發,將發現的所有遺物和遺跡用來恢復古代歷史原貌——這是一種特別摩登的觀念。
一直以來,考古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學科內不斷激烈展開的學術辯論,有些甚至還大大牽動了公眾的情感。施利曼在特洛伊發掘的繼承人之一,一位過早去世的德國學者曼弗雷德·科夫曼(Manfred Korfmann,1942—2005)就有過這樣的親身經歷。科夫曼對他的研究結果進行了分析和判斷,認為這是證明特洛伊在青銅時代就擁有一座占地面積廣闊的下城的依據。而從施利曼就開始調查發掘的希沙利克(Hissarlik)山丘,實際上不是特洛伊古城的全部,那只是建在高處的衛城或城中心部分。這樣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特洛伊的看法。盡管有關下城建筑格局的證據還不是很充分,科夫曼卻像著了迷一樣,立即將一座青銅時代建筑稠密的大型城市的復原圖四處傳揚。像法蘭克·科爾布(Frank Kolb)這樣一些古代史學者,由于他們習慣于考證古史資料,并受過在理論基礎上建立學術概念的嚴格訓練,所以不能認同科夫曼的大膽判斷。科夫曼不久就覺得自己被打上了“考古學的德尼肯 [3]”的烙印。當然,在特洛伊衛城土丘腳下曾經有居民住過,這一點從考古遺跡上看是絕對不容置疑的。但是,科夫曼未能為他所判定的大型城址及時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所以學術界和公眾就不清楚,衛城以外的居住區究竟有多大的面積,房屋建筑是否稠密,是否可以將其視為“城市”,或者只是零星散布著一些宅院、建筑稀疏的村落式的市郊。從這件事上來看,我們可以總結出如下經驗,即在使用考古發掘結果給遺址定性時,對所使用的概念總要持十分慎重的態度。
自然科學改變著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很多學術觀點一旦被動搖,我們對它越是熟知和喜愛,考古學的學術爭論就會越加激烈。然而,任何學科的生存都依賴科學的進步和不斷地反省其學科成果。考古學引入新技術方法,有時也會給人帶來煩惱,比如放射性碳元素斷代方法。直到20世紀60年代,考古學者都是通過將史前文化與(已經進入有文字記載歷史時期的)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或希臘等同時期遺物的比對來進行絕對斷代的,因為這些文明國家已經擁有計算年代的歷法。這種遺物之間的聯系,有時要跨越幾千千米,因而并不總是十分可靠的。當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威拉德·利比(Willard Libby)1960年因發明了放射性碳元素斷代法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時,還沒有人能夠預想到,史前考古學正面臨著一場嚴峻的考驗。碳十四屬于碳元素中的一種放射性同位素,經過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并經過食物鏈被吸收到動物和人體中。因此,任何有機物質都可以通過其中碳十四的衰變換算成歷年而進行絕對斷代。這種方法的斷代結果將很多早期文化當時用傳統方法確定的年代提前了幾百年,由此徹底摧毀了學術界多年來辛辛苦苦勾畫出的一幅非常完整的“世界圖”。正是出于這種原因,碳十四方法幾十年來受到一些學者的堅決抵制,并由此掀起了學者之間的各種“學派”之爭。今天,這一切都早已過去了,大家在回顧這段往事時,都覺得當時的做法既奇怪又可笑。盡管碳十四方法斷代數值最終還需要進一步的糾正,但是這個方法的擁護者們實際上是正確的。然而,多年來有關方面的那些不幸的、非建設性的爭論,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考古學的進步。
值得慶幸的是,考古界接受新技術方法并不總是這樣艱難的。特別是以往的二十年,自然科學徹底改變了考古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考古學是人文科學中最能始終如一地將自然科學方法消化并融入其自身方法中的學科。考古獲取的知識不斷飛躍增長,從而使得我們今天能越來越生動地描繪出一幅古代歷史畫卷。在標本保存良好的前提條件下,利用樹輪法通過辨認樹木年輪可以精確地判定1.2萬年前遠古時期的木質遺物的具體年代。20世紀初期就已經出現了航空攝影考古學,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航空軍事偵察的產物,借助這種方法可以看到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遺跡。在地面上,步行者即便在這樣的遺址上走過,通常也不會發現遺址的任何蛛絲馬跡。同樣在考古中應用很廣的衛星影像,其實是冷戰的結果。蘇聯和美國一開始是利用衛星相互拍攝對方,后來漸漸地把世界的其他地方也都拍攝下來了。值得慶幸的是,這些圖片同時也記錄了大量古代遺址。今天,人們可以從網上下載析像率極高的衛星影像,從中能夠準確地辨別出各種遺跡,其析像分辨率可達到半米。
各種地球物理勘探方法運用到考古中,可以發現埋藏在地下的建筑墻基、灰坑或墓葬。今天,幾乎所有考古發掘都不會放棄這種前期勘察。土壤磷酸鹽分析可以界定人,特別是牲畜的排泄物(即糞便、尿)高度超常的地方,由此可以確定從前牲畜圈棚所在地和其他農村聚落遺址中各部位的功用。
體質人類學是研究人類體格發展的。同樣,形體學(有關外表體態)和古病理學(古人健康狀況)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早期人類的疾病、傷痛、食物營養特征、營養不良和生活習性等諸方面的信息。借助同位素分析可以研究有機體內放射性元素的衰變程度,從而得出人和動物在其一生中都在哪些地區活動過。古遺傳學則不僅提供人與人之間親屬關系的依據以及族群的同種化程度,而且在此期間,隨著采樣數目的不斷增加,甚至可以譜寫人口發展史。公元前6000年代,中歐的第一批農民不是由當地以采集和狩獵為生的中石器時代(約公元前10000—前7000)的土著居民形成的,而很可能是從東南歐遷徙來的移民。這方面考古界雖然以前就有過猜測,但是古遺傳學研究的進步才使這一推測得到科學的證實。
考古動物學和考古植物學的學者研究考古發掘出來的動物和植物的殘骸。這兩個學科不僅對研究古代經濟史有著重大的意義,而且可以推測出古代各個時期的植被和氣候環境。而自然科學考古主要為材料和金屬的分析提供方法,這對古代各個時期的礦山考古和與此相關的原材料的供給研究尤為重要。讀者可以自己評判一下,還有其他人文科學的學科如此大量借助于自然科學的嗎!
其實,考古學也時常為其他學科提供幫助,如地貌(即地球表面)的變化經常是根據考古遺跡來推算年代的。舉例來說,中亞的咸海(Aralsee)逐步干涸的各個階段,都可以借助考古遺址來相當準確地確定其時間。出乎意料的是,咸海的極端干涸不是一個當代才出現的情況,這種現象在中世紀就曾出現。不久前,由于湖水水位下降而使中世紀的遺址在曾經露出水面的地帶重新出現,而這些地帶被淹沒在水下已經有幾個世紀了。
處于各種世界觀辯論中的考古學
不管我們愿意與否,考古總是同政治脫不了干系。然而,一旦極權主義政權利用考古,為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粉飾其表面上看是歷史賦予的神圣使命的時候,就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和深思了。在德國,特別臭名昭著的是,20世紀初古斯塔夫·科辛納(Gustaf Kossinna,1858—1931)作為一名民族主義科學觀的先驅者所扮演的角色。他立論的出發點是,國家、民族、語言和物質文化之間是存在一致性的,而反過來便可以推導出,在一個清楚界定的地區之內,相同的物質文化就代表了一個民族。因此,科辛納以日耳曼民族曾經居住過的地區為依據,將德國領土的界定遠遠向東擴展到今俄羅斯南部,為日耳曼民族的神話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此基礎上,他為后來納粹政權罪惡的侵略戰爭提供了一個臆想出來的歷史緣由。和其他德國人一樣,那時古史學的學科代表,具體到這一實例也包括考古學的學科代表在內,都擔負起不可推卸的罪責。只有少數獨立意識強、有頭腦的人不追隨邪惡,不推波助瀾。他們或是在國內棄職而去,過隱居生活;或是移民出走,逃亡他國。
誠然,把考古變成政治工具,這種現象不僅只在德國存在。科辛納的一個非常有天賦的學生,波蘭人約瑟夫·科斯切夫斯基(Józef Kostrzewski),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用同樣的方法來證明德國戰敗后割讓給波蘭的領土從石器時代起就是波蘭的。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在1990年出兵科威特時,就是從古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Nebukadnezar)的光榮歷史來尋找理由和借口的。他本人總喜歡同這位使古巴比倫擺脫亞述控制而求得獨立的國王相比。無論以前還是現在,把歷史變成獨裁政權所使用的政治工具的契機,總是一脈相承、不會改變的。
今天,處在分崩離析中的伊拉克,只能回顧和反思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偉大歷史,這幾乎是唯一能維系這個國家的紐帶,因為今天的伊拉克人無論是種族還是宗教都存在很大的差異。我們時常發現,在國際上,尤其是那些偏僻和危機叢生地區的人們,都為他們古代文明的成就而自豪。引人注目的考古發現,即便是在偏遠地區也會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考古可以憑借其獲取的悠久歷史經驗,服務于今天和未來的改造和建設,特別是在同伊斯蘭世界對話中發揮作用。在這個過程中,考古學同政治和經濟在結構上的結合可以為解決當今世界的許多問題做出非常具體的貢獻。
比如在也門,德國考古工作者幾年前在一些地區從事考古發掘。那里的居民幾乎沒有任何生活保障,而且對未來的生活也不抱任何希望,也門從而變成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的溫床。德國考古工作者的考古發掘工作大大改變了當地的社會結構,并由此重新給當地人帶來了發展的前景。旅游基礎設施出現了,由此驟然間在各方面產生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如文物的保護及維修、旅游紀念品商店以及賓館和飯店等。之后不久,又建起了學校和醫院。在近東(Nahen Osten)這一最窮困、最落后的地區終于出現了一些有前途的苗頭。但這些已經過去一段時間了。今天,如果有人作為外國考古工作者在那些地方逗留,就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險。
盡管如此,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考古學不僅是一門引人入勝的科學,具有國際性和跨學科等特點,它時常以令人激動和振奮的方式來揭示古代的秘密。而且它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它能促使社會結構的改變。另外,當國際關系在政治上陷于僵持的時候,它可以作為國家之間對話的敲門磚。有時由于國家的政治主張,再加上某些社會群體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通過有意制造對外來文化代表的恐懼,而使情況復雜,這些都會加大考古領域國際合作的難度。例如,伊朗在1979年伊斯蘭宗教革命后,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時間,直到2000年德國考古學者才可以重新與他們的伊朗同事一起開展合作項目。我們所作的多方面努力、外交活動以及在各種接觸中對分寸的把握都得到了相應的回報,因為雙方最終都確信,我們所走的路是正確的。考古是增強雙方相互理解的一把重要的鑰匙,合作研究早期歷史的各個時期,了解人類的古代文化遺產——這些歷史時期在世界觀和意識形態上根本沒有或幾乎沒有歷史負擔。況且如果大家一起來做,可以超乎想象地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系。除此之外,無論以前還是現在,考古研究的中心都是人。考古要探索并重新復原幾千年前的人,努力理解其作為。考古正是要向今天的人傳達這些有關自己祖先過去的知識——考古工作者深信,對其他文化的認知,可以促進對它們的尊重和寬容。這才是真正要達到的人際關系目的,同時也是考古學今天的使命。考古不再是坐在象牙塔里做學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