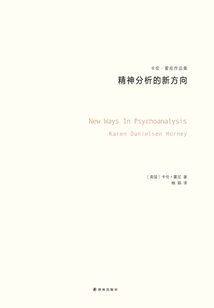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前言
我對當前心理治療結果不甚滿意,因而生出寫作此書的動機,在這本書里我將對精神分析理論做出批評,并重估其價值。我發(fā)現幾乎每一位患者,都會給我們提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以我們現有的精神分析知識似乎遠不足以解決。
一開始,我把這種迷惑歸咎于經驗不足,或有理解方面的盲點,就如大多數心理分析家一樣。我甚至忘了是如何纏著那些比我有著更多經驗的同事,向他們求教一些問題的。比如,弗洛伊德是如何理解“自我”的?或者,他們自己又是如何理解“自我”的?再比如,性虐狂沖動和“肛門‘力比多’”為何有著難以分開的內在聯系?如此之多的取向為何都被看作同性戀的潛在表現行為?可惜,直至現在我也沒有得到比較滿意的解釋。
讀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學概念時,我初次自發(fā)地對精神分析理論產生了懷疑。然后,又是因為讀弗洛伊德對死亡本能的假定,而令這種質疑更深。不過,我開始用批評的眼光思考精神分析理論,已經是幾年以后的事情了。
正如讀者將在整部書中看到的,你一旦陷入弗洛伊德那些逐漸發(fā)展完善起來的理論當中,將很難不被其左右,因為那些理論是如此地能夠自圓其說。只有當你對這些富有爭議性的理論了解之后——而整個體系都是在這些理論的基礎上建立的——你才能更清晰地認識到錯誤的根源,即各個具體理論是如何被埋下錯誤的種子的。我可以很坦率地說,我有資格在本書中對弗洛伊德的理論進行批評,因為十五年來我一直在用他的理論。
對于正統的精神分析,不僅是普通人,就是精神病專家也都有著莫名的反感。這并不單純是因為大家所認為的情感上的困惑,更是因為這些理論確實飽受爭議。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反對者們往往對精神分析全盤否定,不僅將精神分析中值得商榷的部分拋棄,甚至連那些可信的部分也棄之如敝履,另外,同時也否定了精神分析所能提供的真知灼見。我發(fā)現,對于精神分析理論越是抱著批判的態(tài)度,就越能認識到弗洛伊德基本原理的獨特建樹,理解心理問題的方法與道路也就越多。
所以,本書不是以挑剔精神分析的弊病為宗旨,而是力圖通過減少可爭議因素,使精神分析發(fā)揮出它的最大潛能。在不斷探求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我得出這樣的信心:如果我們能擺脫由歷史的局限性決定的理論基礎,并摒棄在此基礎上得出的理論,我們就可以將理解范圍拓展得更為寬廣。
總而言之,精神分析不應該只局限在本能和遺傳心理學的范疇內。就后者來說,弗洛伊德更傾向于把人們后期的怪癖看成是兒童時期欲望或反應的直接重復。他因此認為,若想消除后期的干擾,只需要闡明這種內在的兒童經歷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我們能夠放下這種偏見,不再一味地強調這種成因模式,那么我們就會認識到后期的種種怪異行為或癖好和早期經歷的關系,遠比弗洛伊德的想象更為復雜,說“孤立地重復已往的某些孤立的經歷”就更加不太可能了。無論何種性格結構,都是由兒童期所有經歷的整體所決定,而正是這種性格結構導致了以后的一些問題。因此,對性格結構的分析,要從實際出發(fā),要以現實為依據,這一點尤為重要。
對于現有精神分析的慣性傾向來說,如果把性格趨向與環(huán)境的改變相聯系,而不再看作本能沖動的最終結果,那么問題的重點就會落在塑造性格的生活環(huán)境上。事實上,我們不得不重新尋找導致精神沖突的環(huán)境因素,所以,精神神經質的主要根源,當是來自于人際關系的不和諧。在這種趨勢下,一種以社會學為主的定位模式,取代了以解剖生理學為主的定位模式。我們如果能夠站在另一個角度考慮,而排除片面的“力比多”理論中的愉悅原則,就會發(fā)現人對安全的追求顯然更為重要一些,正是基于對安全的追求,焦慮才會產生,因而我們對焦慮需要有新的認知觀念。可以說,造成精神神經質的原因,既不是俄狄浦斯情結,也不是兒童期的愉悅追求,而是令孩子感到無助、脆弱,覺得世界是存在有潛在威脅的所有的負面影響力。兒童因為害怕這種潛在的危險,為了獲得安全感,便要形成某種神經質的傾向來對抗這個世界。所謂的自戀傾向、受虐傾向或完美主義傾向,只是孩子們設法走出充滿未知危險世界的一種嘗試,而并非是由本能沖動所引發(fā)的。所以說,精神神經質所表現出的焦慮,并不是“自我”對本能沖動被壓倒的恐懼,也不是“自我”被假想中的“超我”所懲罰的頹喪,而是因為其特定的安全保護系統不能夠正常工作的結果。
在接下來的各章節(jié)中,我們將分別討論這些觀點的基本變化對精神分析具體概念的影響。這里我們可以先做一個大概的介紹。
首先,我們不再將性問題當作精神神經質的動因,盡管性問題有時確實是精神神經質的主要癥狀,但是與其說是性方面的困窘造成了精神神經質性格結構,不如說它是精神神經質的結果表現。
其次,道德問題將被格外重視起來。乍看,患者與人爭斗的道德問題只會把人引入死胡同,但必須澄清的是,這些只是呈現于表面的虛假的道德問題。患者應當正視每一種精神神經質所涉及的道德問題,并試著去解決它們。
最后,我們不再把“自我”視為實現或壓抑本能沖動的工具,如此一來,意志、評判和決斷等人類的能力將再次回歸其應有的地位。與此同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自我”將被看作一種神經質現象,而不再是普遍現象。我們不得不承認,精神神經質產生和延續(xù)的最主要根源,就是這種發(fā)乎本能的個人的自我扭曲。
因此,精神神經質實際上是當人陷入困境時所呈現出的一種特殊的求生方式,精神神經質的本質包括來自自我的,或來自他人的困擾,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各種沖突,我們把重點轉移到了造成神經質的根源的所在。這種轉移使得精神分析治療的任務大大放寬。幫助患者控制自己的本能不再是我們的宗旨,而盡量減輕他們的焦慮直到擺脫神經質傾向才是我們的新目標。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新的精神治療目標,就是幫助患者恢復自我,重新煥發(fā)他們的自發(fā)性,找到自己身上的精神重心。
有人說當作家創(chuàng)作一本書的時候,他自己才是這本書的最大獲益者。我很贊同這一說法,因為我確實感覺到自己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收獲良多。對于思想的必要性的系統闡述,已經令我所要闡述的思想清晰明了。至于能否令別人也開卷有益,我現在還不敢說大話。不過我想,和我一樣,很多精神分析者和精神病學家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對于眾說紛紜的各家觀點存有疑惑,不知它們到底是否正確。我并不期待他們能接受我的理論觀點,因為它們并不完整,而且也不是已臻成熟的最終形態(tài),更不是所謂的精神分析領域的“新學派”。我能做的只是把我的想法準確地傳遞給讀者們,讓他們來檢驗這些觀點的真?zhèn)巍N蚁M緯兄谀切┮試烂C的態(tài)度把熱忱置于將心理分析應用在教育、社會工作和人類學的人們,希望能夠幫助他們看清楚自己正在面臨的問題。最后,無論是精神病學者還是普通民眾,但凡拒絕把精神分析當作一種新奇而有待完善的理論結構的人們,我希望他們都能夠通過閱讀本書而對這門學科有一個全新的認知:精神分析有著內在的因果邏輯,是一門能幫助我們認識并理解自己的科學,也是一種了解他人的極富建設性的工具,具有非同尋常的應用價值。
當我對精神分析理論產生懷疑,對于它們的正確性不再篤定的時候,多虧有兩位同事及時地給予我鼓勵和啟發(fā)。他們就是霍洛德·舒爾茨-漢克和威爾漢姆·萊西。舒爾茨-漢克曾對孩童時期記憶的治療效果提出質疑,他強調有必要對沖突發(fā)生時的實際情境進行分析。雖然萊西當時正在潛心研究“力比多”理論,但他指出,應當首要分析神經質患者已經形成的防御型性格傾向。
相比而言,在我形成批判態(tài)度的過程中,其他因素對我的影響倒不是很大。我能了解弗洛伊德思想觀點的基本依據,要歸功于邁克斯·霍克海默的一些對于哲學概念的論著。這個國家向來有追求自由的傳統,這使得我在接受精神分析理論時可以有自己的選擇,正因為這樣,我才有勇氣沿著我認為正確的道路一路前行。除此之外,我熟悉了另一種文化,它在許多方面都與歐洲文化不同,我有幸意識到多數神經質沖突跟文化背景有著密切的關聯。艾力西·弗洛姆的著作又擴展了我在這方面的知識,他在他的講座或論文中每每批評弗洛伊德在文化定位方面的不足。同時,有關個體心理方面的問題,他也給了我新的啟發(fā)。然而令人嘆息的是,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弗洛姆先生尚未發(fā)表他對社會因素在心理學中的重要性的闡述,不然的話我就可以引用他的許多論證了。
我還要借此機會感謝承擔本書的編輯工作的伊麗莎白·托德小姐,她建議我如何更好地組織材料;另外,她的評論也非常具有建設性,這兩者對我的幫助都很大。我還要感謝我的秘書瑪麗·萊弗太太,她工作時從不懈怠,還給予我善意的理解和包容,對我來說這些都是異常珍貴的。最后我要感謝的是愛麗絲·舒爾茨小姐,她在英語理解方面對我?guī)椭艽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