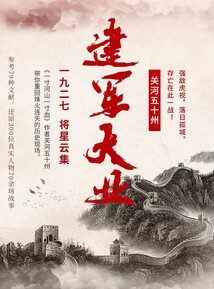
建軍大業(yè)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85評論第1章 力量大似天(1)
1927年3月21日上午,中共江浙區(qū)委秘書夏之栩像往常一樣,前去參加區(qū)委每天召開的碰頭會。路上她碰到了自己的愛人、同去開會的區(qū)委組織部長趙世炎,趙世炎興沖沖地對她說:“快點走,有好消息!”
果然,在隨后的會議上,區(qū)委書記羅亦農(nóng)宣布:北伐軍已于前一天晚上進抵龍華,上海工人今天要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配合北伐軍奪取上海!
大家聽了都振奮不已,散會后,立即分頭回去布置行動。
分手時,趙世炎特意提醒夏之栩,讓她趕快回宿舍一趟,通知“夏娘娘”(夏之栩的母親):“我們今晚都不能回去,戰(zhàn)斗何時結束何時回家,免得她老人家記掛!”
說完,趙世炎就直奔閘北總指揮部。在即將開始的武裝起義中,他必須在前線直接指揮作戰(zhàn)。
提起趙世炎,早期赴歐學習的共產(chǎn)黨人幾乎沒有不佩服的。聶榮臻由衷地說:“我們都很崇拜他。”蔡暢稱贊:“世炎和恩來全身都是聰明。”鄧小平則指出旅歐時期革命組織的領導者,第一是趙世炎,第二是周恩來。事實上,趙世炎在法國時任少共(即中國少年共產(chǎn)黨)總書記,地位確實在周恩來之上。
不能不承認,人的天分是有差別的。比如一起到莫斯科留學,同樣的時間,有的人只能說幾句日常用的俄語,俄語演說和講課根本就聽不懂,而有的人卻能將俄語說到和蘇聯(lián)人一樣溜。
趙世炎屬于后者。有一年他隨李大釗出席蘇聯(lián)大使館召開的紀念會,會上有好幾位不同國籍的外國友人登臺講話,趙世炎即席上場,一連擔任了俄、英、法三種語言的翻譯!
當時做翻譯不是事先擬好翻譯稿,照稿宣讀,而是人家講一段,要緊接著翻一段。趙世炎邊聽邊記,不但翻譯用詞清楚,而且語調(diào)生動有力,聽起來他好像不是在為別人翻譯,倒像是自己在做報告。與會者目睹此景,無不為趙世炎的才華所驚嘆。
革命家
那個時代的人們之所以常常愛把趙世炎拿來和周恩來比,當然是因為兩人在很多方面都有著驚人的一致性。他們的情商和智商都相當高,聶榮臻回憶旅歐時期的趙世炎,說:“接觸過他(指趙世炎)的,不管男女老幼都同他合得來。”
人的性格脾氣千差萬別,但不管哪一種類型,只要跟趙世炎打過交道的,都能和他成為朋友,甚至你只要和他接觸過一次,趙世炎就能在你心目中留下一個揮之不去的印象。
趙世炎在北方工作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一位同志前去找他。雙方之前從未謀面,然而令這位同志意想不到的是,當晚一開始的氣氛竟然就像老熟人重聚一樣。
在聊家常一般地問過對方的情況后,趙世炎說:“革命是偉大的事業(yè),但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需要艱苦,需要奮斗……”
當晚趙世炎的話并不多,可是卻已深深地打動了談話者,讓他堅定地相信趙世炎“是為革命而生,也會為革命而死”。
趙世炎身為中共北方區(qū)領導人,卻從不仗勢壓人,對部下、同事交代工作和解釋問題,總是不厭其煩地反復解說,有時即便他已經(jīng)做了決定,還是會拍拍接受任務者的肩膀,用親熱的口吻問道:“老弟,你看如何?”
在平時的工作中,趙世炎對每一個細節(jié)都考慮得極其周到,毫不馬虎,常說的一句話是:“有時候小問題和大問題同樣重要。”
有一次他到滬西開會,會后與滬西區(qū)工會負責人陳鈞同行。陳鈞手里拿著一張報紙,一般人不會注意這樣的細節(jié),但趙世炎注意到了,他馬上讓陳鈞把報紙收起來,因為在他看來,“這容易暴露身份,普通的市民是不會這樣關心時事的”。
當然,這也可以說是他長期從事地下工作所養(yǎng)成的習慣。為了適應危機四伏的秘密工作環(huán)境,趙世炎要經(jīng)常變換自己的裝束,他有時身穿褐色學生裝或長袍馬褂,拿一根手杖,脖子上還圍一條白綢圍巾,裝扮得和普通學生無異,但有時又穿得西裝革履,很像一個剛剛出洋歸來的留學生。
趙世炎行動機敏有急智。地下黨稱敵人的暗探為“泥巴”,最初大家對甩“泥巴”都缺乏經(jīng)驗,趙世炎在這方面則是個高手。他和大家一起開會,散會后總是笑著說:“我先走,把‘泥巴’帶走,免得麻煩你們。”
趙世炎還是個“工作狂”式革命家,除去工作,沒有別的任何愛好,尤其工作繁忙時,他的腦子在二十四小時之內(nèi)幾乎是不停歇的。
趙世炎一天里的睡眠時間很少,但差不多一睡下就滔滔不絕地說夢話,不是做政治報告,就是辯論問題。某日,他白天做了一個報告,有人聽后提出了不同意見,趙世炎記在心里,晚上說夢話時又重新做了一個報告,并且在報告中對不同意見做出了回應。
眾人見狀都很感動,第二天便開玩笑地對他說:“你晚上的報告比白天好!”
江浙區(qū)委的工作范圍包括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按照一位當事人提供的說法,中共在上海的工作曾經(jīng)非常薄弱,幾任領導都因能力不足或被降級或自動離職。直到羅亦農(nóng)從北方調(diào)來上海,上海的工作才走上正軌,其后隨著趙世炎來滬并出任區(qū)委組織部長,上海的工作變得更加有聲有色,逐漸步入了其歷史上的黃金時期。
趙世炎的長項之一是搞工運,組織工人罷工。上海工人一開始對參加罷工并不是都很積極,有一個工廠的工人就說:“阿拉工人命不好,再出頭不過是個‘土’,只有死了,埋在土里,才能出頭。”
趙世炎很懂得工人的心理,立即加以引導:“‘工’和‘人’加在一起就是天,工人團結起來力量大似天。”他還拿紡織廠的線打比方:“一根線可以拉斷,但是把線扭成繩子,織成布就拉不斷。”
經(jīng)過趙世炎的努力,這個廠很快就建立起了工會組織和糾察隊。
在大革命時期,趙世炎化名施英,那個時候在上海,很少有工人或市民不知道“施英”的。羅亦農(nóng)對趙世炎的才干也非常認可,曾經(jīng)評價說:“世炎能煽動,能工運。”
根據(jù)區(qū)委分工,羅亦農(nóng)主抓全面工作,工人運動由趙世炎、汪壽華負責,其中由趙世炎裁決重大問題,汪壽華主要處理上海總工會的日常事務。
在“羅趙汪”三駕馬車的驅(qū)動下,共產(chǎn)黨在上海終于成為了一支各方都不敢忽視的政治力量。
沒有起義的起義
大革命時代的起義也被報章稱為暴動,暴動一詞據(jù)說最早出處還是來自孫傳芳。
在孫傳芳嶄露頭角之前,北洋軍閥共有兩大派系,分別為吳佩孚的直系和張作霖的奉系,孫傳芳原屬直系,任浙江督軍。1925年秋,他托名“秋操”(即秋季的軍事演習),對控制江蘇和上海的奉軍實施突襲,之后幾乎沒有發(fā)生什么大的戰(zhàn)斗,就將奉軍驅(qū)出了南方。
孫傳芳至此據(jù)有了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號稱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同時他也從直系中分化出來,建立了北洋軍閥內(nèi)部除直奉兩系之外的另一重要派系。
這一事件曾引起共產(chǎn)黨人的極大關注。張國燾提議說:“下次上海發(fā)生戰(zhàn)爭,我們應有準備,把敗退士兵的槍械繳下來,自己武裝,再同得勝的軍閥說話。”
當時國共合作不久,北伐也尚未啟動,所以包括張國燾在內(nèi),誰都沒有想到這個“下次”已經(jīng)是北伐軍和北洋軍之間的戰(zhàn)爭了。
1926年9月,北伐軍攻入江西,孫傳芳急忙把主力部隊調(diào)至江西戰(zhàn)場,上海守備空虛,這就為國共同時創(chuàng)造了一個趁機予以奪取的天賜良機。受廣東國民政府的委派,國民黨代表鈕永建首先趕到杭州,與孫傳芳的部下、浙江省省長夏超秘密談判,將夏超爭取了過來。
10月中旬,夏超看到孫傳芳在江西屢屢敗北,便在杭州公開宣布獨立,歸附國民政府。這時國共也已達成初步協(xié)議,決定里應外合,聯(lián)合在上海發(fā)動起義。
按照各方事先商定的計劃,夏超將進兵上海。一俟夏軍逼近上海,共產(chǎn)黨方面即以工人糾察隊為基干,會同國民黨方面的便衣隊和商團,對上海駐軍實施襲擊,然后占領上海。
可是在后期直系中有悍將之稱的孫傳芳卻絕不是一盞省油的燈,他對夏超早有戒心。夏超派往上海的警備隊剛到嘉興,就敗給了孫傳芳從長江兩岸調(diào)來的軍隊。孫軍乘勝追擊,又占領了浙江,不久連夏超本人也被打死了。
由于通信條件較差,江浙區(qū)委未能及時得知夏超潰敗的消息。鈕永建雖然知道,卻又寄望于通過暗中游說的方式,讓上海駐軍將領效仿夏超,所以他并沒有把這一消息馬上告訴聯(lián)合起義指揮部,只是說時機不成熟,要推遲起義。
這個時候上海灘紛傳北伐軍已攻克九江(實際北伐軍攻克九江還是半個月后的事)。九江既下,就可對南昌實施包圍,說明江西戰(zhàn)事結束在即,孫傳芳已經(jīng)輸定了。江浙區(qū)委據(jù)此信心倍增,由趙世炎領導的準備工作也沒有因為國民黨方面不贊成而中止。
準備期間,趙世炎組織了兩千工人糾察隊員,但武器很少,沒槍的人只好帶一把斧頭。直至10月23日,原計劃中預定起義的那一天,應江浙區(qū)委的要求,鈕永建才從他的經(jīng)費中拿出一萬元,從黑市上為糾察隊買了一百支毛瑟槍。
糾察隊固然力量較弱,然而當時上海的孫部駐軍也僅有警察兩千、步兵一千,這讓江浙區(qū)委多少存有僥幸心理,認為只要冒險發(fā)動一下,再加上夏超兵臨城下,就可以迫使駐軍歸降或潰敗。
當晚,羅亦農(nóng)在鈕永建的寓所客廳里與之談判。到了下半夜,遠處忽然傳來炮聲,把客廳的玻璃窗都給震動了,鈕永建的臉色頓時一變。
原來,停在黃浦江的兩艘小型軍艦已為鈕永建所策動,按照原來的方案,軍艦會先開炮,以炮聲作為起義的信號。可是后來鈕永建又主張推遲起義,自然軍艦到時就不開炮了,令他沒想到的是,軍艦上有個下級軍官被地下黨說服了,這名軍官執(zhí)行江浙區(qū)委的命令,在預定時間過后,仍然偷偷地開了炮。
即便不問,鈕永建也知道是羅亦農(nóng)他們搞出來的,于是連聲責怪羅亦農(nóng),說這么大的事,為什么不預先通知他。到了此時,羅亦農(nóng)才從鈕永建嘴里得知夏超潰敗的消息。
幾乎在同一時間,趙世炎也從鐵路工人那里打聽到了這一消息。一時間,大家都急了,幾個區(qū)委負責人親自跑往各區(qū),分頭通知糾察隊停止起義。
卻說工人糾察隊一直在指定地點待命,等的就是軍艦開炮,但一等再等,等到下半夜兩點多,預定起義的時間早過了,還是沒有聽到炮聲。有人等得不耐煩,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沖了出去。
在區(qū)委下達停止起義的命令后,離區(qū)委較近的閘北立即停止了行動,但離區(qū)委較遠的浦東和南市早已行動起來,根本來不及制止。
其實在起義前夕,上海工人要發(fā)動起義的消息也已經(jīng)嚴重泄密,軍警早就有了準備,部分糾察隊員沖出去不久,便遭到反擊,至第二天凌晨,這次實際并沒有真正發(fā)動起來的起義以失敗告終。
一心三用
在第一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中,共有百余名工人被捕,十余人犧牲。報紙詳細登載了犧牲者被捕、審判和就義的經(jīng)過,犧牲者當中的共產(chǎn)黨員都說自己是國民黨員。這是因為自從國共合作后,共產(chǎn)黨員便都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對外也以國民黨的政治面貌出現(xiàn)。
這一情況在共產(chǎn)黨內(nèi)部引起了反思。瞿秋白看報后感慨地說:“俄國同志當初受刑時,還能慷慨承認自己是布爾什維克,中國同志則連這個權利也沒有!”
作為起義的具體領導者,趙世炎對此更為痛心,試想一下,若是鈕永建不藏著瞞著,早一點把夏超潰敗的消息告訴區(qū)委,區(qū)委又何至于冒著風險貿(mào)然發(fā)動起義,乃至蒙受如此大的損失?
在區(qū)委會議上,趙世炎承認“我們不免太幼稚”,作為教訓,他提出以后不應對國民黨過度依賴,“對鈕永建的繼續(xù)關系要減少,要以秘密的方式對付他,不要像這次專受他的最后決定”。
與此同時,他也檢討起義準備期太短以及發(fā)動不夠等問題,認為即便夏超不潰敗,從“淺薄的準備”和“時機的錯誤”上看,起義仍難以取得成功,或即便一時成功亦難以支持太久。
知恥而后勇,趙世炎又進一步給自己上緊了發(fā)條,成了“超級工作狂”。他日夜奔走、開會、寫文章、調(diào)查研究、個別談話,每天都忙個不停,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夏之栩經(jīng)常在半夜醒來,還看到丈夫在燈下寫東西。有時,趙世炎甚至一連幾天都不眠不休,實在累得不行,就利用開會前等人的時間休息幾分鐘,人員一到齊,便又揉揉眼睛,重新開始工作。
趙世炎原本身體健壯,精力充沛,但這樣超負荷地連軸轉,縱使鐵打的金剛也會感到吃不消。為此,他除了在工作中用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煙來提神外,還常常同時進行幾項工作。
上海工人史照華第一次見到趙世炎時,他正在和羅亦農(nóng)、汪壽華討論問題。史照華看到他一邊嘴上說著,一邊手上還在不停地寫文章,同時又在聽取一個關于鐵路工運的情況匯報。
古人說,一心不能二用,趙世炎是“一心三用”,而且在短短的時間里,他竟然把來自不同方面的幾個問題都圓滿解決了。這讓史照華感到十分驚訝,覺得趙世炎“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其他人亦有同感,說:“施英同志(趙世炎的化名)真了不起,他在同一個時間能做三件事。”
至1927年1月,上海總工會領導下的組織已達一百八十七個,比上年9月增加了一倍,會員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總工會還增設了經(jīng)濟斗爭部和糾察總指揮部,后者主要用于加強對糾察隊的軍事訓練。
軍事訓練的地點一般都設在工廠附近的荒地上,為了掩人耳目,白天不進行操練,只利用晚上秘密進行。各糾察隊有槍的直接練習射擊,暫時沒槍的就拿著用竹頭做成的刀槍,練習立正、稍息和一些簡單的列隊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