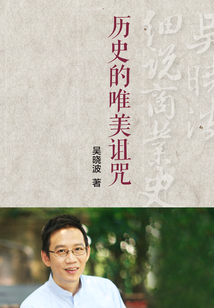
歷史的唯美詛咒(吳曉波細(xì)說商業(yè)史03)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8評(píng)論第1章 歷史名商
靠“周期”成為首富
為商之道關(guān)鍵在于認(rèn)識(shí)周期,同時(shí)善于運(yùn)用周期,在這方面,范蠡無疑是一位世界級(jí)的先覺者。
講周期,是因?yàn)槿魏我粋€(gè)企業(yè)都是生存在三個(gè)周期之中——一是宏觀波動(dòng)周期,二是產(chǎn)業(yè)成長周期,三是企業(yè)生命周期。對(duì)三個(gè)周期的了解及其對(duì)應(yīng),是企業(yè)戰(zhàn)略是否有效的前提之一。那么對(duì)于個(gè)人來說,對(duì)這些周期的掌握,也是成功的關(guān)鍵之一。古往今來,所有在商業(yè)上得大成就者,無一不是掌握了周期規(guī)律的人。
在中國企業(yè)史上,第一個(gè)靠了解周期來從事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人,就是范蠡。范蠡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紀(jì)的春秋末期,在有文字記載的中國商業(yè)史上,他是第一個(gè)被看成首富的人,他的另外一個(gè)名字叫“陶朱公”,這已經(jīng)成了大富豪的代名詞。范蠡的天才之處,就是發(fā)現(xiàn)了周期的存在。
經(jīng)濟(jì)周期是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名詞。為商之道關(guān)鍵在于認(rèn)識(shí)周期,同時(shí)善于運(yùn)用周期,在這方面,范蠡無疑是一位世界級(jí)的先覺者。
他是一位天文學(xué)家,在越國主政時(shí)曾籌建了有史以來第一個(gè)高46丈的觀象臺(tái)。他將天文運(yùn)行與農(nóng)業(yè)豐歉進(jìn)行了周期性研究,并據(jù)此預(yù)測商品供求及價(jià)格的周期性變化趨勢,形成經(jīng)營的策略。他說:“歲星(木星)運(yùn)行到金的位置時(shí)是豐收年,在水位時(shí)是澇災(zāi)年,在木位時(shí)可能有饑荒,在火位時(shí)則是大旱之年。每隔六年有一次豐年、一次平年,每隔十二年出現(xiàn)一次大饑荒。”這里將古代天文知識(shí)與五行學(xué)說結(jié)合起來,認(rèn)為“歲星”即木星在十二年間分別經(jīng)過金、木、水、火等方位而繞太陽一周期,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由豐年到災(zāi)年的一個(gè)周期是相吻合的。
當(dāng)掌握了農(nóng)業(yè)豐歉周期之后,范蠡提出了自己的戰(zhàn)略,他說:“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就是說,只要搞清楚哪些商品是供過于求的,哪些商品是供不應(yīng)求的,就可以知道哪些商品價(jià)格要下跌、哪些商品價(jià)格要上漲——“即知貴賤”。他已認(rèn)識(shí)到,由于市場供求對(duì)生產(chǎn)的影響和調(diào)節(jié),供不應(yīng)求的商品上漲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給的增加和需求的減少,商品價(jià)格就會(huì)下跌——“貴上極則反賤”;反之,供過于求的商品下跌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給的減少和需求的增加,商品價(jià)格又會(huì)回升、上漲——“賤下極則反貴”。換言之,他已從現(xiàn)象上認(rèn)識(shí)到,由于供求關(guān)系的影響,商品的價(jià)格會(huì)圍繞其價(jià)值而上下波動(dòng)。
且不論這一周期性總結(jié)發(fā)現(xiàn)是否完全符合科學(xué),范蠡能夠以長期循環(huán)波動(dòng)的眼光看待客觀世界,無疑已是非常卓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從來就有靠天吃飯的特征,范蠡從氣候和自然條件的變化來探求農(nóng)業(yè)豐歉的周期性循環(huán)規(guī)律,以此掌握未來不同年份的農(nóng)產(chǎn)品尤其是糧食產(chǎn)量的增減趨勢,他能富冠天下,便不是意外的事情了。
在掌握了周期性規(guī)律之后,范蠡提出另外一個(gè)重要的商業(yè)思想,就是“待乏”。所謂“夏則資皮,冬則資,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夏天的時(shí)候要儲(chǔ)備皮毛,冬天的時(shí)候要囤積薄紗,大旱之時(shí)就去造船,澇災(zāi)之時(shí)就去買車,一切都需提前準(zhǔn)備,等待貨物缺乏的時(shí)候,就可獲取百倍、千倍之利。
囤積居奇,自能獲取利潤,但又不可以賭博式地追逐暴利,“貨無留,無敢居貴”——手中的貨物不應(yīng)該讓它久留,不要貪婪地追求過分的高價(jià)。所以,在“待乏”的同時(shí),范蠡還強(qiáng)調(diào)薄利多銷,加快資金的流動(dòng),這樣才能獲得長久的利益。
范蠡的這些商業(yè)思想,百世以降仍然不覺陳舊,將之用于治國,國家可興盛,將之用于治家,家庭可富足,“陶朱公”之所以成為富豪者的代名詞,顯然不僅僅因?yàn)樨?cái)富之多寡,更在于他智慧之高超。
到《全唐詩》里尋找商人
從先秦到南北朝,以商人之“賤”,其形象很少出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之中。而入唐之后,大有改觀。
公元815年,時(shí)年44歲的大詩人白居易被貶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出任司馬一職。第二年的深秋月夜,他到城郊的湓浦口送別友人,突然聽到一艘舟船上有人彈奏琵琶,美妙若天籟之音。他陡發(fā)感懷之情,因作一首長詩相贈(zèng),這就是流傳千古的《琵琶行》。
彈奏之女原本是長安城里的歌妓,此時(shí)則是一位茶商的妻妾。其中關(guān)于那位茶商的詩句有四節(jié),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商人入唐詩,這不是第一首,卻是最出名的,當(dāng)然其形象也是最經(jīng)典的——“商人重利輕別離”。從先秦到南北朝,以商人之“賤”,其形象很少出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之中。而入唐之后,大有改觀,經(jīng)商活動(dòng)及商人生活、心態(tài)成為了描寫的主體。有人做過一個(gè)粗略的統(tǒng)計(jì),唐代的商賈詩約203首,大約是唐以前商賈詩總量的100倍,涉及的詩人共90人。
在這些唐詩中,商人形象大抵有四:
辛苦勞頓——把商人視為一個(gè)正當(dāng)職業(yè),同情他們的謀生艱辛,這是唐人與前代最為不同的地方。白居易有詩曰:“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諳。雪霜行塞北,風(fēng)水宿江南。藏鏹百千萬,沉舟十二三。”黃滔作詩《賈客》,把經(jīng)商比作如在鯨鯢牙齒上行走,艱險(xiǎn)非同尋常:“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jīng)過。”
忙于逐利——追逐利益是商人的職業(yè)本性,唐詩對(duì)經(jīng)商活動(dòng)中的細(xì)節(jié)多有描述。
元稹寫長詩《估客樂》,對(duì)商人的為利而行、以次充好、六親不認(rèn)等等行跡進(jìn)行了細(xì)致描寫,詩中寫到:“估客無住著,有利身則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無不營。火伴相勒縛,賣假莫賣誠。交關(guān)但交假,本生得失輕。自茲相將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頭語,便無鄰里情。”
勾結(jié)權(quán)貴——詩人對(duì)官商勾結(jié)進(jìn)行了揭露,表達(dá)了極大的憤怒。
元稹在《固客樂》中描寫商人以“奇貨通幸卿”,“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主第,點(diǎn)綴無不精”,此外還行賄市卒、縣胥,使他們對(duì)商人“豈唯絕言語,奔走極使令”。從這些詩句中可見,大商賄賂大官,小賈賄交小官,從兩京到地方均極盛行,以致州縣差科盡歸貧下,為弊之深,由此可見。高適有一首《行路難》,寫官商勾結(jié)尤為著名:“君不見富家翁,舊時(shí)貨賤誰比數(shù),一朝金多結(jié)豪貴,萬事勝人健如虎。”
奢侈消費(fèi)——詩人們描寫了商人的奢靡生活和貧富不均的社會(huì)現(xiàn)象。
劉禹錫在《賈客詞》一詩中寫了商人的巧取豪奪之后,繼而描寫其生活的奢華:“妻約雕金釧,女垂貫珠纓。高貲比封君,奇貸通倖卿。趨時(shí)鷙鳥思,藏鏹盤龍形。大艑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關(guān)梁自無征。”施肩吾的《大堤新詠》則描寫了商人在長江大堤沿岸城市尋花問柳的景象:“行路少年知不知,襄陽全欠舊來時(shí)。宜城賈客載錢出,始覺大堤無女兒。”
唐代詩人豁達(dá)天真,觸景皆可入詩,生情俱能成句,從他們的詩句中透露出大量的社會(huì)實(shí)景。開元年間,國力昌盛,工商繁茂,生活在這一時(shí)期的詩人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經(jīng)商風(fēng)尚多有詠誦,李白詩云:“云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
進(jìn)入中唐之后,民間經(jīng)商之風(fēng)更為盛行,元和詩人姚合有詩記錄他在長安城郊所見的景象:“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貞元詩人盧綸有詩記他的友人從軍隊(duì)退役后的生活:“全身出部伍,盡室逐漁商。”也就是說,舉家從賈、全村經(jīng)商的情況在唐代已經(jīng)不再罕見。
朱元璋怎樣搞“穩(wěn)定”?
也是從此之后,在長達(dá)400年的漫長時(shí)間里,中國成為一個(gè)與“世界公轉(zhuǎn)”無關(guān)的、“自轉(zhuǎn)”的帝國。
朱元璋,乞丐出身,當(dāng)上皇帝是在1368年。此前的200多年,漢人受盡了外族的壓迫和侵略,先是南宋偏安百余年,再是蒙古人統(tǒng)治98年。所以,當(dāng)上皇帝后,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讓國家穩(wěn)定下來。
在物理學(xué)上,一個(gè)物體要達(dá)到“穩(wěn)定”的狀態(tài),有兩種實(shí)現(xiàn)途徑,一是在動(dòng)態(tài)中實(shí)現(xiàn),一是在靜態(tài)中實(shí)現(xiàn)。朱先生向往的是第二種狀態(tài)。
當(dāng)一個(gè)統(tǒng)治者想要通過靜止的方式實(shí)現(xiàn)穩(wěn)定,他就會(huì)很自然地接著想——影響“穩(wěn)定”的因素到底有哪些?答案是有兩個(gè),一是外患,一是內(nèi)憂。控制前者的最可靠的辦法是杜絕對(duì)外的一切交流,與各國“老死不相往來”;實(shí)現(xiàn)后者的辦法,則是讓人民滿足其溫飽而民間財(cái)富則維持在均貧的水準(zhǔn)上。
朱元璋確實(shí)也是這么做的。明朝從創(chuàng)建之初起就推行對(duì)外封閉的政策,具體而言,就是“北修長城,南禁海貿(mào)”,把帝國自閉為一個(gè)鐵桶。
在北方,為了防止蒙古勢力的卷土重來,明朝修筑了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guān)的萬里長城,全線劃分為9個(gè)防備區(qū),由重兵駐守,時(shí)稱“九邊”,這些邊關(guān)成為被官府嚴(yán)密管制起來的邊貿(mào)集散地。從此,自漢唐之后就綿延不絕的“絲綢之路”日漸堵塞,中國與歐洲的大陸通道上駝馬絕跡、鴻雁無蹤。
在南邊,朝廷下令禁止民間出海,朱元璋在登基的第四年,1371年12月,就下達(dá)了“海禁令”——“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直到1492年,明朝索性宣布“閉關(guān)鎖國”,而正是在這一年,哥倫布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
在對(duì)內(nèi)政策上,朱元璋大力倡導(dǎo)“男耕女織”。在他的理想中,一個(gè)完美的帝國就應(yīng)該是無貧無富的小農(nóng)社會(huì),“男力耕于外,女力織于內(nèi),遂至家給人足”,每個(gè)人都安于眼前,如鄉(xiāng)野之草,自生自滅,帝國將因此綿延百世,千秋萬代。為了建設(shè)這個(gè)“人間桃花源”,他剪滅了天下豪族,然后在“耕”和“織”兩個(gè)產(chǎn)業(yè)上進(jìn)行重大的變革,逐漸形成了一個(gè)以小自耕農(nóng)為主的農(nóng)耕經(jīng)濟(jì)。
也是從此之后,在長達(dá)400年的漫長時(shí)間里,中國成為一個(gè)與“世界公轉(zhuǎn)”無關(guān)的、“自轉(zhuǎn)”的帝國。而正是在這400多年里,西方社會(huì)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紀(jì),由自由民組成的新興商業(yè)城市成為歐洲的新希望,一場以“文藝復(fù)興”為主題的啟蒙運(yùn)動(dòng)拉開了帷幕。同時(shí),北歐和西歐各國開始海外大冒險(xiǎn)。在政治革命、科學(xué)革命和工業(yè)革命的綜合推動(dòng)之下,“世界時(shí)間”的鐘擺終于從東方猛烈地?fù)u向西方。
如果從靜態(tài)的角度來看的話,朱元璋所追求的“穩(wěn)定”,是一種效率與管理成本同步極低的社會(huì)運(yùn)行狀態(tài),若沒有外來的“工業(yè)革命”的沖擊,竟可能是中國歷史的終結(jié)之處。
黃仁宇便論述說,“在明代歷史的大部分時(shí)期中,皇帝都在沒有競爭的基礎(chǔ)上治理天下。在整個(gè)明代,都沒有文官武將揭竿而起反對(duì)國家。此外,普通百姓對(duì)國家的管理不當(dāng)極為容忍……由于這些條件,王朝能以最低的軍事和經(jīng)濟(jì)力量存在下來,它不必認(rèn)真對(duì)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優(yōu)勢,而是因?yàn)闆]有別的對(duì)手替代它。”
黃仁宇所謂的“替代的對(duì)手”,僅僅是站在競爭的角度觀察,而如果從制度的角度來看,又存在兩種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繼續(xù)延續(xù)明帝國的模式,讓社會(huì)在靜止的、超穩(wěn)定狀態(tài)下緩慢地“自轉(zhuǎn)”;其二,則是出現(xiàn)一種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將之徹底地推翻并更換之。這兩種狀況后來都發(fā)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現(xiàn)在1644年,而第二次則出現(xiàn)在遙遠(yuǎn)的1911年。當(dāng)然這些“后話”,在今天的我們看來,一定也不陌生。
誰是中國的杰克船長?
在正統(tǒng)的中國經(jīng)濟(jì)史上,從來沒有為海盜留一席之地。然而,正是非法的海盜活動(dòng)造就了南太平洋地區(qū)的貿(mào)易繁榮。
《加勒比海盜4》中德普扮演的杰克船長迷倒了一堆人。走出影院,就想著要寫這篇專欄:誰是中國的杰克船長?
中國歷史上海盜最盛的是明朝。朱元璋開國之后,就頒布了海禁令,1492年之后更是強(qiáng)調(diào)“片木不得下海”,當(dāng)海外貿(mào)易的正常渠道被全面封殺之后,非法的海盜事業(yè)就變得十分蓬勃且難以遏制。種種史料顯示,從15世紀(jì)到19世紀(jì)末的400多年里,跨越明清兩代,南中國海是全世界海盜最為盛行的地區(qū)之一,極盛時(shí)多達(dá)15萬人。
明中期,最出名的海盜是一群來自徽南的商人。最早在江浙東南沿海從事走私的是歙縣人許辰江、許本善等。嘉靖初年,歙縣許村的許家四兄弟組成了一個(gè)勢力龐大的海盜集團(tuán),他們以寧波附近的雙嶼島為基地,把商品販銷到了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到了嘉靖中期,許氏集團(tuán)被擊潰,其部下、同樣是歙縣人的汪直起而代之。
除了徽商背景的海盜之外,另外一個(gè)人數(shù)龐大的走私集團(tuán)來自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帶。這些中國籍的海盜與日本浪人糾結(jié)在一起,成了讓明政權(quán)頭痛不已的倭寇之禍,他們游弋于浙閩沿海,有商機(jī)則交易,乘人不備則劫掠。嘉靖年間的抗倭名將胡宗憲寫道:“倭寇與海商其實(shí)是同一個(gè)人,如果開放海禁,倭寇就轉(zhuǎn)身變成了海商,如果實(shí)施海禁,海商就立即變成了倭寇。”
到了明后期,最出名的海盜集團(tuán)是鄭氏家族,父親叫鄭芝龍,兒子名氣更大,叫鄭成功。
鄭芝龍會(huì)講日語和葡萄牙語,與荷蘭人非常熟悉,他還皈依了天主教,教名尼古拉。他原本是海盜李旦的部下,李死后,繼承了他的地盤和勢力,經(jīng)過數(shù)年的攻伐和機(jī)緣巧合,成為南中國最強(qiáng)悍的海盜集團(tuán)。1624年,明廷不得不采取招安政策,任命鄭芝龍為“五虎游擊將軍”,此時(shí),鄭芝龍有部眾3萬余人,船只千余艘。在后來的幾年里,鄭芝龍掃蕩各路海盜,成了唯一的海上霸王。他除了從事走私之外,還向其他商船征收保護(hù)費(fèi),史載:“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三千金,歲入以千萬計(jì),以此富敵國。”
清軍入關(guān)之后,鄭芝龍先是擁立唐王稱帝于福州,受封平虜侯、平國公,掌握軍政大權(quán)。旋即清軍入閩,他又投降了清朝。而他的18歲的兒子鄭成功卻率部出走金門,在其后的15年里,成為最重要的反清勢力。1661年,鄭成功擊敗了占據(jù)臺(tái)灣島的荷蘭人,收復(fù)寶島。
在抗擊清軍的十余年中,鄭氏集團(tuán)仍然牢牢控制了東南沿海的外貿(mào)事業(yè),清政府為了切斷其財(cái)源,三度頒布“遷界禁海令”,實(shí)施了嚴(yán)酷的禁海政策。到1683年,清軍收復(fù)臺(tái)灣,兩年后宣布開海貿(mào)易,隨后又確立了“一口通商”的政策,此后近200年間,再?zèng)]有出現(xiàn)像汪直集團(tuán)和鄭氏集團(tuán)那樣龐大的海盜勢力。
在正統(tǒng)的中國經(jīng)濟(jì)史上,從來沒有為海盜留一席之地。然而,近世史料發(fā)現(xiàn),自16世紀(jì)之后,正是非法的海盜活動(dòng)造就了南太平洋地區(qū)的貿(mào)易繁榮。據(jù)嚴(yán)中平研究,從1550年到1600年前后,海盜商人把大量商品販運(yùn)到馬尼拉,進(jìn)而通過西班牙商人遠(yuǎn)銷到歐洲和美洲。
與此同時(shí),海盜商人還把出產(chǎn)于日本和墨西哥的白銀大量運(yùn)回中國市場。根據(jù)計(jì)算,明朝由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為1.7億兩,西屬美洲流向中國的白銀為1.25億兩,合計(jì)2.95億兩。嚴(yán)中平因此認(rèn)為:“實(shí)際上,中國對(duì)西班牙殖民帝國的貿(mào)易關(guān)系,就是中國絲綢流向菲律賓和美洲,白銀流向中國的關(guān)系。”
海盜經(jīng)濟(jì)是中國經(jīng)濟(jì)歷史上十分重要而隱晦的一頁,如果我們要為海盜商人設(shè)立一座紀(jì)念碑,確乎很難找到合適的代表人物,也無法用簡單的文字來記錄他們的功過。
一位你不知道的中國首富
伍秉鑒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他誠實(shí)謙順的經(jīng)商個(gè)性以及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密切關(guān)系。然而,他對(duì)鴉片泛濫難辭其咎。
亞洲《華爾街日?qǐng)?bào)》曾經(jīng)選出過去一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中國有六個(gè)人入選,分別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伍秉鑒和宋子文。此六人中,有五位大家都比較熟悉,只有伍秉鑒,知道的人很少。今天說說他。
伍秉鑒是六人中唯一的商人。清朝自乾隆之后,只允許廣州“一口通商”,并以特許經(jīng)營的方式讓十多家洋行壟斷其事,伍家就是特許商人之一。伍氏之富聞名天下,1834年,他對(duì)自己的各種財(cái)產(chǎn)進(jìn)行了粗略統(tǒng)計(jì),共約2600萬元。當(dāng)時(shí),清帝國一年的財(cái)政收入為8000萬元左右,伍氏之富可以想見。
伍家并非老字號(hào)的洋行世家,他的父親曾是潘家同文行的賬房先生,后來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自立門戶,自創(chuàng)怡和行。伍秉鑒在32歲時(shí)繼承父業(yè),歷二十余年,終于成為行商的總商。他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二,一是誠實(shí)謙順、敢于吃虧的經(jīng)商個(gè)性,二是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密切關(guān)系。
流傳至今的伍秉鑒故事,大多與“吃虧”有關(guān)。1805年,一家外國商號(hào)按照約定運(yùn)到廣州一批棉花,貨到港后發(fā)現(xiàn)是陳貨,行商們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鑒卻收購了這批棉花,也因此虧了1萬多元。
還有一次,一位欠了伍秉鑒7.2萬銀元的美國波士頓商人,因?yàn)榻?jīng)營不善無力償還債務(wù),欠款在身,離家多年卻不能回國,伍秉鑒撕掉了借據(jù),讓他放心回國。
這些小故事讓西方人印象深刻,他們稱伍秉鑒“在誠實(shí)和博愛方面享有無可指摘的盛名”。當(dāng)時(shí),行商與外商的交易雖然數(shù)額巨大,但全憑口頭約定,從不用書面契約,人格信用自然成了做生意最重要的前提。
伍秉鑒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交情延及父輩,雙方都在長期貿(mào)易中獲得了最大利益。而他的衰落與林則徐禁煙有關(guān)。1839年,朝廷委派林則徐南下禁煙。此刻,夾在政府與洋人之間的,就是伍秉鑒。
后世學(xué)界一直有爭論,洋行商人、特別是伍秉鑒的怡和行到底有沒有參與到鴉片生意之中。從史料上看,怡和行向來做的是茶葉貿(mào)易。然而,也有資料顯示,伍秉鑒和怡和行對(duì)鴉片泛濫難辭其咎。
當(dāng)時(shí)廣州地區(qū)最大的兩個(gè)鴉片走私商是英國寶順洋行和美國旗昌洋行,前者屬于英國東印度公司,后者的老板是伍秉鑒的義子、美國人約翰·福布斯,伍家在旗昌洋行中擁有60%的股份。以伍秉鑒的精明,不可能不知道他最親密的商業(yè)伙伴在從事非法業(yè)務(wù)。
早在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擔(dān)保的美國商船私運(yùn)鴉片被官府查獲,伍秉鑒被迫交出罰銀16萬兩,其他行商被罰5000兩,罰金相當(dāng)于鴉片價(jià)值的50倍。
由這些細(xì)節(jié)看,怡和行即便沒有直接參與鴉片業(yè)務(wù),也至少起到了掩護(hù)和包庇的作用。或許,商人的賺錢本能以及性格中的懦弱一面,是事實(shí)的真相。
從禁煙的第一天起,林則徐就把洋行商人看成了煙商的同謀。他認(rèn)定寶順洋行的英國老板顛地“誠為首惡,斷難姑容”,下令傳訊他“聽候?qū)忁k”。而顛地也非常強(qiáng)硬,竟然提出要林則徐頒發(fā)親筆護(hù)照擔(dān)保他能24小時(shí)內(nèi)回來作為條件。盛怒之下的林則徐當(dāng)即派人鎖拿伍秉鑒的兒子伍紹榮,將他革去職銜,逮捕入獄。伍秉鑒派人前去說情,林則徐斷然拒絕說:“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
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主持了震驚世界的虎門銷煙,共銷毀鴉片兩萬余箱。隨后,義律訴諸武力,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因此爆發(fā)。
1843年9月,一代首富伍秉鑒在內(nèi)憂外患和責(zé)備辱罵聲中去世,終年74歲。在此前幾個(gè)月,他還寫信給在馬薩諸塞州的美國友人J.P.庫森說,若不是年紀(jì)太大,經(jīng)不起飄洋過海的折騰,他實(shí)在十分想移居美國。
110年前的那個(gè)“裱糊匠”
反思那一段歷史,我們必須說,精英階層對(duì)傳統(tǒng)文明的過于自信以及對(duì)制度重構(gòu)的漠視成為中國近代化進(jìn)步的最大障礙。
本文紀(jì)念一位百年前的風(fēng)云人物。
1901年11月7日,當(dāng)時(shí)中國政壇最重要的政治家李鴻章殞于北京城郊的賢良寺,據(jù)說,臨終時(shí)“雙目猶炯炯不瞑”。屈指一算,這是整整110年前的事情了。
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少年時(shí)才情萬種。1842年夏,弱冠之年的他赴京趕考,是年,中英《南京條約》剛簽署,少年李鴻章心憂國難,做《入都》一闋,詩內(nèi)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時(shí)傳誦京城。
1851年,南方爆發(fā)太平天國運(yùn)動(dòng),李鴻章隨曾國藩起兵,由一介儒生而成領(lǐng)軍十萬的一方統(tǒng)帥。之后他又力促洋務(wù)運(yùn)動(dòng),成為中國近代化變革的中流砥柱。早在1864年5月,時(shí)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就在一份奏折中提出要學(xué)習(xí)西方,同時(shí)他還試圖修改千年科舉制度的取士標(biāo)準(zhǔn),在當(dāng)時(shí)十分驚世駭俗。
李鴻章一生辦了很多洋務(wù),回望百年工業(yè)化,他應(yīng)該是第一個(gè)不能忘記的人物。不過,李鴻章一輩人也有很大的局限,那就是,他們始終認(rèn)定中國之落后只在“物器”而已,以為只要有了先進(jìn)的“火器”,中國便可爭勝于天下。
李鴻章等精英階層的這些觀念與同時(shí)代的日本人形成鮮明之對(duì)照。就在李鴻章、曾國藩等人大搞洋務(wù)運(yùn)動(dòng)的同時(shí),日本也開始了明治維新。在一開始,日本的改革家們也曾預(yù)想用“西方的學(xué)識(shí)、日本的精神”作為日本變革的方式。然而,在對(duì)西方各國進(jìn)行一番考察之后,他們意識(shí)到,“這樣的公式與實(shí)行近代化是相背離的”。
明治維新的代表人物伊藤博文便認(rèn)定說:“國家富強(qiáng)之途,要在二端,第一開發(fā)國民多數(shù)之智德良能,使進(jìn)入文明開化之域。第二使國民破舊日之陋習(xí),不甘居被動(dòng)地位,進(jìn)而同心協(xié)力于國家公共事務(wù),建設(shè)富強(qiáng)之國家。”
李鴻章對(duì)伊藤博文的這些觀點(diǎn)非常不以為然,多年嘲笑之。在各自的國家中,兩人聲望與地位相同;在私人交情上,他們“亦友亦敵”,惺惺相惜。反思那一段歷史,我們必須說,精英階層對(duì)傳統(tǒng)文明的過于自信以及對(duì)制度重構(gòu)的漠視成為中國近代化進(jìn)步的最大障礙。其實(shí),直到今天,李氏與伊藤氏的分歧仍然在中國存在。
李鴻章的晚年,過得苦風(fēng)凄雨,他對(duì)自己作如下總結(jié):“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shí)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qiáng)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shí)。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bǔ)西貼,居然成一間凈室,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fēng)雨,打成幾個(gè)窟窿,隨時(shí)補(bǔ)葺,亦可支吾應(yīng)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yù)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shù)能負(fù)其責(zé)?”
1900年,北京爆發(fā)了義和團(tuán)運(yùn)動(dòng),慈禧試圖借勢把洋人趕出去,貿(mào)然向八國宣戰(zhàn),結(jié)果導(dǎo)致“庚子國變”。為了跟列強(qiáng)談判,慈禧急命當(dāng)時(shí)正任職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赴京北上。李鴻章途中路經(jīng)上海,專門召見了幫他搞洋務(wù)的盛宣懷。兩人在位于寶昌路(現(xiàn)今的淮海中路1517號(hào))的盛家花園促膝對(duì)話兩晝夜。臨別,77歲的李中堂與比他小20歲的盛宣懷,執(zhí)手相看淚眼,留下六字曰,“和議成,我必死”。果然,到1901年冬,李鴻章簽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賠款條約《辛丑條約》,賠款總額相當(dāng)于11年的全國財(cái)政收入總和。李某人被看成賣國賊,舉國皆曰可殺。
據(jù)說李鴻章臨終前一日,俄國公使還逼他在條約上簽字,他呈慈禧太后《絕命詩》一首,其中有四句是:“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吊民殘。秋風(fēng)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言辭凄慘,若秋風(fēng)落葉。110年后,我們紀(jì)念這位面孔模糊的“裱糊匠”,也許該有一些當(dāng)世之思。
江湖誰憶穆藕初
穆藕初出生在上海浦東一個(gè)棉商家庭,19歲就進(jìn)了棉花行當(dāng)學(xué)徒,終他一生,都與棉花糾纏在一起。
“你好,吳先生。我叫穆家修,我的父親是穆藕初……”幾個(gè)月前,手機(jī)上突然收到這樣的一條短信。
今天的商業(yè)界,已很少有人知道穆藕初了。不過,在80年前,他卻跟如今的張瑞敏、任正非類似,以管理而聞名全國。
穆藕初出生在上海浦東一個(gè)棉商家庭,19歲就進(jìn)了棉花行當(dāng)學(xué)徒,終他一生,都與棉花糾纏在一起。33歲時(shí),他深感中國棉紡業(yè)的落后,下決心到當(dāng)時(shí)棉業(yè)最發(fā)達(dá)的美國德克薩斯州讀書,這一讀就是整整8年。
1916年11月,穆藕初把全球管理學(xué)的奠基之作、美國人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出版于1911年的《科學(xué)管理原理》翻譯引進(jìn)到了中國。正是在這本書里,泰勒第一次提出了科學(xué)管理理念。穆藕初曾幾次拜訪過泰勒,是唯一跟這位偉大的管理學(xué)家有過切磋的中國人。更有意思的是,穆藕初的中文版竟比歐洲版出得還要早。
穆藕初學(xué)成歸國后,當(dāng)即與兄長籌集20萬兩銀子創(chuàng)辦了上海德大紗廠。一年后,德大生產(chǎn)的棉紗在北京商品陳列質(zhì)量比賽中得到第一名,頓時(shí)一夜成名。棉紡織業(yè)在當(dāng)時(shí)是中國第一大產(chǎn)業(yè),聚集了張謇、榮家兄弟和周學(xué)熙等眾多頂級(jí)企業(yè)家,穆藕初后來居上。德大成功后,他先后籌建了厚生紗廠和鄭州豫豐紗廠。回國五年后,穆藕初一躍與張、榮、周并列成為棉紗業(yè)的“四大天王”。
與其他三位“天王”相比,穆藕初出身科班,對(duì)產(chǎn)業(yè)進(jìn)步和工廠管理創(chuàng)新的貢獻(xiàn)尤為突出。在經(jīng)營工廠的時(shí)候,他先后寫成了《試驗(yàn)移植美棉紡紗能力之報(bào)告》、《紗廠組織法》等長篇文章,對(duì)民族紡織業(yè)的進(jìn)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動(dòng)作用。他發(fā)起“中華植棉改良社”,開辟棉花試驗(yàn)場,大力推廣種植美國的脫字棉。
當(dāng)時(shí),中國紗廠的管理方式十分落后。穆藕初率先取消了工頭制,改為總經(jīng)理負(fù)責(zé)制。另外,他建立新式財(cái)務(wù)制度,把傳統(tǒng)的流水賬改為復(fù)式結(jié)賬法,這也是西方財(cái)務(wù)制度在中國的第一次引進(jìn)。在具體實(shí)務(wù)管理的基礎(chǔ)上,他對(duì)泰勒的科學(xué)管理法進(jìn)行了中國式的改良,總結(jié)出科學(xué)管理的四大原則:無廢才、無廢材、無廢時(shí)、無廢力。此外,他還概括出當(dāng)經(jīng)理的“五個(gè)會(huì)用”原則:會(huì)用人、會(huì)用物、會(huì)用時(shí)、會(huì)用錢、會(huì)利用機(jī)會(huì)。
1928年,穆藕初出任國民政府的工商部次長,相繼編訂了眾多的工商法規(guī)。這位深得美式商業(yè)倫理精髓的實(shí)業(yè)家認(rèn)定,“在人事日趨繁頤,社會(huì)日趨復(fù)雜的現(xiàn)在,無論什么團(tuán)體,都要以法治為本,然后有一定的軌道可循,有一定的規(guī)矩可遵”。
抗戰(zhàn)爆發(fā)后,穆藕初擔(dān)任農(nóng)產(chǎn)促進(jìn)委員會(huì)的主任委員,為了改善后方棉布急缺的情況,他發(fā)明了“七七棉紡機(jī)”,提高生產(chǎn)效率的同時(shí)為抗日做出了重大貢獻(xiàn)。
1943年,穆藕初因罹患腸癌去世,簡陋的奠堂之上,最醒目的一條挽聯(lián)是四個(gè)字——“衣被后方”。
中國這一百年,最大的特征就是善于遺忘。時(shí)至今日,后世商業(yè)界很少有人知道穆藕初了。他的名字偶爾出現(xiàn),卻是在八桿子也打不到的戲曲圈。穆藕初長得風(fēng)流倜儻,一表人才,平生喜歡昆曲、書法、學(xué)佛、養(yǎng)魚和斗鳥,是一個(gè)少見的才子型企業(yè)家。1921年,他感于古老昆曲的日衰,便贊助成立了昆劇保存社和昆劇傳習(xí)所,今天我們還能聽到昆劇,多半還拜穆先生的恩澤。
那次,與穆藕初的公子穆家修在杭州見面,他告訴我,上海社科院和復(fù)旦大學(xué)等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將在11月中旬召開穆藕初管理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以紀(jì)念他誕生135周年。我專撰此文,以表達(dá)自己的敬意。
穆公子學(xué)的是工科,不懂棉花,不擅昆曲,不過卻也生得一表人才,雖至暮年,仍可見乃父當(dāng)日豐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