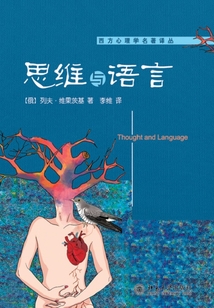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中文版譯序
列夫·維果茨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是俄國著名的心理學家,文化-歷史學說(culture-history theory)的創始人。維果茨基1917年畢業于莫斯科大學(University of Moscow)法律系和沙尼亞夫斯基大學(University of Shaniavsky)歷史-哲學系,因對心理學感興趣而廣泛閱讀了心理學、語言學和其他有關社會科學的著作,并先后在莫斯科實驗心理學研究所和莫斯科心理研究所任職。1934年因患肺病逝世,享年只有38歲。《思維與語言》(Thought and Language)這部代表作刊布于維果茨基逝世后數月。
維果茨基創立的文化-歷史學說,其核心問題是高級心理機能(high psychological function)的發展問題。維果茨基關于高級心理機能的發展觀點,起始于他對意識的看法。針對當時的客觀心理學,他反對把意識從心理學研究領域中完全排除出去,認為辯證唯物主義不否定作為腦的機能和高度組織起來的物質屬性的意識實在性,也不否認對它進行科學的因而也是嚴格客觀的研究的必要性。與意識問題緊密聯系的是高級心理機能問題,維果茨基對高級心理機能的研究,促使他創立了文化-歷史的發展理論。
一
維果茨基認為,傳統上,關于高級心理機能,它的結構、發生和發展,以及它的所有特殊規律性,存在著兩種傾向:一是把它歸結為較簡單程度的過程;一是把它分解為單個的組成成分。前者為客觀心理學(objective psychology),它“始終不承認高級機能和低級機能的差別”;后者為主觀心理學(subjective psy-chology),它認為在每一初級機能之上還聳立著“不知從何而來的第二層次”(即高級機能層次):在機械記憶之上是邏輯記憶,在不隨意注意之上是隨意注意,在再現想象之上是創造性想象,在形象思維之上是概念思維,在低級感情之上是高級感情,在一時沖動的愿望之上是具有遠見的愿望。但這些高級機能的起源并不清楚,這就導致人們認為它們原本是與低級機能一起被預先安排好了的;在發生、機能和結構上同低級機能沒有任何聯系,無法在低級機能上找到自己的本源。
這種關于高級機能和低級機能問題的不正確看法,反映在兒童心理學中,便是不去研究高級心理機能的發生和發展,而是傾向于分析已經形成的、發展的行為形式,或是不研究發展本身的過程及其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的過渡,而是去說明它們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上的單個行為形式。
與上述觀點相反,維果茨基提出了理解發展的文化-歷史原則:心理的發展,應當從歷史的觀點,而不是抽象的觀點,不是在社會環境之外,而是在同它們的作用的不可分割的聯系中,加以理解。這一原則基于這樣一個論點:現代文明的成人的行為是兩種不同發展過程——動物生物進化和人類歷史發展——的結果,由于這樣,最初原始的人變成了現代文明的人。在種系發生(phylogeny)中,這兩個過程是以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發展路線單獨地表現出來的,然而,在個體發生(contogeny)中,它們卻匯合在一起了,因為兒童從生下來的第一天起就處在他的周圍社會環境的一定影響之下。由于這種影響,便使人產生和形成著新的行為系統。這種新的行為系統是在具備一定的生物成熟的情況下形成起來的,它并不要求改變人的生物類型,但由此組成的高級機能(言語思維、邏輯記憶、概念形式、隨意注意和意志等),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則發生著深刻而全面的變化。可見,高級機能是在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中由那些低級機能變成的。“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社會的人改變著自己行為的方式和方法,并使其天生的素質和機能發生變化,形成和創造出新的行為方式——特殊的文化方式。”由此,決定了必須在人的發展中研究心理機能,也即從人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來的始基的形式開始,直到高級行為過程和高級心理過程。
在維果茨基看來,作為人類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心理機能的發展包含著能在質上改變低級心理機能的“心理工具”(mental means)。這種心理工具是一些人為的刺激—手段(stimulate means),當人類掌握了這些刺激-手段并使用它們時,也就使自己擺脫了對現有的、不依他人為轉移的刺激—客體的完全依賴性,使行為有了新形式,也即把高級行為與簡單行為區別開來。維果茨基稱這種心理工具為“記號”(signs)。可以作為記號的例子有:語言、形形色色的號碼和計數、各種記憶裝置、藝術作品、信、圖表、圖紙、地圖和各種各樣的暗號等等,對于動物的條件反射(conditioning)活動來說,記號表明的只是一種信號作用,而對人來說,除此之外還表明了另外一種把他和動物區別開來的東西,那就是意義(meaning)。
意義的原則是一種活動的新原則。信號作用只是對自然界現象聯系的一種消極反映,它完全是由自然界的條件創造出來的,也絕不會超出自然界已有的那個范圍。人的特點是對自然界進行積極的變革(這一點是整個人類歷史的基礎),而這種對自然界的積極變革,要求接通在純粹自然的、天生的行為類型中不可能做到的那種聯系,也即只有借助人工創造的刺激、刺激-手段和使行為有意義的記號才能做到的那種聯系。這種工作類似于電話接線員的活動。無論低級機能或高級機能,都是以暫時條件聯系和典型條件反射的形成為基礎的,這只說明了電話機本身的工作,而當我們說到高級機能時,它類似于接通所需線路的電話員工作。正是電話員本身的工作,包含著與低級行為方式不同的高級行為方式的特殊性。發展的實質便在于此。
以此為依據,維果茨基在發展問題上著重考慮了兩個課題:詞在心理工具中的地位。維果茨基說,言語就其本身意義而言,是社會聯系的核心系統,是社會聯系和文化行為的核心機能。詞是普遍的、到處可以使用的刺激—手段,它可以被廣泛地作為外部的或內部的刺激而加以使用。思維在各種心理機能中的主導地位。機能之間的整個關系系統,基本上決定于在這一發展階段上占支配地位的思維形式。
把上述兩個課題結合起來,使維果茨基廣泛地考察了心理學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思維與語言的問題,它構成了文化-歷史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維果茨基既反對把思維與語言等同起來的觀點,也反對把兩者完全割裂開來的觀點。在維果茨基看來,心理活動是一個復雜的整體,這個整體可以分解為基本的單位,這些基本的單位應該具有整體所固有的一切基本特性。在生物學領域,這種分析的產物就是活的細胞,它保持著有機體所固有的一切基本特性;思維與語言的關系也需要有這樣的單位,它本身包含著言語思維作為整體所固有的特性。在作這樣的分解時,不能把言語思維分解為彼此孤立的元素——思維與語言,然后試圖研究不依賴于言語的思維和不依賴于思維的言語,并把兩者之間的聯系視作兩個不同的過程之間純粹外部的、機械的依賴關系。這樣的分解方式是把復雜的言語思維分解為失去其整體特性的思維與語言兩個元素。
那么,維果茨基所分解的基本單位是什么呢?維果茨基指出,它就是詞的意義——詞的內在方面,對現實的概括反映。詞的意義是兩個彼此緊密聯系的言語機能(社會交往機能和思維機能)的單位。交往必然以詞的意義的概括和發展為前提;人類的交往形式只有依賴于對現實概括反映的思維才有可能表現出來。唯有承認詞的意義這一單位,才能對詞的聲音和它的意義之間的關系有個明確的理解。也就是說,人類言語最本質的標志是聲音和意義的緊密聯系,因為言語的聲音方面的單位不是聲音本身而是有意義的聲音。由此推導,思維與語言的關系是緊密聯系和不可分離的,這種統一使詞與其意義的聯系不同于純粹聯想的聯系。維果茨基高度概括了這一基本觀點:“思維不是在言語中表現出來的,而是在言語中實現出來的。”
這樣,思維與語言的關系就不能被看做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它始終是一個過程:從思維向言語的運動和從言語向思維的運動。言語的兩個方面(內部的、意義的方面和外部的、聲音的方面)彼此具有特殊的運動規律;思維在言語中的具體化,同時也就是對具體表現在言語中的意義結構的改變,也即“思維的語法成了言語的語法”。在維果茨基看來,從意義向聲音轉化的復雜過程,形成了一條基本的使言語思維本身更加完善的路徑。
具體說來,維果茨基在言語思維問題上,同兩種觀點進行了論爭:
1.唯理主義的言語思維理論。以W。斯特恩(W。Stern)為代表的唯理主義言語思維理論強調言語的“有意性”,強調“瞬間發現符號及其意義”的可能性。所謂言語的“有意性”,意指對某種內容的指向,或者說“意義”。用斯特恩的話說,“人類在心理發展的某個階段,獲得了在發出聲音的時候去意指某種事物的能力,去提到某種客觀事物的能力”。實際上,這些有意義的行為已經是思維行為了;它們的出現意味著言語的唯理化和具體化。而所謂“瞬間發現符號及其意義”,意指兒童能以一次了結的方式意識到每一物體都有它永久性的象征(ermanent symbol),一種識別它的合宜的模型(pattern)——也就是說,每件事物都有個名字。當兒童能夠意識到一些象征并能意識到需要這些象征時,可以說這已經是在特定意義上的一種思維過程了。
然而,在維果茨基看來,斯特恩的麻煩在于把“有意性”這種專門要求作出發生學(genetics)解釋的言語特征(也即這種“有意性”如何在演化過程中形成)看成是言語發展的根源之一,一種驅動力量,一種生來就有的傾向,一種強烈的欲望。這種“有意性言語”不知出自何方:它既沒有歷史,也沒有任何來源。按照斯特恩的觀點,它是基本的、原始的,是“一勞永逸的”自發地冒出來的。“當斯特恩以這種方式看待有意性的時候,他用一種唯理主義的解釋取代了發生學的解釋……這種用需要解釋的事物來解釋一件事的方式是一切唯理主義理論的基本缺點,也是斯特恩理論的基本缺點。”同樣,維果茨基也認為,觀察和實驗研究都表明,兒童只是在以后稍長的時間里才能獲得符號和意義之間的關系,或者掌握符號的功能性用途。這是因為,掌握符號和意義之間的關系,以及過渡到用符號操作,不會由兒童的瞬間發展或瞬間發明而產生。兒童不是以一次了結的方式發現語言意義的。發現語言意義的過程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該過程既有它的“自然歷史”(也就是說,在更加原始的發展水平上它的早期開端和過渡形式),也有它的“文化歷史”(也即具有它自己的一系列階段,它自己的量的發展,質的發展,以及功能的發展,它自己的動力和規律)。大量的研究表明:兒童發現詞和物體之間的聯系并不立即使兒童清楚地意識到符號和符號所指對象的象征性關系(這是充分發展的思維的特征),對于兒童來說,詞長期以來是物體的一種屬性或者一種特征,而不僅僅是一種符號;兒童先掌握物體-詞的外部結構,然后掌握符號-符號所指對象的內部關系。兒童的發現實際上并不是突然的發現,這種發現表面看來是瞬間產生的,實際上是一系列時間的和復雜的“分子”(molecular)變化導致言語發展中那個關鍵時刻的到來。
2.關于“自我中心言語”(egocentric speech)的看法。按照J。皮亞杰(J。Piaget)的觀點,聯系兒童邏輯特征的紐帶是兒童思維的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這種自我中心主義在發生上、結構上和功能上處于我向思考(autistic thought)和定向思考(di-rected thought)之間的中間位置。這里,定向思考是有意識的,它追求存在于思考者心中的目標;它是智慧的,適應現實并努力影響現實;它可以通過語言進行交流。我向思考則是下意識的(subconscious),它容易受到真理的影響,也容易受到謬誤的影響;它所追求的目標以及它所解決的問題本身并不存在于意識之中;它不適應外部現實,但卻為自身創造了一種想象的或夢幻的現實;它保持嚴格的個體化,以意象形式進行運作。因此,為了進行交流,必須求助于兜圈子的說話方式,通過象征以及虛構的手法,以激發引起我向思考的情感。介于這兩種思維方式之間的是自我中心的思維。皮亞杰還認為,言語和思維發展的一般方向是:從我向言語和思維過渡到社會化言語和思維,從主觀的胡思亂想過渡到關系的邏輯性。因此:從性質上說,自我中心言語的根源在于兒童的最初的非社會性;自我中心言語最后會完全消亡,為社會言語所取代。
然而,與皮亞杰產生分歧的是,維果茨基認為,自我中心言語并不僅僅作為兒童活動的一種伴隨物。除了成為一種表述手段和一種解除緊張的手段之外,它在特定的意義上很快成為一種思維工具——一種尋求和規劃解決問題的工具。維果茨基曾以實驗中的一個事實來說明自我中心言語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一項活動的進程:一名5歲的兒童正在畫一輛市內有軌電車,期間他的鉛筆頭突然斷了。兒童用力撳鉛筆,但是紙上顯示不出筆跡,只有深深的沒有顏色的一條線痕。這時兒童自言自語地說:“鉛筆斷了。”接著便把鉛筆丟在一邊,隨手拿起水彩筆,開始畫一輛出了交通事故后的破電車,并不時地自言自語,講他畫中發生的變化。據此,維果茨基認為自我中心言語不只是一種副產品,或者一種不干擾主旋律的伴奏。“我們觀察到自我中心言語如何在一開始標志著一項活動的結局或轉折,然后逐步地朝中心移動,最后達到活動的開始部分,呈現出指導性的、計劃性的作用,并把兒童的行為提高到有目的的行為的水平。”
而且,維果茨基認為,兒童最初的言語就是純粹社會性的,自我中心言語不是從我向言語轉化到社會言語,而是從外部社會言語轉化到內部個人言語。言語越來越成為思維的工具,而兒童思維的發展則依賴于他對這種思維活動的社會工具的掌握。自我中心言語在從有聲言語到內部言語的演化過程中是一個過渡階段。在實驗中,年齡稍大兒童和年幼兒童的行為表現是不同的。“年長兒童默不作聲地對情況進行考察,然后找出解決辦法。當兒童被問到他正在思考什么東西時,他所給的答案相當于學前兒童的大聲思考。這就表明學前兒童通過自我中心言語實施的同樣的心理運算(mental operation)已經讓位于學齡兒童的無聲的內部言語。”維果茨基指出,由于有聲的自我中心言語和內部言語完成了同樣的功能,這樣的相似性表明,當自我中心言語消失時,它并沒有簡單地消亡,而是“轉入了地下”,也即變成了內部言語。當這種轉化發生時,面臨困難的兒童便一會兒求助于自我中心言語,一會兒求助于沉默反應。“我們的假設是,內部言語的過程幾乎在學齡開始便得到發展并變得穩定,它引起那個階段觀察到的自我中心言語的迅速終止。”
在這個問題上,維果茨基的觀點是,全部發展遵循著以下路線:言語的主要功能(不論是兒童的還是成人的)是交流,是一種社會接觸。因此,兒童的最初言語基本上是社會性的。開始時它是混合的和多功能的(global and multifunctional),后來功能開始分化。當兒童將社會性的行為形式轉移到個人內部心理功能方面,像和其他人交談一樣開始對自己交談時,自我中心言語發生了。隨著兒童的發展,自我中心言語逐步轉化為內部言語,這種內部言語既服務于我向思考,又服務于邏輯思維。
三
維果茨基在思維與語言的發展問題上,堅持這樣的觀點:思維的發展與言語的發展并不對應,它們的兩條發展曲線是交叉的。這兩條曲線可能會變成直線,齊頭并進,甚至在某個時期會合并成一條線,但它們總是又要叉開的。這個規律對種系發生和個體發生都是適用的。為此,維果茨基從種系發生、個體發生、自我中心言語向內部言語過渡,以及概念的形成等四個方面探討了思維與語言的發展。
1.種系發生上的思維與語言問題。維果茨基認為,在動物身上,思維和言語產生的根源各不相同,發展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維果茨基以W。苛勒(W。Koehler)和R。耶基斯(R。Yerkes)的研究為例指出,在動物身上出現初期的思維能力與言語完全沒有什么關系。類人猿會制造和使用工具,也會迂回曲折地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這個過程中,類人猿所表現出的創造力,雖然只能算作初步的思維,但仍歸屬于思維發展的前語言階段(prelinguistic phase)。
然而,這不等于說類人猿沒有自己的語言。在維果茨基看來,類人猿的語言有著與眾不同之處。例如,黑猩猩是非常合群的動物,在群體內它們有著各種各樣的“語言交際”形式:首先,它們有一套感情豐富的表情,包括變化臉部表情、打手勢、嗓子發音等。其次,它們做一些表示社交情感的動作,包括表示問候的手勢等。黑猩猩既能“理解”相互之間的手勢和嗓音,又能通過手勢和嗓音來“表示”與其他成員有關的欲望。如果黑猩猩要別的成員做什么動作或一起做什么動作,它通常自己先做一遍。例如,它若要“邀請”另一只黑猩猩跟著它走,它就會推那黑猩猩一下,并表演走路的起步動作;它若要另一只黑猩猩給它一個香蕉,它就會朝空中抓一下。所有這些動作都是直接與行為本身有關的手勢。維果茨基認為,這些觀察證實了W。馮特(W。Wundt)的看法,即示意性手勢是人類語言發展過程的第一階段,類人猿的某些手勢是處于理解性和示意性之間的某種形式。維果茨基稱“這個過渡階段的手勢是從純粹的感情豐富的表情跨向客觀性語言的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動物達不到這個客觀表述的階段:黑猩猩能夠玩弄彩色黏土,先是用嘴唇和舌頭“畫畫”,后來再用畫筆“畫畫”,可是它們的“作品”根本一點也不表述什么。“在它們的作品里顯示不出有什么跡象表達客觀性含意。”在這個過程中,類人猿所表現出的“語言交際”,雖然只能算作原始的語言,但仍可歸屬于語言發展的前智力階段(pre-intellectual phase)。
由此,維果茨基就種系發生過程中思維與語言的發展歸納出下述幾個結論:思雛與言語的發展根源是不相同的;這兩個機能發展的方式各不相同,相互之間沒有依賴性;類人猿在某些方面(萌芽狀態的運用工具能力),表現出某種人類那樣的智力,而在完全不同的其他方面(社交性嗓音和手勢),表現出某種像人類那樣的語言;在類人猿身上沒有人類所特有的思維與語言之間非常接近的一致性;在思維與語言的發展過程中,思維發展的前語言階段和語言發展的前智力階段有著明顯的區別。
2.個體發生上的思維與語言問題。就個體發生而言,思維與語言發展的關系要復雜得多。維果茨基認為,已有的客觀證據表明,兒童思維發展過程有一個前語言階段。為此,他引用了卡爾·比勒(Karl Buehler)的發現。比勒認為兒童的行為很像黑猩猩,因此兒童生命中的這個階段可以被恰當地稱做“黑猩猩期”:“在我們的被試身上,這個時期相當于10個月、11個月和12個月……兒童的首次創作發生在這個黑猩猩期,雖然那是非常初級的創作,但對兒童的心理發展是極其重要的。”維果茨基從有關的兒童實驗中得出結論認為,早期的智力反應并不依賴于言語。“過去人們說言語是動物人化的開始,但是在言語之前還有同運用工具的能力有關的思維,也就是對機械性聯系的理解,以及為了機械性目的進行機械方法的設計,或者說得更簡單點,在有言語之前,行動就有了主觀的意義。”
在個體發生中,兒童言語發展過程有一個前智力根源。維果茨基指出,兒童的牙牙學語、哭叫,甚至發出第一個詞語,很顯然是與思維發展毫無關系的“言語”發展階段。這些表現形式一直被視作以情感為主的形式,除了具有發泄的功能外,還具有社交的功能。維果茨基引證說,有關兒童行為最初形式的研究,以及對兒童聽到講話聲音所作的最初反應的研究,表明了言語的社交功能在第一年里就已經非常明顯;對于講話聲音所作的明顯反應,早在生命的第三周里就可看到;在第二個月里就可看到獨特的社交反應。“這些研究證實了笑聲、含糊不清的說話聲、動作等等都是自兒童生命的最初幾個月就有的社交手段。”
到了2歲左右的某一時刻,思維與語言發展的曲線會出現會合,從而引起一種行為的新形式。這個關鍵時刻,即言語開始為智力服務,思維開始用言語表達的時刻,是由兩種行為表現出來的:兒童對詞語有著主動的好奇心,對每一件新事物都要問“這是什么”。兒童的詞匯量迅速、飛快地擴展。在這個轉折點之前,兒童只擁有少量的詞匯,這些詞(如同在條件反射中那樣)替代物品、人、行動、心情或欲望。在那個年齡,兒童只知道人家提供給他的詞匯。現在,情況起了變化:兒童感到有一種說詞語的需要,通過提出各種問題,意欲學會表示事物的語言符號。“他好像發現了詞語的符號功能。”言語在早期是情感、意動的,現在進入了智力的階段。思維與語言發展的兩條曲線會合在一起了。
由此,維果茨基就個體發生過程中思維與語言的發展歸納出下述幾個結論:思維與語言在個體發生的過程中發展根源不同;在言語發展中,存在一個前智力階段,而在思維發展中,存在一個前言語階段;在某個關鍵時刻之前,兩條發展曲線是不同的,互相之間是獨立的;在某個關鍵時刻,兩條曲線開始會合,于是思維變成了言語的東西,而言語變成了智力的東西。
3.言語的發展過程。維果茨基把言語的發展過程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原始或自然階段。這一階段與思維發展中的前言語和言語發展中的前智力相一致。這時,言語的運作是以原始形式出現的,因為它們是在行為的原始水平上逐步形成的。
第二,幼稚的心理(naive psychology)階段。該階段類似于幼稚的物理(naive physics)表現,也即兒童對自己的身體和周圍的事物有了物理特性的經驗,這些經驗運用到工具使用方面,兒童首次表現出萌芽中的實際智力。這個階段在兒童的言語發展中是非常明確的,其具體表現是,兒童在尚未理解語法形式和結構所表示的邏輯運作之前已能正確使用若干言語。例如,兒童在尚未真正懂得原因、條件、時間等關系之前就會用“因為”、“如果”、“當……時候”、“但是”等詞語。看來,“他未掌握思維的句法就先掌握了言語的句法”。
第三,外部符號階段。隨著幼稚的心理經驗的不斷積累,兒童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其特征是有了外部符號,這是在解決內在問題時用作輔助手段的外部運作。該階段的具體表現有兒童撥弄自己的手指來數數,采用一定的助記輔助手段或記憶術來幫助記憶等等。在言語發展過程中,這個階段的特點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言語。
第四,內部生長階段。這時,外部運作向內轉化,并在這一過程中經歷了深刻的變化。兒童開始用腦子數數,運用“邏輯記憶”,也就是說,運用內部的聯系和內部的符號。在言語發展過程中,這是內部的、無聲的言語階段。然而,在這一階段,外部運作和內部運作之間仍有不斷的相互作用,一種形式常常很容易地變為另一種形式,接著又變回來。當內部言語用來為外部言語作準備時(例如,在仔細考慮即將要做的講座時),內部言語在形式上可能接近外部言語,或者甚至完全變得像外部言語。“內部的和外部的行為之間沒有明顯的分界線,各自都影響著對方。”
4.關于概念的形成。當時,在概念的形成問題上,存在著一種以N。阿赫(N。Ach)為代表的觀點,認為概念形成的基本因素不是聯想,而是從目的的觀念和人所面臨的課題的觀念而來的決定的意向。對此,維果茨基指出,無論是課題,或是由課題所引起的決定的意向,它們本身還不能解釋達成目的的過程。概念形成的主要問題是實現相應的心理運作的手段問題。“只有研究言語功能的使用及其發展,言語在每一年齡階段上各種性質不同的、發生上彼此聯系的應用形式,才是研究概念形成的關鍵。”
在概念形成問題上,維果茨基重點研究了科學概念和日常概念。前者指教學過程中掌握的概念,后者指日常生活過程中形成的概念。科學概念的特征是運用它們時的理解性和隨意性。這一點使科學概念從本質上與日常概念區別開來,因為日常概念是還未被理解的和很少能隨意運用的,它產生自兒童的個人經驗。在適當組織的教學過程中,科學概念的發展會勝過日常概念的形成。前者的發展對后者的形成有著相當的影響。兒童只有通過科學概念的大門才能達到理解,同時,為了形成科學概念,也需要日常概念發展到一定程度。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維果茨基看來,科學概念和日常概念的發展是循著相反的方向行進的:日常概念是從概念的低級屬性向高級屬性“自下而上”地發展的,科學概念則是從概念的高級屬性向低級屬性“自上而下”地發展的。“科學概念通過日常概念從下面產生出來,日常概念通過科學概念從上面產生出來。”但是,相反的發展途徑并沒有消除兩種概念形式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
維果茨基把發展和教學的相互關系同科學概念和日常概念的問題密切地聯系起來。他反對把教學和發展看做是兩個互不依賴的過程的觀點,也反對把兩個過程等量齊觀的觀點。在維果茨基看來,發展是一個統一的過程,盡管在不同階段上它與教學處于不同的關系之中。在這種具有差別的關系之中,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教學始終并應當走在發展的前面,而不要落在發展的后面。”
四
維果茨基倡導的文化-歷史發展學說,以及由該學說派生出來的思維與語言的發展觀點,對前蘇聯心理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無論是他的同事,還是他的助手和學生,都富有成效地使這一影響得以擴大。然而,對維果茨基的觀點不是沒有反對意見,這些意見集中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1.對文化-歷史發展觀提出的抽象社會學觀點的批評。批評指出,在人類心理的歷史發展中,文化-歷史發展觀只看到了一個因素——發明內部工具、符號、實現某種心理機能的手段。其實,人類的心理生活是極其復雜的,這種復雜性的歷史發展,隨著社會發展的整個進程,依從于社會關系的具體內容,依從于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一定時代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對于這種復雜多樣的歷史發展本身,文化-歷史發展觀不僅沒有加以闡明,甚至沒有指出它應當加以研究的一個問題。由此推導,文化-歷史發展觀對歷史原則的理解似乎過于狹隘了。
2.對個體發生中劃分出心理機能的自然發展和文化發展的批評。維果茨基認為,兒童心理發展過程沿著自然發展和文化發展這兩條路徑行進,它們在個體發生中是緊密地融合在一起的。但是,從直接現實的心理過程向間接的心理過程(運用符號)的過渡,是在兒童發展的較晚時期(學齡時期)實現的。這就產生了矛盾。也就是說,它一方面承認人在出生最初幾天就受社會制約這一事實,另一方面卻認為從直接心理過程向間接心理過程的過渡是在學齡時期實現的,從而把自然發展和文化發展人為地割裂開來,暴露出他所提出的基本觀點之間的矛盾。
3.對內部言語的本質和起源的觀點的批評。維果茨基認為,內部言語起源于自我中心言語,它是“對自己”的言語,而外部言語則是“對別人”的言語。在維果茨基看來,自我中心言語是從外部言語向內部言語過渡的形式,或者說是內部言語的早期形式,是連結外部言語和內部言語的中間環節。外部言語轉變為自我中心言語意味著社會言語向個體言語的過渡,所以,內部言語從心理本質上說是一種特殊的形成物;它不是去掉聲音的言語,而是一個獨特的言語機能。批評者指出,維果茨基自相矛盾的結論使得人們難以理解自我中心言語是外部言語和內部言語的中間環節。維果茨基的結論是:內部言語出現得較晚。甚至在學齡期兒童身上,它還是高度易變的、不穩定的。批評者的依據是:從聽者重復(無聲地)聽到的東西當中可以看到內部言語的萌芽;聽言語并非簡簡單單地聽,到一定程度,聽者如同和對話者一起談話一樣。既然言語是交際的手段,那么它就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談話的地方不僅有說者,而且也有聽者。在交談的場合,無論是說者還是聽者,他們都在思考同樣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說意味著出聲地想,聽意味著默默地想。聽說雙方其實談論的是同一東西,只是一個出聲,一個默默而已。由此推導,沒有思維的言語不是言語,沒有言語的思維也不存在。言語和思維,外部言語和內部言語是同時發展起來的。正如外部言語一樣,內部言語也是社會產生的言語。內部言語的起源,不應當在自我中心言語中去尋找,而應當在可以發現一切言語起源的地方——交際中去尋找。
上述這些批評基本上是在維果茨基逝世之后提出來的。由于這些批評意見沒有得到答復,因此也就沒有論爭,沒有結果。
李維
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