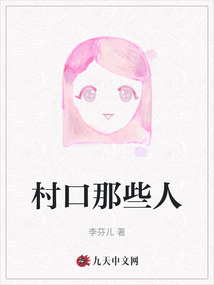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村口
長期的漂泊讓靈魂好似習(xí)慣流浪,所以養(yǎng)成了不愛回村的性格。但是對于作為農(nóng)村重要情報中心的村口,我印象深刻,小時候,村口是人滿為患的。
天剛蒙蒙亮,石板路還沁著露水的涼意,村口就已經(jīng)活過來了。賣菜的農(nóng)人挑著擔(dān)子,扁擔(dān)吱呀呀地響,小板車推著的各種應(yīng)季的瓜果蔬菜,青菜還沾著泥土,水靈靈的,那時候還有那種走街串巷的手藝人和雜貨鋪子,買菜的婦人挎著竹籃,討價還價聲與招呼聲此起彼伏。老樟樹下,幾張磨得發(fā)亮的小木凳從不空閑,總是坐著幾個閑聊的老人,煙袋鍋子一亮一滅,像夏夜的螢火。
我最愛那時的清晨,陽光從東山頭爬上來,一點點漫過青瓦屋頂,將村口的一切鍍上金邊。賣豆腐腦的老陳總會多給我一勺糖漿,而我祖母則會和她的老姐妹們坐在石碾旁,一邊揀菜一邊說笑。那時的村口,連空氣都是熱鬧的,混雜著新鮮蔬菜的清香、油炸果子的焦香和人間煙火的溫暖。
隨著日頭升高,下田的下田,上學(xué)的上學(xué),村口的人漸漸少了。到了晌午,多半只剩下些拄著拐杖的老人,但他們依然讓那里充滿生機——下棋的爭吵聲,評書廣播的咿呀聲,還有永遠說不完的家常里短。即便只剩下他們,村口還是熱鬧的,像一棵老樹,枝葉或許稀疏了,根卻牢牢抓著土地。
但是那時候的村口也不是每天那么熱鬧的,很多的時候是那些老人支撐著村口,幾條刻著隱約圖案的石條子靠著老舊的石頭墻,幾條破凳子......一群年過半百的人......
長大后,我開始躲著村口走。
那些熟悉而陌生的面孔會突然亮起眼睛,枯枝般的手抓住你的胳膊:“喲,這不是……那誰家的娃嗎?都長這么大了!”然后便是連珠炮似的追問:在哪工作?掙多少錢?結(jié)婚沒?有孩子沒?
更令人窘迫的是,他們總會聚在一起,像研究出土文物般端詳你,然后開啟一場多米諾骨牌式的身份確認:
“這是誰家的來著?”“哦,老李家二姑娘的孩子嘛!”“不對不對,你看那眉眼,分明是老王家的大小子!”“想起來了!是不是那個小時候偷劉婆家杏子從樹上摔下來的淘氣包?”
每一塊“骨牌”倒下,都會引發(fā)一陣唏噓感嘆,把我的前世今生翻個底朝天。我只能僵笑著,仿佛一個誤入他人領(lǐng)地的冒犯者,匆匆找借口逃離。那時的村口,成了一座我必須迂回繞行的記憶迷宮,每一句問候都讓我無端緊張。
今年清明,我回老家送一位故去的長輩。車子駛進村,我下意識地準(zhǔn)備繞路,卻忽然意識到已無必要——村口空了。
那棵老樟樹還在,樹下的木凳生了青苔空空。石條子孤零零地立著,一半埋在荒草里。曾經(jīng)擠滿菜販的空地上,只有幾只麻雀在跳躍。陽光依然明亮,卻照出一片寂寥。
我怔怔地站著,試圖尋找過去的痕跡。這時,一個佝僂的身影從巷口慢慢挪出來。我認出是劉奶奶,從前最愛拉著我說“小時候抱過你”的那位。她老得幾乎縮成了一團,像一棵風(fēng)干了的莊稼。
“劉奶奶!”我提高聲音喊她。
她茫然地抬頭,混濁的眼睛努力辨認著,然后擺著哆嗦的手,指了指耳朵:“聽不見啦……耳朵背了……”
我走近些,大聲說:“我是李家的小子!小時候您常給我糖吃!”
她瞇著眼看了我好一會兒,臉上的皺紋慢慢舒展,像是記起來了,又像只是出于禮貌地點頭。那雙曾經(jīng)靈巧地剝豌豆的手,如今像枯枝般顫抖著。
葬禮結(jié)束后,我去村里的公墓獻花。一排排墓碑靜立在山坡上,像沉默的觀眾。我無意間瞥過那些碑上的照片,突然愣住了——
這張是賣豆腐腦的老陳,總是多給我一勺糖漿。那張是下棋最較真的王爺爺,輸了會氣得掀棋盤。那是總愛說媒的趙婆婆,見著年輕人就要介紹對象。還有劉爺爺、張奶奶、陳大伯……
黑色相框里的,全是曾經(jīng)駐扎在村口的身影。他們曾在那里說笑爭吵,傳遞消息,觀察世界,度過一個又一個晨昏。如今,他們靜靜地躺在這里,而村口也隨著他們的離去,漸漸失去了聲音。
我站在墓碑間,忽然明白了村口是什么——它從來不只是個地理概念,而是一個舞臺,上演著一代代人的生命戲劇;是一個容器,盛放著聚散離合的人間煙火。
夕陽西下,我最后一次走過村口。空蕩蕩的場地上,風(fēng)吹起幾片落葉,打著旋兒。有那么一瞬間,我仿佛又聽到了從前的喧鬧聲——叫賣聲、笑語聲、爭吵聲,那些熟悉的聲音交織在一起,在時光深處回蕩。
我知道,明天的太陽依然會升起,但陽光再也照不見那些熟悉的身影。村口終于安靜了,而我的童年,也真正地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