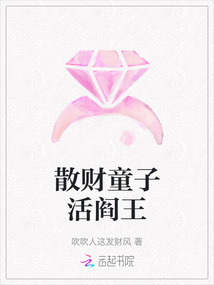
散財童子活閻王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散財童子活閻王
我穿回1984年,綁定了暴富系統。
系統說:賬戶余額清零才能續命,否則立刻暴斃。
我含淚在國營商場撒錢,鄰居罵我敗家子。
直到我花光積蓄買下無人問津的股票認購證。
股災那天,散戶們排隊跳樓。
我舉著喇叭在交易所門口喊:“都別跳!你們的股票我雙倍收了!”
突然系統提示音響起:“檢測到宿主超額完成散財任務...”
“生命值+50年,獲得隱藏技能——點石成金。”
那天,我燒光了價值千萬的股票。
火光中,我看見那個總罵我的鄰居姑娘,淚流滿面舉著喇叭回喊:
“沈星河!你燒的不是紙!是我的嫁妝——”
意識像沉在冰冷粘稠的油底,每一次掙扎都牽扯著撕裂般的痛楚。沈星河猛地吸了一口氣,肺葉火辣辣地疼,仿佛吸進去的不是空氣,而是碎玻璃渣子。
眼睛艱難地睜開一條縫,渾濁的光線刺了進來。視線花了半晌,才勉強聚焦。入眼是斑駁脫落的黃泥墻皮,一張糊著舊報紙的破木桌,墻角堆著幾個印著“尿素”字樣的空蛇皮袋,散發著一股混合著劣質煙草和潮濕霉爛的怪味。唯一能證明這地方屬于人類文明的,是桌上那個印著紅雙喜的搪瓷缸子,邊緣豁了個口,杯底沉著可疑的褐色茶垢。
“這他媽是哪兒……”沈星河喉嚨干得像砂紙摩擦,聲音嘶啞微弱,帶著宿醉般的混沌。
他最后的記憶,還停留在電腦屏幕刺眼的藍光上。出版社編輯冰冷刻薄的郵件:“星河啊,你這稿子……市場反應太冷淡了,我們也很為難。要不,你考慮轉行?”緊隨其后的是催命符般的銀行短信:“您尾號XXXX的賬戶房貸扣款失敗,余額不足,請及時……”
然后,就是一陣天旋地轉的黑暗。
就在這時,一個毫無起伏、冷冰冰的電子合成音,突兀地在他腦海深處炸開:
【暴富系統激活中……綁定宿主:沈星河。】
【初始生命值:72小時。】
【核心規則:宿主個人銀行賬戶(或等值財富載體)余額歸零,方可按消耗財富額度1:1兌換生命時長(單位:元=小時)。余額非零狀態下,生命值耗盡即死。】
【警告:余額不為零,生命倒計時不可逆。當前余額:3.00元。生命值剩余:72小時。】
【新手引導任務:72小時內,完成首次財富清零。任務獎勵:無。失敗懲罰:抹殺。】
沈星河渾身一激靈,像是被一盆冰水混合物從頭頂澆下,連骨髓都凍透了。他猛地坐起身,動作太大扯得那張吱呀作響的破木床一陣劇烈搖晃。心臟在胸腔里瘋狂擂鼓,撞得肋骨生疼。
系統?暴富系統?清零余額才能活命?
他幾乎是連滾帶爬地撲到那張破木桌前,顫抖的手在桌面上胡亂摸索。指尖觸到一個硬硬的、冰冷的小本子。他一把抓過來,封皮是深綠色的,印著褪色的國徽和“活期儲蓄存折”幾個字。
翻開。最新一行記錄,日期是……1984年?5月?17日?存款余額:叁元整。
下面一行小字,清晰地印著開戶行:中國人民銀行南城支行勝利路儲蓄所。
1984年?3塊錢?
沈星河只覺得一股寒氣從腳底板直沖天靈蓋,眼前陣陣發黑。他穿回了四十年前!成了一個兜里只有三塊錢的窮光蛋!還被綁定了這么個要命的鬼系統!不把錢花光,三天后就得暴斃?
巨大的荒謬感和冰冷的恐懼瞬間攫住了他,讓他像離了水的魚一樣徒勞地張著嘴,卻發不出任何聲音。冷汗瞬間浸透了身上那件洗得發白、領口磨出毛邊的藍色工裝。
“冷靜……冷靜!”沈星河狠狠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劇痛和血腥味讓他混亂的腦子清醒了一瞬。他強迫自己運轉起那個曾經構思過無數種致富方案的小說家大腦。
規則是:清零余額,才能續命。財富載體……存折里的錢是載體,那現金呢?實物呢?這年頭,買東西總行吧?
“花掉!必須馬上花掉這三塊錢!”這個念頭如同燒紅的烙鐵,燙得他坐立不安。三天?不,一秒他都不想等!誰知道這該死的系統會不會抽風提前清零?窮困潦倒和立刻暴斃之間,傻子都知道怎么選。
沈星河一把抓起桌上那個搪瓷缸子,胡亂灌了幾口里面不知放了多久、帶著鐵銹味的涼水。冰涼的液體滑過喉嚨,稍微壓下了一點喉嚨里的灼燒感。他深吸一口氣,帶著一種奔赴刑場的悲壯,攥緊了那本仿佛有千鈞重的綠色存折,一把拉開那扇吱嘎作響、仿佛隨時會散架的破木門。
門外是一條狹窄、坑洼不平的胡同。陽光有些刺眼,空氣里彌漫著煤球燃燒的硫磺味、公共廁所飄來的氨水味,以及不知誰家中午燉菜散發的咸菜疙瘩味兒。低矮的磚房、灰撲撲的院墻、墻根下曬著太陽打盹的老人、穿著打補丁衣服追逐打鬧的孩子……一切都蒙著一層泛黃的舊照片濾鏡。
沈星河顧不得感受這撲面而來的八十年代風情,也顧不得鄰居們投來的或好奇或冷漠的目光。他像一顆出膛的炮彈,憑著腦海中模糊的“勝利路儲蓄所”的方向感,悶頭沖了出去。腳下坑洼的土路硌得他腳底板生疼,劣質塑料涼鞋的帶子幾乎要磨斷。
儲蓄所是一排平房里隔出來的一小間。玻璃柜臺后面,坐著兩個穿著深藍色工裝、梳著齊耳短發的女營業員,一個在織毛衣,一個在嗑瓜子,眼皮都懶得抬一下。
“取……取錢!”沈星河沖到柜臺前,氣息還沒喘勻,聲音帶著急切的顫抖,把存折從那個小小的窗口塞了進去,“全取!三塊!都取出來!”
織毛衣的女營業員慢悠悠地放下毛線針,抬眼瞥了他一下,那眼神像是在打量一件礙事的舊家具。她拿起存折,慢條斯理地翻開,核對,拿起一個木頭章子,蘸了蘸紅印泥,“啪”地一聲蓋在存折上。然后拉開抽屜,慢吞吞地數出三張薄薄的、印著女拖拉機手圖案的淺綠色紙幣,又從旁邊一個鐵盒子里捻出幾個分幣(兩分、一分),一并從小窗口推了出來。
“點點。”營業員毫無感情地說了一句,又拿起了毛線針。
沈星河一把抓起那三塊錢和幾個分幣,紙幣的邊緣有些粗糙,帶著油墨的味道。他根本沒心思點,緊緊攥在手心,那幾張薄薄的紙片此刻仿佛有千鈞重,又像是一塊滾燙的烙鐵。
錢到手了!載體變了!現在,它們變成了現金!
下一步,花掉!立刻!馬上!
儲蓄所對面,就是一家國營副食品商店。灰撲撲的玻璃柜臺后面,擺著些蔫頭耷腦的蔬菜、用黃草紙包著的散裝餅干、粗鹽、醬油醋瓶子,還有……柜臺最里面,似乎放著幾個油紙包。
沈星河的目光瞬間鎖定了那里。他沖進商店,直奔那個柜臺。
“同志!那個!油紙包的!是什么?”他指著里面,聲音因為緊張和激動有些變調。
售貨員是個胖胖的中年婦女,正低頭織著毛線坎肩。聞言抬起頭,懶洋洋地看了一眼:“哦,果脯。杏脯。一塊二一斤。”
“買!買兩斤!”沈星河想都沒想,脫口而出。三塊錢,花掉兩塊四,還能剩六毛!不夠!要清零!他目光飛快掃過柜臺,“那個!那個餅干!散裝的!多少錢?”
“奶油餅干,八毛一斤。”
“買一斤!”沈星河的心在滴血,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這荒唐的揮霍。他掏出那三張綠色的一元紙幣,又添上幾張毛票和分幣,一股腦拍在柜臺上,“快!”
胖售貨員被他這“豪橫”的架勢弄得愣了一下,看看錢,又看看這個臉色發白、眼神直勾勾的年輕人,嘟囔了一句:“急什么咯……”但還是慢吞吞地起身,拿起秤盤和油紙。
沈星河死死盯著她稱重、打包的動作,每一秒都像在油鍋里煎熬。他能感覺到自己后背的冷汗又冒出來了。直到兩個油紙包和找零的幾張分幣(一分、兩分)被推到他面前,他看都沒看那些分幣,一手抓起兩個油紙包,轉身就走。
走出商店門口,午后的陽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沈星河卻覺得渾身發冷。他低頭看了看手里的油紙包,又摸了摸褲兜里剩下的那幾個分幣。
清零了嗎?
他屏住呼吸,集中精神在腦海中瘋狂呼喚:“系統!系統!余額!我的余額!清零了嗎?清零沒有?!”
【財富載體掃描中……】
【現金余額:0.09元。】
【警告:宿主當前余額非零!生命倒計時持續中!剩余生命值:71小時58分47秒……46秒…45秒…】
冰冷的電子音,如同喪鐘。
沈星河只覺得眼前一黑,腳下一個踉蹌,差點一頭栽倒在塵土飛揚的胡同里。他扶著旁邊粗糙冰冷的磚墻,大口喘著氣,心臟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死死攥住,疼得他彎下腰。
九分錢!他媽的就剩九分錢沒花出去!
那幾個該死的分幣!
他顫抖著手伸進褲兜,掏出那幾枚冰冷的、邊緣有些磨損的硬幣。一枚五分,兩枚兩分。加起來,不多不少,九分錢!
巨大的恐懼和一種被戲耍的荒謬憤怒瞬間淹沒了他。他猛地揚起手,想把這該死的九分錢狠狠砸在地上!但手臂抬到一半,硬生生僵在了半空。
砸了?硬幣還在,系統會不會判定“財富載體”依然存在?就算砸了,碎片算不算?萬一系統較真……
不行!不能冒險!
必須花掉!一分不剩地花掉!
他像一頭瀕死的困獸,紅著眼睛在胡同口四處張望。目光掃過路邊支著破木板賣針頭線腦的老頭,掃過挑著擔子吆喝“磨剪子嘞戧菜刀”的手藝人……最后,定格在副食品商店旁邊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那里蹲著一個頭發花白、滿臉皺紋的老阿婆。她面前鋪著一小塊洗得發白的藍布,上面整整齊齊地擺放著幾小堆蔬菜:一小捆葉子發蔫的小蔥,一小堆沾著泥的土豆,還有……幾個用稻草捆著的、圓溜溜、青皮帶白霜的東西。
是冬瓜!不大,也就比拳頭大一圈。
沈星河像看到了救星,幾乎是撲了過去,帶起的風吹動了阿婆額前的幾縷白發。
“阿婆!冬瓜!冬瓜怎么賣?”他的聲音嘶啞急切。
老阿婆被他嚇了一跳,渾濁的眼睛里帶著點怯意和茫然,慢吞吞地伸出兩根枯瘦的手指,比劃了一下:“兩……兩分錢一個。”
“買!”沈星河立刻把手里攥得滾燙的那枚五分硬幣塞到阿婆手里,根本不等她反應,“買一個!不用找了!”他飛快地彎腰,抓起一個最小的青皮冬瓜,轉身就走,腳步快得像逃命。
老阿婆拿著那枚五分硬幣,愣愣地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胡同拐角,又低頭看看自己手里多出的三分錢(五分買兩分的冬瓜,她該找回三分),布滿皺紋的臉上寫滿了困惑和一絲不易察覺的惶恐。
沈星河抱著那個冰涼的、帶著泥土腥氣的冬瓜,一路狂奔回那間散發著霉味的破屋。反手“砰”地一聲甩上門,背靠著冰涼的門板,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心臟幾乎要跳出嗓子眼。
冬瓜被他隨手扔在墻角,骨碌碌滾了幾下,停在那個尿素袋子旁邊。
“系統!現在呢?清零了嗎?”他幾乎是吼出來的,聲音在狹小的空間里回蕩。
【財富載體掃描中……】
【現金余額:0.00元。】
【實物財富載體(冬瓜)價值評估:約0.02元。】
【警告:宿主當前余額非零!生命倒計時持續中!剩余生命值:71小時58分…】
“操!”沈星河一拳狠狠砸在旁邊的黃泥墻上,震得墻皮簌簌落下。劇痛從指骨傳來,卻遠不及心底那滅頂的絕望和荒謬感強烈。
冬瓜也算錢?這他媽破系統是周扒皮轉世嗎?!連個冬瓜都不放過!
他猛地沖到墻角,抄起那個無辜的青皮冬瓜,高高舉起,面目猙獰,就要把它砸個稀巴爛!
【警告:檢測到宿主意圖銷毀低價值實物財富載體。若載體消失,系統將默認其價值歸零。但此行為存在不可控風險,可能觸發“惡意規避規則”懲罰機制。請宿主謹慎操作。】
冰冷的電子音適時響起,如同一盆冰水,澆滅了沈星河狂暴的怒火。
他高舉著冬瓜的手臂僵在半空,劇烈地顫抖著。砸?萬一觸發了更可怕的懲罰呢?不砸?難道抱著這個冬瓜過三天,然后等死?或者……吃掉它?
吃掉?吃掉算不算銷毀?系統會不會判定為“消耗”?“消耗”能不能算清零?
沈星河腦子里亂成一鍋滾燙的粥,無數念頭瘋狂碰撞。他死死盯著手里這個青皮疙瘩,仿佛盯著一個隨時會爆炸的炸彈。
最終,求生的本能壓倒了憤怒和恐懼。他緩緩放下手臂,抱著那個冬瓜,像個瘋子一樣,對著空氣,對著那看不見摸不著的系統,咬牙切齒地低吼:
“好!好!算你狠!老子吃!老子把它吃到肚子里!吃到渣都不剩!我看你還算不算!”
他沖到破木桌前,拿起那個豁口的搪瓷缸子,里面還有半缸子涼水。然后,他低下頭,張開嘴,對著手里那個還沾著泥土和草屑的冬瓜,狠狠地一口咬了下去!
“咔嚓!”
一聲脆響。生冬瓜堅硬、冰涼、寡淡無味,帶著一股濃烈的青澀土腥氣,瞬間充滿了口腔。
沈星河眉頭緊鎖,胃里一陣翻江倒海。但他不管不顧,像一頭餓瘋了的野獸,對著那個無辜的冬瓜,一口,又一口,機械而兇狠地啃噬起來。堅硬的瓜瓤刮擦著喉嚨,冰涼粗糙的瓜肉塞滿了口腔,土腥味直沖腦門。
“呃…嘔……”生理性的反胃讓他幾次干嘔,眼淚鼻涕不受控制地涌出。但他強行壓下惡心感,強迫自己吞咽。牙齒和生瓜肉摩擦的聲音,在寂靜破敗的小屋里顯得格外清晰,格外詭異。
墻角堆著的尿素袋子沉默著,脫落的墻皮沉默著,只有他粗重的喘息和令人牙酸的啃噬聲在回蕩。
【財富載體掃描中……】
【實物財富載體(冬瓜)…持續消耗中…價值持續遞減…】
【警告:宿主當前余額非零!生命倒計時持續中…】
冰冷的提示音如同跗骨之蛆,陰魂不散。沈星河充耳不聞,只是更加用力地咀嚼著,吞咽著,仿佛要將這該死的系統規則也一并嚼碎、咽下肚去!
日子在一種荒誕的、錙銖必較的揮霍中向前爬行。
沈星河成了勝利路這一片“著名”的敗家子。他仿佛患上了“金錢恐懼癥”,口袋里不能留一分錢超過一小時。國營菜站里蔫巴巴的蔬菜,副食店里積了灰的罐頭,供銷社里尺碼不對的解放鞋……只要手頭有幾個鋼镚兒,他就立刻沖進去,買下最不值錢或者最沒用的東西。
“喲,沈作家,又來‘接濟’我們啦?”菜站的大嬸看到他,臉上堆起職業性的假笑,眼神里卻滿是毫不掩飾的鄙夷,“今天有處理的白菜幫子,一分錢一堆!管夠!”
沈星河面無表情地遞過分幣,接過那堆散發著輕微腐爛氣息的菜葉,轉身就走。身后傳來毫不避諱的議論:
“嘖嘖,好好的一個文化人,咋成這樣了?”
“聽說寫東西沒人看,瘋魔了唄!”
“敗家啊!真是糟蹋爹娘的血汗錢!”
更刺耳的,是隔壁院門“吱呀”一聲推開時,那道清冷又帶著明顯厭惡的目光。住在隔壁小院的蘇晚晴,是附近小學的音樂老師。她總是穿著洗得發白的藍色列寧裝,梳著兩條烏黑的麻花辮,氣質清冷得像早春枝頭帶霜的花。每次沈星河拎著那些“戰利品”狼狽地路過她家門口,總能感受到那兩道目光,像冰錐子一樣扎在他背上。
“沈同志,”有一次,他抱著一堆處理價買來的、散發著刺鼻樟腦丸味的舊毛線團回來,正好在窄窄的胡同里和蘇晚晴狹路相逢。她微微蹙著秀氣的眉,聲音不高,卻清晰地穿透了午后的嘈雜,“人活著,總得有點志氣。靠糟蹋東西過日子,不體面。”
沈星河腳步一頓,胸口像被什么堵住了,悶得發慌。他想解釋,喉嚨卻像是被那堆毛線團堵住了。最終,他只是把頭埋得更低,抱著那堆散發著怪味的毛線,匆匆從她身邊擠了過去,留下身后一聲極輕、卻清晰無比的嘆息。
他成了所有人眼里的笑話,一個徹頭徹尾的廢物、敗家子。只有他自己知道,每一次看似瘋狂的“揮霍”,都是與死神擦肩而過。系統冰冷的倒計時,就是他頭頂懸著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直到那天下午,他揣著剛“散”掉工資(街道小廠打零工糊紙盒掙的十幾塊錢)后剩下的最后三毛六分錢,漫無目的地游蕩到了區工人文化宮門口。
文化宮的鐵柵欄外,人聲鼎沸,比菜市場還要喧鬧。烏泱泱的人群擠在一起,伸長了脖子,像一群爭食的鴨子。人群中心,擺著幾張刷了綠漆的簡陋木桌,后面坐著幾個穿著藍色工裝、戴著紅袖章的工作人員,個個滿頭大汗,嗓子都喊啞了。
“寶安聯合投資公司!原始股認購證!支援國家建設!機會難得啊同志們!”
“一塊錢一張!一塊錢一張!”
“走過路過不要錯過!買了就是支持特區發展!”
擴音喇叭的嘶吼聲震得人耳膜嗡嗡作響。幾個紅袖章舉著一沓沓印著粗糙圖案、蓋著大紅印章的紙片,在人群上方揮舞。那紙片黃不拉幾,紙質粗糙,像極了過年時糊窗戶的劣質油紙。上面印著“深圳寶安聯合投資公司股票認購證”的字樣,還有面額“壹股”的小字。
人群的反應卻極其冷淡。
“啥玩意兒?股票?能當飯吃還是能當布票使?”
“一塊錢一張?搶錢啊!買斤肉才多少錢?”
“就是!一張破紙片,糊窗戶都嫌脆!誰買誰傻子!”
“走走走,別耽誤功夫,電影快開場了!”
“紅袖章”們喊得聲嘶力竭,唾沫橫飛,回應他們的只有嗡嗡的議論、不耐煩的推搡和毫不掩飾的嗤笑。那粗糙的認購證被隨意地丟在桌上,被風吹得嘩啦作響,有的甚至被擠掉在地上,沾滿了腳印。
沈星河像一尊泥塑木雕,僵在人群外圍。他的目光死死鎖住那些被踐踏的、粗糙的黃色紙片,瞳孔深處仿佛有電流竄過!
深圳寶安聯合投資公司!股票認購證!
他塵封的記憶閘門被猛地撞開!前世那些模糊的財經史料、那些講述“老八股”傳奇的紀錄片片段,如同決堤的洪水般洶涌而出!就是它!中國資本市場的真正起點!幾個月后,這堆被所有人視為廢紙的東西,將如同坐上了火箭,價格打著滾地往上翻!最終會變成燙手的金疙瘩!而再過幾年,當狂熱褪去,泡沫破裂,那場席卷全國的股災……
一個冰冷又瘋狂的計劃,瞬間在他腦海中成型!
這哪里是廢紙!這是他沈星河唯一的生路!是他擺脫這無休止的、令人窒息和屈辱的“散財”煉獄的唯一鑰匙!更是他……向那個該死的系統,向這個操蛋的命運,發起致命一擊的武器!
一股難以言喻的熱流猛地沖上頭頂,驅散了連日來的陰霾和絕望。他的手指因為激動而微微顫抖,手心那三毛六分錢的硬幣被攥得滾燙。
他不再猶豫,像一頭發現了獵物的豹子,猛地撥開前面擋路的人群,力量大得驚人。
“讓開!都讓開!”他嘶啞地吼著,不顧周圍人驚愕和嫌惡的目光,奮力擠到那張綠色的木桌前。
汗水順著他的額角流下,滴進眼睛里,一片刺痛模糊。但他不管不顧,死死盯著桌后那個喊得嗓子冒煙的紅袖章,聲音因為極度的渴望和緊張而變調,尖銳地劃破了嘈雜:
“同志!認購證!我買!全買!有多少買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