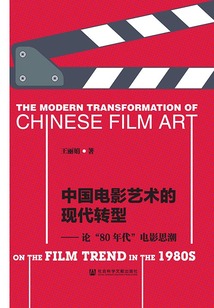
中國電影藝術(shù)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論“80年代”電影思潮
最新章節(jié)
- 第18章 后記
- 第17章 主要參考文獻(xiàn)
- 第16章 重塑理想
- 第15章 《結(jié)語 涅槃——“80年代”中國電影思潮流變的反思》:穿越歷史
- 第14章 市場化趨勢與電影娛樂消費(fèi)
- 第13章 《“80年代”中國電影思潮動(dòng)因:開放性的語境》:文化批判熱潮與電影藝術(shù)革新
第1章 《導(dǎo)論》:中國電影藝術(shù)本質(zhì)體認(rèn)溯源
中國電影僅有百年歷史,但其間滄海桑田,多有變遷。有研究者指出,自20世紀(jì)30年代開始,中國電影就發(fā)生了“劃時(shí)代的變革”,由萌芽時(shí)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性質(zhì)”轉(zhuǎn)化為具有現(xiàn)代意識(shí)的“革命電影文化”,生發(fā)出前所未有的意識(shí)形態(tài)內(nèi)容。[1]還有研究者認(rèn)為,“40年代下半葉,中國古典電影內(nèi)部現(xiàn)代藝術(shù)因素已相對集中的出現(xiàn),中國電影的母體從整體上顯示出古典形態(tài)向現(xiàn)代形態(tài)蛻變的朕兆”,“走近了現(xiàn)代電影的大門”[2]。不少當(dāng)代學(xué)者則指出,新時(shí)期中國電影呈現(xiàn)多方面、多層次的歷史轉(zhuǎn)向。[3]應(yīng)該說,上述歷史分析都擁有充分的現(xiàn)實(shí)依據(jù),它們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描述了特定歷史時(shí)期中國電影發(fā)展的某些癥候;但就電影的藝術(shù)本質(zhì)而言,學(xué)界對于其變遷軌跡及發(fā)展規(guī)律等核心問題鮮有具體明晰的結(jié)論。中國電影的本質(zhì)屬性是什么?作為舶來品,在這塊文化底蘊(yùn)深厚的土地上,它歷經(jīng)一個(gè)多世紀(jì)的生長,形成了怎樣與眾不同的電影品性?20世紀(jì)下半葉風(fēng)雷激蕩的歲月,孕育并觸發(fā)了中國電影怎樣的跌宕蛻變?今天的中國電影,真的已經(jīng)敲開了“現(xiàn)代電影”的大門了嗎?解答諸如此類的問題,要沿著中國電影的藝術(shù)現(xiàn)代性脈絡(luò),厘清本質(zhì)特征,探尋概念內(nèi)涵,方可把握中國當(dāng)代電影的歷史流變及其規(guī)律,這是本書寫作的基本出發(fā)點(diǎn)。
那么關(guān)于中國電影的藝術(shù)本質(zhì),近百年來電影前輩們留下了怎樣的思考呢?最直接明了且廣為人知的是“影戲”與“電影”的爭執(zhí),即中國電影姓“戲”還是姓“影”。在程季華的《中國電影發(fā)展史》和鐘大豐的一系列研究文章中,都明確指認(rèn)中國電影在最初半個(gè)多世紀(jì)中充當(dāng)?shù)氖莻鹘y(tǒng)戲劇的化身,“電影即‘影戲’”[4]。
1896年8月11日,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電影放映在上海徐園舉辦,當(dāng)時(shí)《申報(bào)》所刊廣告即名之為“西洋影戲”。1897年9月5日,上海《游戲報(bào)》刊登的中國第一篇影評題目為《觀美國影戲記》。[5]而最為重要的是,“影戲”之名下所包含的是中國電影的戲劇本質(zhì)。徐卓呆評論早期中國電影時(shí)如是說:“影戲雖是一種獨(dú)立的興行物,然而從表現(xiàn)的藝術(shù)看來,無論如何總是戲劇。戲之形式雖有種種不同,而戲劇之藝術(shù)則一。”[6]言下之意,電影作為新興事物引入中國,其表現(xiàn)形式固然與中國傳統(tǒng)戲劇不同,舞臺(tái)變成了銀幕,真人幻化成影像,但其本質(zhì)屬性是戲劇藝術(shù),其藝術(shù)原則亦與戲劇一致。早期電影理論家侯曜也明確表示,“影戲是戲劇之一種”,“具有表現(xiàn)、批評、調(diào)和、美化人生”的功能。[7]可見,從中國電影源頭考察,電影被納入中國戲劇范疇,西方電影單純的“雜耍”品性被附加上了“反映人生”的社會(huì)功能。對影戲有過深入研究的現(xiàn)代電影史學(xué)家鐘大豐先生在《“影戲”理論歷史溯源》一文中,進(jìn)行了翔實(shí)精辟的闡釋。他指出:“影戲”以帶有濃厚戲劇化色彩的技巧為外衣,包裹著從功能目的論出發(fā)的戲劇式敘事本體。[8]陳南在《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思潮評析》一書里表達(dá)了相似的看法:“所謂影戲電影,指的是一種強(qiáng)調(diào)戲劇特征的電影樣式和電影觀念,具有‘載道’的審美價(jià)值取向。”[9]
這種獨(dú)特的戲劇本質(zhì)是中國電影的藝術(shù)特色。它從電影落地中國之際就凸顯出來。有研究者認(rèn)為這正是中國電影的民族特色。但顯然,這種極具本土化的“中國特色”之形成更多的是電影這個(gè)“獨(dú)立興行物”入鄉(xiāng)隨俗的自在結(jié)果。
首先,中國歷史悠久的戲劇藝術(shù),以其深厚的藝術(shù)積淀和巨大的影響力,將漂洋過海的電影納入麾下,致使中國電影從一開始就有賴于戲劇傳統(tǒng),并形成與傳統(tǒng)戲劇藝術(shù)相融合的特點(diǎn)。比如,從拍攝內(nèi)容和方法看,中國最初的電影幾乎都是舞臺(tái)戲曲的銀幕翻版。從第一部國產(chǎn)短片《定軍山》到《春香鬧學(xué)》,早期中國電影人的電影制作其實(shí)就是舞臺(tái)戲曲的實(shí)錄,完全遵循舞臺(tái)戲劇程式化的藝術(shù)規(guī)則。“攝影機(jī)放在劇場中央的‘舞臺(tái)視點(diǎn)’,沒有角度、距離、方位、速度的變化,畫面景別很單一,‘永遠(yuǎn)是一個(gè)遠(yuǎn)景’。”[10]換言之,這時(shí)的電影是以舞臺(tái)場面拍攝方法制作的銀幕戲劇。因此,中國電影觀眾最初獲得的關(guān)于中國電影的印象實(shí)際上是戲劇式的。這種先入為主的藝術(shù)熏陶在日積月累中涵養(yǎng)了中國電影觀眾的獨(dú)特審美定式;它反過來又成為中國影戲發(fā)育生長的深厚土壤。戲劇的傳統(tǒng)就這樣在中國電影與觀眾的默契交流中潛滋暗長起來。自1913年始,中國電影正式進(jìn)入故事片拍攝階段,盡管作品內(nèi)容、情節(jié)各異,人物性格迥然,但以故事為核心、以教化為宗旨的主流創(chuàng)作傾向始終未有實(shí)質(zhì)性改變。即使到了40年代,蘇聯(lián)蒙太奇電影理論開始逐步影響“影戲”的傳統(tǒng)戲劇式技巧,但也只是以敘事蒙太奇手段取代了戲劇舞臺(tái)式調(diào)度,“影戲”戲劇式敘事本體的性質(zhì)依然如故。1947年公映的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是個(gè)中典范。在藝術(shù)處理上,電影弱化了傳統(tǒng)戲劇的舞臺(tái)場面調(diào)度,通過情景調(diào)度突出人物戲劇沖突,強(qiáng)化感人的故事性,使悲劇性主題得到了完美的演繹。作品因此榮獲了捷克第十屆卡羅維發(fā)利國際電影節(jié)特別獎(jiǎng)。這種秉持戲劇敘事原則的電影創(chuàng)作主流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jì)70年代末。
當(dāng)然中國電影的“影戲”特色,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那一代電影從業(yè)人員的選擇。當(dāng)時(shí)電影界的主創(chuàng)人員大多來自戲劇行業(yè),即原先是文明戲的編劇和演員,即使電影研究者、影評家也不例外。鄭正秋、任彭年、但杜宇、侯曜、周劍云、徐卓呆無一不與戲劇藝術(shù)存在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11]這種經(jīng)歷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將戲劇藝術(shù)與電影藝術(shù)相掛鉤,其中鄭正秋的電影觀念及其創(chuàng)作就很有代表性。作為由戲劇評論家“轉(zhuǎn)行”而來的早期中國電影具有影響力的編導(dǎo),鄭正秋提出:影戲乃戲劇之一新品種,是寫實(shí)的戲劇。在他的電影創(chuàng)作中,自覺實(shí)踐著戲劇的“原則”——有系統(tǒng)的情節(jié),有組織的語言,有相當(dāng)?shù)母本埃兴囆g(shù)的動(dòng)作,有極深刻的表情,有人生真理的發(fā)揮,有人類精神的表現(xiàn)。所不同的是,與傳統(tǒng)戲劇相比,影戲一反戲劇藝術(shù)的假定性,彰顯的是寫實(shí)性(真實(shí)美)。因此,盡管“我們覺得扮演影戲之動(dòng)作與表情,較舞臺(tái)劇更為細(xì)膩而自然,則戲之重要使命,豈可棄之不顧?為統(tǒng)一名稱,顧名思義起見,不如徑名‘影戲’”[12]。可見,“電影即影戲”原是立足戲劇而來的。講究戲劇性和故事性的創(chuàng)作意識(shí)深深地浸染了中國電影藝術(shù)的最初胚芽,并在它后續(xù)的發(fā)展中烙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印記。
其次,“影戲”藝術(shù)本質(zhì)中鮮明的“載道”意識(shí)則直接受到中國傳統(tǒng)文藝思想的影響。“文以載道”在中國文藝創(chuàng)作歷程中流傳深廣。它不僅在藝術(shù)觀念上規(guī)約了藝術(shù)與現(xiàn)實(shí)間的致用關(guān)系,而且涵化了中國藝術(shù)家獨(dú)特的創(chuàng)作意識(shí)和思維習(xí)慣——?jiǎng)?chuàng)作者們自覺地從功能目的出發(fā)去從事文藝活動(dòng)。這種意識(shí)習(xí)慣連同藝術(shù)規(guī)約成為影戲教化觀的孵化溫床。
在《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思潮評析》一書中,陳南指出:“反映早期中國人對電影認(rèn)識(shí)的第二個(gè)觀念便是秉承傳統(tǒng)的文藝觀‘詩言志’、‘文以載道’,主張電影應(yīng)該成為教育的手段和工具,擔(dān)負(fù)起表現(xiàn)人生、批評人生、調(diào)和人生、美化人生的重任。”[13]在《中國電影發(fā)展史》中,程季華也指出:“鄭正秋提倡新劇,認(rèn)為戲劇必須是改革社會(huì)、教化群眾的工具。”鄭正秋的電影作品《難夫難妻》“作為我國第一部故事短片的意義,便在于它接觸了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內(nèi)容,提出了社會(huì)的主題”[14]。鐘大豐因此認(rèn)為,鄭正秋作為中國電影的拓荒者,最主要的貢獻(xiàn)就“在于他開創(chuàng)了中國電影從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生活和從戲劇舞臺(tái)藝術(shù)方面吸取豐富的創(chuàng)作營養(yǎng)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為中國電影藝術(shù)道路的開辟奠定了基礎(chǔ)”[15]。而從早期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的整體情形看,鄭正秋代表的正是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的主流,其主要特點(diǎn)之一就是“這些影片大多披著一層社會(huì)教化功能的外衣,鼓吹所謂‘含有褒善貶惡之意義’的主旨。以此為依據(jù)來編演故事”[16]。可見,傳統(tǒng)文藝觀中藝術(shù)與現(xiàn)實(shí)的致用關(guān)系已作為中國電影藝術(shù)家自覺的創(chuàng)作意識(shí)沉淀在電影深處,凝結(jié)為中國電影本性中最醒目的核心內(nèi)容。
當(dāng)然,“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觀念同樣支配著絕大多數(shù)的電影觀眾及電影批評家,它以既成的審美習(xí)慣和鮮明的批評標(biāo)準(zhǔn)引領(lǐng)著中國電影的價(jià)值取向。史載中國最早的一篇影評《觀美國影戲記》就由觀影而感慨人生:“近有美國電光影戲,制同影燈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旋見現(xiàn)一人影,兩西女作跳舞狀,黃發(fā)蓬蓬,憨態(tài)可掬。……又一為美國之馬路,電燈高燭,馬車戰(zhàn)往如游龍,道旁行人紛紛如織,觀者至此幾疑身入其中,無不眉為之飛,色為之舞。忽燈光一明,萬象俱滅。”“觀畢,因嘆曰:天地之間,千變?nèi)f化,如蜃樓海市,與過影何以異?自電法既創(chuàng),開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無穹之秘。如影戲者,數(shù)萬里在咫尺,不必求縮地之方,千百狀而紛呈,何殊乎鑄鼎之像,乍隱乍現(xiàn),人生真夢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觀。”[17]這種“人生如夢”的感悟,多少反映了中國觀眾在審美心理上對于藝術(shù)“載道”意識(shí)的習(xí)慣性觸發(fā),顯示了中國人對藝術(shù)內(nèi)涵的哲理性、啟發(fā)性的關(guān)注。而在電影批評家那里,這樣的關(guān)注顯得更為深切。獨(dú)鶴在《觀〈血淚碑〉影劇后之我見》一文里力申要拍“有主義的影戲”的主張,“最好能切中時(shí)弊,對于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加以切實(shí)的批評”[18]。若璞在《我之中國電影談》中提出,中國電影至少應(yīng)“含有褒善貶惡之意義”[19]。洪深倡導(dǎo)要“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fēng)為主旨”[20]。郁達(dá)夫則從批評電影的墮落的角度申明他對中國電影的態(tài)度:“大眾的藝術(shù)品(指電影,引者注),稍一不慎,就要流為填補(bǔ)低級趣味的消遣品,而失掉真正的藝術(shù)品的固有性質(zhì)。”[21]毫無疑義,在這些評論家心目中,中國電影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在于它嚴(yán)肅的積極的教諭功能。
綜上所述,中國電影在百年歷史進(jìn)程中,從創(chuàng)作實(shí)踐和理論批評兩個(gè)維度,不懈探索電影藝術(shù)的本質(zhì)。經(jīng)過半個(gè)多世紀(jì)的努力,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影戲體系:中國電影隸屬于戲劇藝術(shù),在藝術(shù)審美方面具有獨(dú)特的寫實(shí)美,在表現(xiàn)形式方面借助電光媒介實(shí)現(xiàn)蒙太奇(鏡頭)調(diào)度,但其核心是編演故事(敘事本體),達(dá)成社會(huì)教化目的。這種全然迥異于“movie picture”“movie”的體認(rèn),成為今天中國電影藝術(shù)的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在極大程度上制約著中國當(dāng)代電影發(fā)展的方向,而前人的探索亦成為后來者研究電影藝術(shù)歷史轉(zhuǎn)型的重要路標(biāo)。事實(shí)上,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界不少人關(guān)注過三四十年代以降中國電影的變化。如30年代左翼電影出籠,“給抽象的為人生和教化社會(huì)的主張賦予了更具體的時(shí)代和階級的內(nèi)容,努力使之成為宣傳革命思想的斗爭武器”[22],因而有了“革命電影”說;再如,三四十年代開始廣泛引介蘇聯(lián)普多夫金的敘事蒙太奇理論,開啟了對全盤照搬戲劇的舞臺(tái)場面性拍攝技巧的改良,逐步形成一套以敘事蒙太奇為主要特征的電影表現(xiàn)技巧,“影戲”的名稱也逐漸被“電影”所取代。但實(shí)際上“影戲”體系遠(yuǎn)未終結(jié)。從中國電影藝術(shù)本質(zhì)的規(guī)定性去考察,上述的種種“革命”或者局限于主題內(nèi)容與功能取向的調(diào)整,或者停留在外在表現(xiàn)技巧的改進(jìn)(敘事蒙太奇是致力于達(dá)成敘事藝術(shù)性的有效電影技巧),而并未引發(fā)影戲內(nèi)涵的本質(zhì)變更——一方面,“在整個(gè)中國電影理論框架中,電影媒介和技巧對敘事的從屬地位并沒有改變”[23],重故事的敘事本體追求依然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另一方面,教化社會(huì)的實(shí)用性電影功能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得到了強(qiáng)化。如“十七年”電影基本延續(xù)了“左翼電影”的模式。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的創(chuàng)作原則使它自覺保留了具有廣泛觀眾基礎(chǔ)的戲劇電影形式,在功能上強(qiáng)調(diào)以社會(huì)主義精神改造和教育人民,在主題上著重表現(xiàn)工農(nóng)兵與階級敵人斗爭的時(shí)代要求,在表現(xiàn)技巧上用敘事蒙太奇充當(dāng)營構(gòu)戲劇沖突的主要手段。比起三四十年代的電影,“十七年”電影甚至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政治功能的作用。“文革電影”主體是“革命樣板戲”。它“以戲?yàn)橹鳎菓蚯交蛭璧甘降奈枧_(tái)再現(xiàn)而已,帶有非常多的非電影因素,不僅沒有促進(jìn)電影藝術(shù)的長進(jìn),反而更讓電影成為戲曲的附庸,喪失了自己的本質(zhì)特性”[24]。直到80年代,寫意美學(xué)、紀(jì)實(shí)美學(xué)、影像美學(xué)以及娛樂美學(xué)等各種電影思潮洶涌而至,中國影戲傳統(tǒng)體系在多方夾擊下發(fā)生了本質(zhì)裂變,中國電影才逐步擺脫敘事本體意識(shí),不斷調(diào)整電影藝術(shù)與社會(huì)時(shí)代的關(guān)系,并日趨豐富電影內(nèi)涵品質(zhì),形成了以影像為本體的時(shí)空藝術(shù),完善了集審美、教育與娛樂于一體的現(xiàn)代電影本質(zhì),由此開啟了中國電影富有現(xiàn)代意義的轉(zhuǎn)型歷程。
注釋
[1]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fā)展史》(第一卷),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第14頁;李少白:《電影歷史及理論》,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第69頁。
[2]陳山:《人文電影的新景觀》,《當(dāng)代電影》1996年第2期。
[3]陸紹陽:《中國當(dāng)代電影史》,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4,第70頁;周星:《中國電影藝術(shù)史》,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第218~224頁。
[4]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fā)展史》是中國第一部電影史著作,具有權(quán)威性。鐘大豐是影戲理論研究專家,對此發(fā)表過一系列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是論文《“影戲”理論歷史溯源》和著作《中國電影史》。
[5]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fā)展史》(第一卷),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第8頁。
[6]徐卓呆:《影戲者戲也》,民新特刊《三年以后》號,1926年12月。
[7]侯曜:《影戲劇本作法》,《當(dāng)代電影》1986年第1期。
[8]鐘大豐:《“影戲”理論歷史溯源》,《當(dāng)代電影》1986年第3期。
[9]陳南:《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思潮評析》,同濟(jì)大學(xué)出版社,2002,第9頁。
[10]陳南:《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思潮評析》,同濟(jì)大學(xué)出版社,2002,第6頁。
[11]見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fā)展史》關(guān)于“亞細(xì)亞影戲公司演員合同”部分內(nèi)容,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第21頁。
[12]羅藝軍主編《中國電影理論文選》(上),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2,第13頁。
[13]陳南:《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思潮評析》,同濟(jì)大學(xué)出版社,2002,第8頁。
[14]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fā)展史》,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第18~19頁。
[15]鐘大豐、舒曉鳴:《中國電影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第13頁。
[16]鐘大豐、舒曉鳴:《中國電影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第14頁。
[17]商雍松:《觀美國影戲記》,原載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戲報(bào)》第74號,轉(zhuǎn)引自《影視文化》第4期《中國電影發(fā)生的歷史文化背景》一文,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1,第49頁。
[18]獨(dú)鶴:《觀〈血淚碑〉影劇后之我見》,《明星特刊》第27期,1927年11月。
[19]若璞:《我之中國電影談》,《電影》第4期,1924年8月。
[20]洪深:《我的打鼓時(shí)期已經(jīng)過了嗎?》,《洪深文集》第4卷,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第517頁。
[21]羅藝軍主編《中國電影理論文選》(上),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2,第87頁。
[22]鐘大豐:《“影戲”理論歷史溯源》,《當(dāng)代電影》1986年第3期。
[23]鐘大豐:《“影戲”理論歷史溯源》,《當(dāng)代電影》1986年第3期。
[24]周星:《中國電影藝術(shù)史》,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第20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