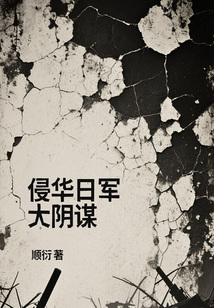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日本走向侵略之路
1868年,日本進入了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在明治天皇的引領下,實施了廣為人知的“明治維新”。這一系列改革不僅幫助日本擺脫了被歐美列強吞并的命運,還推動了其迅速崛起為一個強國。然而,這也為日本的侵略擴張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侵略。日本的間諜活動和各種謀略,正是在這種擴張主義思想的驅動下展開的。
盡管日本的侵略擴張行動大多是在明治維新之后才開始,但其侵略意識早在幕府末期便悄然萌芽。當時,許多思想家提出了“海外雄飛論”和“攘夷論”,這些理論暗含著對外擴張的強烈動機。日本學界一度熱烈討論如何侵占朝鮮、中國東北,甚至整個亞洲,許多知名人物如本多利明、佐藤信淵、橋本左內和佐久間象山,都積極推動這一思想。本多利明在其《西域物語》中提到,日本若想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必須通過占領堪察加、庫頁島及滿洲(即今天的中國東北)來實現。他甚至將這視為“日本帝國主義復興的開端”。
佐藤信淵則在《宇內混同秘策》一書中明確表達了他的雄心。他認為日本作為天帝所賜的“最初的國家”,理應掌控世界,并將滿洲納入其版圖。他還進一步提出,從中國到東南亞,直至印度,最終將世界各國一一并吞。
在明治維新前,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吉田松陰,他的觀點也為日本后來的擴張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吉田松陰曾在一封信中透露,雖然日本與歐美列強的條約已定,但他仍主張通過侵略亞洲的其他地區來“補償”日本的損失。他特別指出,朝鮮、滿洲和臺灣是非常理想的目標。
吉田松陰提出的“欺弱避強”的策略,主張一方面在外交上屈從于歐美列強,另一方面則通過擴張亞洲,尤其是中國,來增強日本的國力。這一思潮被后來的明治政府采納,并發展成了“大陸政策”,即將中國大陸作為日本擴張的主要目標。
明治維新的勝利讓日本擺脫了歐美列強的壓迫。剛剛松了一口氣的日本政府,立即將擴張主義擺上了日程。1868年,明治天皇發布的《安撫萬民之宸翰》中提到,政府將繼承祖先的偉業,開拓四方,確保國威遠播。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征服朝鮮成為了日本的第一步。
木戶孝允,作為當時日本政府的核心人物,早在1868年12月便在日記中提出了征韓的計劃。他寫道:“朝鮮問題非常緊急,必須立即派遣使節前往,若朝鮮不服,則可動用武力,以彰顯日本的威嚴。”而12月19日,日本政府便通過對馬藩主向朝鮮遞交了一份國書。由于其中使用了“皇”和“敕”等只有中國皇帝才可使用的措辭,朝鮮方面認為這是一種侮辱,拒絕接收國書。這一舉動被日本視作朝鮮對其的“不禮”,并成為日后發動侵略的借口。
隨后,木戶孝允、巖倉具視等人開始為出兵朝鮮進行詳細的計劃。木戶在給大村益次郎的信中詳細闡述了他的戰略設想:“我們應先通過武力占領釜山等地,逐步推進。若交戰,應保持冷靜,務必確保長遠戰略,不可急于求成。”與此同時,日本外務省的大丞柳原前光也撰寫了《朝鮮論稿》,強調朝鮮的地理位置重要,北鄰滿洲,西接中國,是實現日本國土完整的關鍵。
不久后,佐田白茅被派往朝鮮調查,并回國上書明治天皇。他提出,征服朝鮮不僅是增強國力的戰略步驟,還能大大提升日本在亞洲的軍事威望。他認為,若成功征服朝鮮,日本不僅能強化自身的軍隊,還能迅速將其作為進入中國東北和其他亞洲國家的跳板。
在日本政府的擴張政策中,朝鮮的侵占雖然已經成為既定方針,但具體實施的時機卻在政府內部引發了不同意見,形成了兩個派別:一派是“即征派”,另一派則是“緩征派”。
即征派的主力人物包括明治政府的參議、西鄉隆盛,以及一些改革派的九州武士。1868年,日本內戰剛剛結束,改革派的佐田白茅便向政府提出了征服朝鮮的建議。他不僅多次上書天皇,還獲得了外務官員森山茂和大村益次郎等人的支持。隨著時間的推移,西鄉隆盛也積極推動這一主張,主張以迅速出兵的方式征服朝鮮。除了朝鮮,西鄉和其他一些政府高官還討論了攻占中國臺灣的計劃,認為可以先通過外交手段,確保歐美列強不會干預,然后突然出兵,占領臺灣。西鄉等人的提案曾一度獲得明治天皇的認可。
在日本國內的局勢尚未完全穩定之時,仍然發生著一些封建士族的叛亂。明治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并不寬裕。基于這些考慮,巖倉俱視、大久保利通等一部分人堅決反對立即對外發動戰爭,他們形成了所謂的“緩征派”。這兩位作為剛剛從歐美考察歸來的特命全權大使,認為即征派中的一些人多為反對明治政府的中下層武士。如果此時對朝鮮出兵,可能會使這些人迅速壯大勢力,形成對政府的威脅。因此,他們主張先進行國內的改革,增強國家的綜合實力,待時而動,向外擴張。經過一番爭論,最終巖倉成為代理太政大臣,緩征派的力量逐漸占據了上風。不久之后,西鄉隆盛被撤職,并最終在九州叛亂中敗亡。
掌握了實權的巖倉和大久保等人,在1874年實施了西鄉曾提議的計劃,開始侵略臺灣,發動了日本近代史上首次的對外戰爭。接著,他們又在1875年通過江華島事件,逼迫朝鮮政府與日本簽訂《朝日修好條規》,為后來的侵占朝鮮奠定了基礎。朝鮮從此淪為日本的附屬國,而日本在朝鮮半島獲得了各種特殊權益,進一步推進了其擴張政策。
日本政府對朝鮮的侵略,只是其對外擴張的第一步,而真正的目標則是中國。明治政府在實施對朝鮮的侵略時,已經將目光投向了中國,期待借此作為擴張的跳板。這一行動實際上是日本政府走向帝國主義的開始。
對于這些侵略行動,盡管背后有強盜邏輯的支持,日本也需要為自己的行動找一些理論依據。一些學者開始提出所謂的“脫亞論”和“興亞論”,以此來為侵略行為辯護。1885年,在中法戰爭中,盡管中國在軍事上取得了一些勝利,最終卻被迫與法國簽訂不平等條約,這一屈辱的結果更加激發了日本政府的侵華野心。此時,國內一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開始鼓吹對外擴張,尤其是侵略中國。
其中,福澤諭吉便是最為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脫亞論》,公開宣揚日本應當脫離亞洲,走向西方文明的道路。他認為,日本的國民精神已經從亞洲的落后狀態中脫穎而出,而中國仍處于衰敗邊緣,岌岌可危。福澤明確表示,日本應該拋棄與亞洲其他國家的聯系,采取歐美國家的手段,直接對待中國和朝鮮,以武力來獲取自己想要的利益。
此番言論在當時的日本社會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很多學者、文人、政客紛紛借助媒體發表支持擴張主義的觀點,鼓勵政府加速侵略步伐。比如柴四郎的小說《佳人奇遇》便采用了“脫亞論”的思想,呼吁日本加入掠奪中國的行列。小說很快成為暢銷書,鼓動了民眾的擴張情緒。與此同時,一些政治團體和組織也成立了,積極宣傳這一侵略主張,聲援日本加快侵略中國的步伐。
在日本政府的對外宣傳中,為了掩飾其擴張主義的野心,并爭取其他亞洲國家的支持與合作,甚至試圖贏得它們的同情,日方提出了一個特別的理論——所謂的“興亞論”。這個論調的核心目的,是號召亞洲各國聯合起來,抵抗西方列強,尤其是當時的俄國威脅。1880年,伴隨著政府在背后的支持,一群政治人物發起了“興亞會”,大力倡導這一理論,其中“興亞主義”的倡導者之一便是荒尾精。他提出的“興亞策”比起其他理論更加系統化,也充滿了侵略性。
荒尾精在他的“興亞策”中指出,19世紀下半葉,歐洲列強的勢力不斷向東擴張,幾乎吞噬了整個亞洲,只有日本、朝鮮和中國這三國尚未淪陷。然而,在這三國中,唯有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成功地進行改革,迅速崛起為強國。相比之下,中國和朝鮮則顯得異常貧弱,疲弱不堪,尤其在歐洲列強的壓迫下,這兩個國家幾乎無力自保,處于崩潰的邊緣。荒尾精認為,既然如此,日本就應當對這些鄰國的困境表示關心。即便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日本也應當扶持中國和朝鮮,幫助它們恢復元氣,進而實現東亞的繁榮和穩定。
荒尾精描繪了一個宏偉的藍圖:他認為,作為東亞的領導者,日本應當利用中國豐富的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打造強大的軍力,最終使日本成為全球的霸主。他強調,“東洋文明的輝煌必將照亮整個世界,亞洲的威風將響徹四海。”在他看來,這不僅僅是日本百年大計,更是當下急需完成的使命。
更進一步,荒尾精宣揚了日本獨特的“皇國體制”,他堅信日本是“天命所歸”的民族,理應主導整個東亞的事務。對于“字內統一論”的主張,他自信地表示,日本是唯一有能力實現全球統一的國家,理應承擔領導責任。荒尾精的這一思想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吸引了不少日本民眾,尤其是那些志在“大東亞復興”的人們。一些失意的政治人物和浪人武士紛紛投身其中,夢想以日本為中心,振興亞洲。雖然少數人如宮崎寅藏確實懷著拯救中國的初心,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事業,但更多的人則最終成為了侵華戰爭的先鋒,甚至不乏間諜和軍事謀士。
到了1889年,隨著代表軍國主義勢力的山縣有朋成為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局勢逐漸發生了變化。次年3月,山縣有朋向明治天皇遞交了一份名為《外交政略論》的文件,提出了廣受爭議的“主權線”與“利益線”理論。他宣稱,國家的獨立與安全不再僅僅依靠防守主權線,而應通過保護所謂的“利益線”來實現。他解釋道,“主權線代表國家的疆域,而利益線則是與主權密切相關的戰略區域。如今,國際形勢復雜,單純防守主權線已無法保障國家獨立,必須通過保護利益線來確保國家安全。”
在他的理論中,朝鮮成為了日本“利益線”的核心地帶。他指出,如果其他國家侵犯了日本的“利益線”,日本應當采取強硬手段予以驅逐。這一理論為日本的侵略行為提供了理論支持,使得日本能夠合理化其對外擴張的行動。山縣有朋的“保護利益線”理念,最終為日本的侵略戰爭提供了理論依據,并為后來的甲午戰爭鋪平了道路。自此以后,日本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以這一政策為指導,展開了對朝鮮、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侵略行動,持續擴張其在東亞乃至全球的勢力。
在日本開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期間,間諜活動和情報搜集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日本政府積極利用各種手段,派遣特工和間諜滲透進入中國,執行從情報收集到制造社會動蕩等一系列的任務,為其軍事擴張提供支持。這些間諜活動的主導力量主要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等軍事機關構成,同時也有一些右翼民間組織參與其中,它們通常與政府及軍方有著緊密的聯系。陸軍和海軍的間諜活動是日本軍事行動的核心,外務省有時也會參與到其中。
回顧日本從明治維新到甲午戰爭期間的軍事體制變化,可以看到,間諜活動和戰略謀劃的作用日益突出。1868年,明治政府推翻了幕府體制,開始設立新的軍事指揮機構,逐步發展出了以軍隊和海軍為主的強大體系。1878年,日本仿效德國的軍事體制改革,將參謀局從陸軍省獨立出來,設立了參謀本部,成為直屬于天皇的軍令機關。從此,參謀本部的設立標志著日本逐漸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而它對外進行間諜活動的目的之一,就是為日本的擴張計劃做好準備,尤其是針對中國、朝鮮和俄國等鄰國。
到了1893年,日本的軍事指揮體系逐漸完善,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成為了日本最主要的軍事情報和間諜指揮機關。大本營的設立進一步增強了這些機關的協調能力,成為了指揮全軍、制定戰爭計劃以及派遣間諜的中心。大本營不只是指揮戰爭的工具,它還成為了對外間諜活動的核心。
在這一系列的間諜活動中,有兩位人物的作用尤為突出,他們分別是川上操六和樺山資紀。川上操六,出身于鹿兒島,曾參與多個軍事考察,他的情報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國和朝鮮。他曾親自率隊考察中國的軍事力量,包括兵員、武器裝備以及軍隊的作戰能力。尤其是在天津訪問期間,他通過與李鴻章的接觸,深入了解了中國的軍事狀況,并得出結論認為“中國不足畏”,這一觀點促使他更加堅定了日本對中國侵略的決心。
另一方面,樺山資紀同樣對日本的間諜活動起到了關鍵作用。作為海軍高級將領,他早期在中國執行情報任務,后來參加了甲午戰爭,并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擔任海軍大臣期間,樺山資紀不僅為日本海軍的擴張做出了貢獻,還為日本海軍的情報活動奠定了堅實基礎。
除了軍方的參與,日本的一些右翼團體也積極參與了間諜和謀略活動。其中,玄洋社尤為出名,它被認為是日本第一個在海外進行秘密間諜行動的組織。正如英國著名的情報史學者理查德·迪肯所指出,盡管日本的情報機構最初并不強大,但通過與一些愛國秘密社團合作,快速提升了其情報能力,最終使得日本的間諜活動在短短幾十年內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玄洋社成立于1881年,地點位于九州的福岡,創始人包括頭山滿、平岡浩太郎與箱田六輔等人。平岡浩太郎擔任了社長職務。社名的由來源自一段自夸的話,意思是如同玄海(位于九州北部的玄海灘)洶涌的波濤,力量能撼動天際。玄洋社宣揚的宗旨包括“尊皇衛民”和“愛國重民”,并提出了所謂的天皇主義、國權主義和民權主義三大原則。然而,隨著日本逐漸走向軍國主義,玄洋社的立場發生了變化,它開始激烈支持對外擴張,倡導侵略其他國家。與軍方、財閥及官僚之間的關系緊密,使它成為日本對外戰爭中的積極推動者,甚至在間諜活動和策劃謀略方面,成為了軍方的重要幫手,外界給予它“恐怖組織與間諜學校”的稱號。一系列的陰謀活動,往往與頭山滿和平岡浩太郎這兩個名字緊密相連。
頭山滿,1855年出生于福岡縣。早年曾參與反對政府的運動,甚至加入了西鄉隆盛的叛亂,結果被捕入獄。1878年,他和其他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向陽社。到了1881年,頭山滿通過號召“辦教育培養民權”,聯合其他政治團體,成立了玄洋社。此后,他積極鼓吹“尊皇主義”和“國家主義”,并在對外政策上提倡“大亞細亞主義”,力推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略,尤其在日本政界和社會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頭山滿還親自策劃了許多恐怖活動,例如1889年向外務大臣大限重信投擲炸彈事件,和1913年暗殺外務省政務局長阿部守太郎的行動。中國末代皇帝溥儀曾回憶過頭山滿的影響力,稱他的黨羽滲透到中國的各個階層,從清朝末年的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無不充滿了深謀遠慮的活動。許多日本名人,如土肥原、廣田、平沼、香月等,都曾是頭山滿的學生,深受其思想的影響。
據說,頭山滿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留著銀色的長須,面容慈祥,尤其喜愛玫瑰花,并在花園中度過大部分時光。盡管如此,他卻在這樣的寧靜氛圍中,策劃了一個又一個陰險的陰謀,使得他的“慈祥”面容和狠毒的心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如鄭孝胥所形容的那樣,頭山滿的外表和性格,看似溫和,實則冷酷無情。
平岡浩太郎,生于1851年,同樣來自九州福岡縣。年輕時,他曾參與西鄉隆盛的叛亂活動,結果被捕入獄,獲釋后便投身于“民權運動”。隨著玄洋社的成立,平岡浩太郎成為了社長。在他的領導下,玄洋社逐漸擴大其活動范圍,平岡浩太郎不僅參與政治活動,還經營銅礦和煤礦,為日本政府的擴張提供了資金支持。1884年,他與末廣重恭、中江篤介等人來到上海,開辦東洋學館,培養間諜和策士。甲午戰爭前,他積極參與反華宣傳,與參謀本部的次長川上操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結成了志同道合的聯盟。甲午戰爭后,平岡浩太郎的活動重心轉向了俄羅斯,他策動玄洋社成員開展情報收集工作。1894年以后,平岡浩太郎多次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在日本政界擁有極大的影響力。
在頭山滿與平岡浩太郎的共同領導下,玄洋社迅速發展壯大,成為了日本軍方對外進行間諜活動和策略部署的重要力量,參與了多次針對他國的陰謀和行動,為日本的軍國主義擴張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