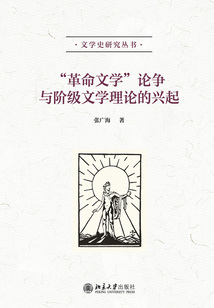
“革命文學(xué)”論爭(zhēng)與階級(jí)文學(xué)理論的興起
最新章節(jié)
- 第32章 注釋
- 第31章 后記
- 第30章 參考文獻(xiàn)
- 第29章 結(jié)語(yǔ)
- 第28章 小結(jié)(6)
- 第27章 在文學(xué)與政治之間——茅盾與革命文學(xué)派圍繞小資產(chǎn)階級(jí)問(wèn)題的論爭(zhēng)
第1章 《緒論》:“革命”與“革命文學(xué)”在近代中國(guó)的生成
1895年10月,在謀劃廣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逃出廣州,并于11月中旬輾轉(zhuǎn)抵達(dá)日本神戶。據(jù)隨行的興中會(huì)會(huì)員陳少白記述:
到了神戶,就買(mǎi)份日?qǐng)?bào)來(lái)看看。我們那時(shí),雖然不認(rèn)識(shí)日文,看了幾個(gè)中國(guó)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見(jiàn)“中國(guó)革命黨孫逸仙”等字樣,赫然耀在眼前。我們從前的心理,以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們的行動(dòng)只算造反而已。自從見(jiàn)了這張報(bào)紙以后,就有“革命黨”三字的影象印在腦中了。[1]
這段話為“革命”一詞在漢語(yǔ)語(yǔ)境中的意義轉(zhuǎn)換提供了一個(gè)生動(dòng)的例證。在中國(guó)傳統(tǒng)語(yǔ)境中,“革命”主要意指“湯武革命”式的改朝換代。這種含義自然不能為追求現(xiàn)代政體之建立的“革命者”接受,故而他們只愿意把自己的行為理解為“造反”。[2]但由于“革命”本就具有造反和根本變革等相通于revolution的含義,又受日本把revolution譯為“革命”的影響,在當(dāng)時(shí)的漢語(yǔ)世界,用“革命”來(lái)泛指各種謀求現(xiàn)代變革的“造反”行為的用法其實(shí)已不罕見(jiàn),并日漸流行起來(lái);“法國(guó)革命”則成為“革命”的范本。[3]不過(guò)直到1902年,梁?jiǎn)⒊詧?zhí)意指出,“革命”并非revolution的“確譯”,蓋因其在中國(guó)“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當(dāng)Revo.之意也”,并主張以“變革”譯之。梁?jiǎn)⒊⒅匾院蠊麃?lái)驗(yàn)證是否為真“革命”,而反對(duì)拘泥于以暴力推翻一姓統(tǒng)治的“形式”革命,其意圖在于和革命派爭(zhēng)奪“revolution”的闡釋權(quán),確證自家“變革”路徑的合法性;對(duì)革命正當(dāng)性的堅(jiān)持、對(duì)革命意味著“若轉(zhuǎn)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一新世界”[4]的理解,其與革命派并無(wú)區(qū)別。
梁?jiǎn)⒊岢淖g法并未產(chǎn)生什么影響,這主要因?yàn)椤案锩币辉~所包含的隱秘暴力和根本推翻的意味,實(shí)在是對(duì)revolution的最佳移譯,由此生出的話語(yǔ)快感更為其他詞語(yǔ)難以比擬。[5]擔(dān)心革命異化為王朝易姓,固然也植根于革命的進(jìn)化訴求,但已然從屬于革命的后果。
革命是一種“造反”,但與“造反”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它植根于現(xiàn)代社會(huì)追求進(jìn)步的意識(shí)形態(tài)。啟蒙運(yùn)動(dòng)解放了人的理性,伴隨著對(duì)自我理性能力之確信的增強(qiáng),“人們普遍接受按照一個(gè)新的、更好的模式重新組織社會(huì)的信念”[6],這為革命的產(chǎn)生做了思想鋪墊。而同時(shí),革命也開(kāi)始在不同語(yǔ)境下被不同意識(shí)形態(tài)塑造,從而顯示出不同形態(tài)。
在清末,雖然革命被民眾接受的程度有日趨升高之勢(shì),但離被多數(shù)民眾普遍接受仍有較遠(yuǎn)距離,對(duì)革命的恐懼仍然籠罩著人心,以革命為號(hào)召的團(tuán)體也主要只有同盟會(huì)一家。民初,“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輿論興起,同盟會(huì)亦轉(zhuǎn)型為議會(huì)政黨,“革命”似將偃旗息鼓。但1913年宋教仁案后孫中山發(fā)起“二次革命”,“革命”的號(hào)召再次崛起。到了1920年代初期,伴隨著北洋政府執(zhí)政合法性的急遽流失,革命已為多數(shù)黨派認(rèn)同,“除中國(guó)國(guó)民黨外,新起的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和中國(guó)青年黨亦以革命為訴求。革命的形勢(shì)由清末的‘一黨獨(dú)革’演變?yōu)椤帱h競(jìng)革’的局面”。[7]
1924年1月,國(guó)共兩黨合作展開(kāi)“國(guó)民革命”。這時(shí),支配了兩黨“革命”理解的是受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jí)斗爭(zhēng)理論改造的三民主義;自然,兩黨的意識(shí)形態(tài)并未劃一,共產(chǎn)主義革命觀和三民主義革命觀既有大量重疊,也有顯著差異。這表現(xiàn)為共產(chǎn)主義革命在根柢里是階級(jí)革命,它追求在國(guó)民革命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無(wú)產(chǎn)階級(jí)專政;同時(shí),它也不局限于民族主義范疇內(nèi)的“反帝”,而追求世界革命的目標(biāo)。[8]國(guó)民革命與此前的中國(guó)革命有了顯著不同,它傾向于謀求社會(huì)關(guān)系的根本變革。身處國(guó)民革命高潮時(shí)期的毛澤東,在目睹了湖南農(nóng)村階級(jí)革命“好得很”的形勢(shì)之后,對(duì)“革命”做了一個(gè)后來(lái)產(chǎn)生了世界性影響力的界定:
革命不是請(qǐng)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huà)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zhì)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dòng)〈,〉是一個(gè)階級(jí)推翻一個(gè)階級(jí)的權(quán)力的暴烈的行動(dòng)……[9]
這里的“革命”,顯然是階級(jí)斗爭(zhēng)視野下的革命;但受制于國(guó)民黨主導(dǎo)國(guó)共合作的時(shí)代條件,它并不能得到完美的張揚(yáng)。伴隨著北伐戰(zhàn)爭(zhēng)的快速推進(jìn),這種訴諸階級(jí)對(duì)抗的革命在戰(zhàn)爭(zhēng)后方一度有如火如荼的發(fā)展,不過(guò)其所采取的主要形態(tài)為發(fā)生在農(nóng)村的階級(jí)對(duì)抗,但也終因其發(fā)展迅猛,加速了國(guó)共合作的破裂。[10]1927年南昌起義后,中共的革命活動(dòng)轉(zhuǎn)入地下?tīng)顟B(tài)。
與“革命”在近代中國(guó)的生成與發(fā)展相應(yīng)的,是“革命文學(xué)”在文壇的出現(xiàn)并趨向活躍。“革命文學(xué)”這一名詞何時(shí)首次在中國(guó)出現(xiàn),不易判斷。有學(xué)者曾選編晚清文獻(xiàn)輯成《晚清革命文學(xué)》一書(shū),全書(shū)近20萬(wàn)字,輯錄文獻(xiàn)中僅出現(xiàn)了一次“革命文學(xué)”,即楊守仁在其小冊(cè)子《新湖南》中談到俄國(guó)無(wú)政府黨時(shí),指出壓制愈強(qiáng)則反抗愈烈,“故夫壓抑者,反對(duì)之良友,而破壞之導(dǎo)師也。是故俄國(guó)之虛無(wú)主義,自革命文學(xué)時(shí)期,升而為游說(shuō)煽動(dòng)時(shí)期;自游說(shuō)煽動(dòng)時(shí)期,升而為暗殺恐怖時(shí)期”[11]。楊守仁1902年留日,《新湖南》1903年在日出版,此處表述明顯參考了日本學(xué)者煙山專太郎于1902年出版的專著《近世無(wú)政府主義》。“革命文學(xué)時(shí)期”,在該書(shū)中即寫(xiě)作“革命文學(xué)の時(shí)期”。[12]不過(guò)楊氏并未對(duì)“革命文學(xué)”的內(nèi)涵做進(jìn)一步闡發(fā),考察文意,指的大體是富有革命宣傳作用的文章。《晚清革命文學(xué)》選錄“革命文學(xué)”作品,依據(jù)的標(biāo)準(zhǔn)也是“宣傳革命的文字泛稱為革命文學(xué)”[13],整本書(shū)沒(méi)有收錄一篇嚴(yán)格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學(xué)”作品。檢索各大數(shù)據(jù)庫(kù)會(huì)發(fā)現(xiàn),在清末及民國(guó)建立后十年內(nèi),針對(duì)“革命文學(xué)”的提倡或討論極少。最早稍有系統(tǒng)地論述“革命文學(xué)”問(wèn)題的當(dāng)屬梁?jiǎn)⒊K瑯邮艿健督罒o(wú)政府主義》的影響,于1905年初在《新民叢報(bào)》發(fā)表《俄羅斯革命之影響》一文,提到尼古拉一世時(shí)期的俄國(guó),“行絕對(duì)嚴(yán)酷之專制政治”,導(dǎo)致“人民益顛沛無(wú)所控訴”,于是“及[反]動(dòng)力漸起,革命文學(xué),盛于時(shí)矣”。梁?jiǎn)⒊⑶医Y(jié)合俄國(guó)文學(xué)的發(fā)展演進(jìn),論證了俄國(guó)的“革命運(yùn)動(dòng)之第一期即文學(xué)鼓吹期也”。[14]
1907年初,革命黨人廖仲愷在《民報(bào)》上翻譯了煙山專太郎的《近世無(wú)政府主義》第三章,其中重點(diǎn)論述了楊守仁所曾引述的俄國(guó)無(wú)政府主義的三期發(fā)展。雖然廖仲愷在標(biāo)題中將“革命文學(xué)の時(shí)期”譯為“文學(xué)革命時(shí)代”,但當(dāng)系誤譯,因?yàn)檎闹羞€是譯作“革命文學(xué)之時(shí)期”。[15]不過(guò)該譯文更多論述的是革命思潮影響下的俄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僅有一處專門(mén)提及“革命文學(xué)”。即1861年冬,面對(duì)保守勢(shì)力反撲,俄國(guó)虛無(wú)黨、社會(huì)黨、立憲黨等展開(kāi)輿論回?fù)簦跋鹿P千言,倚馬可待”,“傳檄全國(guó)青年”,“革命文學(xué)之景運(yùn),昌明極矣”。[16]可見(jiàn),此處的“文學(xué)”含義已經(jīng)十分泛化,溢出了“文學(xué)”的現(xiàn)代含義之外,而與“文章”大體同義。至1912年,又有人翻譯過(guò)一篇《革命與文學(xué)》,介紹了法國(guó)和俄國(guó)的革命運(yùn)動(dòng)對(duì)文學(xué)的影響,但基本上把文學(xué)的變化視作對(duì)革命的反映,而未論述文學(xué)是否也能對(duì)革命產(chǎn)生重要影響。[17]不過(guò)此文便是在現(xiàn)代意義上使用“文學(xué)”概念。在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語(yǔ)境中,文學(xué)的現(xiàn)代含義已經(jīng)快速輸入,但傳統(tǒng)含義尚未退場(chǎng)。兩種“文學(xué)”——或說(shuō)兩種“革命文學(xué)”——的雜陳仍然在延續(xù)。直到1923年,汪精衛(wèi)給《南社叢選》所作的序言,對(duì)“文學(xué)”的革命作用給予了高度評(píng)價(jià),但其所謂“革命文學(xué)”其實(shí)仍不脫傳統(tǒng)文章的范疇,而未界定與一般的“革命之文字”有何區(qū)別:
中國(guó)之革命文學(xué),自庚子以后,始日以著。其影響所及,當(dāng)日之人心,為之轉(zhuǎn)移,而中華民國(guó)于以成。此治中國(guó)文學(xué)史者,所必不容忽也。近世各國(guó)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學(xué)為之前驅(qū)。此革命文學(xué)之采色,必爛然有以異于其時(shí)代之前后。中國(guó)之革命文學(xué)亦然。核其內(nèi)容,與其形式,固不與庚子以前之時(shí)務(wù)論相類(lèi),亦與民國(guó)以后之政論,絕非同物。蓋其內(nèi)容,則民族民權(quán)民生之主義也。其形式之范成,則含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國(guó)學(xué),以經(jīng)義史事諸子文辭之菁華,為其枝干;其一,根柢于西學(xué),以法律政治經(jīng)濟(jì)之義蘊(yùn),為其條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扶。……革命黨人所能勇于赴義,一往無(wú)前百折而不撓者,持此革命文學(xué)以自涵育,所以能一變?nèi)倌陙?lái)淹淹不振之士氣。使即于發(fā)揚(yáng)蹈厲者,亦持此革命文學(xué)以相感動(dòng)也。[18]
但汪精衛(wèi)的文字也揭示出,情辭動(dòng)人的文字足以成為革命的先驅(qū);這種認(rèn)識(shí)便是“革命文學(xué)”所以應(yīng)該存在的最堅(jiān)實(shí)理由。還在1921年,鄭振鐸和費(fèi)覺(jué)天便明確指出了這一點(diǎn)。在一篇題名《文學(xué)與革命》的文章中,鄭振鐸首先援引了費(fèi)覺(jué)天的信件。費(fèi)氏在信中感慨五四后青年很快日漸消沉,并認(rèn)為青年的奮發(fā)必須依賴感情的激發(fā),文學(xué)于是成為重要工具:“單從理性的批評(píng)方面,攻擊現(xiàn)制度,而欲以此說(shuō)服眾人,達(dá)到社會(huì)改造底目的,那是辦不到的。必得從感情方面著手。好比俄國(guó)革命吧,假使沒(méi)有托爾斯泰這一批的悲壯、寫(xiě)實(shí)的文學(xué),將今日社會(huì)制度,所造出的罪惡,用文學(xué)的手段,暴露于世,使人發(fā)生特種感情,那所謂‘布爾扎維克’恐也不能做出甚么事來(lái)。”因?yàn)橛袑?duì)理性與情感之效用的這種看法,費(fèi)氏提出,現(xiàn)在中國(guó)最為迫切的便是“產(chǎn)出幾位革命的文學(xué)家”,“激刺大眾底冷心,使其發(fā)狂,浮動(dòng),然后才有革命之可言”。所以中國(guó)“能夠擔(dān)當(dāng)改造底大任,能夠使革命成功的,不是甚么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家,而是革命的文學(xué)家”。鄭振鐸完全同意費(fèi)覺(jué)天的意見(jiàn),繼而指出,“理性是難能使革命之火復(fù)燃的。因?yàn)楦锩烊皇歉星榈氖隆薄8锩鹩凇耙驗(yàn)橥春奕碎g的傳襲的束縛,所以起了自由的呼聲;因?yàn)榭戳吮粔浩鹊妮氜D(zhuǎn)哀鳴,所以動(dòng)了人道的感情”。而觸發(fā)革命的感情“只有文學(xué),才能勝任”,因?yàn)椤拔膶W(xué)本是感情的產(chǎn)品”,所以它“最容易感動(dòng)人,最容易沸騰人們的感情之火”。此一立基于人性情感之共鳴的“革命文學(xué)”模式在大革命時(shí)期被發(fā)揚(yáng)光大,一直到“革命文學(xué)”論爭(zhēng)時(shí)期才被立基于階級(jí)意識(shí)和階級(jí)情感分裂理論的無(wú)產(chǎn)階級(jí)“革命文學(xué)”模式取代。鄭振鐸其實(shí)在當(dāng)時(shí)就已經(jīng)對(duì)何以會(huì)被取代做了提示,即他指出,投身革命幾乎都因?yàn)椤皠?dòng)了人道的感情”,“至于因確信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而趨向于社會(huì)革命的路上走的,恐怕是很少”。[19]
對(duì)文學(xué)的革命效能給予如此高規(guī)格的強(qiáng)調(diào),源于對(duì)情感之作用的高規(guī)格認(rèn)識(shí);后來(lái)持理性節(jié)制情感學(xué)說(shuō)的梁實(shí)秋,對(duì)這種革命文學(xué)自然難以首肯。但還在更早的時(shí)候,魯迅依據(jù)對(duì)文學(xué)培養(yǎng)精神之能力的認(rèn)識(shí),就給予過(guò)文學(xué)相似的高度評(píng)價(jià)。雖然魯迅也指出,“由純文學(xué)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shù)之本質(zhì),皆在使觀聽(tīng)之人,為之興感怡悅……與個(gè)人暨邦國(guó)之存,無(wú)所系屬,實(shí)利離盡,究理弗存”,但也正因文學(xué)可以使“人乃以幾于具足”,于是便具有了保家衛(wèi)國(guó)的重要作用。魯迅論述的摩羅詩(shī)人雖并不斤斤于功利,但無(wú)不具有偉大的社會(huì)效用。比如當(dāng)魯迅談及德國(guó)詩(shī)人時(shí),認(rèn)為“故推而論之,敗拿坡侖者,不為國(guó)家,不為皇帝,不為兵刃,國(guó)民而已。國(guó)民皆詩(shī),亦皆詩(shī)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20]。論及俄國(guó),乃認(rèn)為俄羅斯的崛起本源于三名詩(shī)人。[21]而波蘭人也是被詩(shī)人感動(dòng),于是舉行大起義。[22]魯迅雖未提及“革命文學(xué)”,但其所論述的“文學(xué)”,未嘗不可以“革命文學(xué)”名之。魯迅的此一認(rèn)知,其后雖被諸多因素沖淡,但也不絕如縷地延續(xù)入大革命時(shí)期。[23]
雖然有著重視文學(xué)的革命效用的呼聲,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革命文學(xué)”并未成為被重點(diǎn)號(hào)召的對(duì)象。不論是近代的“詩(shī)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shuō)界革命”,還是后來(lái)的“文學(xué)革命”,“革命”雖與“文學(xué)”并稱,但“革命”一詞的采用不過(guò)表示對(duì)革命的追摹與憧憬,并無(wú)直接地借文學(xué)以發(fā)起革命的意圖。中國(guó)的“革命文學(xué)”提倡,1920年后才盛行開(kāi)來(lái)。興起的原因,一則由于國(guó)外“革命文學(xué)”的激發(fā)[24],二則由于革命與革命思潮的快速崛起,而后者顯然為主因。
1923年開(kāi)始,中國(guó)的“革命文學(xué)”提倡漸入高潮。1923年提倡革命文學(xué)的主要陣地是中國(guó)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tuán)的機(jī)關(guān)刊物《中國(guó)青年》,提倡者主要是鄧中夏、惲代英、蕭楚女等早期共產(chǎn)黨人,但他們還并未重點(diǎn)打出“革命文學(xué)”的旗幟,提倡的要點(diǎn)是要求文學(xué)承擔(dān)起社會(huì)改造的使命,要求文學(xué)家積極投身于革命,而訴諸的重點(diǎn)仍然在“感情”方面。比如惲代英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是“人類(lèi)高尚圣潔的感情的產(chǎn)物”,所以文學(xué)家必須“投身于革命事業(yè),培養(yǎng)你的革命的感情”,才可能創(chuàng)作出“革命文學(xué)”。[25]1924年提倡革命文學(xué)的主要陣地則是國(guó)民黨的機(jī)關(guān)報(bào)《民國(guó)日?qǐng)?bào)》的副刊《覺(jué)悟》。此時(shí)國(guó)共合作已經(jīng)展開(kāi),國(guó)民革命也開(kāi)始推行,國(guó)民黨的宣傳活動(dòng)日趨正規(guī)化[26],于是《覺(jué)悟》上出現(xiàn)了一大批明確提倡“革命文學(xué)”的宣傳文字(如其中一篇便題名《請(qǐng)智識(shí)階級(jí)提倡革命文學(xué)》[27])。對(duì)革命文學(xué)的提倡仍多依據(jù)于感情具有勝于理性的力量。比如當(dāng)看到葉圣陶在《文學(xué)》上提出革命者更為急需,革命文學(xué)不必刻意鼓吹,革命者的作品無(wú)不含有革命的意味時(shí)[28],中共黨員許金元便在《覺(jué)悟》上批評(píng)葉圣陶,指出,“理智”只能告訴人們?cè)摬辉撟鲆患拢軟Q定去不去做的只有“情感”,“文學(xué)底原動(dòng)力正是情感”,所以提倡“革命文學(xué)”是造成革命者的重要途徑。[29]幾乎完全是費(fèi)覺(jué)天和鄭振鐸觀點(diǎn)的翻版。另一位中共黨員沈澤民則特別看重革命文學(xué)統(tǒng)一民眾情緒的作用:
文學(xué)者不過(guò)是民眾的舌人,民眾的意識(shí)的綜合者:他用銳敏的同情,了澈被壓迫者的欲求,苦痛,與愿望,用有力的文學(xué)替他們渲染出來(lái);這在一方面,是民眾的痛苦的慰藉,一方面卻能使他們潛在的意識(shí)得了具體的表現(xiàn),把他們散漫的意志,統(tǒng)一凝聚起來(lái)。一個(gè)革命的文學(xué)者,實(shí)是民眾情緒生活的組織者。這就是革命的文學(xué)家在這革命的時(shí)代中所能成就的事業(yè)![30]
革命文學(xué)的作用在于統(tǒng)一民眾的革命情緒,可謂大革命時(shí)期革命文學(xué)宣傳的普遍內(nèi)容。大革命失敗后成立的太陽(yáng)社,最初也持此一認(rèn)知。[31]
與此同時(shí),創(chuàng)造社也開(kāi)始從一個(gè)提倡天才、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社團(tuán)向“革命”轉(zhuǎn)向,成員陸續(xù)投身大革命的浪潮當(dāng)中,理論主張也偏向到革命文學(xué)方面來(lái)。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徹底的自我否定。創(chuàng)造社的理論本就糾纏于審美無(wú)功利與功利主義的復(fù)雜關(guān)系中,其浪漫的情感主張其實(shí)天然地傾向于革命。當(dāng)他們提倡革命文學(xué)時(shí),也仍然致力于從人性與情感的層面來(lái)立論。成仿吾的革命文學(xué)公式為:“(真摯的人性)+(審美的形式)+(熱情)=(永遠(yuǎn)的革命文學(xué))。”[32]郭沫若則把革命文學(xué)看作實(shí)現(xiàn)情感共鳴的重要工具,并把情感的強(qiáng)烈和普遍程度視作判斷革命文學(xué)優(yōu)劣的標(biāo)準(zhǔn):
我們知道文學(xué)的本質(zhì)是始于感情終于感情的。文學(xué)家把自己的感情表現(xiàn)出來(lái),而他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識(shí)的或無(wú)意識(shí)的——總是在讀者心中引起同樣的感情作用的。那嗎作家的感情愈強(qiáng)烈愈普遍,而作品的效果也就愈強(qiáng)烈愈普遍。這樣的作品當(dāng)然是好的作品。……革命時(shí)代的希求革命的感情是最強(qiáng)烈最普遍的一種團(tuán)體感情,由這種感情表現(xiàn)而為文章,來(lái)源不窮,表現(xiàn)的方法萬(wàn)殊,所以一個(gè)革命的時(shí)期中總含有一個(gè)文學(xué)的黃金時(shí)代了。[33]
在大革命時(shí)期,作為革命中心的廣州和武漢都有著熱烈的“革命文學(xué)”實(shí)踐和理論提倡。[34]總體而言,這些“革命文學(xué)”,雖也時(shí)常混雜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原理,但大都以訴諸人性的情感共鳴為要旨,并難免有泛濫成俗套的趨勢(shì),以致被魯迅譏為“同情文學(xué)”[35]。它們的命運(yùn),終結(jié)于“革命文學(xué)”論爭(zhē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