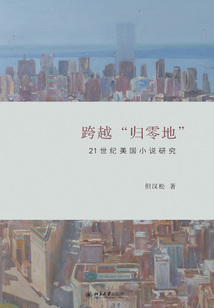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前言
在所有關(guān)于雙子塔的攝影作品中,最觸動我的不是爆炸和廢墟,而是1997年美國小說家唐·德里羅(Don DeLillo)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英文版的封面用圖。畫面的背景是云遮霧繞的世貿(mào)中心雙子塔,前景則是一座教堂的山墻和十字架的剪影,右上角還有一只形狀如同飛機(jī)的海鳥。這些視覺元素以一種詭異的未卜先知,暗示了這個城市來自空中的危險以及即將升騰的爆炸煙霧。事實(shí)上,在世貿(mào)中心遺址對面不遠(yuǎn)處,就有一座建于1766年的圣保羅禮拜堂,那里還豎立著曼哈頓島上一些先民們的古老墓碑,它們比這個國家的歷史還久遠(yuǎn)。這個教堂在1970年代見證了世貿(mào)中心大樓充滿爭議的修建過程,也在21世紀(jì)的頭一年見證了作為全球金融資本主義象征的雙子塔的爆燃和垮塌。盡管雙子塔倒塌時能量極大,周圍很多建筑受到?jīng)_擊,但近在咫尺的圣保羅禮拜堂卻安然無恙,這的確是9·11事件中一件不大不小的神跡。于是,在紐約消防員和警察搶險救災(zāi)的最初幾周里,這個教堂成為了“歸零地”(Ground Zero)旁的一座“圣殿”,不僅是市民們悼念亡者的地方,也是換班消防員臨時休息的場所。
2008年夏天,我作為中美富布賴特項(xiàng)目的訪問學(xué)生,第一次來到美國。初秋的一次紐約之行,我特意去看曼哈頓下城的世貿(mào)中心廢墟,剛好路過這個古老的教堂,就進(jìn)去參觀。讓我驚訝的是,里面還保留著當(dāng)年救災(zāi)人員用過的行軍床,還有用犧牲消防員的照片和紀(jì)念徽章裝飾的紀(jì)念角。在布道講壇的上方,懸掛著一個醒目的條幅,寫著“俄克拉荷馬人民與紐約同在”。當(dāng)時我突然想到,在9·11之前,美國本土發(fā)生的最大一次恐怖襲擊,正是在俄克拉荷馬——1995年,那個叫蒂莫西·麥克維(Timothy McVeigh)的人將7000磅的炸藥裝在卡車上,運(yùn)到俄克拉荷馬城聯(lián)邦政府大樓樓下引爆,造成了168人死亡,500多人受傷。不過,與9·11的19名劫機(jī)犯不同,麥克維是美國白人,而且作為海灣戰(zhàn)爭的老兵,他甚至還自詡為“愛國者”。麥克維被執(zhí)行死刑的時間是2001年6月11日,當(dāng)時美國人或許舒了一口氣——畢竟,這個在美國本土制造了最嚴(yán)重的恐怖襲擊的人被處死了。但誰能想到,僅僅三個月之后,更大的悲劇發(fā)生了!
也是在2008年,我作為博士生訪問學(xué)者在馬里蘭大學(xué)英文系旁聽了琳達(dá)·考夫曼(Linda Kauffman)教授的“美國當(dāng)代小說”課。她在課堂上特別推崇的書,正是德里羅前一年剛出版的《墜落的人》(Falling Man)。那本書的封面,同樣令我印象深刻:業(yè)已消失的雙子塔聳立在萬米高空的云海中,作為世俗之物的摩天樓仿佛被賦予了一種“后現(xiàn)代崇高”。考夫曼教授在課堂上拿著這本書告訴學(xué)生們,美國最偉大的在世作家終于用小說對那次改變世界的恐怖襲擊做出了回應(yīng),為了這一天的到來,美國批評家們已經(jīng)等待了很久。正是在那個時刻,我萌生了研究9·11文學(xué)的想法。
時光荏苒,14年過去了,我的生活和這個世界一樣,已經(jīng)有了太多變化。2019年8月,我再次作為富布賴特項(xiàng)目訪問學(xué)者,帶著家人來到弗吉尼亞的夏洛特維爾生活學(xué)習(xí)。此時,人們似乎不再經(jīng)常提起9·11,但當(dāng)今世界發(fā)生的很多大事件,又和那次恐怖襲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美國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戰(zhàn)爭,它們成為該國史上最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時間超過了越戰(zhàn)、“二戰(zhàn)”和美國內(nèi)戰(zhàn);原本被認(rèn)為針對美國霸權(quán)主義的恐怖襲擊變身為全球恐怖主義,如病毒般侵襲倫敦、巴黎、馬尼拉、孟買、內(nèi)羅畢、摩加迪沙、布魯塞爾、奧斯陸、基督城等等,極端分子對平民制造的殺戮每隔一段時間就成為世界新聞的頭條;“阿拉伯之春”、敘利亞內(nèi)戰(zhàn)觸發(fā)了巨大的地緣政治危機(jī),造成了歐洲史無前例的難民潮,由此又間接引發(fā)了英國脫歐和極右政治勢力在歐洲多國的興起;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主義在“后9·11”時代登上了美國政治舞臺,他推行強(qiáng)硬的反移民立場和政治單邊主義,引燃反全球化的貿(mào)易戰(zhàn)……
在這14年里,不僅世界有了不一樣的面貌,美國文學(xué)、歐洲文學(xué)乃至世界文學(xué)也都有了重大變化。有更多涉及9·11、恐怖主義、反恐、伊拉克戰(zhàn)爭和阿富汗戰(zhàn)爭的小說相繼問世,當(dāng)中不乏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經(jīng)典之作,有些已經(jīng)獲得了重要的文學(xué)獎項(xiàng)。誠然,嚴(yán)肅文學(xué)對于9·11及其之后世界變化的再現(xiàn)存在一定的滯后性,但文學(xué)絕不只是時代風(fēng)潮的傳聲筒,而是積極參加了話語生產(chǎn)和媒介化過程,并以文學(xué)獨(dú)特的內(nèi)省、多元、共情和含混,介入“后9·11”文化的眾聲喧嘩中,對抗大眾媒體和國家機(jī)器的壟斷性話語。美國批評家萊昂納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曾說過:“文學(xué)是最充分、最全面地思考多樣性、可能性、復(fù)雜性和困難性的人類活動。”[1]鑒于9·11事件及“后9·11”狀況的復(fù)雜性,文學(xué)家當(dāng)然會直面這一挑戰(zhàn),并將之作為當(dāng)代文學(xué)的重要母題加以書寫。
在談?wù)?·11文學(xué)這個話題之前,有必要先對我們耳熟能詳?shù)?·11事件做一番歷史梳理。但其實(shí)更重要的前期工作,反倒是先理解何為“事件”(event)。在《韋伯斯特字典》(Websters Universal Dictionary)中,event的釋義是“某件發(fā)生之事(尤其指重要或矚目的事)”。如果考察一下詞源,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它來自拉丁語evenire,意思是“出現(xiàn)、到達(dá)、發(fā)生”,往往意味著“變化、影響”。[2]這樣的字典解釋看似無甚稀奇之處,但對于當(dāng)代西方哲學(xué)家而言,event卻是一個殊為復(fù)雜的關(guān)鍵概念。法國思想家福柯認(rèn)為,事件是與歷史的斷裂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事件的出現(xiàn)往往伴隨著對社會規(guī)范和知識系統(tǒng)的觀念重構(gòu)。對巴迪歐(Alain Badiou)來說,事件有著更為核心的本體論地位。在《存在與事件》(Being and Event)中,巴迪歐說“事件”不是事物秩序產(chǎn)生的“影響”,而事物秩序的“斷裂”(rupture),正是在這種斷裂中真理才得以開啟。[3]德里達(dá)亦有相似的看法,他認(rèn)為事件意味著“一種絕對的驚奇”[4],并認(rèn)為它“具有無限的秘密形式”[5],無法被理解和預(yù)設(shè)。
由此可見,對于哲學(xué)家而言,事件并非簡單的“發(fā)生之事”,而是對我們?nèi)粘I睢⒊WR規(guī)范乃至歷史進(jìn)程的一種打破。在巴迪歐的視野里,最典型的“事件”是耶穌受難、法國大革命、美國獨(dú)立戰(zhàn)爭和納粹屠猶。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發(fā)生在2001年9月11日紐約和華盛頓特區(qū)的恐怖襲擊才成為一次事件。這不僅僅是因?yàn)樗囊?guī)模之大(19人同時劫持了四架波音客機(jī))、傷亡之巨(2977人因此殞命,還有更多的生者因?yàn)楦鞣N后遺癥,遭遇了身體和精神的雙重苦痛)和影響之廣(億萬觀眾在電視和互聯(lián)網(wǎng)直播中目睹北塔被另一架客機(jī)撞上,目睹雙子塔先后倒塌),更是因?yàn)樗囊饬x棲居于曖昧不明的歷史地帶,因?yàn)槲覀儗@個“到來之物”的理解仍然處于永恒的延宕之中。
那么,當(dāng)我們在談?wù)?·11時,我們到底在談?wù)撌裁矗窟@其實(shí)是一個相當(dāng)棘手(如果不是無解)的問題。9·11的事件性決定了它不能僅僅在既有的歷史認(rèn)識框架里被理解和闡釋,與此同時它又比法國大革命那樣的歷史事件更具有當(dāng)代性。所以,9·11帶來的后續(xù)影響非但沒有終結(jié),反而正在我們當(dāng)下的國際政治、意識形態(tài)、文學(xué)想象和日常生活中不斷地發(fā)酵、顯露、變形。我們對它的認(rèn)識不僅無法一蹴而就,而且可能就在我們談?wù)撍南乱幻耄硞€極端分子自殺式炸彈會在巴黎、紐約、孟買、悉尼或倫敦引爆,使得我們對9·11的理解瞬間就會變得不同。試問,在當(dāng)年曼哈頓目擊那次恐怖襲擊的時刻,誰會想到全球恐怖主義的病毒會在今天蔓延得如此猖獗?甚至可以說,我們已經(jīng)無法徹底跳脫9·11來看今日之世界——反恐戰(zhàn)爭、“愛國者法案”、國土安全部、倫敦恐怖襲擊、“虐囚門”、伊拉克戰(zhàn)爭、“棱鏡”計劃、斯諾登、敘利亞內(nèi)戰(zhàn)、“伊斯蘭國”的興起、巴黎恐怖襲擊、歐洲難民危機(jī)等等,無不直接或間接源于星期二的那次事件。
這次恐怖襲擊深刻定義了全球化時代人類共同體的命運(yùn)與困局,它早已超出了某個一時一地的突發(fā)事件的孤立影響,成為全世界被恐怖主義襲擾的象征性開端。斗轉(zhuǎn)星移,十幾年后,當(dāng)恐怖主義的陰影已經(jīng)無比真實(shí)地潛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我們終于發(fā)現(xiàn),其實(shí)沒有哪個國家和社會可以在全球恐怖主義的肆虐中作壁上觀。行文至此,我想到了一個叫呂令子的女孩。9·11發(fā)生的那一年,這位沈陽女孩年僅12歲,即將升入東北育才學(xué)校(東三省最著名的重點(diǎn)中學(xué)之一)就讀,而沙尼耶夫兄弟倆在那一年剛追隨父母,從動蕩的車臣輾轉(zhuǎn)來到美國生活。后來,這位中國女孩飛躍重洋赴美留學(xué),就讀于波士頓大學(xué)。2013年4月15日,就在她與同學(xué)圍觀馬拉松比賽時,沙尼耶夫兄弟倆放在垃圾箱里的自制炸彈突然爆炸,奪去了她年僅23歲的生命。
波士頓馬拉松恐怖襲擊是9·11后發(fā)生在美國本土的最嚴(yán)重的一次恐怖襲擊,一共造成三人死亡,呂令子是其中的一位。生于1993年的恐怖分子喬卡·沙尼耶夫被捕前藏在一個民宅院子中的小艇里,他在一張紙上寫下作案的原因:報復(fù)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對穆斯林的打擊。他還在游艇的船身上留下了兩個英文單詞:“Fuck America”。呂令子之死就像一個寓言,深刻描述了在“后9·11”世界,原本遠(yuǎn)隔萬里、毫無瓜葛的人們?nèi)绾伪辉幃惖芈?lián)結(jié)在一起,并在突如其來的殺戮和報復(fù)中,共同淪為恐怖活動的犧牲品。所以,我始終認(rèn)為,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無論國籍、膚色、信仰或階級為何,對恐怖主義都沒有置身事外的幸運(yùn)或冷眼旁觀的特權(quán),這是由我們所處的“全球命運(yùn)共同體”所決定的。
作為一個生于中國、長于中國的學(xué)者,我感到這樣的時代的文學(xué)藝術(shù)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這不僅是因?yàn)榭植婪肿邮褂玫臉O限暴力最大限度地劫持了大眾傳媒的關(guān)注和想象,從而與文學(xué)藝術(shù)構(gòu)成了競爭關(guān)系,更是因?yàn)榭植乐髁x暴力背后隱藏的邏輯,與文學(xué)藝術(shù)所試圖追求的理想是背道而馳的。如德里羅在一部小說里所言,“(小說家追求的是)含混、矛盾、低語和暗示。而這恰恰是你們(恐怖分子)想去摧毀的”[6]。恐怖暴力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它制造了一種恐懼的政治,而大眾傳媒往往受到資本的挾裹和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無法真正深入地清理這種暴力對于社會肌理的巨大傷害。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一員,我深感全世界的文學(xué)批評家亟須在當(dāng)下展開行動,去對21世紀(jì)陸續(xù)產(chǎn)生的9·11文學(xué)作品做出有價值的闡釋和批評,并以此為契機(jī)去推動更復(fù)雜深遠(yuǎn)的意義生產(chǎn)。我堅信,9·11文學(xué)研究不應(yīng)局限于曼哈頓“歸零地”一時一地的災(zāi)難事件,而應(yīng)在現(xiàn)代性造成的歷史斷裂線中,尋找和反思這種暴力的緣起與流變。
* * *
基于這樣的認(rèn)識,本書將9·11和與之有關(guān)的文學(xué)作品/文學(xué)事件放在寬泛的歷史語境下加以解讀,希望獲得更大的歷史景深。一方面,發(fā)生于新世紀(jì)伊始的9·11恐怖襲擊有著自己的獨(dú)特性(譬如它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景觀并被不斷地媒介化),它不是任何戰(zhàn)后地緣沖突的簡單復(fù)現(xiàn),而是構(gòu)成了當(dāng)代全球史的斷裂點(diǎn)。另一方面,圍繞9·11的國家悲悼和媒體再現(xiàn)往往受制于一種簡單化的文化邏輯,具有不言而喻的短視性。西方主流文化對9·11的悲情化再現(xiàn),讓“歸零地”仿佛具有了某種神圣的意義,讓紐約的受難者們構(gòu)成了一個特殊的、排外的道德共同體。9·11主流敘事往往顯露出西方中心主義的自戀,以及全球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褊狹,因此批評家需要關(guān)注那些具有真正歷史思維的9·11文學(xué)作品,將這次恐怖襲擊放到奧斯維辛、廣島、德累斯頓、俄克拉荷馬等歷史坐標(biāo)構(gòu)成的連續(xù)體中加以討論。
我希望在這本書中實(shí)踐的批評方法,正是這樣一種基于歷史聯(lián)結(jié)的文本話語和審美分析,既重視產(chǎn)生現(xiàn)代恐怖主義的具體而微的時代語境,也觀照恐怖對各個時代的宗教、文化和社會心理意識的深遠(yuǎn)影響。恐怖,不只是當(dāng)代反全球化極端力量的暴力宣泄和話語宣傳,也自古以來就浸淫在人類文明的演進(jìn)及內(nèi)部沖突中。只有當(dāng)我們以更復(fù)雜、更歷史的思維來看待這種特殊的暴力形式,才能更準(zhǔn)確、更深刻地把握現(xiàn)代性和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他者之怒。當(dāng)然,對9·11小說中的恐怖話語進(jìn)行分析并不容易,因?yàn)檫@種話語的語用效果往往是含混的,而且恐怖事件往往不能憑借行動說出自身。換言之,恐怖分子想說的,和他們的恐怖襲擊實(shí)際上說出的,以及受眾接收到的,常常會有著天壤之別。行動一旦轉(zhuǎn)為語言,會帶來巨大的個體理解偏差,也將在不同的闡釋共同體中被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轉(zhuǎn)譯和中介化。按克萊默(Jeffory A.Clymer)的說法,恐怖分子依賴的語言模型之所以往往無法奏效,是因?yàn)樾袆拥氖茉挿绞钱愘|(zhì)的聽眾,“他們的態(tài)度、同情心和政治立場會有巨大的差異”[7]。
這種所指和能指之間的巨大罅隙,使得一些研究者主張對恐怖主義的研究需要采取一種后結(jié)構(gòu)主義的立場,甚至強(qiáng)調(diào)恐怖主義事件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文本化的建構(gòu),它沒有任何脫離語言本身的實(shí)質(zhì)意義。當(dāng)代人類學(xué)家艾倫·費(fèi)爾德曼(Allen Feldman)就認(rèn)為:“(事件的)順序和因果性既是一種道德建構(gòu),也是隱喻建構(gòu),所以事件并非實(shí)際發(fā)生的。事件是可以被敘述的東西。事件是由文化所決定的意義組織起來的行動。”[8]費(fèi)爾德曼通過對北愛爾蘭暴力史的民族志寫作,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概念,即“敘事集團(tuán)”(narrative bloc),強(qiáng)調(diào)暴力敘事生成過程中的多重變量。在這個模型下,事件(event)、作用方(agency)和敘述(narration)三者構(gòu)成了“敘事集團(tuán)”,這種集團(tuán)是“一種彈性的組織,涉及語言、物質(zhì)化的人工制品和關(guān)系。關(guān)于暴力的敘事集團(tuán)調(diào)動了星叢般的事件和關(guān)于事件的話語,從而構(gòu)成一個大寫的事件”[9]。與費(fèi)爾德曼類似,祖萊卡(Joseba Zulaika)和道格拉斯(William A.Douglass)在影響深遠(yuǎn)的《恐怖與禁忌》(Terror and Taboo)一書中,甚至宣稱“不管它還可能是別的什么,恐怖主義是印刷出來的文本……恐怖主義是制造情節(jié)行動的文本,敘事順序是一種道德和話語的建構(gòu)”[10]。
誠然,9·11文學(xué)批評關(guān)注的不只是一個大寫的事件,而是圍繞9·11產(chǎn)生的“敘事集團(tuán)”,它體現(xiàn)了恐怖事件和社會、媒介、語言、敘事的復(fù)雜牽扯與勾連。然而,我們也需要警惕單純從后結(jié)構(gòu)主義立場(無論這種思想資源和批評實(shí)踐是來自哲學(xué)、人類學(xué)、社會學(xué),還是別的學(xué)科)出發(fā)的恐怖主義研究。對于那些親歷恐怖創(chuàng)傷的人來說,恐怖主義也只是“印刷出來的文本”,而缺乏任何本質(zhì)的真相嗎?將事件性歸結(jié)為敘事的建構(gòu),這實(shí)際上已經(jīng)在向相對主義的后現(xiàn)代詭辯術(shù)立場發(fā)生危險的移動。因此,本書既看重9·11事件在敘事上的多義性和媒介化過程中的建構(gòu)性,同時也會認(rèn)真思考9·11事件給生命個體在情感維度上帶來的影響,這涉及創(chuàng)傷、悲悼、共情、記憶等多個方面。
第一章“藝術(shù)與恐怖”將首先嘗試以一種“去9·11化”的方式來思考9·11事件。或者說,在準(zhǔn)備談?wù)?·11之前,我們需要先朝歷史的源頭眺望,思考藝術(shù)與恐怖之間的曖昧關(guān)系。從艾柯論丑的歷史,再到伊格爾頓對《酒神的女祭司》中“神圣暴力”的考察,一個不便言明的歷史真相浮現(xiàn)出來,即:恐怖和文明從來都是如影隨形的,雖然后者常自詡理性的價值觀,并妖魔化自身文明之外的他者,但在人類文明得以確立秩序的過程中,無處不見恐怖的陰森鬼影。浪漫主義以降的現(xiàn)代藝術(shù)(尤其是先鋒藝術(shù))曾熱切地期待,希望用想象的暴力進(jìn)行越界,來反抗資本主義的同一化邏輯,挽救被現(xiàn)代性湮沒的有機(jī)個體和家園。然而,“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沖撞在我們的時代從未平息,非理性作為一種文化迷因(meme)從未在啟蒙時代之后真正離場,對資本主義文明的“無名怨憤”(ressentiment)不斷激發(fā)藝術(shù)家和恐怖分子將暴力作為自己的表達(dá)方式。藝術(shù)家和恐怖分子的共謀/競爭關(guān)系,以及文學(xué)藝術(shù)在恐怖時代的特殊認(rèn)知價值,構(gòu)成了本書審視9·11文學(xué)的重要出發(fā)點(diǎn)。
第二章“見證與共同體”則是另一種對9·11文學(xué)的歷史語境化。這里,我之所以強(qiáng)調(diào)從奧斯維辛到曼哈頓“歸零地”的連續(xù)性,并非暗示這兩個事件之間具有無懈可擊的類比關(guān)系,而是試圖從大屠殺文學(xué)批評中汲取理論資源,用于9·11文學(xué)批評。雖然阿多諾(Theodor Adorno)一再強(qiáng)調(diào)奧斯維辛之后文學(xué)再現(xiàn)的絕境,以及“屠猶”對于西方文化合法性的瓦解,但正如米勒(J.Hillis Miller)所言,“毒氣室”悖論所造成的不可再現(xiàn)性,不應(yīng)該成為阻擋見證的借口。相反,對這些人為災(zāi)難進(jìn)行“見證”,不是在用審美符號復(fù)刻那些人類肉身被納粹化作青煙的極端情境,而是利用文學(xué)的施為性,在法律無法觸及的灰色地帶,言說在奧斯維辛“人之為人”的恥辱和困局。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的《這是不是個人》是講述奧斯維辛的最佳范例之一。9·11事件雖然在暴力的極端性上無法和“屠猶”相提并論,但燃燒的雙子塔、絕望的受困者和墜落者同樣讓小說家面臨著不可再現(xiàn)性的難題,也同樣深刻觸及了文學(xué)如何見證和如何反思共同體等重大問題。米勒甚至告訴我們,在關(guān)塔那摩和阿布格萊布的監(jiān)獄里,那些穿著橘色囚服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同樣處于一種阿甘本所言的“牲人”狀態(tài),納粹集中營的幢幢鬼影在反恐戰(zhàn)爭中同樣顯現(xiàn)了出來。
第三章探討“前9·11”小說,重點(diǎn)研究了梅爾維爾的《抄寫員巴特爾比》和康拉德的《間諜》。本書似乎仍然是在“朝后”看,然而這種策略與前兩章一樣,是基于對狹義“9·11小說”概念的一種解域化。我認(rèn)為,9·11的前史對于理解這個當(dāng)代事件至關(guān)重要。梅爾維爾筆下那個孤僻的抄寫員堅持說“我寧愿不”,這種消極抵抗暗示了早在基地組織之前,就有人對曼哈頓發(fā)動了恐怖襲擊。德勒茲等人認(rèn)為,巴特爾比是從語言內(nèi)部生發(fā)出一種恐怖的反抗力量,但我更傾向于認(rèn)為它蘊(yùn)含著本雅明式“神圣暴力”的潛能。甚至可以說,沒有哪篇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像這篇19世紀(jì)中期的中篇小說那樣,展現(xiàn)了資本主義內(nèi)部深刻的文化矛盾,以及極端他者的顛覆可能。同樣,康拉德的《間諜》從另一個方面觸及了資本主義的敵人——無政府主義者。在被媒體譽(yù)為“第一部9·11小說”的《間諜》中,康拉德以極為矛盾的態(tài)度,反諷式地剖解了19世紀(jì)末倫敦的無政府主義者如何試圖對公眾的想象力進(jìn)行一場破襲,以及反恐的警察力量運(yùn)作的隱秘邏輯。我認(rèn)為康拉德無意于刻畫一組無政府主義者的滑稽群像,小說家對無政府主義者及其“行動宣傳”暴力的書寫,不僅僅指向這場運(yùn)動背后隱秘運(yùn)作的人性之惡,而且代表了這位波蘭外來者對英國及歐洲大陸當(dāng)時反恐政治的矛盾態(tài)度。只有重返《間諜》這個反諷文本的歷史構(gòu)建現(xiàn)場,我們才能更準(zhǔn)確地把握那個時期的康拉德與新興的全球帝國之間的曖昧關(guān)系,并由此提煉和重申這部寫于20世紀(jì)初期的政治小說對于“后9·11”時代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從第四章“9·11小說與創(chuàng)傷敘事”開始,本書開始討論傳統(tǒng)意義上的9·11文學(xué)作品,所選文本也是當(dāng)代美國文學(xué)中的經(jīng)典——《墜落的人》《特別響,非常近》和《轉(zhuǎn)吧,這偉大的世界》。本書希望通過這一章,重新激活國內(nèi)學(xué)界對于創(chuàng)傷敘事的討論,這意味著對9·11小說的討論不僅要揭示恐怖襲擊如何造成了心理障礙和記憶缺陷,更要關(guān)注“創(chuàng)傷”作為一種批評話語,是如何在20世紀(jì)被建構(gòu)和獲得廣泛流通的。卡魯斯(Cathy Caruth)的創(chuàng)傷理論承襲了弗洛伊德、拉康、德曼等人,但其獨(dú)創(chuàng)性在于對創(chuàng)傷聲音的發(fā)掘,從而將創(chuàng)傷癥候視為一種朝向他者和他者發(fā)出的“雙重講述”。然而,卡魯斯對于不可再現(xiàn)性、不可理解性的過度強(qiáng)調(diào),讓創(chuàng)傷敘事最終成為反對闡釋的堡壘。如果不加甄別地在9·11文學(xué)批評中沿用卡魯斯的創(chuàng)傷理論,或許將進(jìn)一步阻塞“我們”與他者對話的通道,讓創(chuàng)傷凝固為一種自戀式的創(chuàng)傷文化。這里,我做的工作與卡普蘭(E.Ann Kaplan)和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頗為相似,就是通過細(xì)讀德里羅、弗爾和麥凱恩的9·11小說,從多元的、跨學(xué)科的創(chuàng)傷理論入手,在西方左翼和右翼主導(dǎo)的創(chuàng)傷政治之外尋找第三條道路,從而為“修通”(working through)歷史創(chuàng)傷尋找建設(shè)性的方案。
在第五章“極端他者和暴力”中,我將關(guān)注點(diǎn)從受害者轉(zhuǎn)向施害方,探究極端他者的恐怖暴力如何影響了當(dāng)下社會對于普通他者的認(rèn)知。本章討論的文本是哈米德的《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和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兩部小說的共性在于所采用的他者視角,雖然前者關(guān)注的是普通他者,后者則是極端他者。哈米德和厄普代克都在努力用9·11小說提供一種“反敘事”,打破西方中心主義對于穆斯林他者的刻板化再現(xiàn),把他者問題放入當(dāng)前復(fù)雜的多元文化中加以考量。兩位小說家筆下的穆斯林他者根植于9·11之后的創(chuàng)傷文化,昌蓋茲和艾哈邁德深深浸淫美國文化,他們并不像阿富汗基地組織的那些極端分子,或慕尼黑清真寺那些密謀襲美的“圣戰(zhàn)”者;相反,他們處于一種后殖民文化的第三空間,9·11之后美國矯枉過正的反恐讓他們開始質(zhì)疑并仇恨美國文化。在這種他者視角的敘事中,我們得以窺見恐怖敘事中復(fù)雜的地緣矛盾和歷史記憶,也進(jìn)一步認(rèn)清了在“后9·11”文化中全球化面臨的深刻危機(jī)。通過對阿薩德(Talal Asad)、本雅明、阿倫特、泰勒(Charles Taylor)和加繆等人思想作品的解讀,我試圖讓9·11文學(xué)中的他者問題不僅僅停留在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的異質(zhì)想象中,而是為暴力批判本身找到一種更具文化包容性、跨學(xué)科性的基礎(chǔ)。
第六章“他者倫理和共情”將焦點(diǎn)微調(diào),從他者政治的領(lǐng)域轉(zhuǎn)移到他者倫理,并加入情感研究的維度,進(jìn)一步豐富9·11文學(xué)研究的理論內(nèi)涵。在本章中,我同樣以文學(xué)文本和批評文本為雙軸,不僅涉及薩特的存在主義中的他者問題,還把列維納斯、德里達(dá)、米勒、哈貝馬斯等人放入討論場域,從而將“后9·11”的他者倫理變成了一種“眾聲喧嘩”的復(fù)調(diào)效果。這些關(guān)于他者的倫理學(xué)思考并不是為我們處理9·11文學(xué)中的他者問題提供了現(xiàn)成的倫理解決方案,而是燭照了這個問題極端的復(fù)雜性和異質(zhì)性。如果說他者倫理試圖回答的是“我們”如何與“他們”相處,那么在很多人看來,共情似乎是修復(fù)恐怖主義造成的族群和文化撕裂的最佳解藥。不過,我認(rèn)為共情在這里依然是問題本身,而非答案。通過對麥克尤恩的《星期六》和瓦爾德曼的《屈服》等作品的分析,本書試圖傳遞一個看似悲觀、卻更為審慎的觀點(diǎn):跳出主體的藩籬去與他者實(shí)現(xiàn)共感或共情,固然是一種更為開明進(jìn)步的做法,但這樣的情動是基于身體的物性,往往繞過了更為復(fù)雜的情感、記憶、認(rèn)知等大腦過程,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大眾媒體的媒介化過程的影響。“后9·11”時代共情的限度在于它的選擇性和脆弱性,作家本人亦只能借助主觀想象去言說和再現(xiàn)共情。本章所分析的兩部小說以頗為不同的立場,展現(xiàn)了文學(xué)藝術(shù)與敘事共情之間不確定的價值實(shí)踐。
本書最后一章是“‘后9·11’文學(xué)中的戰(zhàn)爭書寫”,我將目光投向了伴隨美國反恐戰(zhàn)爭而產(chǎn)生的戰(zhàn)爭小說,選擇了三部風(fēng)格迥異的作品來做文本細(xì)讀:鮑爾斯的《黃鳥》、方登的《漫長的中場休息》和克萊的《重新派遣》。充滿痛苦和詩意的《黃鳥》更像是對于美國戰(zhàn)爭文學(xué)傳統(tǒng)的一種繼承,士兵在異國戰(zhàn)場經(jīng)歷了道德的成長,并需要面對戰(zhàn)爭帶來的無解的存在主義危機(jī)。《漫長的中場休息》則通過高密度的諷刺,透過一個從戰(zhàn)場暫時歸來的英雄連隊(duì)的視角,展現(xiàn)了美國戰(zhàn)爭文化與流行文化之間的相互滲透,從而體現(xiàn)了伊拉克戰(zhàn)爭的當(dāng)代性。短篇小說集《重新派遣》是首部榮獲“國家圖書獎”的伊拉克戰(zhàn)爭題材作品,克萊的新意在于多視角、多主體地反思伊拉克戰(zhàn)爭復(fù)雜且矛盾的多重面相,而非單純地書寫反戰(zhàn)主題和“戰(zhàn)壕抒情”,或重復(fù)從前戰(zhàn)爭文學(xué)經(jīng)典中的“戰(zhàn)場諾斯替主義”。我認(rèn)為,反恐戰(zhàn)爭的后人類技術(shù)形態(tài)和媒介化特征,賦予了這些新型戰(zhàn)爭小說某種獨(dú)特性,它們對戰(zhàn)爭話語在美國“后9·11”社會構(gòu)建的新現(xiàn)實(shí)進(jìn)行了有力的批判和介入,從而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戰(zhàn)爭中正義、創(chuàng)傷敘述和士兵責(zé)任等問題。
時至今日,9·11作為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依然在不斷地帶來余震和漣漪,它沒有向我們昭示它的終極意義。但有一點(diǎn)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我們已經(jīng)并且將在相當(dāng)長一段時間內(nèi)繼續(xù)生活在“后9·11”的歷史情境下。必須承認(rèn),雖然本書醞釀了多年,但對于9·11及其文學(xué)再現(xiàn)這樣處于不斷生成中的當(dāng)代事件,我依然不可避免地處于盲人摸象的狀態(tài)中。書中的某些觀點(diǎn)或許很快就會被瞬息萬變的世界地緣政治、新型互聯(lián)網(wǎng)文化、后理論人文思潮和大腦認(rèn)知科學(xué)的最新進(jìn)展所否定或更新。21世紀(jì)的未來會往何處去?嚴(yán)肅文學(xué)是否會在互聯(lián)網(wǎng)化的大眾傳媒和恐怖分子的夾擊下日益萎靡?文學(xué)藝術(shù)是否還能對極端暴力做出有力的言說,并改變?nèi)祟惖挠^念?這些問題都是本書希望回答但又無法給出滿意答案的。它們既是當(dāng)代西方文學(xué)研究的挑戰(zhàn)所在,也是其魅力所在——它吸引了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各國學(xué)者,去參與批評話語的生產(chǎn)和傳播,去繼續(xù)捍衛(wèi)這個狂暴時代文學(xué)藝術(shù)的合法性和深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