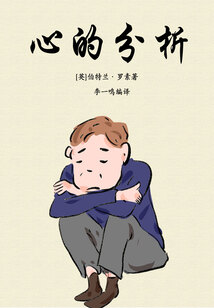
心的分析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序言
這部書是由企圖調和兩種不同的傾向產生的,一種在心理學中,另一種在物理學中,初時看起來,它們雖似乎不兼容,讓我對于兩者都表同情。在一方面,許多心理學者,特別是行為論派的心理學者,傾向于采取一種大都為唯物論的論旨,作為一種方法的——如果不是玄學的——東西。他們使心理學有增無已地依賴生理學和外部的觀察,并且傾向于把物看做比心更為著實而無可懷疑的東西。同時,一般物理學者,特別是愛因斯坦(Einstein)和其他相對論的解釋者,已經使“物”越來越不是物質的。他們的世界是由“事情”組成,而“物”是由一種邏輯的構造,從事情得來的。例如任何人一讀厄丁托(Eddington)教授的“空間時間與重力”(1920年出版),將看見一種舊式的唯物論不能從現代物理學獲得贊助。我想,在行為論者的世界中具有永久價值的東西,是感覺物理學為現今存在的最基本的科學。但物理學如果不假定物的存在——情形似乎是如此——這種論旨不能稱為唯物論的。
我以為調和心理學唯物論的傾向和物理學反唯物論的傾向的意見,是詹姆士(W.James)和美國新實在論者的意見,依照這種意見,兩者所由構成的世界的“材料,”既不是心理的,也不是物質的。而是一種“中立的材料。”我在本書中,對于有關心理學的現象,曾努力發揮這種意見,頗為詳盡。
瓦特孫(J.B.Watson)教授和倫思(T.P.Nunn)博士首先翻開我的手稿,并給予許多有價值的提示,謹致謝意;窩爾格穆慈(A.Wohlgemuth)君對于重要的著作給我許多很有用的報告,同樣致謝。本哲學文庫的編者繆耳赫德(Muirhead)教授曾有幾種提示,為我所利用,也當承認他的幫助。
拙著在倫敦和北京以講演的形態出現,關于欲望的一講已經在科學會刊布過。
本書有少數引中國為喻的地方,都是我到中國前所寫的,希讀者不要認為在地理上是精確的。當我對不熟悉的事物要作解釋時,只是用“中國”作為“一個遠距離國家”的同義語。
1921年1月序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