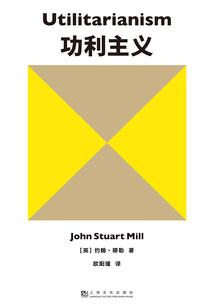
功利主義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導讀
作為哲學的一門分支科學,倫理學(Ethics)也被稱為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它以道德為研究對象,要解決的是道德和利益的問題;其中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利益與道德的關系,二是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之間的關系。人們對這個基本問題的不同回答,不但決定了各種道德體系的原則與規范,也決定了各種道德活動的評判標準和價值取向。由于探究的是最終價值的本質和評判人類行為對錯的標準,以便為人類的行為提供道德指導,并在解決社會沖突和促進社會和諧方面提供幫助,因此倫理學也被譽為一門“使人類光榮的科學”。
在近代西方哲學史上,穆勒晚年所著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1861年),無疑是倫理學領域濃墨重彩的一筆。它不僅奠定了穆勒作為近現代功利主義哲學理論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對近現代的西方倫理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還讓這種影響逐漸傳播到了東方,使得功利主義如今仍在全球許多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出于這個原因,商務印書館早在近一百年前的20世紀30年代,就已引入和出版了該書的中譯本。此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讀者閱讀經典名著的興趣日漸高漲,國內又陸續出版了多種譯本,讓更多讀者接觸到了穆勒及其著作,也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了穆勒的觀點和功利主義倫理學。不過,因為哲學著作大多以說理和邏輯論證為重點,普通讀者閱讀起來無疑會覺得乏味,倫理學著作自然也不例外,所以我們這次重譯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獻給普通讀者一個真正的盡可能通俗的譯本。為此,我們秉持揚長避短的原則,一方面努力吸納其他譯本的優點、克服其不足,另一方面努力厘清和捋順前后文之間的邏輯關系,提升閱讀體驗。
為了更好地閱讀和理解《功利主義》,我們不妨先來了解一下它的作者穆勒的生平和著述、功利主義的發展情況,以及這種倫理學的優點與局限性等方面,然后簡要梳理《功利主義》的內容,讓讀者在閱讀之前有個大致的了解。
一、穆勒:非常規教育的典范和功利主義哲學的接班人
穆勒全名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19世紀英國一位杰出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評論家及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他也是著名的功利主義哲學家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1773—1836)的長子。在父親的精心安排下,約翰·穆勒從3歲起學習希臘文和算術,8歲開始了解拉丁文、代數、幾何,9歲就嘗試讀一些希臘史學家的重要著作,12歲時接觸邏輯學和哲學;因此,少年階段結束時,穆勒已經具備了廣博的知識。據約翰·穆勒自述,這種非常規教育使得他比同齡人“早起步了25年”,最終不出所望地成了西方早期教育的成功典范之一。
穆勒接受的這種早期教育,是建立在功利主義倫理學的基礎上的。詹姆士與英國著名的功利主義哲學家、法理學家、經濟學家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朋友,兩人都深受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心理理論影響,認為人的心靈最初就像一張白紙,思想則來自感覺經驗(sense-experience)的積累;也就是說,只要從小開始進行適當的訓練,一個人的心靈可以吸收和理解的知識量可以遠超常人的想象(如今我們還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洛克是英國哲學家及醫生,被譽為“自由主義之父”,而邊沁本身曾是神童。所以,詹姆士用對兒子的培養來驗證這種理論,就不足為奇了。在成長的過程中,約翰·穆勒與邊沁常有接觸,且在邊沁死后還負責整理其著作,因此自然而持續地受到了功利主義思想的浸潤,最終成了他們的接班人和功利主義學派的領軍人物。
盡管穆勒在他的自傳中曾經肯定地說,任何一個身體健康的普通孩子經過相同的訓練都可以達到相同的結果——似乎他很贊同這種訓練——但對于捍衛個人自由的穆勒而言,他在接受這種訓練的過程中其實是毫無個人自由和快樂可言的。他完全就是詹姆士與邊沁兩人的試驗對象,因為在自傳的一個早期版本中,穆勒曾稱“我的教育不是愛的教育,而是畏懼的教育……我父親的孩子們既不愛他,也不會帶著任何溫暖的情感去愛其他任何一個人”;他的一位朋友則稱,穆勒小的時候沒有童年,因為他從不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對生活可謂一竅不通[1]。
不過,正是由于這種訓練讓他積累了深厚的古典哲學功底,青年時期的穆勒才能對政治經濟學、法學、心理學、邏輯學等領域展開深入的研究,并且發表了很多相關的論文。1823年,年僅17歲的穆勒進入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任職。這種輕松的公務生涯,使得他有了大量的時間從事學術研究和思考;于是,他開始大量瀏覽和分析持不同觀點者的著作,并且逐步修正和完善了原來的功利主義觀,撰寫了《邏輯體系:演繹與歸納》(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1843年,嚴復曾譯之為《穆勒名學》)、《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1848年)、《論自由》(On Liberty,1859年,參見拙譯《論自由》,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論代議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861年)、《婦女的屈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年)等不朽的作品。本書就是穆勒系統而全面地論述功利主義倫理觀的一部名作,它奠定了穆勒作為功利主義學派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晚年的穆勒還擔任過一屆國會議員(1865年—1868年),在任內曾為改革法案與勞動階級的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并且極力參與政治與社會改良工作,真正踐行了自己秉持的功利主義道德。
二、功利主義倫理學概述
功利主義是一種把實際效用或利益作為道德標準的倫理學說,亦稱“功利論”“效用論”或“效用(功用)主義”等,是近現代西方社會中的主流思潮——自由主義的三大派別之一(剩下兩個派別是自由平等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
早在功利主義正式成為一種哲學理論之前,世間就出現了功利主義思想的雛形。有人認為功利主義源于古希臘的快樂主義倫理學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亞里斯提卜(Aristippus,約公元前435年—公元前356年)所創立的昔勒尼學派(Cyrenaics)。亞里斯提卜把認識論中的感覺論和倫理學中的快樂主義結合起來,認為感覺是“真”與“善”的標準;他把蘇格拉底的“至善”理解為快樂,聲稱感官快樂和個人享受就是人生的追求目的。也就是說,他認為最高的善只能存在于快樂之中,快樂則是衡量一切價值的尺度,因此倫理學就是一種追求最大快樂的學說。公元前4世紀的伊壁鳩魯(Epicurus,公元前341年—公元前270年)、公元前5世紀的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約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等哲學家,都可以說是功利主義的古代先驅。受此影響,近現代的許多哲學家與倫理學家也都具有功利主義傾向。東方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隨者倡行的倫理學說里,就存在著類似的功利主義思想。比如《墨子·非攻下》中的“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帶給人們許多的利益,功勞很大,所以上天會賞賜于他),顯然就與功利主義中的“最大幸福原則”不謀而合。此外,宋代的思想家葉適與陳亮也曾主張功利之學。
雖說源流久遠,但功利主義倫理學卻是到了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之后,以這場運動和人性的發揚為歷史基礎才得以真正形成的。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和洛克兩人繼承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的傳統,論證了功利主義的人性基礎(趨樂避苦的本性),設想了人們實現共同利益的方法和途徑,從而初步構筑了功利主義的理論體系。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夕,愛爾維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和霍爾巴赫(Paul-Henri Dietrich baron,d Holbach,原名Paul Heinrich Dietrich,1723—1789)兩人則把功利主義理想化,為反對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提供了思想動力。德國的黑格爾(G.M.F.Hegel,1770—1831)從純粹的理論思辨方面著手,論證了功利主義理論是啟蒙運動帶來的最終結果。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后,功利主義通過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和邊沁獲得了進一步發展。接下來,邊沁和穆勒父子又把功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完美地結合起來,使之變成了西方古典經濟學的思想基石。此后,再經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1838—1900)、摩爾(G.E.Moore,1873—1958)等人的批判、修正與完善,功利主義倫理學不斷發展和傳播至今,成為了一種具有跨文化影響力的思想體系。
1781年,邊沁率先提出了“功利主義”一詞。他認為,所謂的道德就在于追求快樂,而快樂的根源又在于利益得到滿足,因此利益即功利就是人們行為的唯一目的和檢驗標準,是人類獲得幸福的基礎。由于他把社會看作個人的總和,把社會利益看作個人利益的總和,因此邊沁得出結論——道德生活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是功利主義的總體原則,簡稱最大幸福原則。只不過,邊沁對快樂或幸福的量化研究過于簡單,因為他認為不同種類行為的唯一差異就在于它們會產生出不同程度的快樂;他還認為,我們既無必要、也不可能去證明功利主義道德——功利主義原則是最高的道德原則,而最高原則是不言自明的。所以,邊沁功利主義理論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
穆勒的功利主義則更為精致,因為他引入了“質”的量度,圍繞著“最大幸福”這一核心原則,論證了快樂與幸福還有“更高等的”和“更低等的”之分,并且將“幸福”與“單純的滿足”區分開來。他認為,對真正的功利主義而言,一個主要的目標就是讓盡可能多的人盡可能地獲得幸福,而不是讓他們盡可能地獲得滿足。他承認,理智的、情感的、想象的和道德情操上的快樂要比純粹的感官快樂有價值得多。比如,穆勒說:“假如有人發問,問我說的快樂在‘質’的方面具有差異是什么意思,或者僅僅就快樂而言,除了‘量’更大以外,究竟是什么讓一種快樂比另一種快樂更加可貴,那么,我給出的回答可能只有一個。在兩種快樂當中,假如所有或幾乎所有體驗過二者的人都明確地偏好其中的一種,而不管他們是否覺得自己有道德義務去偏好它,那么,它就是更值得我們去追求的那種快樂。假如那些對兩種快樂都相當熟悉的人認為其中之一遠遠優于另一種,因而更喜歡它,就算知道它會帶來更多的不滿足感也不改初衷,并且不會由于天性使得他們可以獲得更多的另一種快樂而放棄前者,那我們就完全有理由認為,這是因為受到偏愛的那種快樂在‘質’的方面具有一種遠遠超過了‘量’的優勢,以至于相對而言,‘量’就變得無足輕重了。”[2]
邊沁和穆勒都認為人類的行為完全以快樂和痛苦為動機,而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幸福,所以是否促進幸福就成了檢驗人類一切行為對錯的標準。因此,功利主義倫理學不僅在哲學領域有著重要的意義,還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現當代西方的主流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英國哲學家、法理學家哈特(H.L.A.Hart,1907—1992)論及功利主義的歷史命運時指出,功利主義曾經“是被廣泛接受的信念”,構成了英美自由主義哲學的基礎;在近代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至少對西方傳統的政治哲學界來說,他們的基本信念都是“某種形式的功利主義……必然會揭示政治道德的實質。”[3]即便是到了如今,功利主義理論也仍在眾多領域里直接或間接發揮著或隱或顯的作用,因此值得我們去研究。
三、《功利主義》:一部簡短而深刻的功利主義倫理學著作
《功利主義》篇幅雖然簡短,卻是一部不朽的功利主義倫理學名著。它不僅對功利主義的基本精神、核心概念、主要原理做出了相當完備而又深入清晰的闡述,而且從功利主義的立場出發,澄清了道德倫理學中的一些根本問題,是論述功利主義的代表之作。下面我們就來簡單講一下這部作品的基本內容,以便更好地幫助讀者提綱挈領地去領會全作。
全書共有五章,其中的第一章就是總論。穆勒開門見山,首先指出了道德倫理學的現狀,指出人類“在解決頗具爭議的是非標準問題上一直都沒有什么進展”,并且如今對至善即道德基礎的問題仍然存有爭議,依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接著,穆勒對比了其他科學的情況,分析了歸納倫理學與直覺倫理學之間的差異與不足,批判了康德倫理學思想的局限性,并且得出了“檢驗是非的標準必定是確定對錯的手段,而不是一種已經確定了對錯的結果”和功利原則即邊沁所稱的最大幸福原則對形成各種道德學說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功利主義觀點對先驗派倫理學家來說必不可少的結論。他指出,盡管功利原則屬于終極目的,因而“無法直接加以證明”,但他可以提出許多“能夠決定理智究竟是贊成還是不贊成功利學說”的考量因素,從“證明”一詞的寬泛含義上去論證這種理論。因此,這一章實際上是說明了穆勒寫《功利主義》的目的和所用的論證方法。
在第二章里,穆勒不但論述了功利主義的含義,還澄清了這種理論中的一些基本觀點和核心概念。他引入了一系列反對功利主義的觀點,然后逐一批駁、分析和論證,并且在此過程中對倫理學的基本問題、主要原理做出了經典的回答和界定。
承認功利或最大幸福原則屬于道德根基的信條,認為行為之所以正確,是因為它們有增進幸福的傾向,而行為之所以錯誤,則是因為它們有造成不幸的傾向。所謂的幸福,就是指快樂且沒有痛苦;所謂的不幸,就是指痛苦且沒有快樂。快樂與擺脫痛苦是唯一值得追求的兩大人生目的,而所有值得追求的東西(在功利主義理論和其他任何一種理論中,這些東西都不勝枚舉)之所以值得追求,要么是因為它們本身含有內在的快樂,要么就是因為它們屬于增進快樂和防范痛苦的手段。
也就是說,功利主義倫理學認為,唯一能夠判定行為對錯的最終道德標準,就是看行為能否增進人的幸福;而人生唯一的終極目標,就是追求幸福、追求快樂和擺脫痛苦。當然,這里的快樂并不是指“禽獸的欲求”即純粹的感官快樂,人生也并不是“禽獸的生活”,因為“人類擁有種種比禽獸的欲求更加高尚的官能;一旦認識到這些官能,那么凡是不能滿足這些官能的東西,我們都不會視之為幸福”。所以,在對有些人認為把快樂當成人生最高目標的信條“是一種只配得上豬玀去擁有的信條”進行批駁時,穆勒指出“承認某些類型的快樂要比其他快樂更值得追求和更加重要這個事實,與功利原則完全一致”。
接下來,穆勒雖然沒有明說,卻引入了“質”的量度,對邊沁的快樂量化研究進行了批判和修正。他這樣做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在評價其他所有事物的時候,我們會考慮到‘質’和‘量’兩個方面,而在評價快樂的時候,卻認為只需考慮‘量’這一個方面,無疑是一種很荒謬的觀點。”引入了“質”的量度之后,自然就有了層次較高的快樂與層次較低的快樂之分。他認為,“在兩種快樂當中,……受到偏愛的那種快樂在‘質’的方面具有一種遠遠超過了‘量’的優勢,以至于相對而言,‘量’就變得無足輕重了”,所以“那些同等地熟悉并且能夠同等地重視和享受兩種快樂的人,確實會極其顯著地偏好那種能夠運用其高等官能的生活方式”。換言之,由于人類擁有“對自由和人格獨立的熱愛”,因此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單純的、低等的感官快樂。正是在此基礎上,穆勒寫下了這樣一句名言:“做一個不滿足的人,勝過做一頭滿足的豬;寧可做一個不滿足的蘇格拉底,也不要做一個滿足的傻瓜。”
穆勒還分析和批駁了其他一些觀點,比如“許多擁有層次較高的快樂的人偶爾也會經不住誘惑,把層次較高的快樂置于層次較低的快樂之后”,并指出“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有意偏愛低級快樂,而是因為他們只能獲得這種快樂,或他們只能繼續享有這種快樂”。他由此得出結論,最大幸福原則并不是指行為人自身的最大幸福,而是指整個人類的最大幸福。再比如,有些人由于認為“幸福是不可企及的”以及“人類沒有幸福也能生存”,所以得出“任何形式的幸福都不可能是人類生活和行為的理性目的”的結論。對此,穆勒反駁“功利不止包括追求幸福,還包括防范或者減輕不幸”,實際上就是包括了我們所說的趨利和避害兩個方面。雖然人類可以在沒有幸福的情況下生活,但高尚者只是“為了某種被他們視為比個人幸福更加重要的東西,才過著沒有幸福的生活”;事實上,“這種自我犧牲必定是為了實現某種目的,而且這種目的并不是自我犧牲本身”,而是為了“增進世間的幸福”。功利主義“拒絕承認犧牲本身是一種善行”,因為“一種犧牲若是不會增進幸福,或沒有增進幸福的傾向,那就是一種浪費”。他總結道:“構成功利主義評價正確行為之標準的幸福,并不是指行為人自身的幸福,而是指所有相關者的幸福。”功利主義道德理想的完美形式就是“己所欲,施于人”和“愛鄰如己”,也就是“要求世人戒除明顯有害于整個社會的行為”。
最后,穆勒澄清了世人對功利主義的一些其他誤解,比如認為功利學說是一種“無神論的學說”“一種不道德的學說”,把“功利”冠以“私利”之名,以及其他反對功利主義的陳詞濫調,等等。
第三章論述了功利原則這種道德標準的終極約束力問題。穆勒首先指出“功利原則具備其他任何一種道德體系所具有的一切約束力”,而這些約束力又分為兩種,即內在約束力和外在約束力。然后,穆勒重點論述了其中的內在約束力,指出它是“我們內心的一種情感,是一種隨著違反義務而產生的、強烈程度不一的痛苦”,是“良知的本質”。接下來,穆勒探討了義務感(即道德情感)究竟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后天習得的,指出不管它是具有先驗性起源還是后天習得的,對功利原則都沒有影響。功利主義道德具有一種強大有力的天然情感基礎,即“與我們的同胞保持和睦一致的愿望”,也就是顧及他人的利益;只要承認普遍幸福是道德標準,這種情感基礎就會成為功利主義道德的力量。所以,這種道德情感就是功利主義道德,即最大幸福原則的終極約束力。
第四章探討了對功利原則的證明問題。哲學的本質就是批判與論證,因此對道德標準的證明是倫理學中的關鍵問題。穆勒在總論中就已指出,他對功利主義理論的證明屬于寬泛意義上的,所以本章中的證明,自然也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邏輯證明。對于“幸福是唯一值得我們去追求的目的”這一點,穆勒首先運用了類比的方法:“能夠證明一個物體可見的唯一證據,就是人們確實看到了這個東西;能夠證明一種聲音可以被聽見的唯一證據,就是人們確實聽到了這種聲音。……同理,我認為可以證明任何一種東西值得追求的唯一證據,就是人們確實想要得到它。”
由于每個人都是因為相信自己可以獲得幸福才去追求自身的幸福,因此普遍幸福就是值得普遍去追求的。他認為,這個事實就證明了“幸福是一種善——每個人的幸福對其自身來說都是一種善,因此普遍幸福對所有人組成的整體而言也是一種善。幸福既然已經確立為行為的目的之一,所以也成了道德標準之一”。
只不過,這種論證的邏輯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從每個人都追求自身幸福的事實,并不能直接得出人人都追求普遍幸福的結論。更何況,本章前文中曾指出,功利主義道德在原則上會允許為了普遍幸福而犧牲某些人的利益,這種情況對犧牲者來說,無疑也并不屬于他自身的幸福。
此外,穆勒闡述了幸福與美德之間的關系。美德不但是實現幸福的手段,而且是幸福的組成要素,是幸福的一部分;美德“本身就是一種善”,因此要求我們“把熱愛美德視為促進普遍幸福的首要條件”。他還分析了意志和渴望之間的區別,指出“我們常常并不是因為渴望才想要獲得某種東西,而完全是因為我們想要獲得某種東西才會心生渴望”,并且進一步說明了增強世人道德意志的方法,那就是“讓他們渴望獲得美德”,喚起他們想要變得道德高尚的意志,培養出行善的習慣。
第五章論述了正義與功利之間的聯系。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因為“在所有的思辨時代,導致人們難以接受‘功利或幸福是檢驗對錯的標準’這一學說的最大障礙,向來都是正義的觀念”。穆勒先是列舉了正義與不正義的幾種情形:尊重任何一個人的法定權利是正義的,而侵犯任何一個人的法定權利則是不正義的;正義是每個人都應當得到自己應得的東西,而一個人獲得了不應得到的利益或被迫遭受了不應遭受的禍害,則是不正義的;失信于人是一種公認的不正義;有失公允并非正義之舉。然后,他從詞源的角度,指出構成“正義”概念的原始要素是遵守法律,但并不是所有的違法行為都會激發“不正義”的情感。正義與慷慨或善行之間的特定區別,就是某個人擁有一種與道德義務相關的權利,即“正義不僅是指做某事符合道德、不做某事則是不道德的,還意味著某一個人能夠要求我們將某種東西當成他的道德權利”。所以,正義涉及到權利,“無論什么情況,只要存在權利,就屬于事關正義的問題,而不屬于行善這種美德的問題”。這些方面,實際上就是給出了正義的定義。
接下來穆勒指出,伴隨著正義觀念而來的情感(正義感)含有兩大基本要素:一是懲罰侵害者的愿望,二是知道或相信有確定的受侵害者。既然正義是指捍衛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權利和利益,那么社會就應當出于普遍功利的考慮去捍衛這種權利和利益。人類的所有利益中,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利益,“沒有哪個人能夠在不安全的情況下生存;我們免遭禍害以及長久獲得一切善的整體價值的能力,全都有賴于安全,因為我們如果隨時都有可能被任何一個暫時比我們強大的人奪走一切,那么除了當下的滿足感,就沒有什么東西對我們有任何價值了”。但是,由于正義與權利、利益相關,所以不同的人會擁有不同的正義觀念,甚至同一個人的正義觀念在不同場合下也有可能不同。只有根據功利原則,才能解決這個方面的爭論,“除了功利主義,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從這些混亂中解脫出來”。
最后,穆勒指出正義是某些類別的道德準則的統稱,個人權利的概念則是正義觀念的本質,并且“檢驗和判斷一個人是否適合作為人類一員生存于世的標準,就在于他是否遵從這些道德準則”。正義也是某些社會功利的恰當統稱,它們比其他社會功利重要得多,并且更具絕對性與義務性,因此建立在功利基礎之上的正義感提出的要求(即正義義務)更明確,約束力也更強大。
綜觀全書,穆勒是結合運用立論與駁論的方法,做到了立中有駁、駁中有立,比較完善而全面地論述了功利主義的基本原理,澄清與修正了以前(主要是邊沁)的功利主義理論。盡管后人對穆勒的功利主義進行了許多批判,引發了一些學術論爭,但不可否認的是,功利主義倫理學如今仍在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仍是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的主要道德基礎。只不過,我們在研究功利主義、閱讀穆勒這部《功利主義》時須持批判的態度,結合歷史和現實、自身經驗與文化差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多角度而審慎地加以理解和吸收。
四、翻譯方面:兩個問題
最后,譯者還有兩個涉及翻譯的問題,須向讀者簡單說明一下。
首先就是本書作者“穆勒”和“功利主義”這兩個譯名的問題。按照發音來看,穆勒(Mill)譯成“密爾”或“米爾”更加準確;事實上,如今出版的不少譯作中也已不再使用“穆勒”這個譯名。但出于遵循傳統和保持一致的考慮,在這里仍然將其譯作穆勒。至于“功利主義”,也是如此。功利(Utility)與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兩詞的本義分別為中性的“效用(或功用)”和“效用主義(或功用主義)”,并不帶有貶義;但眾所周知的是,“功利”二字在我國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貶義詞,常含重利輕義、投機鉆營、自私自利等意。若是說一個人功利心重,那就是說這個人的行為或態度都是為了給自己謀取利益。從本書中不難看出,穆勒的功利主義倫理觀與自私自利是截然相反的。可以說,“功利主義”這個譯名正是很多人對功利主義倫理學持有負面觀點的一大原因。因此,我們原本應當像如今很多的哲學譯作一樣,棄用這個帶有貶義的譯名。但是,由于用“功利主義”一詞來指代穆勒的效用主義倫理學已經深入人心,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加上考慮到貿然改譯之后,部分讀者有可能產生困惑和新的誤解,所以我們在假定絕大部分讀者都明白穆勒的功利原則就是最大幸福原則,而絕對不是指個人私利和幸福的前提下,仍然沿用了這個譯名。
其次就是譯文整體方面的問題。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翻譯既是一個信息轉換與傳播的過程,也可以說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在轉換時,由于涉及到解碼源語言和重新編碼成目標語言兩個方面,所以譯文會不可避免地帶有譯者自身的色彩(包括對源語言的理解是否充分準確,以及在目標語言方面的表達水平和行文習慣等)。再則,由于傳播的對象眾多,人們接受轉換(翻譯)后的信息時,在理解力、閱讀習慣、邏輯思維能力、自身經歷等方面各有不同,所以他們對譯文的閱讀感受和看法自然也會千差萬別。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的理解、品位、喜好來加以判斷;在這個方面,譯者與讀者都是一樣。
如今世人公認的翻譯標準,就是晚清翻譯大家嚴復提出的“信、達、雅”三原則(值得一提的是,穆勒的著作也是嚴復率先譯介到中國來的)。好的翻譯應該是在忠實于原文(信)的基礎上,用目標語言將文義表達得通順自然(達),并且帶有一定的文采(雅);這樣才能讓讀者既沒有理解困難,還產生閱讀興趣。不過,嚴復也將這三大原則稱為“譯事三難”,并且說“求其信,已大難矣”;因此,他提出的實際上是翻譯的最高標準,非集文化之大成者很難達到。我們很少看到被世人交口稱贊的上乘譯作,原因就在于此。譯者立志于翻譯事業,但同時也深知自己才疏學淺;盡管已譯有一些作品,譯作中也大多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而在翻譯《功利主義》這樣的哲學名著時尤為如此。與其他許多譯者相比,拙譯都難以望其項背,故須先請讀者包涵,本人誠摯接受批評和指正。
感謝果麥文化的信任。若書中存在翻譯錯誤和不足之處,再次懇請讀者不吝賜教。
歐陽瑾
2023年7月
注釋
[1]參見M.圣約翰·帕克(M.St John Packe)《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傳》(The Life of John Stuart Mill),塞克華寶出版社,1954年。如無特別說明,均為譯者注。
[2]參見本書第二章。前言部分含有眾多引文。如無特別注明,它們都引自對應的正文章節。
[3]參見哈特《功利與正義之間》(Between Utility and Right),見于艾倫·萊恩(Alan Ryan)編著《自由觀》(The Idea of Freedom),牛津大學出版社,1979年,第7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