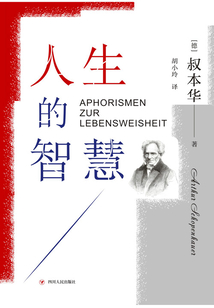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導論
幸福不是唾手可得的東西:
在我們內部很難找到它,
在別處不可能找到它。
——尚福爾[1]
在這里,我完全是從內在的意義來使用“人生的智慧”這一概念的,即從藝術的意義而言,就是要盡可能愉快地、幸福地度過一生,就是一種能夠被稱為幸福學說的指南:如此說來,它指導我們如何獲得一種“幸福的存在”。那么這種“幸福的存在”,從純粹客觀的觀點看,或者更確切地說(因為這里重要的是主觀的判斷)是在冷靜地、仔細地思考之后,或許又能夠被解釋為肯定比非存在更好。從“幸福的存在”這一概念可以推論出,我們要為了它本身而依戀它,而不僅僅出于面對死亡的恐懼;還可以得出,我們想要看到它永恒地延續下去。那么是否人性的生活符合這樣一種存在的概念,或者只能夠符合這樣一種存在的概念,這是一個問題。眾所周知,我的哲學對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相反,幸福學說則是以對這個問題的肯定回答為前提的。也就是說,這恰好是以先天的錯誤為基礎的,在我的代表作[2]的第2卷第49章的開篇處我揭露了這個錯誤。然而為了能夠擬定這樣一種幸福學說,我在此不得不完全放棄由我的真正的哲學所導出的更高的、形而上學-倫理學的立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在這里所給出的全部解釋都基于一種折中,即只要是這種解釋仍停留在一般的、經驗的立場上并且包含著該立場的錯誤。照這么說,解釋的價值只能是有限的,因為幸福學說這個詞本身只是一種委婉的表達。此外,我的解釋并不試圖面面俱到;這部分是因為這個話題是說不盡的;部分是因為如果要說盡,我就不得不重復其他人已經說過的話。
就我所能記起的,與我這本起草的箴言具有相似動機的,只有卡爾丹諾的《逆境的益處》[3]。這本書頗值一讀,可以作為我的這本書的補充。盡管亞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辭學》第一部書的第5章插入了一個簡短的有關幸福學說的論述,但那只是泛泛而談。我并沒有采用這些前輩的論述,因為編纂不是我的工作;更何況,假如這么做我就會丟失觀點的統一性,而這種統一性是此類作品的靈魂。當然,一般說來,一切時代的智者們都說過相同的話,而愚人們則做過與之相反的相同之事,未來還將如此。因此伏爾泰說:“我們離開時,這世界仍然愚蠢邪惡,正如我們降臨時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