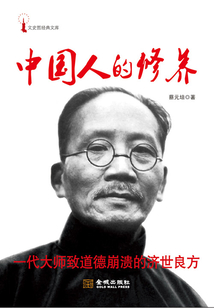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8章 關于國民之修養(2)
- 第7章 關于國民之修養(1)
- 第6章 中學修身教科書(下篇)(2)
- 第5章 中學修身教科書(下篇)(1)
- 第4章 中學修身教科書(上篇)(2)
- 第3章 中學修身教科書(上篇)(1)
第1章 華工學校講義(1)
1916年3月,華法教育會為籌備廣設華工學校,推廣對在法華工的教育,先期招收教師24人,開設師資班。這一師資班于當年4月3日開學,由蔡元培先生考驗新生,并為該班編寫德育、智育講義,名曰《華工學校講義》,蔡元培先生親自授課,以便這些師資轉授華工。
德育三十篇
■合群
吾人在此講堂,有四壁以障風塵;有案有椅,可以坐而作書。壁者,積磚而成;案與椅,則積板而成者也。使其散而為各各之磚與板,則不能有壁與案與椅之作用。又吾人皆有衣服以御寒。衣服者,積綿縷或纖毛而成者也。使其散而為各各之綿縷或纖毛,則不能有衣服之作用。又返而觀吾人之身體,實積耳、目、手、足等種種官體而成。此等官體,又積無數之細胞而成。使其散而為各各之官體,又或且散而為各各之細胞,則亦焉能有視聽行動之作用哉?
吾人之生活于世界也亦然。孤立而自營,則凍餒且或難免;合眾人之力以營之,而幸福之生涯,文明之事業,始有可言。例如吾等工業社會,其始固一人之手工耳。集伙授徒,而出品較多。合多數之人以為大工廠,而后能適用機械,擴張利益。合多數工廠之人,組織以為工會,始能漸脫資本家之壓制,而為思患預防造福將來之計。豈非合群之效與?
吾人最普通之群,始于一家。有家而后有慈幼、養老、分勞、侍疾之事。及合一鄉之人以為群,而后有守望之助,學校之設。合一省或一國之人以為群,而后有便利之交通,高深之教育。使合全世界之人以為群,而有無相通,休戚與共,則雖有地力較薄、天災偶行之所,均不難于補救,而兵戰、商戰之慘禍,亦得絕跡于世界矣。
■舍己為群
積人而成群。群者,所以謀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群而危險,非群中之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保群,而群將亡。則不得已而有舍己為群之義務焉。
舍己為群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群中,群亡則己隨之而亡。今舍己以救群,群果不亡,己亦未必亡也;即群不亡,而己先不免于亡,亦較之群己俱亡者為勝。此有己之見存者也。一曰,立于群之地位,以觀群中之一人,其價值必小于眾人所合之群。犧牲其一而可以濟眾,何憚不為?一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為群之一人;人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為群之眾人。此無己之見存者也。見不同而舍己為群之決心則一。請以事實證之。一曰從軍。戰爭,罪惡也,然或受野蠻人之攻擊,而為防御之戰,則不得已也。例如比之受攻于德,比人奮勇而御敵,雖死無悔,誰曰不宜?二曰革命。革命,未有不流血者也。不革命而奴隸于惡政府,則雖生猶死。故不憚流血而為之。例如法國一七八九年之革命,中國數年來之革命,其事前之鼓吹運動而被拘殺者若干人,臨時奮斗而死傷者若干人,是皆基于舍己為群者也。三曰暗殺。暗殺者,革命之最簡單手段也。殲魁而釋從,懲一以儆百,而流血不過五步。古者如荊軻之刺秦王,近者如蘇斐亞之殺俄帝尼科拉司第二,皆其例也。四曰為真理犧牲。真理者,和平之發見品也。然成為教會、君黨、若貴族之所忌,則非有舍己為群之精神,不敢公言之。例如蘇格拉底創新哲學,下獄而被鴆;哥白尼為新天文說,見仇于教皇;巴枯寧道無政府主義,而被囚被逐,是也。
其他如試演飛機、探險南北極之類,在今日以為敢死之事業,雖或由好奇競勝者之所為,而亦有起于利群之動機者,得附列之。
■注意公眾衛生
古諺有云:“千里不唾井。”言將有千里之行,雖不復汲此井,而不敢唾之以妨人也。殷之法,棄灰于道者有刑,恐其飛揚而瞇人目也。孔子曰:“君子敝帷不棄,為埋馬;敝蓋不棄,為埋狗。”言已死之狗、馬,皆埋之,勿使暴露,以播其惡臭也。蓋古人之注意于公眾衛生者,既如此。
今日公眾衛生之設備,較古為周。誠以衛生條件,本以清潔為一義。各人所能自營者,身體之澡浴,衣服之更迭,居室之灑掃而已。使其周圍之所,污水停潴,廢物填委,落葉死獸之腐敗者,散布于道周,傳染病之霉菌,彌漫于空氣,則雖人人自潔其身體、衣服及居室,而衛生之的仍不達。夫是以有公眾衛生之設備。例如溝渠必在地中,溷廁必有溜水,道路之掃除,棄物之運移,有專職,有定時,傳染病之治療,有特別醫院,皆所以助各人衛生之所不及也。
吾既受此公眾衛生之益,則不可任意妨礙之,以自害而害人。毋唾于地;毋傾垢水于溝渠之外;毋棄擲雜物于公共之道路若川流。不幸而有傳染之疾,則亟自隔離,暫絕交際。其稍重者,寧移居醫院,而勿自溷于稠人廣眾之間。此吾人對于公眾衛生之義務也。
■愛護公共之建筑及器物
往者園亭之勝,花鳥之娛,有力者自營之、而自賞之也。今則有公園以供普通之游散;有植物、動物等園,以為賞鑒及研究之資。往者宏博之圖書,優美之造象與繪畫,歷史之紀念品,遠方之珍異,有力者得收藏之,而不輕以示人也。今則有藏書樓,以供公眾之閱覽,有各種博物院,以興美感而助智育。且也,公園之中,大道之旁,植列樹以為庇蔭,陳坐具以供休憩,間亦注引清水以資飲料。是等公共之建置,皆吾人共享之利益也。
吾人既有此共同享受之利益,則即有共同愛護之義務;而所以愛護之者,當視一己之住所及器物為尤甚。以其一有損害,則爽然失望者,不止己一人已也。
是故吾人而行于道路,游于公園,則勿以花木之可愛,而輕折其枝葉;勿垢污其坐具,亦勿踐踏而刻畫之;勿引杖以擾猛獸;勿投石以驚魚鳥;入藏書樓而有所誦讀,若抄錄,則當慎護其書,毋使稍有污損;進博物院,則一切陳列品,皆可以目視,而不可手觸。有一于此,雖或幸逃典守者之目,而不遭誚讓,然吾人良心上之呵責,固不能幸免矣。
■盡力于公益
凡吾人共同享受之利益,有共同愛護之責任,此于《注意公眾衛生》及《愛護公共之建筑及器物》等篇,所既言者也。顧公益之既成者,吾人當愛之;其公益之未成者,吾人尤不得不建立之。
自昔吾國人于建橋、敷路,及義倉、義塾之屬,多不待政府之經營,而相與集資以為之。近日更有獨力建設學校者,如浙江之葉君澄衷,以小販起家,晚年積資至數百萬,則出其十分之一,以建設澄衷學堂。江蘇之楊君錦春,以木工起家,晚年積資至十余萬,則出其十分之三,以建設浦東中學校。其最著者矣。
雖然,公益之舉,非必待富而后為之也。山東武君訓,丐食以奉母,恨己之失學而流于乞丐也,立志積資以設一校,俾孤貧之子,得受教育,持之十余年,卒達其志。夫無業之乞丐,尚得盡力于公益,況有業者乎?
英之翰回,商人也,自奉甚儉,而勇于為善;嘗造倫敦大道;又憫其國育嬰院之不善,自至法蘭西、荷蘭諸國考察之;歸而著書,述其所見,于是英之育嬰院為之改良。其歿也,遺財不及二千金,悉以散諸孤貧者。英之沙伯,業織麻者也,后為炮廠書記,立志解放黑奴,嘗因辯護黑奴之故,而研究民法,卒得直;又與同志設一放奴公司,黑奴之由此而被釋者甚眾。英之萊伯,鐵工也,憫罪人之被赦者,輒因無業而再罹于罪,思有以救助之;其歲入不過百鎊,悉心分配,一家衣食之用者若干,教育子女之費若干,余者用以救助被赦而無業之人。彼每日做工,自朝六時至晚六時,而以其暇時及安息日,為被赦之人謀職業。行之十年,所救助者凡三百余人。由此觀之,人茍有志于公益,則無論貧富,未有不達其志者,勉之而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貢問于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日,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舉孔子所告,而申言之也。西方哲學家之言曰:“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其義正同。例如我有思想及言論之自由,不欲受人之干涉也,則我亦勿干涉人之思想及言論;我有保衛身體之自由,不欲受人之毀傷也,則我亦勿毀傷人之身體;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不欲受人之窺探也,則我亦慎勿窺人之秘密;推而我不欲受人之欺詐也,則我慎勿欺詐人;我不欲受人之侮慢也,則我亦慎勿侮慢人。事無大小,一以貫之。
顧我與人之交際,不但有消極之戒律,而又有積極之行為。使由前者而下一轉語曰:“以己所欲施于人。”其可乎?曰是不盡然。人之所欲,偶有因遺傳及習染之不善,而不軌于正者。使一切施之于人,則抑或無益而有損。例如腐敗之官僚,喜受屬吏之諂媚也,而因以諂媚于上官,可乎?迷信之鄉愚,好聽教士之附會也,而因以附會于親族,可乎?至于人所不欲,雖亦間有謬誤,如惡聞、直言之類,然使充不欲勿施之義,不敢以直言進人,可以婉言代之,亦未為害也。
且積極之行為,孔子固亦言之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者,立身也;達者,道可行于人也。言所施必以立達為界,言所勿施則以己所不欲概括之,誠終身行之而無弊者矣。
■責己重而責人輕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韓退之又申明之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其足以反證此義者,孟子言父子責善之非,而述人子之言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原伯及先且居皆以效尤為罪咎。椒舉曰:“唯無瑕者,可以戮人。”皆言責人而不責己之非也。
準人我平等之義,似乎責己重者,責人亦可以重,責人輕者,責己亦可以輕。例如多聞見者笑人固陋,有能力者斥人無用,意以為我既能之,彼何以不能也。又如怙過飾非者,每喜以他人同類之過失以自解,意以為人既為之,我何獨不可為也。不知人我固當平等,而既有主觀、客觀之別,則觀察之明晦,顯有差池,而責備之度,亦不能不隨之而進退。蓋人之行為,常含有多數之原因:如遺傳之品性,漸染之習慣,薰受之教育,拘牽之境遇,壓迫之外緣,激刺之感情,皆有左右行為之勢力。行之也為我,則一切原因,皆反省而可得。即使當局易迷,而事后必能審定。既得其因,則遷善改過之為,在此可以致力:其為前定之品性、習慣、及教育所馴致耶,將何以矯正之;其為境遇、外緣、及感情所逼成耶,將何以調節之。既往不可追,我固自怨自艾;而茍有不得已之故,決不慮我之不肯自諒。其在將來,則操縱之權在我,我何餒焉?至于他人,則其馴致與迫成之因,決非我所能深悉。使我任舉推得之一因,而嚴加責備,寧有當乎?況人人各自有其重責之機會,我又何必越俎而代之?故責己重而責人輕,乃不失平等之真意,否則,跡若平而轉為不平之尤矣。
■勿畏強而侮弱
崧高之詩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而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御。”人類之交際,彼此平等;而古人乃以食物之茹、吐為比例,甚非正當;此仲山甫之所以反之,而自持其不侮弱、不畏強之義務也。
畏強與侮弱,其事雖有施受之殊,其作用亦有消極與積極之別。然無論何一方面,皆蔽于強弱不容平等之謬見。蓋我之畏強,以為我弱于彼,不敢與之平等也。則見有弱于我者,自然以彼為不敢與我平等而侮之。又我之侮弱,以為我強于彼,不必與彼平等也,則見有強于我者,自然以彼為不必與我平等而畏之。跡若異而心則同。矯其一,則其他自隨之而去矣。
我國壯俠義之行有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言見有以強侮弱之事,則亟助弱者以抗強者也。夫強者尚未浼我,而我且進與之抗,則豈其浼我而轉畏之;弱者與我無涉,而我且既而相助,則豈其近我而轉侮之?彼拔刀相助之舉,雖曰屬之俠義,而抱不平之心,則人所皆有。吾人茍能擴充此心,則畏強侮弱之惡念,自無自而萌芽焉。
■愛護弱者
前于《勿畏強而侮弱》說,既言抱不平理。此對于強、弱有沖突時而言也。實則吾人對于弱者,無論何時,常有惻然不安之感想。蓋人類心理,以平為安,見有弱于我者,輒感天然之不平,而欲以人力平之。損有余以益不足,此即愛護弱者之原理也。
在進化較淺之動物,已有實行此事者。例如秘魯之野羊,結隊旅行,遇有獵者,則羊之壯而強者,即停足而當保護之沖,俟全隊畢過,而后殿之以行。鼠類或以食物餉其同類之瞽者。印度之小鳥,于其同類之瞽者、或受傷者,皆以時贍養之。曾是進化之深如人類,而羊、鼠、小鳥之不如乎?今日普通之人,于舟車登降之際,遇有廢疾者,輒為讓步,且值其艱于登降而扶持之。坐車中或婦女至而無空座,則起而讓之;見其所攜之物,有較繁重者,輒為傳遞而安頓。此皆愛護弱者之一例也。
航行大海之船,猝遇不幸,例必以救生之小舟,先載婦孺。俟有余地,男子始得而占之。其有不明理之男子,敢與婦孺爭先者,雖槍斃之,而不為忍。為愛護弱者計,急不暇擇故也。戰爭之不免殺人,無可奈何也。然已降及受傷之士卒,敵國之婦孺,例不得加以殘害。德國之飛艇及潛水艇,所加害者眾矣;而輿論攻擊,尤以其加害于婦孺為口實。亦可以見愛護弱者,為人類之公意焉。
■愛物
孟子有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茍有親仁之心,未有不推以及物者,故曰:“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子傅,曰:“夫不忍于麑,又且忍于兒乎?”可以證愛人之心,通于愛物,古人已公認之。自近世科學進步,所以誘導愛物之心者益甚。其略如下:
一、古人多持“神造動物以供人用”之說。齊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嘆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于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并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鮑氏之言進矣。自有生物進化學,而知人為各種動物之進化者,彼此出于同祖,不過族屬較疏耳。
二、古人又持“動物唯有知覺,人類獨有靈魂”之說。自生理學進步,而知所謂靈魂者,不外意識之總體。又自動物心理學進步,而能言之狗,知算之馬,次第發現,亦知動物意識,固亦猶人,特程度較低而已。
三、古人助力之具,唯賴動物;竭其力而猶以為未足,則恒以鞭策叱咤臨之,故愛物之心,常為利己心所抑沮。自機械繁興,轉運工業,耕耘之工,向之利用動物者,漸以機械代之。則虐使動物之舉,為之漸減。
四、古人食肉為養生之主要。自衛生發見肉食之害,不特為微生蟲之傳導,且其強死之時,發生一種毒性,有妨于食之者。于是蔬食主義漸行,而屠獸之場可望其日漸淘汰矣。
方今愛護動物之會,流行漸廣,而屠獵之舉,一時未能絕跡;然授之以漸,必有足以完愛物之量者。昔晉翟莊耕而后食,唯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先生只去其一,何哉?”莊曰:“獵是我,釣是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晚節亦不復釣。全世界愛物心之普及,亦必如翟莊之漸進,無可疑也。
■戒失信
失信之別有二:曰食言,曰愆期。
食言之失,有原于變計者,如晉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是也。有原于善忘者,如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是也。有原于輕諾者,如老子所謂“輕諾必寡信”是也。然晉文公聞軍吏之言而答之曰:“得原失信,將焉用之?”見變計之不可也。魏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不敢忘約也。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言季布不輕諾,諾則必踐也。
愆期之失,有先期者,有后期者,有待人者,有見待于人者。漢郭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謂違信于諸兒,遂止于野,及期乃入。明不當先期也。漢陳太丘與友期行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時七歲,戲門外。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不至,則是失信。”友人慚。明不可后期也。唐肖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豈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友至,乃去。眾嘆服。待人不愆期也。吳卓恕為人篤信,言不宿諾,與人期約,雖暴風疾雨冰雪無不至。嘗從建業還家,辭諸葛恪。恪問何時當復來。恕對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恕至,一座皆驚。見待于人而不愆期也。
夫人與人之關系,所以能預計將來,而一一不失其秩序者,恃有約言。約而不踐,則秩序為之紊亂,而猜疑之心滋矣。愆期之失,雖若輕于食言,然足以耗光陰而喪信用,亦不可不亟戒之。
■戒狎侮
人類本平等也。而或乃自尊而卑人,于是有狎侮。如王曾與楊億同為侍從。億善談謔,凡寮友無所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吾不敢與戲。”非以自曾以外,皆其所卑視故耶?人類有同情也。而或者乃致人于不快以為快,于是狎侮。如王風使人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幾死,因大笑為樂是也。夫吾人以一時輕忽之故,而致違平等之義,失同情之真,又豈得不戒之乎?
古人常有因狎侮而得禍者。如許攸恃功驕慢,嘗于聚坐中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吾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后竟殺之。又如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厚,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中,而性褊躁,常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左右白其母,救得止。夫操、武以不堪狎侮而殺人,固為殘暴;然許攸、杜甫,獨非自取其咎乎?
歷史中有以狎侮而啟國際間之戰爭者。春秋時,晉郤克與魯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齊君之母肖同侄子,踴于踣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肖同侄子笑之,聞于客。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鞍大戰。齊師大敗。蓋狎侮之禍如此。
其狎侮人而不受何種之惡報者,亦非無之。如唐高固久在散位,數為儔類所輕笑,及被任為邠寧節度使,眾多懼。固一釋不問。宋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赴試京師,自詣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曰:“似君人物來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后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文懿,恐甚,意其不忘前日之言也。文懿特差昭言知眉州。如斯之類,受狎侮者誠為大度,而施者已不勝其恐懼矣。然則何樂而為之乎?
是故按之理論,驗之事實,狎侮之不可不戒也甚明。
■戒謗毀
人皆有是非之心:是曰是,非曰非,宜也。人皆有善善惡惡之情: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宜也。唯是一事之是非,一人之善惡,其關系至為復雜,吾人一時之判斷,常不能據為定評。吾之所評為是、為善,而或未當也,其害尚小。吾之所評為非、為惡,而或不當,則其害甚大。是以吾人之論人也,茍非公益之所關,責任之所在,恒揚其是與善者,而隱其非與惡者。即不能隱,則見為非而非之,見為惡而惡之,其亦可矣。若本無所謂非與惡,而我虛構之,或其非與惡之程度本淺,而我深文周納之,則謂之謗毀。謗毀者,吾人所當戒也。
吾人試一究謗毀之動機,果何在乎?將忌其人名譽乎?抑以其人之失意為有利于我乎?抑以其人與我有宿怨,而以是中傷之乎?凡若此者,皆問之良心,無一而可者也。凡毀謗人者,常不能害人,而適以自害。漢申咸毀薛宣不孝,宣子況賕客楊明遮斫咸于宮門外。中丞議不以凡斗論,宜棄市。朝廷直以為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宜與疻人同罪,竟減死。今日文明國法律,或無故而毀人名譽,則被毀者得為賠償損失之要求,足以證謗毀者之適以自害矣。
古之被謗毀者,亦多持不校之義,所謂止謗莫如自修也。漢班超在西域,衛尉李邑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章帝怒,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干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北齊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劭。劭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劭字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皆是實事。劭不為癡。”皆其例也。雖然,受而不校,固不失為盛德;而自施者一方面觀之,不更將無地自容耶?吾人不必問受者之為何如人,而不可不以施為戒。
■戒罵詈
吾國人最易患之過失,其罵詈乎?素不相識之人,于無意之中,偶相觸迕,或驅車負擔之時,小不經意,彼此相撞,可以互相謝過了之者,輒矢口罵詈,經時不休。又或朋友戚族之間,論事不合,輒以罵詈繼之。或斥以畜類,或辱其家族。此北自幽燕,南至吳粵,大略相等者也。
夫均是人也,而忽以畜類相斥,此何義乎?據生物進化史,人類不過哺乳動物之較為進化者;而爬蟲實哺乳動物之祖先。故二十八日之人胎,與日數相等之狗胎、龜胎,甚為類似。然則斥以畜類,其程度較低之義耶?而普通之人,所見初不如是。漢劉寬嘗坐有客,遣蒼頭沽酒。遲久之。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我懼其死也。”又苻秦時,王惰性剛峻,疾董榮如仇讎,略不與言,嘗曰:“董龍是何雞狗者,令國士與之言乎?”(龍為董榮之小字。)榮聞而慚憾,遂勸苻生殺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夫或恐自殺,或且殺人,其激刺之烈如此。而今之人,乃以是相詈,恬不為怪,何歟?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怒一人而辱及其家族,又何義乎?昔衛孫蒯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詬之曰:“爾父為厲。”齊威王之見責于周安王也,詈之曰:“咄嗟,爾母婢也。”此古人之詬及父母者也。其加以穢辭者,唯嘲戲則有之。《抱樸子·疾謬篇》曰:“嘲戲之談,或及祖考,下逮婦女。”既斥為謬而疾之。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徵舒之母,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靈公卒以是為徵舒所殺。而今之人乃以是相詈,恬不為怪,何歟?
無他,口耳習熟,則雖至不合理之詞,亦復不求其故;而人云亦云,如嘆詞之暗嗚咄咤云耳。《說苑》曰:“孔子家兒不知罵,生而善教也。”愿明理之人,注意于陋習而矯正之。
■文明與奢侈
讀人類進化之歷史:昔也穴居而野處,今則有完善之宮室;昔也飲血茹毛,食鳥獸之肉而寢其皮,今則有烹飪、裁縫之術;昔也束薪而為炬,陶土而為燈,而今則行之以煤氣及電力;昔也椎輪之車,刳木之舟,為小距離之交通,而今則汽車及汽舟,無遠弗屆;其他一切應用之物,昔粗而今精,昔簡單而今復雜,大都如是。故以今較昔,器物之價值,百倍者有之,千倍者有之,甚而萬倍、億倍者亦有之,一若昔節儉而今奢侈,奢侈之度,隨文明而俱進。是以厭疾奢侈者,至于并一切之物質文明而屏棄之,如法之盧梭,俄之托爾斯泰是也。
雖然,文明之與奢侈,固若是其密接而不可離乎?是不然。文明者,利用厚生之普及于人人者也。敷道如砥,夫人而行之;漉水使潔,夫人而飲之;廣衢之燈,夫人而利其明;公園之音樂,夫人而聆其音;普及教育,平民大學,夫人而可以受之;藏書樓之書,其數巨萬,夫人而可以讀之;博物院之美術品,其值不貲,夫人而可以賞鑒之。夫是以謂之文明。且此等設施,或以衛生,或以益智,或以進德,其所生之效力,有百千萬億于所費者。故所費雖多,而不得以奢侈論。
奢侈者,一人之費,逾于普通人所費之均數,而又不生何等之善果,或轉以發生惡影響。如《呂氏春秋》所謂“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酒厚肉,務以自疆,命之曰爛腸之食”是也。此等惡習,本酋長時代所遺留。在昔普通生活低度之時,凡所謂峻宇雕墻,玉杯象箸,長夜之飲,游畋之樂,其超越均數之費者何限?普通生活既漸高其度,即有貴族富豪以窮奢極侈著,而其超越均數之度,決不如酋長時代之甚。故知文明益進,則奢侈益殺。謂今日之文明,尚未能剿滅奢侈則可;以奢侈為文明之產物,則大不可也。吾人當詳觀文明與奢侈之別,尚其前者,而戒其后者,則折中之道也。
■理信與迷信
人之行為,循一定之標準,而不至彼此互相沖突,前后判若兩人者,恃乎其有所信。顧信亦有別,曰理信,曰迷信。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也。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是因而后有是果,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于事理之較為復雜者,輒不能了然。于其因果之相關,則妄歸其因于不可知之神,而一切倚賴之。其屬于幸福者,曰是神之喜而佑我也,其屬于不幸福者,曰是神之怒而禍我也。于是求所以喜神而免其怒者,祈禱也,祭告也,懺悔也,立種種事神之儀式,而于其所求之果,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顧信之,是迷信也。
礎潤而雨,征諸濕也;履霜堅冰至,驗諸寒也;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符諸情也;見是因而知其有是果,亦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既歸其一切之因于神,而神之情不可得而實測也,于是不勝其僥幸之心,而欲得一神人間之媒介,以為窺測之機關,遂有巫覡卜人星士之屬,承其乏而自欺以欺人:或托為天使,或夸為先知,或卜以龜蓍,或占諸星象,或說以夢兆,或觀其氣色,或推其誕生年月日時,或相其先人之墳墓,要皆為種種預言之準備,而于其所求果之真因,又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顧信之,是亦迷信也。
理信則不然,其所見為因果相關者,常積無數之實驗,而歸納以得之,故恒足以破往昔之迷信。例如日食、月食,昔人所謂天之警告也,今則知為月影、地影之偶蔽,而可以預定其再見之時。疫癘,昔人所視為神譴者也,今則知為微生物之傳染,而可以預防。人類之所以首出萬物者,昔人以為天神創造之時,賦畀獨厚也;今則知人類為生物進化中之一級,以其觀察自然之能力,同類互助之感情,均視他種生物為進步,故程度特高也。是皆理信之證也。
人能祛迷信而持理信,則可以省無謂之營求及希冀,以專力于有益社會之事業,而日有進步矣。
■循理與畏威
人生而有愛己愛他之心象,因發為利己利他之行為。行為之己他兩利,或利他而不暇利己者為善。利己之過,而不惜害他人者為惡。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也。
蒙昧之世,人類心象尚隘,見己而不及見他,因而利己害他之行為,所在多有。有知覺較先者,見其事之有害于人群,而思所以防止之,于是有賞罰:善者賞之,惡者罰之,是法律所托始也。是謂酋長之威。酋長之賞罰,不能公平無私也;而其監視之作用,所以為賞罰標準者,又不能周密而無遺。于是隸屬于酋長者,又得趨避之術,而不憚于惡;而酋長之威窮。
有濟其窮者曰:“人之行為,監視之者,不獨酋長也,又有神。吾人即獨居一室,而不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為善則神賜之福,為惡則神降之罰。神之賞罰,不獨于其生前,而又及其死后:善者登天堂,而惡者入地獄。”或又為之說曰:“神之賞罰,不獨于其身,而又及其子孫:善者子孫多且賢,而惡者子孫不肖,甚者絕其嗣。”或又為之說曰:“神之賞罰,不唯于其今生也,而又及其來世:善者來世為幸福之人,而惡者則轉生為貧苦殘廢之人,甚者為獸畜。”是皆宗教家之所傳說也。是謂神之威。
雖然,神之賞罰,其果如斯響應乎?其未來之苦樂,果足以抑現世之刺沖乎?故有所謂神之威,而人之不能免于惡如故。
且君主也,官吏也,教主也,輒利用酋長之威,及神之威,以強人去善而為惡。其最著者,政治之戰、宗教之戰是也。于是乎威者不但無成效,而且有流弊。
人智既進,乃有科學。科學者,舍威以求理者也。其理奈何?曰,我之所謂己,人之所謂他也。我之所謂他,人之所謂己也。故觀其通,則無所謂己與他,而同謂之人。人之于人,無所不愛,則無所不利。不得已而不能普利,則犧牲其最少數者,以利其最大多數者,初不必問其所犧牲者之為何人也。如是,則為善最樂,又何苦為惡耶?
吾人之所為,既以理為準則,自然無恃乎威;且于流弊滋章之威,務相率而廓清之,以造成自由平等之世界,是則吾人之天責也。
■堅忍與頑固
《漢書·律歷》云:“凡律度量衡用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考工記》曰:“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鏈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賈疏曰:“金謂銅也。”然則銅之質,可由兩方面觀察之:一則對于外界儻來之境遇,不為所侵蝕也;二則應用于器物之制造,又能調和他金屬之長,以自成為種種之品格也。所謂有似于士君子之行者,亦當合兩方面而觀之。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猶夫銅之不變而有常乎?是謂堅忍。孔子曰:“見賢思齊焉。”又曰:“多聞擇善者而從之。”孟子曰:“樂取于人以為善。”荀子曰:“君子之學如蛻。”非猶夫銅之資錫以為齊乎?是謂不頑固。
堅忍者,有一定之宗旨以標準行為,而不為反對宗旨之外緣所憧擾,故遇有適合宗旨之新知識,必所歡迎。頑固者本無宗旨,徒對于不習慣之革新,而為無意識之反動;茍外力遇其惰性,則一轉而不之返。是故堅忍者必不頑固,而頑固者轉不堅忍也。
不觀乎有清之季世乎?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以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和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然一經庚子聯軍之壓迫,則向之排外者,一轉而反為媚外。凡為外人,不問賢否,悉崇拜之;凡為外俗,不問是非,悉仿效之。其不堅忍為何如耶?革命之士,慨政俗之不良,欲輸入歐化以救之,可謂不頑固矣。經政府之反對,放逐囚殺,終不能奪其志。其堅忍為何如耶?堅忍與頑固之別,觀夫此而益信。
■自由與放縱
自由,美德也。若思想,若身體,若言論,若居處,若職業,若集會,無不有一自由之程度。若受外界之壓制,而不及其度,則盡力以爭之,雖流血亦所不顧,所謂“不自由毋寧死”是也。然若過于其度,而有愧于己,有害于人,則不復為自由,而謂之放縱。放縱者,自由之敵也。
人之思想不縛于宗教,不牽于俗尚,而一以良心為準。此真自由也。若偶有惡劣之思想,為良心所不許,而我故縱容之,使積漸擴張,而勢力遂駕于良心之上,則放縱之思想而已。
饑而食,渴而飲,倦而眠,衛生之自由也。然使飲食不節,興寐無常,養成不良之習慣,則因放縱而轉有害于衛生矣。
喜而歌,悲而哭,感情之自由也。然而里有殯,不巷歌,寡婦不夜哭,不敢放縱也。
言論可以自由也,而或乃訐發陰私,指揮淫盜;居處可以自由也,而或于其間為危險之制造,作長夜之喧囂;職業可以自由也,而或乃造作偽品,販賣毒物;集會可以自由也,而或以流布迷信,恣行奸邪。諸如此類,皆逞一方面極端之自由,而不以他人之自由為界,皆放縱之咎也。
昔法國之大革命,爭自由也,吾人所崇拜也。然其時如羅伯士比及但丁之流,以過度之激烈,恣殺貴族,釀成恐怖時代,則由放縱而流于殘忍矣。近者英國婦女之爭選舉權,亦爭自由也,吾人所不敢菲薄也。然其脅迫政府之策,至于燒毀郵件,破壞美術品,則由放縱而流于粗暴矣。夫以自由之美德,而一涉放縱,則且流于粗暴或殘忍之行為而不覺。可不慎歟?
■鎮定與冷淡
世界蕃變,常有一時突起之現象,非意料所及者。普通人當之,恒不免張皇無措。而弘毅之才,獨能不動聲色,應機立斷,有以掃眾人之疑慮,而免其紛亂,是之謂鎮定。
昔諸葛亮屯軍于陽平,唯留萬人守城。司馬懿垂至,將士失色,莫之為計。而亮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息鼓,大開西城門,掃地卻灑。懿疑有伏,引軍趨北山。宋劉幾知保州,方大會賓客;夜分,忽告有卒為亂;幾不問,益令折花勸客。幾已密令人分捕,有頃禽至。幾復極飲達旦。宋李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息,密檄瀛洲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軍器完足,人無知者。真宗詰之。曰:“兵機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奸人所為。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是皆不愧為鎮定矣。
鎮定者,行所無事,而實大有為者也。若目擊世變之亟,而曾不稍受其刺激,轉以清靜無為之說自遣,則不得謂之鎮定,而謂之冷淡。
晉之叔世,五胡云擾。王衍居宰輔之任,不以經國為念,而雅詠玄虛。后進之士,景慕仿效,矜高浮誕,遂成風俗。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眾心。事若近乎鎮定。然不及為備,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不至今日。”此冷淡之失也。
宋富弼致政于家,為長生之術,呂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唯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歲之盛衰,而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心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弼謝之。此極言冷淡之不可也。
觀衍之臨死而悔,弼之得書而謝,知冷淡之弊,不獨政治家,即在野者,亦不可不深以為戒焉。
■熱心與野心
孟子有言:“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跖之徒也。”二者,孜孜以為之同,而前者以義務為的,謂之“熱心”;后者以權利為的,謂之“野心”。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此熱心也。故禹平水土,稷教稼穡,有功于民。項羽觀秦始皇帝曰:“彼可取而代也”;劉邦觀秦始皇帝曰:“嗟夫!大丈夫當如是也。”此野心也。故暴秦既滅,劉、項爭為天子,血戰五年。羽嘗曰:“天下洶洶數歲者,徒為吾兩人耳。”野心家之貽害于世,蓋如此。
美利堅之獨立也,華盛頓盡瘁軍事,及七年之久。立國以后,革世襲君主之制,而為選舉之總統。其被舉為總統也,綜理政務,至公無私。再任而退職,躬治農圃,不復投入政治之旋渦。及其將死,以家產之一部分,捐助公共教育及其他慈善事業。可謂有熱心而無野心者矣。
世固有無野心而并熄其熱心者。如長沮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馬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是也。凡隱遁之士,多有此失;不知人為社會之一分子,其所以生存者,無一非社會之賜。顧對于社會之所需要,漠然置之,而不一盡其力之所能及乎?范仲淹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李燔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諒哉言乎!
且熱心者,非必直接于社會之事業也。科學家閉戶自精,若無與世事,而一有發明,則利用厚生之道,輒受其莫大之影響。高上之文學,優越之美術,初若無關于實利,而陶鑄性情之力,莫之與京。故孜孜學術之士,不失為熱心家。其或恃才傲物,飾智驚愚,則又為學術界之野心,亦不可不戒也。
■英銳與浮躁
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呂氏春秋》曰:“力重突,知貴卒。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此言英銳之要也。周人之諺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幾。”諸葛亮之評劉繇、王郎曰:“群疑滿腹,眾難塞胸。”言不英銳之害也。
楚丘先生年七十。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曰:“使逐獸麋而搏虎豹,吾已老矣;使出正詞而當諸侯,決嫌疑而定猶豫,吾始壯矣。”此老而英銳者也。范滂為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此少而英銳者也。
少年英銳之氣,常遠勝于老人。然縱之太過,則流為浮躁。蘇軾論賈誼、晁錯曰:“賈生天下奇才,所言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系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兵,兇事也,尚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俱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矣。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至于晁錯,尤號刻薄,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改法令,天下騷然。至于七國發難,而錯之術窮矣。”韓愈論柳宗元曰:“子厚前時少年,勇于為人,不自貴重,顧借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材不為世用,道不行于時。使子厚在臺省時,已能自持其身,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皆惜其英銳之過,涉于浮躁也。夫以賈、晁、柳三氏之才,而一涉浮躁,則一蹶不振,無以伸其志而盡其才。況其才不如三氏者,又安得不兢兢焉以浮躁為戒乎?
■果敢與魯莽
人生于世,非僅僅安常而處順也,恒遇有艱難之境。艱難之境,又非可畏懼而卻走也,于是乎尚果敢。雖然,果敢非盲進之謂。盲進者,魯莽也。果敢者,有計劃,有次第,持定見以進行,而不屈不撓,非貿然從事者也。
禹之治水也,當洪水滔天之際,而其父方以無功見殛,其艱難可知矣。禹于時毅然受任而不辭。鑿龍門,辟伊闕,疏九江,決江淮,九年而水土平。彼蓋鑒于其父之恃堤防而逆水性、以致敗也,一以順水性為主義。其疏鑿排導之功,悉循地勢而分別行之,是以奏績。
墨翟之救宋也,百舍重繭而至楚,以竊疾說楚王。王既無詞以對矣,乃托詞于公輸般之既為云梯,非攻宋不可。墨子乃解帶為城,以褋為械,使公輸般攻之。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懼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夫以五千里之楚,欲攻五百里之宋,而又在攻機新成、躍躍欲試之際,乃欲以一處士之口舌阻之,其果敢為何如?雖然,使墨子無守圉之具,又使有其具而無代為守圉之弟子,則墨子亦徒喪其身,而何救于國哉?
藺相如之奉璧于秦也,挾數從者,赍價值十二連城之重寶,而入虎狼不測之秦,自相如以外,無敢往者。相如既至秦,見秦王無意償城,則嚴詞責之,且以頭璧俱碎之激舉脅之。雖貪橫無信之秦王,亦不能不為之屈也。非洞明敵人之心理,而預定制御之道,烏能從容如此耶?
夫果敢者,求有濟于事,非沾沾然以此自矜也。觀于三子之功,足以知果敢之不同于魯莽,而且唯不魯莽者,始得為真果敢矣。
■精細與多疑
《呂氏春秋》曰:“物多類,然而不然。”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淮南子》曰:“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炫耀: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夫物之類似者,大都如此,故人不可以不精細。
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又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度哉?”莊子曰:“人者厚貌深情,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之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皆觀人之精細者也。不唯觀人而已,律己亦然。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孟子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蓋君子之律己,其精細亦如是。
精細非他,視心力所能及而省察之云爾。若不事省察,而妄用顧慮,則謂之多疑。列子曰:“人有亡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也;顏色,竊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也。俄而揚其谷,而得其。”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視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變,以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皆言多疑之弊也。
其他若韓昭侯恐泄夢言于妻子而獨臥;五代張允,家資萬計,日攜眾鑰于衣下。多疑如此,皆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者也。其與精細,豈可同日語哉?
■尚潔與太潔
華人素以不潔聞于世界:體不常浴,衣不時浣,咳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灑掃,廁所任其熏蒸,飲用之水,不加滲漉,傳染之病,不知隔離。小之損一身之康強,大之釀一方之疫癘。此吾儕所痛心疾首,而愿以尚潔互相勸勉者也。
雖然,尚潔亦有分際。沐浴灑掃,一人所能自盡也;公共之清潔,可互約而行之者也。若乃不循常軌,矯枉而過于正,則其弊亦多。南宋何佟之,一日洗濯十余遍,猶恨不足;元倪瓚盥颒頻易水,冠服拂拭,日以數十計,齋居前后樹石頻洗拭;清洪景融每靦面,輒自旦達午不休。此太潔而廢時者也。
南齊王思遠,諸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后,猶令二人交拂其坐處。庾炳之,士大夫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床;宋米芾不與人共巾器。此太潔而妨人者也。
若乃采訪風土,化導夷蠻,挽救孤貧,療護疾病,勢不得不入不潔之地,而接不潔之人。使皆以好潔之故,而裹足不前,則文明無自流布,而人道亦將歇絕矣。漢蘇武之在匈奴也,居窟室中,嚙雪與氈而吞之。宋洪皓之在金也,以馬糞燃火,烘面而食之。宋趙善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為煮藥。瑞士沛斯泰洛齊集五十余乞兒于一室而教育之。此其人視王思遠、庾炳之輩為何如耶?
且尚潔之道,亦必推己而及人。秦苻朗與朝士宴會,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謂之肉唾壺。此其昧良,不待言矣。南宋謝景仁居室極凈麗,每唾,輒唾左右之衣。事畢,聽一日浣濯。雖不似苻朗之忍,然亦縱己而蔑人者也。漢郭泰,每行宿逆旅,輒躬灑掃;及明去后,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斯則可以為法者矣。
■互助與依賴
西人之寓言曰:“有至不幸之甲、乙二人。甲生而瞽,乙有殘疾不能行。二人相依為命:甲負乙而行,而乙則指示其方向,遂得互減其苦狀。”甲不能視而乙助之,乙不能行而甲助之,互助之義也。
互助之義如此。甲之義務,即乙之權利,而同時乙之義務,亦即甲之權利:互相消,即互相益也。推之而分工之制,一人之所需,恒出于多數人之所為,而此一人之所為,亦還以供多數人之所需。是亦一種復雜之互助云爾。
若乃不盡義務,而唯攫他人義務之產業為己權利,是謂依賴。
我國舊社會依賴之風最盛。如乞丐,固人人所賤視矣。然而紈袴子弟也,官親也,幫閑之清客也,各官署之冗員也,凡無所事事而倚人以生活者,何一非乞丐之流亞乎?
《禮·王制》記曰:“瘖聾、跛躃、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晉胥臣曰:“戚施直镈,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廢疾之人,且以一藝自贍如此,顧康強無恙,而不以倚賴為恥乎?
往昔慈善家,好賑施貧人。其意甚美,而其事則足以助長依賴之心。今則出資設貧民工藝廠以代之。饑饉之年,以工代賑。監禁之犯,課以工藝,而代蓄贏利,以為出獄后營生之資本。皆所以絕依賴之弊也。
幼稚之年,不能不倚人以生,然茍能勤于學業,則壯歲之所致力,足償宿負而有余。平日勤工節用,蓄其所余,以備不時之需,則雖衰老疾病之時,其力尚足自給,而不至累人,此又自助之義,不背于互助者也。
■愛情與淫欲
盡世界人類而愛之,此普通之愛,純然倫理學性質者也。而又有特別之愛,專行于男女之間者,謂之愛情,則以倫理之愛,而兼生理之愛者也。
生理之愛,常因人而有專泛久暫之殊,自有夫婦之制,而愛情乃貞固。此以倫理之愛,范圍生理之愛,而始有純潔之愛情也。
純潔之愛,何必限于夫婦?曰既有所愛,則必為所愛者保其康健,寧其心情,完其品格,芳其聞譽,而準備其未來之幸福。凡此諸端,準今日社會之制度,唯夫婦足以當之。若于夫婦關系以外,縱生理之愛,而于所愛者之命運,恝然不顧,是不得謂之愛情,而謂之淫欲。其例如下:
一曰納妾。妾者,多由貧人之女賣身為之。均是人也,而儕諸商品,于心安乎?均是人也,使不得與見愛者敵體,而視為奴隸,于心安乎?一納妾而夫婦之間,猜嫌迭起,家庭之平和為之破壞;或縱妻以虐妾,或寵妾而疏妻,種種罪惡,相緣以起。稍有人心,何忍出此?
二曰狎妓。妓者,大抵青年貧女,受人誘惑,被人壓制,皆不得已而業此。社會上均以無人格視之?吾人方哀矜之不暇,而何忍褻視之。其有為妓脫籍者,固亦救拔之一法;然使不為之慎擇佳偶,而占以為妾,則為德不卒,而重自陷于罪惡矣。
三曰奸通。凡曾犯奸通之罪者,無論男女,恒為普通社會所鄙視,而在女子為尤甚,往往以是而摧滅其終身之幸福:甚者自殺,又甚者被殺。吾人興念及此,有不為之慄慄危懼,而懸為厲禁者乎?
其他不純潔之愛情,其不可犯之理,大率類是,可推而得之。
■方正與拘泥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蓋人茍無所不為,則是無主宰,無標準,而一隨外界之誘導或壓制以行動,是烏足以立身而任事哉,故孟子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又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言無論外境如何,而決不為違反良心之事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謂視聽言動,無不循乎規則也。是皆方正之義也。
昔梁明山賓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后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取還錢。唐吳兢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后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一則寧失利而不肯欺人,一則既不誣友,又不畏勢。皆方正之例也。
然亦有方正之故,而涉于拘泥者。梁劉進,兄獻每隔壁呼進。進束帶而后語。吳顧愷疾篤,妻出省之,愷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趣令妻還。雖皆出于敬禮之意,然以兄弟夫婦之親,而尚此煩文,亦太過矣。子從父令,正也。然而《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孔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于不義。”然則從令之說,未可拘泥也。官吏當守法令,正也。然漢汲黯過河南,貧民傷水旱萬余家,遂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民,請伏矯制之罪。武帝賢而釋之。宋程師孟,提點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遘兇歲,賑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饑者盡死矣。”竟發之。此可為不拘泥者矣。
■謹慎與畏葸
果敢之反對為畏葸;而魯莽之反對為謹慎。知果敢之不同于魯莽,則謹慎之不同于畏葸,蓋可知矣。今再以事實證明之。
孔子,吾國至謹慎之人也,嘗曰:“謹而信。”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多見闕殆,慎行其余。”然而孔子欲行其道,歷聘諸侯。其至匡也,匡人誤以為陽虎,帶甲圍之數匝,而孔子弦歌不輟。既去匡,又適衛,適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陳諸國而適蔡。陳、蔡大夫,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絕糧,七日不火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圍既解,乃適楚,適衛,應魯哀公之聘而始返魯。初不以匡、宋、陳、蔡之厄而輟其行也。其作《春秋》也,以傳指口授弟子,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是其謹慎也。然而筆則筆,削則削。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晉侯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初無所畏也。故曰:“慎而無禮則葸。”言謹慎與畏葸之別也。人有恒言曰:“諸葛一生唯謹慎。”蓋諸葛亮亦吾國至謹慎之人也。其《出師表》有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然而亮南征諸郡,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其伐魏也,六出祁山,患糧不繼,則分兵屯田以濟之。初不因謹慎而怯戰。唯敵軍之司馬懿,一則于上邦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再則于鹵城之前,又登山掘營不肯戰,斯賈詡、魏平所謂畏蜀如虎者耳。
且危險之機,何地蔑有。試驗化電,有爆烈之虞,運動機械,有軋轢之慮,車行或遇傾覆;舟行或值風濤;救火則涉于焦爛,侍疫則防其傳染。若一切畏縮而不前,不將與木偶等乎?要在諳其理性,預為防范。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漢諺曰:“前車覆,后車戒。”斯為謹慎之道,而初非畏葸者之所得而托也。
■有恒與保守
有人于此,初習法語,未幾而改習英語,又未幾而改習俄語,如是者可以通一國之言語乎?不能也。有人于此,初習木工,未幾而改習金工,又未幾而改習制革之工,如是而可以成良工乎?不能也。事無大小,器無精粗,欲其得手而應心,必經若干次之練習。茍旋作旋輟,則所習者,旋去而無遺。例如吾人幼稚之時,手口無多能力,積二三年之練習,而后能言語,能把握。況其他學術之較為復雜者乎?故人不可以不有恒。
昔巴律西之制造瓷器也,積十八年之試驗而后成。蒲豐之著自然史也,歷五十年而后成。布申之習圖畫也,自十余歲以至于老死。使三子者,不久而遷其業,亦烏足以成名哉。
雖然,三子之不遷其業,非保守而不求進步之詐也。巴氏取土器數百,屢改新窯,屢傅新藥,以試驗之。三試而栗色之土器皆白,宜以自為告成矣;又復試驗八年,而始成佳品。又精繪花卉蟲鳥之形于其上,而后見重于時。蒲氏所著,十一易其稿,而后公諸世?布氏初學于其鄉之匠工,盡其技,師無以為教;猶不自足,乃赴巴黎,得縱目于美術界之大觀;猶不自足,立志赴羅馬,以貧故,初至佛棱斯而返,繼止于里昂,及第三次之行,始達羅馬,得縱觀古人名作,習解剖學,以古造象為模范而繪之,假繪術書于朋友而讀之,技乃大進。晚年法王召之,供奉于巴黎之畫院;末二年,即辭職,復赴羅馬;及其老而病也,曰:“吾年雖老,吾精進之志乃益奮,吾必使吾技達于最高之一境。”向使巴氏以三試之成績自畫,蒲氏以初稿自畫,布氏以鄉師之所授、巴黎之所得自畫,則其著作之價值,又烏能煊赫如是;是則有恒而又不涉于保守之前例也;無恒者,東馳西騖,而無一定之軌道也。保守者,躑躅于容足之地,而常循其故步者也。有恒者,向一定之鵠的,而又無時不進行者也;此三者之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