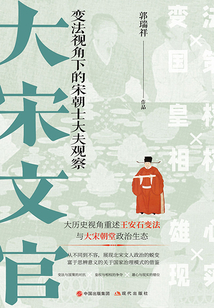
大宋文官:變法視角下的宋朝士大夫觀察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序
這是一個風云激蕩的時代,每個人都希望這個國家更好,而結果卻適得其反。
宋神宗雄心壯志,渴望建立唐太宗那樣的偉業,實現富國強兵,殲滅西夏,收復燕云,恢復大唐疆土。他孝祖敬長,緩和了父皇時期朝廷宗親的緊張關系;他夙夜憂嘆,不敢絲毫怠慢朝政,常常與臣下議論朝政到日晡(下午四點左右)而不知饑餓;他選賢任能,努力尋找心目中的魏鄭公(魏徵)、諸葛亮;他獨具膽略,果斷啟動變法,短時間內改變了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他體恤民眾,面對旱災之下的《流民圖》潸然淚下;他理順吏治,幾乎改變了冗官這個積重難返的局面;他銳意振作,熙河開邊兩千里,對西夏形成戰略包圍。無論私德還是國事,他都近乎是一個完美的皇帝。
然而正是宋神宗的事業,最終使體制趨于保守,朝政陷于黨爭,民力近于困敝,五路攻夏慘敗而歸。他去世時仍年富力強,卻又力不從心,只能發出功敗垂成的喟嘆。
王安石有著同代諸公遠遠不及的眼光、智慧、毅力。他站在夏、商、周三代的脊梁上俯視時代,把時代放在歷史的洪流中去考量,看得清百年帝國的弊端與需求。他像一名醫生,為帝國診斷、治療,幫助其康復,恢復其強壯的體魄;他像一名農夫,在田間除草、澆灌、施肥,只為禾苗茁壯成長;他像一名俠士,從不在意別人的眼光,只為心中的理想迎難而上、披荊斬棘、勇往直前。他是變法的總設計師,也是變法的推動者、實施者,幾乎以一人之力改變了帝國的精神特質,改變了財富版圖,改變了政治氣候。千百年來,他永遠是宋朝乃至古今社會繞不開的人物。
王安石的變法提振了宋朝的精氣神,卻又成為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津津樂道的文人政治發生異變,監督制衡體制受到破壞,增加的國家財富卻消耗到無德無功沒有前景的戰爭中,還成為皇帝揮霍、奸臣享樂的溫床。
司馬光是道德家、學問家,在人們心目中他是君子和正義的化身。他恪守禮制,心中始終有一個安邦治國和齊家修身的標桿;他崇尚仁政,為減輕民眾負擔鼓與呼;他正氣凜然,敢于諍言,從不為個人利益后退半步;他是非分明,不因人因事因時而風搖柳擺。他為知遇感恩,放棄前程隨恩公外放,不離不棄;他對家庭負責,潔身自愛,決不沾染士大夫的不良習氣;他為理想堅守,寧愿放棄權力,退避三舍,也不在原則問題上與政敵握手言和;他決不自暴自棄,仕途不得意時忍受寂寞,一個人完成皇皇巨著《資治通鑒》,為國家興亡提供歷史借鑒。然而正是這樣一個鑒悟古今的智者、風高骨潔的君子,在最后的執政時光里,讓朝廷陷入瘋狂的清算和報復之中,黨爭如烈焰般熊熊燃燒起來。新法盡廢、新黨盡逐,除了打擊和斗爭,政治越來越保守最終無所作為,政體越來越專制最終毫無活力,文化越來越狹隘,最終水火難容。
優秀的皇帝率領杰出的士大夫,王左馬右,沒能挽回宋朝衰敗的頹勢,卻加劇了王朝覆亡的步伐。
宋英宗、宋神宗時期是宋朝重要的窗口期,也是兩千多年皇權社會重要的轉折期。這時和稍后整個社會發生的一系列的深刻變化,其影響至少延續到19世紀末。
——由中央集權轉向帝王專制。宋朝建立之初,吸取唐末五代武將干政、軍閥割據的教訓,奪其權、制其糧、收其兵,天下大權皆歸中央,終宋一朝再未出現權臣或藩鎮威脅皇權的現象,中央集團達到頂峰。
中央集權不等同于帝王專制,在宋朝的制度設計中,包括皇權、相權在內的各種權力互相制約,沒有誰能夠為所欲為。比如設立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以分解宰相權力,宰相和臺諫系統又對皇權構成制約。
臺諫權力在宋仁宗朝達到頂峰,可以引導輿論,可以阻撓皇帝任免官員,可以改變皇帝的敕令詔書。臺諫制度也因掣肘過度帶來了行政效率低下等問題。到了宋英宗、宋神宗時期,一來出于滿足帝王個人欲望的需要,二來為了強有力推動變法,皇帝和宰相刻意打壓臺諫,任用親信,縮減他們的權力,不再采納他們的建議,將臺諫邊緣化和虛置架空。王安石經過變法之后,神宗又推行元豐改制,改革官僚體系,削弱宰相權力,臺諫機構更是形同虛設,由此帝國的中央集團逐步過渡為帝王專制。
當然,從中央集團到帝王專制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在實施過程中不斷有新的演變和發展,到明清廢除了宰相,變為內閣制度和軍機處制度。明清的政治體制走向,源于元豐改制。
——由文人政治轉向文人黨爭。自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起,宋朝一直刻意壓制武將,重用文人,文人迎來了史無前例的高光時刻。傳說宋太祖立下盟碑,發誓“不殺士大夫及言官”,文人與帝王分享權力,得以深度參與到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社會統治和治理的各個方面,這就是以帝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為主要特征的文人政治。
最早提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皇帝是漢高祖劉邦,但漢朝政權很快被世家大族、外戚和宦官掌控,真正的讀書人很難進入權力的核心,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并未能很好地貫徹執行。世家大族直到唐末才退出歷史舞臺,科舉取士成為進入仕途的主要途徑,為共治天下創造了條件,文人政治在宋朝得以實現。
自古文人相輕,文人聚集的地方容易發生爭執,如果形成派系,結成同黨操弄政治,便形成了黨爭。仁宗朝文臣尚能和而不同,誕生了范仲淹、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等優秀的政治家。不過慶歷間已經出現了黨爭苗頭,仁宗及時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到了英宗、神宗朝,由于推行變法,朝臣觀點相左,矛盾激化,形成支持和反對變法的兩大陣營,稱為新黨和保守黨,黨爭失控。此后兩派不遺余力打壓對方,除了擠壓對方的政治空間,甚至試圖從肉體上消滅對方,極大地破壞了北宋的政治生態,消耗了行政資源,敲響了帝國覆亡的喪鐘。
——由戰略防守轉向戰略進攻。神宗少年即位,血氣方剛,不滿足于真宗、仁宗朝對契丹和西夏的妥協茍且,立志建功邊陲、恢復舊疆,體現在對外關系上,一改過去懷柔、防守的政策,對西夏展開了全面的戰略進攻。
熙寧元年,留意西北的進士王韶向神宗上《平戎策》,成為對西夏的基本方略。此后王韶熙河開邊兩千里,對西夏形成戰略包圍之勢。元豐四年(1081),宋五路攻夏,雖然最后失敗,但宋朝對西夏的戰略進攻之勢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
——由開放包容轉向內斂保守。在宋神宗朝,北宋道學(后來的理學)形成,以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顥“北宋五子”為代表,基本完成道學理論體系構建,并不斷擴大在士大夫和下層社會中的影響。道學提出“氣節”一詞,在強調知識分子社會責任的同時,主張“存天理,滅人欲”,中國主流哲學思想由開放包容轉向內斂保守。
元祐更化加劇了整個社會的保守傾向。在政治膠著和政治焦灼的情況下,司馬光不分青紅皂白,將新法中實施的政策全部復辟回去,連西北占領西夏的土地也退了回去,一切“恢復原貌”。再加上瘋狂地打壓新黨,給人的文化暗示就是:拒絕創新,拒絕包容。行政的示范作用是強烈的,整個社會趨于保守在所難免。南宋檢討北宋失國的教訓,將責任推給革新變法的王安石,幾乎全盤接受了元祐更化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此后的中國社會便失去創新的動力,政治體制和國民精神冥頑不化、萎靡不振,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
自秦始皇建立皇權,中國帝制處于不斷變革和完善之中,但任意一次變革都不如宋朝的深刻和徹底,尤其是政治體制中的帝王專制、意識形態中的程朱理學。本書還原變革時期朝廷上下的風云開合,揭示這種變化的形成演變和內在邏輯,希望能為讀者深刻理解宋朝乃至整個皇權社會的政治特質、政治走向提供充沛的史實和思考的維度。
本書從嘉祐年間仁宗議立皇子寫起,訖于元祐更化。仁宗無子,在過繼時又搖擺不定,英宗內心驚懼不安,造成他性格上的偏激謬妄,加劇了宋朝的內憂外患。神宗面臨著仁宗盛治和英宗無所作為的雙重壓力,急于振作,所以選擇了積極的對外政策和激進的變法革新。追本溯源,風起于青萍之末,仁宗議立皇子埋下了變革的誘因。熙豐變法遭遇困境,中間幾度停續,至元祐高太后垂簾、司馬光執政,徹底否定新政,毫無保留地廢除新法,標志著變法失敗。同時,元祐更化讓新黨舊黨矛盾激化,北宋由此進入黨爭時代。從嘉祐到元祐,才能完整表現出熙豐變法的來因去果,這是本書以這一歷史階段為描述對象的落筆考量。
本書的骨干資料來源于《續資治通鑒長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行文中不再一一標出,其他出處如《宋史》、宋人筆記在文中以腳注的形式予以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