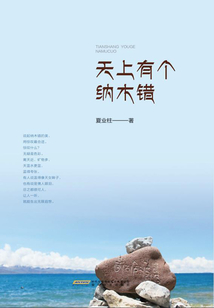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走在八廓街上
瑪吉阿米的月亮
去拉薩繞不開八廓街,不想去也得去,它是拉薩老城的核心,老拉薩味道濃,不去八廓街等于沒去西藏。我去西藏前,對八廓街的印象是從電視節目里獲得的,熱鬧而不乏時尚,感覺與云南麗江、湖南鳳凰古城類似,是酒吧和咖啡屋的天下。去西藏后發現,影像的感覺與親身走近大有差別,八廓街與我見過的所有街區都不同,與其說是街,不如說是轉經道,藏民骨子里就沒拿它當街,而是把它當成一條朝圣的路,一條能把人的靈魂引渡上天的路。
據傳,八廓街最初是因轉經而生。吐蕃時期,今天的拉薩老城區一帶還很荒涼,到處是沼澤水塘,松贊干布為了迎娶尼泊爾的赤尊公主,專為她建了大昭寺。公主從尼泊爾帶來的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也被當作頂級圣物供奉在大昭寺內。從那時起,藏民為了一睹釋迦牟尼尊容,就開始朝圣,朝圣的人越來越多,圍繞著大昭寺便形成了固定的朝圣道路,也就是轉經道。大昭寺周邊因此出現了旅館、帳篷、臨時民居等供人吃喝拉撒的場所,這便是最初的八廓街。當然,那時的八廓街還只是雜亂的聚居區,與今天的八廓街有天壤之別。但從那時起,八廓街再沒蕭條過,春夏秋冬,始終人氣很旺。而熱鬧也始終只在那一小塊,直至今天,雖然拉薩已擴大了數倍,八廓街依舊是當初的規模。有人說它長三里,寬三丈,有八條岔巷伸向八方,故又衍生出八角街的稱呼。我多次去過八廓街,始終沒辨清八個方向。我想,要是從空中俯瞰,八廓街的形狀沒準像蜘蛛網。實際上它的功能不亞于一張網,不僅網住了萬千信徒的心,也網住了拉薩的古舊、時尚、繁華、肅穆和神圣。
在西藏,朝圣是了不得的大事,飯可不吃,經不可不轉,信徒以能到大昭寺朝圣為榮,故而也以到八廓街轉經為幸。藏語中,“八”是中間之意,“廓”是轉經道之意,“八廓”連起來說,就是順時針轉經一圈的意思,可見八廓街得名就源于轉經。任何人一進大昭寺街口,就會身不由己地順時針“隨波逐流”。有人說拉薩有六條轉經道,八廓街是首選,信徒們每天要繞八廓街轉三圈,風雨無阻。更有不少拖家帶口磕長頭轉圈的,不諳世事的孩童跟著父母,掛著羊皮墊子,戴著手板,舉手摸腦又捫心,一步一匍匐,向前磕長頭,天長日久,街心的地面被磕出光溜溜的一條印跡。磕長頭向來是八廓街最吸引人的風景,磕的人是那么虔誠,對來往人流視若無睹;看的人總是很好奇,想不明白哪股子力量把人變得這么虔誠,八廓街的魅力多半就在這看和被看中。
八廓街到底有多少人轉過經,永遠是謎。我每次走過八廓街,都被磕長頭的信徒吸引,那些打扮各異、口音有別的男女,有的是信徒,有的是旅人,到了這里,都成了“轉經人”,捻佛珠、握經輪、磕長頭,五花八門,在八廓街的艷陽藍天下,形成了強大的氣場,每每看到,便忍不住想拍下他們。但我從不知道他們來自哪里,怎么來,又到哪里去,我想,每個磕長頭的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故事,或悲或喜,只有朝圣的心是一致的,他們都向往一個共同的天國。
在八廓街最神圣的還不是轉經,而是前往大昭寺朝拜。大昭寺是八廓街的心臟,是八廓街的靈魂,皆因寺里有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等身像很有故事:大昭寺初建時,供奉的是赤尊公主帶來的八歲等身像,那時文成公主與她從大唐帶來的十二歲等身像都在小昭寺。到了金城公主時期,因小昭寺動亂,金城公主為了保護娘家的寶貝,特意將小昭寺十二歲等身像與大昭寺八歲等身像調了位置,從此八歲等身像就到了小昭寺,而十二歲等身像就安放在了大昭寺,成了大昭寺的鎮寺之寶,被萬眾敬仰,信徒們見像如見佛陀。無數人不遠萬里,跋山涉水來拉薩,只為對圣像祈愿。也有不少信徒不惜花重金,對等身像貼金涂彩,原本木質的等身像被信徒們一次次塑身貼金,越來越高,越來越豐滿,如今頭臉和身軀早已超過了十二歲佛陀的大小,成了一尊真正的貼金大佛,端坐在大昭寺正中的神龕中,任何信眾見它都須抬頭仰視。
大昭寺無疑成了八廓街的核心,春夏秋冬,年復一年,它始終游人如織,有虔誠的信徒,也有普通的看客,男女老少一撥接一撥地擁向寺內,使這座古老的寺廟原本不大的空間顯得越發狹小和擁擠。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除了專來朝圣的信眾能夠虔誠地禮佛,游客大多跟著導游,人云亦云地看熱鬧,少有能氣定神閑地品味什么的,有的人在擠擠碰碰中,連等身像在哪都難以找見。我有一次在寺內遇見兩個東北人,他們糊里糊涂地進了寺,卻不知道干什么,納悶地咨詢我。當我說看釋迦牟尼等身像時,他們好像仍沒明白,更不知等身像在哪。我第一次進大昭寺也是糊里糊涂的,后來陪人參觀多了,才知道個大概。再進大昭寺,我就直接沖著等身像行進,避過不少擁擠。這時我才知道等身像只許遠觀,除非花錢貼金,否則不許靠近。當然貼金也非常人能為,只能由僧人專辦,信眾們花的是錢,換的是心安。我沒見到貼金的場面,卻每次都見有信徒面像許愿。不知道他們都為什么許愿,許的什么愿,或許在這座古老寺廟的強大氣場里,個人的定力往往變得特別脆弱吧,哪怕是不知所以然地跟風,也總能找到所以為之的理由。
也是轉經,帶動了八廓街商業。與別處不同的是,八廊街的商品要么與宗教有關,要么與民俗有關,沒有大件電器;店面也小,有的賣成品,有的亦店亦坊,招牌都別致醒目。寺廟法器、加查木碗、日喀則卡墊、拉孜藏刀、那曲蟲草隨處可見,尼泊爾披肩、印度香料也不難買到,只是少見異國商人。有趣的是,小巷里還深藏著修鞋、補鍋、鑲牙、縫藏靴的老行當,它們仿佛在做最后的堅守。但八廓街并非購物天堂,任何普通商品在這里都不普通。我在八廓街很少有購物的沖動,陪內地來的幼兒園園長買過手串一類小玩意,價格比別處高,當然感覺也不同,畢竟是在八廓街,全國也只有這么一處。
正兒八經買東西只有一次,是陪朋友買唐卡,在八廓街古巷里不懂裝懂、討價還價地溜達了一下午。八廓街唐卡店很多,價格卻不便宜,原因就在于不愁沒有顧客,更不愁沒有外行的顧客。在八廓街,容易為唐卡動心的人不少,而懂唐卡的人不多。唐卡是特別的藝術品,制作難,欣賞也難,外行人很難一眼看出好壞,這就為商家留了太多的空間。造型、大小、色彩、內容都關乎價格,而制作方式更重要,純手工的,功夫在畫外,是上品。八廓街的唐卡所以有名,主要是因手工作坊多,在八廓街上,要想買一張純手工繪制的唐卡,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并不難,難的是買到真正的大師作品。我對八廓南街一帶唐卡作坊印象很深,狹窄的小巷里,唐卡店和作坊隨處可見,有的畫賣兼有,有的只賣不畫,有的畫師兼店員,有的老板兼畫師又兼店員。每家唐卡店做派都相似,顏料、畫架、畫稿隨處擺放,只有唐卡端正地掛在墻上,唐卡在藏民心中是流動的佛堂,沒有人不敬重。我們進店時,總是小心翼翼,唯恐壞了規矩。貨比三家后,我們相中了一家小店。店里只有兩個年輕人在作畫,對我們光顧并不在意,顯然心思在作畫上。見我們真心買,他們才邊畫邊與我們交流,最終,朋友花六百元買了一幅白度母,年輕人說那是他們師傅的作品,畫了一個多月,我們感覺即便不便宜,也值。
與商業同步的是休閑。在寸土寸金的八廓街中藏了不少茶館、咖啡屋和酒吧,它們像點綴,沒承想成了年輕人的天堂。他們或駕車或徒步,或結伴或單身,輾轉來八廓街尋夢。那次我和朋友在著名的娜姆瑟德餐廳就餐,鄰桌是上海的幾個年輕人,竟然專為那家餐廳而來。他們上網搜,打電話找,做足了功課,就為吃一頓。而我嘗了幾道所謂的名吃后,感覺名氣遠大于味道,我甚至沒填飽肚子。另一家名為瑪吉阿米的館子更是名揚海內外。很多年輕人來瑪吉阿米,就為那一輪東山頂的月亮。我路過瑪吉阿米都是與人同行,每次都想進去坐坐,每次都看到食客爆滿,第一次因為沒等到座位,悵然而歸,后來幾次還算幸運,都如意地找到了座位,每次都點了不同的花樣,而每次我都覺得不對我口味,環境也不舒適。館子很小,一樓不開門,二、三層營業,憋屈又黑暗,墻壁、桌椅、餐具也很隨意,仿佛煙熏過,據說是為了老舊味。來這里的都是年輕人,仿佛滿腦子都在懷舊,一個個坐在充滿老舊味的環境里遐想。當我看到排隊等座位的食客時,我懷疑他們都在湊熱鬧,為的是說不清的感覺,這種感覺如今漸成時尚,還有了好聽的名字——“小資”。
倒是八廓街的老建筑更對我胃口。八廓街是地道的老拉薩,也是地道的老西藏,倘若有心,細細品味其中的一磚一瓦,就等于品讀了拉薩的過去和西藏的歷史。我每次都因時間倉促,不能細細品味八廓街,但我知道在轉經道上、小胡同里,到處都是老舊的建筑,有大院,有莊園,有府邸,也有神廟,它們都曾有過耐人尋味的過去。北街的清朝駐藏大臣舊址、南街的根敦群培故居都已成了德育基地,它們都成了游客免費參觀的場所。而更多的老建筑還藏在深閨,有的成了民居,有的空空如也,比如索康家族、帕拉家族的宅院,兩大家族都曾權傾一時,因為有過并不光彩的過去,只能默默地湮沒在八廓街的白墻黑瓦里,迎送著高原的朝陽和落日,今天沒有多少人記起它們,更沒人愿意花時間去品讀。但我知道,它們都是極有分量的建筑,是八廓街作為中國歷史文化街區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我走過八廓街時,總是被那些漂亮的老建筑吸引,禁不住就想弄清背后的故事,而我又總是做不到,這令我很遺憾。我始終覺得,要看老西藏就去拉薩,要看老拉薩就去八廓街,要看八廓街必看老建筑,這是很簡單的推理。正是老建筑的存在,八廓街才有了色彩和輪廓,才有了無數悲歡往事和流年古韻,才吸引著云集的旅人、信徒和商賈,這也許正是八廓街的獨特魅力,而這些,是商貿、宗教、飲食永遠難以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