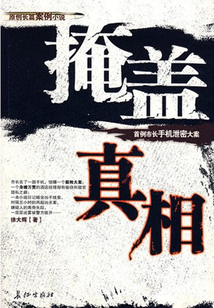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35章 手機里的謀殺拼圖(11)
- 第34章 手機里的謀殺拼圖(10)
- 第33章 手機里的謀殺拼圖(9)
- 第32章 手機里的謀殺拼圖(8)
- 第31章 手機里的謀殺拼圖(7)
- 第30章 手機里的謀殺拼圖(6)
第1章 命案在迷霧中浮懸(1)
1
一道眼淚在兩個姣好的臉上干了,頭部彈穿的窟窿流下的血漿呈紫紅色,如一坨果凍凝得十分均勻。法醫注意彈孔、粉塵什么的,死者淚水的細節被完全忽略,因為被殺者的眼淚不屬于痕跡范疇。
“張隊,你看這兒。”柳雪飛叫張國華,指著一扇窗戶說,“窗戶像似新開過。”
柳雪飛是市刑警支隊副隊長,張國華是支隊長,負責現場勘查的指揮。
張國華將虛開的窗戶小心翼翼地推開,探出頭向下望,見到二樓的平臺頂,實際是二層裙樓的屋頂。他所在的殺人現場是三樓的一個房間。假定兇手作案可以攀上這個平臺,然后再爬進三樓來,此房間在酒店的后身不臨街,又給一道很高的圍墻遮擋,即使爬上爬下,也不易被人發現。
“張隊,空調房間窗戶不該開的。”柳雪飛說。
“有道理。”張國華贊同。他吩咐勘查現場搜尋物證痕跡的刑警:“劉浩,窗口加細。”
“是,張隊。”劉浩應聲到窗戶前。
女偵察員裴菲菲在衛生間門前發現一個血鞋印,她喊:“劉浩,你看這兒!”
幾個刑警圍過去,劉浩蹲下來,小心翼翼地提取鞋印。
張國華走回到里間,法醫進行檢查,翻動了尸體,仰面的姿勢變成側臥,眼淚的痕跡不復存在,一灘新鮮的血從金色的發間流出,一條紅綢帶一樣纏繞著,這是死者之一九花。
“完了嗎?”張國華問。
“完啦。”法醫拉上床單,蓋住光赤的死者。
“雪飛,安排辨認吧。”張國華說,“找幾位同樓層的服務員和帶班什么的最好。”
柳雪飛去叫人。
服務員等候在一樓大廳里,她們低聲議論著,話題顯然是這場兇殺,表情不盡相同:平靜的、木然的、也有驚恐的。
“下來了。”有人說了句。
眾服務員的目光一齊投向樓梯,柳雪飛走下來,停在最后一級臺階上,問:“誰是負責人?”
一個細高挑個兒,身著店服的女人走過來:“黃經理不在,我姓安,是酒店的副經理。”
柳雪飛迅速掃一眼面前的女人,說:“你跟我來。”
副經理安然,年齡稍長一些,酒店員工都親切地叫她安姐,有時黃總經理也叫,不過他叫的聲音有別于眾員工,安字拖音很長,然后是姐,和那條街上豆腐匠的叫賣聲音極其相似。
“豆--腐!”
“安--姐!”
隨刑警上樓的安姐腳步越來越沉,將要在三樓看到什么,她早想象到了。
今晨,最早發現血案現場的服務員,尖刺的喊叫聲響徹整幢大樓,沒有一人不被驚動,大多數是給驚醒的,都知道出事了。
“殺人啦!”
“殺人啦!”
安姐宿舍也在三樓,離發生血案的房間有一段距離,畢竟是同一個樓層,聽到的喊聲格外真切。短暫的愣怔后,她撒腿朝喊叫聲方向跑去。
那時,第一位目擊血案現場的女服務員,強烈的精神刺激使她身子堅挺地向前走了幾步,然后轟然在安姐面前倒下去,嚇昏的人表情特別難看,姣好的臉給恐懼揉皺成一張紙,手指扎撒著,像一個落水后掙扎的求生者。
哪個房間殺了人呢?需要做出判斷,安姐在想是顧暈倒的服務員,還是去殺人的現場?短短的猶疑后,安姐直奔敞開門的房間。啊!她看到駭人的場面,雙人床上的兩人頭發間朝外涌血,人血流出體外的瞬間是粉紅色,如清晨綻放花朵那般鮮艷。
大片的紅顏色閃現,像張藝謀一部電影。安姐的眼里充滿紅色,沒看清床上的人是誰,她比暈倒在走廊里的服務員理性一些,喊道:
“來人吶,快來人!”
最先到達的是保安,職業加訓練使他們在突發的事件面前,沉著而冷靜。
“怎么啦,安經理?”
“殺人……”安姐語無倫次。
保安第一個反應是舉起手中的器械--橡皮棍,沖入房間。
報警前,安姐先撥了總經理黃毛的手機。她懷疑兩個死者之中就有黃毛。在這個房間里過夜,除九花外,只有他。如果撥他的手機,室內有鈴聲響起,自然是他無疑。
黃毛的手機關機,屋內也沒有希望的響鈴聲。
“報警!”安姐對自己喊。
警察到來,三樓被封鎖。安姐也沒權力到三樓來,她聽從警察安排,把全體員工都集中在一樓大廳里,一個都不準外出。
“你叫什么名字?”房間門口,張國華問。
“安然。”
“哦,張隊,她是副總經理。”柳雪飛說。
“安經理,請你認一下她們是誰。”張國華見安姐臉色蒼白,說,“不過你不要害怕,其實死人沒什么可怕的。”
安姐稍微平靜一下,走進去。
法醫慢動作掀起床單。
“她叫九花。”安姐指認了死者,說:“她還是大堂經理。”
“另一位呢?”張國華問。
九花的頭發是金色,自然的金色,像成熟的麥穗顏色。
小慧頭發也是金色,小慧的頭發是染的,比九花的發色油亮一些。安姐說:“這位是小慧。”
“確認嗎?”刑警問。
“確認。”安姐肯定說。
“安經理,過會兒我們再談,你再叫兩名服務員來。”張國華說。
“叫誰來?”安姐問。
“隨便,是你們店的員工就行。”張國華說。
辨認死者,也用不著太多的人,有三兩個人,能夠確定死者的身份就可以了。
安姐下樓去叫人。
“張隊,死者是本酒店的員工無疑。”柳雪飛說。
窗外傳來嘈雜的聲音。
“雪飛,你在這兒組織著辨認,我去應付一下記者們。”張國華把辨認死者的事交給柳雪飛,走出房間。
遇到突發事件,動作僅次于119、110的大概是媒體記者,傳媒的時代么。
此刻,酒店外邊的秩序有點亂。多家媒體的記者蜂擁而至。
命案的現場勘查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警戒線穿越了院落,圍觀的人群被限制在警戒線以外,幾家媒體的記者見縫插針,向警察提問題。
“幾個人被殺?”記者問。
負責維護現場的警察很講原則,他們的任務是警戒,與此無關的事無權力去做。他們用了標準的詞匯:無可奉告。
“兇手使用什么兇器?”記者問。
警察將背部給了記者們。
“我們是‘城市新聞快車’頻道的記者……”電視臺記者扛著攝像機,擠在人群最前面,“請問……”
張國華的出現使警戒線整體朝前悠了悠,說明大家向前擁擠。他對記者們熟悉,刑偵支隊長不只一次面對鏡頭。
“張隊!”記者們也和刑警們一樣叫張國華。
“大家好。”張國華走到警戒線前,與記者打招呼。
“什么時候可以放我們進去啊?”有記者問,“拍攝一下現場。”
“對不起,現場勘查還在進行之中,大約一小時后你們可以進入。”張國華明確答復。
“張隊,能向我透露一下血案的情況嗎?比如說……”記者追問。
張國華知道記者不先睹為快地得到點什么,是不肯罷休的。他說:“法醫初步鑒定,血案大約在昨夜零時左右發生,兩名服務員在房間里被槍殺,其中的一位是大堂的經理,人已死亡。”
“請問張隊,作案的兇手是幾人?”
“對不起,現場勘查還沒結束。”張國華說。
“警方有了犯罪線索嗎?張隊,能談一下你對此案的看法嗎?”
張國華說聲對不起,在記者們追問聲中轉身進樓,身后悶熱的空氣里一片張隊、張隊的呼喊聲。
走進大廳,柳雪飛已被紅顏色包圍,員工在向他提問,或是,他在問員工。見張國華進來,聲音才翅膀一樣飛走。
“張隊,確定了,是他們的員工。一個名叫九花,一個叫小慧。”柳雪飛說著識別尸體的結果。
2
凌厲習慣去西山晨練,回來路經八馬路露天農貿市場買菜,風雨不誤,幾乎和鐘表一樣準時。
“我出去啦。”凌厲穿好晨練裝,臨出門前向懶洋洋在床上的年輕妻子說。
妻子郭影身子慵懶眼睛卻不懶,在丈夫的身上游覽一遍,發現了錯誤,說:“衣服扣子亂串門。”
“哦,是啊。”凌厲低頭見第三個扣子鉆進了第二個扣眼兒,系錯了位。
郭影愛說這類生動的俏皮話,丈夫經常系錯位扣子,有時分不清襯衣的前后。
“看見沒,衣服前后長短不一樣,還有商標,商標都在前面的。”她在說一種小常識。
盡管這樣,凌厲還是時不時出差兒,還出過笑話。有一天他去上班,秘書見了局長就想笑。
“怎么啦?”他感到莫名其妙,反過來問秘書。
“我覺得局長的衣服……”秘書吞吞吐吐,比劃一下自己的前襟。
條件反射,凌厲也看自己的衣服,和別人在你面前摸一下鼻子,你也摸一下一樣。可是,他沒發現有什么不妥。他問:“我到底怎么啦?”
“局長衣服的商標……我是說,那只狐貍……”
凌厲坐上民政局長的位置,韓國金狐貍短衫是他穿上身的第一件名牌服裝,還是郭影先斬后奏,買來不得不穿的。不過,妻子弄回差不多一群狐貍,休閑褲是金狐貍,皮鞋是金狐貍,腰帶也是金狐貍。他說,“我成了狐貍局長。”偏偏金狐貍和他開玩笑,他穿反了衣服,那只金狐貍背面朝前,毛色發灰。他有些不好意思:“我穿反盆(顛倒)了。”
“我說嘛,還以為金狐貍褪了毛。”秘書詼諧,在局里,只有秘書敢跟局長開這種不咸不淡的玩笑,大家都知道他們有淵源,沒淵源,下級誰和上級開玩笑。
金狐貍笑話發生后,凌厲特別注意是不是穿反了衣服。金狐貍沒再搞錯,金色的狐貍他牢牢地記住。但是,他還是不可避免地出差,襪子、襯褲什么的,左右、前后顛倒,不是什么是非,顛倒就顛倒了,尤其是襯褲在里邊,也沒人看見。當然他自己有感覺,有時兜屁股,那一定穿反了,他默默承受不說。
好在,郭影經常糾正他,臨出屋必須校正一遍。因此他玩笑地說:“你是我的校對。”
“形象設計師。”
“我走啦。”凌厲改正了扣子,讓它們回到合適的位置上,出門去晨練。
房間門關上,郭影翻了身,臉沖著墻。簡裝修的墻,準確說是只刮了大白的房間墻壁,用料講究了些,是仿磁的那種。白白的一片沒什么好看的,落上一只蒼蠅、甲殼蟲就有意思了。如果大海上沒有船,只是一片水,大概就沒人看海了。
她在那個早晨就這樣無聊地想著,每天早晨她都有一個無聊時段,離開床她并不是懶惰的女人,一天手腳不閑地做事,在她上班的親近小動物協會,四個人辦公桌子的衛生她全包了,包括清洗杯上的茶垢。
也許是老夫少妻都是如此的生活習慣,多勤快的女人在床上也變了。她曾認真地想過,沒人愿意離開大樹的陰涼地兒。
凌厲是郭影蔽蔭的樹木,近些年她更有了依靠的感覺。女人最終還不是依靠男人!丈夫比自己大21歲,如今,老夫少妻成為城市的一道風景。
不指望白墻會出現奇跡,它不是電影幕布,《功夫》、《夜宴》什么的也不會放映。但是,白墻在幾個夏天里,演著她心靈里的電影。片名不確定,隨心所欲。有時,幾部穿插映放。
在這個后來成為刻骨銘心記憶的早晨,郭影有段電影是井東的晨景。從一個角度看西山,她看到某種動物身上部件形狀似的山體,此刻更雄壯挺拔,太陽用紅色的光線撫摸它,使它充滿誘惑力。一兩條小道通向山間,晨練的人中她看到熟悉的身影,丈夫慢跑的動作彰顯生命的活力。
好像有雷聲傳來,聲音不是來自墻壁,是窗戶外邊的聲音。要下雨了嗎?她坐起來,手牽扯窗簾,看到漸漸陰沉的天空,嘟囔一句:“他沒帶傘。”
雨并沒立刻下來,或者說沒那么痛快地下來。有時,雷也說謊。響來響去,天空也未裂開縫,雨點篷著沒漏下來。
兩個和著蜂蜜的饅頭,一杯牛奶,一盤醋泡的蘿卜皮,是凌厲的早餐。
郭影看下表,按微波爐的開關,加熱食物。在此之前,她弄好紅心蘿卜皮,這種有著心里美的蘿卜,皮脆,口感好。切它時,她故意帶些瓤兒,用紫粉色做點綴。
凌家住四樓,從一至三樓上樓的腳步聲中,郭影能準確無誤地辨清丈夫的腳步。從7點到7點30分,有十幾人次上下樓,竟沒有一個是她等待的人。
“怎么搞的,還沒回來?”郭影只好第三次熱牛奶。
過了8點,郭影坐不住了。她要上班的,盡管親近小動物協會不用坐班,去還是要去的,本打算今天去。
“老是不帶電話。”她埋怨道。
事實上,帶電話到西山也沒用。通訊覆蓋了全世界,就是無法覆蓋西山,為此,井東市的電信部門大傷腦筋。什么卡、什么手機到西山都不好使,有那么點兒微弱信號,接聽斷斷續續,別想聽完整的句子。這是所有人去西山不帶手機的原因,凌厲也不例外。
9點多仍舊不見丈夫的影子,也沒電話打回來。半路給哪位朋友拉去喝早茶的事情發生過,不回來吃早餐,他會打回電話告訴妻子的。
“會不會出現意外?”郭影驀然有種不祥之感。
前幾天,民政局的一位科長,早晨離家時好好的,拎著鳥籠子到西山遛鳥,剛把鳥籠子掛在樹上,眼前一黑,跌倒后再沒爬起來。那只鳥在那個早晨叫得凄慘,不是鳴唱,而是悲啼,整個西山給鳥叫得吊唁大廳似的。
“人太脆弱。”凌厲慨言。
“是啊,是啊!”妻子同感,生命實在太脆弱。
不能再等了,郭影決定去西山,出門時帶上兩把傘。
“如果遇到一個50多歲的男人……”郭影一條腿踏進出租車,身子還沒完全進來,就囑咐司機幫他留心路上的行人,擔心與丈夫走兩岔去。
“您還沒說去哪兒。”司機提醒道。
“哦,西山。”郭影說。
出租車開到半路,她忽然叫停車。
“你不是去西山嗎?”
“那么多話!”郭影責備司機,丟下車錢。
出租車司機悻然離去。
郭影去西山半路途中下車,是她想起一件事。丈夫說他要吃青椒炒驢板腸,她說她去買,他說哪天晨練回來自己買,天天路經農貿市場,順便買回來。
“還不是嫌我買不好。”她說。
“不是買不好,怕你不認貨。”他說。
郭影承認,丈夫是小百科,知道很多生活知識。驢板腸,是傳統的鄉村名菜,有句謠諺:寧舍爹和娘,不舍驢馬板腸。可見好吃至極。如今養驢的少了,市場上出售的驢板腸,小販子做了手腳,用牛腸來以假亂真。一般人還吃、認不出來,郭影哪里分得清真驢馬板腸、假驢馬板腸啊。
“但愿他在挑選驢板腸呢!”郭影這樣想,希望是如此。
出售驢馬板腸的攤位前沒幾個人,也沒什么驢馬板腸出售。廣告牌子上寫的是牛蹄筋,牛頭肉……郭影沒見到丈夫的影子。
郭影穿越菜市場,遇到三五個熟人,都說沒見到凌局長。整個菜市場像一根管道,她從這一端進去,再從另一端出來,日復一日,它吞吐著蔬菜和市民。
看來凌厲沒被吞吐,或許他因什么事耽擱,人還滯留在西山,郭影打車去西山。
西山突然間變臉,氣氛異常緊張,數輛警車封堵了進山的路口。進山禁止通行,出山受到盤問。
郭影乘坐的出租車已和司機說好,直接開到山間,直到無法再向前走為止。情況發生了變化,警察設的路障,攔截住進山的車輛。
“不能往前開了。”司機說。
“我們說好,你送我上山。”郭影說。
其實郭影也看到了警察,嘮叨幾句下了車。她以為車不讓通行,人總可以,沒走幾步,給警察攔住:
“對不起同志,不可以往前走啦。”
“我去西山。”郭影說。
“西山不準進。”警察說。
“為什么?”郭影問。
警察似乎失去了耐心,說:“不準進山就是不準進山。”
郭影聽出警察的語氣變冷變硬,她這時才注意到站得遠一點的警察背著槍,對“56”半自動步槍、“64”微聲沖鋒槍、“79”式沖鋒槍、“85”式輕型沖鋒槍槍械不甚了解,反正警察背的不是手槍。影視劇里出現這種場面就是圍捕兇犯,現實生活中,她沒親眼見過動槍的場面。
“西山到底怎么啦?”郭影淺聲問。關乎自己的丈夫,她首先想到凌厲天天來西山晨練,現在人可能在山上。
“你不要再問了,沒事還是走開的好。”警察說,見她探問的目光,加上一句,“西山今晨發生了血案。”
“血案?你說血案?”郭影用驚恐的眼神望著警察。
“血案。”警察說。
“我丈夫在山上啊!”郭影心里一陣發緊,“他來晨練,來得很早,一個人來……”
兩名警察走近,他們交頭接耳,眼睛沒離開郭影,說著什么,其中有一名警察還瞥一眼山間。
郭影的心一陣比一陣揪緊,本來丈夫沒按時回家出現了異常,認為他應該在的地方卻發生了命案,放在誰的身上都要聯想很多。她的面色變得慘白,心跳劇烈,此時難說出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