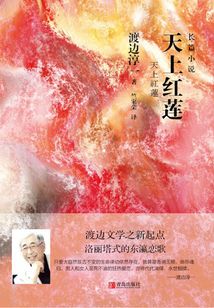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曲水宴后
一進入彌生[1]時節,陽光日漸和煦,日照也仿佛驟然延長了。
雖已是酉時[2],但庭園里依然亮如白晝。正前方假山石旁盛開的一簇簇金黃色的棣棠花,好似欲挽留那夕陽殘照一般,愈加搖曳生輝,燦燦炫目。
白天,在此大炊殿內剛剛舉行了“曲水之宴”。
據傳,直至四五十年前,世人為祛除自身污穢,于彌生第一個巳時,乘舟楫出海尋訪陰陽師做祓,或將偶人置于小舟之上放流,即所謂行“上巳之祓”已成習俗。
不知自何時起,該習俗逐漸廢止,如今只保存了載偶人放舟的儀式,而載于小舟之上的偶人也置換為酒杯與賦詩,即所謂“曲水之宴”了。
依照白河法皇[3]意愿,今日午后,該宴于此庭園內舉行。白河法皇的親朋至交、皇親貴戚及女房等數十人前來赴宴。
午時[4],眾嘉賓陸續到齊后,沿蜿蜒迂回地流向碧池的曲水之畔,各據一席之地,當自上游漂來的小舟流經自己面前之際,賓客務必將載于小舟之上的杯中酒一飲而盡,并將一首即席賦詩置于小舟上。
眾賓朋在沐浴著融融春陽的庭園里飲酒賦詩,乍看之下,風騷嫻雅,悠游逸樂,然此宴過后,所吟之詩將公之于世,任由世人品評,因而絕非可以等閑視之。
今日亦如既往,眾來賓伴著裊裊管弦之音,無不詩興大發,盡抒胸臆,其中尤令眾人發出驚呼之聲的,當屬白河法皇吟誦的這首:
似幻似夢無從辨,但覺君身軟如緞。
那情景是現實還是夢境,現在全然記不得了,只有你那柔嫩肌膚的感觸仍然那么清晰。
如此狂放不羈之詩,竟然吟誦于曲水流觴之宴,眾來賓莫不為之驚詫,紛紛猜測何人所作。待得知乃白河法皇御詠,皆啞然失聲。沉寂片刻后,頓時發出一片贊嘆:“真是好詩啊!”
也難怪,此等香艷情詩,竟是今年已六十有二的白河法皇所詠,恐怕無人能夠想見。
誠然,今日赴宴者中,抑或有人能猜到此詩為法皇御作,想必是察覺到近來法皇那如火般熾熱的情思之故。
“不過,何至于在那樣的場合……”
掌管法皇御所大炊殿的女房[5]大納言內侍[6],望著曲終席散、靜寂無聲的庭園,悄聲低語。
雖說吟詩理當發乎真情實感,然此類“曲水之宴”,似無須這般大膽表露心曲。
盡管相互唱和乃此宴之慣例,但畢竟只是將詩與杯一同置于流經面前的小舟之上,即興賦一首感懷,以添游興足矣。
譬如,應邀前來赴宴的藤原信通便吟誦了一首:
葉自飄零水自流,吾情枉然隨波游。
引得眾人發笑。
與之相比,法皇御詩何等情真意切、發自肺腑啊。
如此一來,法皇有了新的心上人之事,將會盡人皆知。
不消說,法皇盡可以想其所想、愛其所愛。天上人若墜入情網,為情所困,正所謂“天上天下,平安之明證”。
但另一方面,世人會挖空心思探究法皇所愛究竟何人,爾后圍繞該女子,各色人等將各揣心思,蠢蠢欲動。
“但愿法皇能夠適可而止。”身著唐裝[7]和裳裙[8]的內侍暗自叨念著,沿東走廊輕步行至車宿[9],拉開隔扇。
在此等候差遣的車副頭[10]慌忙回顧,向內侍施了一禮。
“璋子公主還沒到嗎?”
“是。剛剛派人去催了。”
“馬上再派人去催……”
車副頭點點頭,去招呼其他車副頭,內侍見狀便沿走廊往回走。
然后沿回廊往西去,快走到位于中央的寢殿[11]時,只見白河法皇突然撥開簾子,走出殿來。
法皇為何突然出來了?
大納言內侍不禁退后一步,垂首侍立,法皇略顯焦躁地問道:“還沒到嗎?……”
“是。報告陛下,已于半刻之前派車去接,爾后又派人去催了。”頭戴烏帽子[12]、身著白色直衣[13]的法皇,默默地將目光從屋檐移向日暮時分的庭園。
“估計片刻便到。”內侍安慰般說道。
話音剛落,白河法皇便不耐煩地說:“太慢了……”
今日之約是依照法皇旨意定下的,召璋子公主曲水之宴結束后的申時[14]前來見駕。
可是,殿堂里的時鐘已鳴報申時,仍未見璋子公主人影,現在已酉時過半了。
其實,從璋子公主居住的二條富小路殿到此大炊殿,走路也不過半個時辰。
況且,眼下她與養母衹園女御[15]分住于不同的御殿,完全可以無所顧忌地出行。
不用說,前去迎接她的牛車已經派出,此時早已到達二條富小路殿了。
“會不會有什么事?”
“奴婢未聽說。若璋子公主有事的話,當會即刻來報。”
法皇焦慮不安地開合著手中的折扇,朝御殿入口的東中門方向張望。
“公主一到,奴婢立刻會送入殿內,請陛下先回御座坐下等候。”內侍勸道。法皇仿佛沒有聽見,依然站著不動。
竟然能夠讓被權中納言藤原宗忠稱頌為“威滿四海,天下歸服”的法皇如此專候,恐怕很難說是正常之舉了。
“上次,也遲到了。”法皇說道。
誠然,璋子公主并非初次遲到。兩天前,以及五天前奉召前來時也都遲到了,雖說比今日早些。
也許因法皇連日頻繁召見,公主身心過于疲憊吧。但上次璋子公主來赴約時,未見絲毫疲倦之色。十四歲正值青春妙齡,即便法皇在床帷之內百般施愛,公主也不至于怎樣疲勞的。
想必有其他緣故吧,莫非璋子公主有什么難言之隱?
內侍正猜想時,法皇看穿了內侍心思似的問道:“難道說那孩子有什么不痛快嗎?”
“陛下的意思是?”
“鬧別扭等等。”
“那怎么可能……”
法皇一統天下,不可能有人敢于違忤。
非但如此,若蒙法皇召見,乃十二萬分之榮幸,凡女子無不歡喜若狂,一刻不敢耽擱,立即應詔前來侍寢。承受法皇的恩澤雨露,正是生為女人的最高名譽,亦是關系到一門一族飛黃騰達的大好事。
璋子公主居然無視法皇召見,屢屢遲到,實在非同尋常。
內侍一直低眉垂眼地恭立一旁,見話已至此,暗下決心斗膽向法皇進一言。
“恕奴婢冒昧,有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但講無妨。”
得到允許后,內侍環顧四周,見左右無人,便向法皇跟前跨近一步道:“依奴婢猜測,公主恐怕是在耍性子。”
“耍性子?”
“是的。璋子公主畢竟還是年少女子。”
雖說十四歲作為女人已具備足以魅惑男人的肉體,但頭腦尚嫌幼稚。
“再說得清楚一些。”
“是。”內侍又朝四周看了看,奏道,“或許璋子公主也想要得到某種實物了。”
“什么實物?”
“譬如法皇陛下深愛公主的明證……或信物……”
“笑話……”法皇突然將折扇遮擋著嘴呵呵笑起來,“寡人愛情的明證,璋子再清楚不過了,早已算不得問題!”
的確,近來法皇已關懷備至地將二條富小路殿的豪華宅邸送予璋子公主,還為她添置了華麗衣裳,以及眾多的隨從仆人等,讓她過著錦衣玉食、極盡奢華的生活。
迄今為止,法皇的嬪妃之中尚無人獲此恩寵。
“你是說她還不滿足嗎?”
“不是。奴婢知道,陛下的心意公主已心有戚戚,絕無任何不滿。”
“那么,還有其他什么嗎?”
“奴婢可以斗膽稟告嗎?”
“可以,快快說來。”
“遵命……”內侍再度頷首,深吸一口氣,以使自己鎮定。
“凡女子受到君王寵愛,確乎無上榮幸之事,更何況承蒙尊貴的法皇陛下恩寵,自當感謝圣恩,感激之情言語難以盡表。只是,除此之外,倘若還能得到足可確認陛下之深情厚愛的、實實在在的名分或地位的話……”
“地位?”
“正是。啟稟陛下,璋子公主是陛下最愛的女人,自然毫無疑問。對此,想必璋子公主也心知肚明。不過,公主尚無與陛下此意相對應的、可向朝廷內外明示的地位或稱謂。”
法皇凝望著空中陷入了沉思,然后平靜地問道:“你是指冊立為更衣[16]或局[17]嗎?”
“不止于此……”
“你的意思是,這樣不能使她滿意嗎?”
“衹園妃的稱呼是女御。”
法皇驟然睜大了眼睛,然后緩慢地點了點頭。
“如此說來,她是想當女御了?”
“不,這個還說不好……奴婢只是覺得公主想要這些也未可知……”
聽到這里,法皇露出了淺淺的微笑:“既然想要,為何不跟我直說?”
“可是,無論跟陛下多么親近,這種事情璋子公主也難于……”
“原來如此。”法皇微微首肯道,“明白了。我現在回寢殿,璋子一到,立刻請她過來。”
“遵旨。”內侍躬身施禮,待抬起頭時,只見法皇早已朝著通向寢殿的回廊走去了。
當晚,璋子公主到達時已過酉時,天色已昏暗下來。
接到車宿來報公主已到達,內侍急忙沿回廊前去迎接時,璋子公主已走進了東中門。
內侍慌忙施了一禮,脫口道:“法皇正等得心焦呢。”
璋子公主含笑點頭,表示已知曉,然后沿著回廊朝寢殿走去。
此時法皇已從寢殿迎出來了,也許是聽見什么動靜了吧。法皇向璋子公主伸開雙臂,仿佛在說“你可來了”似的,璋子公主立刻撲進穿白色直衣的法皇懷里。
“噢,怎么才來,怎么才來!”
法皇緊緊摟抱著袿衣[18]裝束的璋子公主,用右手慈愛地撫摸著她那如瀑布般長長的黑色秀發。
法皇正如饑似渴地盼望一親這妙齡少女的芳澤不假,可何至于將內心的渴求這般袒露無遺呢?
內侍本以為法皇會責備璋子姍姍來遲,讓自己苦苦等候多時,誰料想,法皇未露出一絲一毫的嗔怪之意。
內侍暗自思忖,長此以往,璋子公主會更加任性,無從約束,可現在對法皇說什么也是聽不進去的。當務之急需請示一下,接下來在寢殿內,他們打算如何度過。
“請問陛下……”內侍對仍然緊緊擁抱的兩人開口問道,法皇終于意識到什么似的,放開了璋子公主。
“可以準備晚膳了嗎?”
法皇再次扭頭瞧著璋子公主,等到她點頭,法皇才道:“用膳吧。”
看樣子,法皇要和遲到的璋子公主一起用膳。
“是,馬上準備。”內侍鞠了一躬,剛一離開,兩人便手牽手朝寢殿走去。
憑著對整個過程的觀察,內侍感覺璋子公主不像是因有事而遲到,很可能僅僅是一時耍小性,出門晚了而已。
果真如此的話,便可以肯定是年輕女子在撒嬌了。
內侍沿回廊返回東配殿時,悄悄搖了搖頭。
璋子公主的撒嬌是否行得通,全看今后他們兩人的關系發展到怎樣的程度了。
內侍自言自語著,吩咐御膳房,馬上備膳。
半個時辰之后,坐在御座上的法皇和璋子公主面前擺上了晚膳。
外面天色已黑透,殿內正中央的燈臺清晰地照出了并肩而坐的法皇和璋子公主。
看得出,雖說是用膳,法皇也想讓璋子公主坐在自己身邊。
在他們面前,御膳房的女房恭恭敬敬地一盤一盤地擺放著御膳。
法皇面前的懸盤有四條腿的方托盤。鑲嵌著紫檀打底的描金螺鈿,上面擺放了清蒸鮑魚、鮭魚絲和鯛魚干。
其他高腳盤里盛著松子、榛子、棗、石榴等果品。
下面的方托盤上,還放著準備斟酒的銀質酒壺和酒盅。
法皇嗜好飲酒,而璋子公主幾經熏染后,也能陪法皇飲上幾杯了。
今天法皇也是早早拿起酒壺,要給璋子公主斟酒了。
“不,我來……”
璋子公主雖然伸出了手,但法皇已不容分說給她的杯子里斟上了酒,然后,才輪到璋子公主給法皇斟酒。按規矩應由女房給他們斟酒,但她們見兩人正情意綿綿,不敢打擾,只好侍立一旁,瞧得眼直。
與法皇這般親密無間,交杯換盞地進膳的后妃,遍觀四海之內,除璋子公主之外再無他人。
內侍見此情景,便留下安藝和但馬二女房侍候,自己先行告退。剛一退下,便聽到法皇和璋子公主發出朗朗的笑聲。
真不愧是一對相親相愛、情深意篤的愛侶,但這般旁若無人是否妥當呢?
內侍忽覺不安起來,挪動著碎步退出了寢殿。
話又說回來,法皇陛下對于女人是多么重情重義啊。
內侍回憶起了迄今為止耳聞目睹的法皇的愛情經歷。
法皇出生于六十一年前,即天喜元年(1053)六月。作為當時的皇太弟,即后來的后三條天皇的第一皇子降生,諱號“貞仁”。
延久元年(1069)四月,法皇十七歲時被立為太子,稱為貞仁親王;當年八月,迎娶權大納言藤原能長的養女道子公主為東宮妃。
但道子時年二十八,比皇太子年長十一歲之多,加上性格內向,據說皇太子與東宮之間感情并不和諧。
或許因此緣故,兩年后,延久三年(1071),攝關[19]家的嫡系,左大臣藤原師實的養女賢子公主入侍東宮為妃。
賢子妃年方十五,小東宮四歲,且十分聰慧可人,很快便集東宮的寵愛于一身,使得道子妃愈加受到冷落。
至延久四年(1072),貞仁親王二十歲時,父君后三條天皇讓位于他,成為白河天皇,賢子妃被立為中宮正宮[20]。
賢子妃雖比道子妃后入宮,但貴為攝關家養女,且受到天皇專寵,自然是普天慶賀,不在話下。
賢子妃成為中宮之后,天皇對賢子妃的愛情有增無減,賢子妃亦仿佛回報天皇的寵愛一般,陸續誕下敦文親王、善仁親王,以及媞子內親王、令子內親王、禎子內親王。
誰承想,這樣一位健康、多產的婦人,卻于應德元年(1084)九月突然病倒,不久便病入膏肓。
根據宮中禁忌,患病者需由宮內遷回娘家,但天皇舍不得與中宮分開,仍讓她留在宮中,并招來眾多陰陽師為中宮祈求康復。
雖如此,中宮亦未能痊愈,于當月末,年僅二十八歲便撒手人寰。
內侍聽說,當時的內大臣藤原師通將此事的經緯載于日記,曰:“萬人泣涕不已。”
此外,他還詳細記述了中宮去世后白河天皇悲痛欲絕的情狀,直到翌年,天皇仍沉浸于無盡的哀思之中,以致竟日待在夜御殿[21]里唏噓傷悲,不理朝政。
天皇還為已故中宮祈福,于比睿山[22]麓東坂本建立圓德院,于比睿山的橫川建立勝樂院,又于醍醐建立圓光院,以及在法勝寺內建造常行堂等。
在建立這些寺院的同時,大江匡房起草的《法勝寺常行堂供奉愿文》和《圓德院供奉愿文》等文章的字里行間,均滲透了這段時期天皇對中宮的悲嘆追思,不過,內侍對這些文章只是聽說,并未親眼看過。
此后,白河天皇雖讓位成了上皇,仍未能忘懷中宮賢子,因而一直未納新妃子或女御,只是時常臨幸身邊侍奉的女房,甚至沉湎男色,滿足一時的生理需求。
可以說,自寬治到康和年間,白河上皇的荒淫無度,放浪形骸,是由于無法忘懷中宮賢子,自從見到衹園女御,才終于收回了漂泊之心。
這位衹園女御,原本是源惟清的妻室,據說作為下級女房在白河上皇身邊侍候時,被上皇看中后,迅速受到寵愛。
然而,這位女御的丈夫惟清,曾任三河[23]守,因妻子被法皇奪走,而對法皇懷恨在心。
法皇察覺后,為獨占女御,更為鏟除禍根,便冠以“詛咒法皇”之罪,將惟清及其姻親流放。以上雖是道聽途說,不清楚詳情,但與此相近之事件確實存在。
衹園女御受法皇專寵已有十年之久。康和末年時,她名義上是侍妾,實際擁有不亞于妃子或中宮的權勢。
大約從這一時期開始,內侍也獲得侍奉法皇的機會,因此對這些事情記憶猶新。
內侍記得,自己侍奉法皇后不久,女御被安置在衹園附近一座奢華無比的宅第里,隨時奉召去侍奉法皇,且常常被留在法皇的御所侍寢。
九年前,即長治二年(1105),法皇在衹園神社東南角建造了阿彌陀堂,安放了一尊一丈六尺高的阿彌陀像。那年秋天,以東寺[24]的大僧都[25]范俊為率引高僧,舉行了供奉儀式。
參列者有權中納言藤原宗通、藤原仲實、參議左大弁源基綱,以及所有的殿上人[26]。場面之盛大,令內侍至今難以忘懷。
翌年,女御又在鳥羽殿御堂舉行了五部《大乘佛經》的講經。除賢暹等眾高僧外,權大納言藤原公實、藤原經實、權中納言藤原仲實等公卿也盡數出席。
不消說,這些奢華盛典皆仰賴法皇之威光,凡出席者無不是憑借衹園女御才成為法皇的寵臣的。
然而,女御雖得到法皇的萬般寵愛,卻始終心有一憾,即至今未能懷上法皇之子。
若有幸妊娠,那么此子,以及女御自己將會獲得怎樣的地位啊。光是想想女御都會激動不已,唯此事令她甚感遺憾之至。
于是,對自己生育已不抱希望的女御決定收養一個女兒。
此時有幸被選中的是女御的“親信”之一,藤原公實的女公子。
公實屬于藤原氏北家的閑院流[27],是正二品大納言實季的大公子,相當于白河法皇陛下的堂兄弟。
這位公實與其夫人光子[28]之間生有八子,其最小的女兒璋子成了女御的養女。
也有人說,此乃當時實力迅速增長的閑院流對白河院政[29]示好。
因此,璋子公主自幼便時常有機會見到法皇。她五歲的時候,法皇還出席了璋子公主的著袴慶典[30]。
其后,養母每次奉詔去法皇寓所,璋子公主都跟隨前往。時而鬧著玩地與法皇同枕而眠,睡覺時甚至將她的小腳伸進法皇懷里。
當然,法皇起初只是出于單純的嬉戲,無意間觸摸到璋子公主的肌膚,而璋子公主似乎也喜歡法皇床上的舒適溫暖,懷著懵懵懂懂的好奇心,睡到法皇身邊的。
再說,旁邊躺著養母女御,璋子公主自知不過是女御的女兒,所以三人同床,并不感覺特別不自然吧。
不曾想,兩次三番睡在一起后,法皇開始對璋子公主的身體感興趣了。
不過,縱然貴為法皇,當著女御的面也不可能隨心所欲的。
大概某日女御要回去時,法皇命璋子公主留下,兩個人繼續在床上玩耍時,不知不覺便結合了吧。
內侍因不在法皇身邊侍候,對此事內情不甚了解,但據其他女房說,是很自然地發展到男女情交的。
但內侍還是無法想象,有著祖孫般年齡差距的男人和女人竟然會交合。也許正因為年齡差距很大,法皇才對璋子公主感興趣的吧?
爾后他們的交往可謂異乎尋常,半年過后,對法皇而言,璋子公主已是不可或缺的掌中寶玉了。
這段情緣堪稱忘年之交,可喜可賀。然而,迄今為止法皇最愛的女人一直是衹園女御。
女御萬沒想到會遭遇自己的養女——視如己出的璋子公主的背叛。當然,背叛了女御愛情的是法皇本人,但情敵竟然是璋子公主。真不知在此事上,法皇乃至璋子公主究竟是如何考慮的。
于是,自去年夏天起,女御推說身體不適或眩暈等等不再去法皇的御所伴駕了。與此同時,璋子公主的來訪次數迅速增加,則是確鑿無疑的事實。
他們兩情相悅、互相愛戀之事,自下級女房至車副之流,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
無論是法皇還是璋子公主,都稱得上是毫不介意他人非議的天真爛漫之人,或曰色膽包天之人,全然無意遮遮掩掩、避人耳目。
不過,也許是璋子公主覺得愧對養母女御,抑或是女御對璋子抱怨了什么,今年初,法皇另外賜給璋子公主一座宅邸,使她得以和女御分開居住,因而自由自在多了。
今晚璋子公主雖說遲到了,但并未爽約。此時,兩人又若無其事地親親熱熱說笑了,真是匪夷所思。
難道說是法皇一廂情愿,而璋子公主只是虛與委蛇呢,還是璋子十分享受這種狀態呢?他們的真實內心實在是讓人琢磨不透,不知今后會是怎樣的前景。
無論怎樣,但愿不致出現麻煩事態便好。內侍回到自己住處后,仍愁緒難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