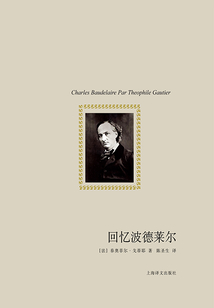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中譯本序
對現代詩歌和文藝思想貢獻最大的詩人或許應推波德萊爾。但是,為人誤解最甚的作家也莫過于波德萊爾。文藝上的貢獻,不僅反映于為人們帶來多少新穎、可愛的東西,還反映于吸取和發揚了文學傳統中多少優秀的成分;而文藝上的誤解,既可表現于詆毀或貶損,亦可表現于稱譽或宣揚。僅就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有關波德萊爾的文字材料而言,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和評價他的貢獻、而且少有這樣或那樣誤解的東西,還不算多。我們倒是看中了英國學者蓋伊·桑(Guy Thorne)編譯的這本紀念冊式的小書,因為其中或褒或貶每每恰到好處,而且著重于事實和作品本身的涵義,少有連篇累牘的空論。這本書以著名的法國詩人、藝術理論家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1811—1872)的《波德萊爾的生平和對他親切的回憶》一文為主體。翻開《惡之花》的扉頁,我們便可以看到,這一近代最負盛名的抒情詩集就是題贈給戈蒂耶的。波德萊爾稱他為自己“非常親愛和非常尊敬的老師和朋友”,是毫不虛誑的。戈蒂耶對這位晚于自己一代的“學生和朋友”也極為同情和賞識。他在波德萊爾去世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就寫下了這篇情深意切而又洋洋灑灑的大文,既是回憶錄,更是風格別致的作家傳論。蓋伊·桑稱之為“傳記杰作”,散文中不可多得的“珠玉”,也是不虛誑的。現在將戈蒂耶這篇文章的題目稍加簡化作為全書的書名,同時還收入波德萊爾本人的詩、文、書信以及英國編譯者蓋伊·桑的比較研究文字,相信這些確實是對這位非凡的詩人的極好回憶與紀念。目前,世界上涉及波德萊爾的各種文字資料,少說也有上千種,其中不乏獨特、新穎的論說以及差堪與蓋伊·桑編譯的文字比肩的譯介。即使這樣,我們譯出這本資料來源較早的“波德萊爾紀念冊”,可以說仍然很有意義:讀者可以比較一下,相對于一百多年前的情況來說,我們現在的鑒賞力和知解力究竟又有多大的進步!
不少現代人可能已不覺得戈蒂耶的文章有多么大的妙處,多數現代派詩人可能也不太欣賞他們尊為“偉大的先驅者”之波德萊爾所采用的那種嚴謹的詩歌形式。時代形成的這些欣賞距離是不足為怪的;細心的讀者或者反而會從這種距離中悟出一些審美法則。我們知道,作為批評家的戈蒂耶,正好處于歐洲浪漫主義的“傳記式批評”盛況未衰和唯美主義的“印象式批評”方興未艾之際。他這篇文字可以說是這兩種批評風格的美妙結合,加上他自己那支詩筆中靈氣的烘染,堪稱以回憶和評述為內容的“文學散文”。初讀之下,有人或許會不滿其中不少旁騖的“閑筆”以及隨處可見的“矜才炫學”的典故,其實,只有這樣才能最節省筆墨、最活靈活現地提供波德萊爾所處的社會和文化環境。這些對于我們來說已經陌生難辨的東西,如果不是經由與詩人志趣相投的同時代人道出,恐怕早已湮沒了。
以上的辯解肯定不會使現代批評理論家滿意,因為他們早已唾棄“印象式”的甚或“傳記式”的東西。“科學化”是現代批評理論連帶著批評實踐的大勢所趨。批評家們絞盡腦汁去組構他們的“體系”,創造或采擷“科學性”和“玄學性”的術語和表達方式,他們多數沒有閑情逸致去寫批評性的“文學散文”,也不屑或無能為之。縱觀各國許多知名的現代文學批評理論家和文學研究者,實質上多半是文化學者而不是文學家,便知筆者所言不謬。我們指出這方面的特點,絲毫沒有與新批評潮流對抗之意,而僅僅因為戈蒂耶這篇文章會給予現代文學批評界這樣的啟示:不僅包括與傳統有千絲萬縷聯系的文人學士,而且包括業余以審美欣賞為主要目的的廣大現代讀者,內心上都要求保留“印象式”和“傳記式”這一類“舊批評”中的精華成分。相對來說,他們很少問津于學院式的現代批評。
文學藝術以及許多人文科學門類固然都有鮮明、強烈的時代性,但同時又具有更頑強、執拗的傳統性。舊東西必定會融化進新東西之中,甚至經過改頭換面,又復活過來了。中國古代的幾次“古文運動”、震撼世界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都是這方面的顯例。據此,我們不妨推測,現代批評發展到鼎盛的巔峰,有可能再回過頭來與“印象式”等傳統批評融合為一,從走過頭的純思辨領域拉回到原來的藝術領域來,但同時仍保持其“科學的”、執著于真理的進步勢頭。如果作此設想之后再來借鑒戈蒂耶這篇“印象式”的杰作,便不難領略個中雋永的意味。
蓋伊·桑認為戈蒂耶的這篇文章連一字一句都更移不得,當然只不過是溢美之辭。不過,戈蒂耶在印象式的敘述和描寫中,解釋和闡發了人們甚至迄今還不甚理會的一些問題的真諦,卻是千真萬確的。盡管戈蒂耶主要從他的藝術主張出發來考察和判斷這些問題,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仍不能不承認他向我們提供了相當卓越的歷史透視。例如,長時期以來,我們因為波德萊爾是所謂的“頹廢派”代表人物而疏遠他,歷代正統的文學批評家也因此全面否定波德萊爾創造性的文學業績,但戈蒂耶當時就指出,波德萊爾對“頹廢”或“頹廢主義”(Decadence)有他自己獨特的解釋,他不過認為盛極一時的法國浪漫主義詩歌已經發展到自己的巔峰,而從他開始就要“衰落”或“走下坡路”了。當然,這不過是自謙之辭,其中蘊含著他推陳出新之意。“Decadence”一詞按其本義也是指客觀事物的上述發展狀態,但后來卻主要引伸為主觀態度上的“頹廢”;聯系波德萊爾私生活中的某些過失,尤其是他的代表作《惡之花》給人的表面印象,更坐實了“頹廢主義”的存在,而波德萊爾便成了世界近代文學藝術領域中這一“宗派”的開山祖師了。細讀戈蒂耶這篇“回顧”之作,我們就會明白“名不副實”的情況隨處可見,不僅美名是如此,惡謚也不例外。
當然,波德萊爾繼英國浪漫主義大詩人拜倫之后,作為另一位“惡魔派”首領,卻因此而在“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世界文學潮流中大享盛名,盡管如此,我們遠離一切虛名,追求本源,平平實實地考察波德萊爾給我們留下的一份風格獨異的文學遺產,仍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現代主義”如同它所頡頏或反撥的“浪漫主義”一樣,也有風靡一世的魔力,當它也整體式微或銷聲匿跡之后,仍會給人類文化留下一些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其中波德萊爾的文學生涯必定是最富有傳奇色彩的“始作俑者”。我們將不會因為他“離經叛道”而完全棄之不顧,也不會因為他可以當作“現代主義”的旗幟來標舉而將之奉若神明。事實上,每一位偉大的作家都因為他超脫時尚、不同于流俗而為人們所永久紀念。所謂“浪漫派”與“現代派”的對立并非是絕對的:波德萊爾本人對維尼、雨果,尤其對戈蒂耶的推崇(他們反過來對波德萊爾也是如此器重),他詩中對浪漫主義理想(如對貝雅特里齊這一形象)的眷戀,他奉以為師的美國作家愛倫·坡的浪漫主義的奇詭手法,都證實波德萊爾像他自己所認為的那樣,本質上還是一個浪漫主義者。至于以俗濫的方式對尤其是“現代主義”以及其他文學時尚加以調弄或“戲擬”的“后現代主義”,則與波德萊爾相距甚遠,故不在此多所涉論。
波德萊爾比一般的浪漫主義者更深刻獨到之處在于,他從他自身的體驗和穎悟中認識了人類與生俱來的“反常性”,并且最早地以精湛的詩藝,集中、完美地表現了這種“反常性”。如果我們也從這種角度來看待他文學上的“頹廢”,不禁就會將之稱為詩中的“現實主義的勝利”了。難怪不止一位中外學者將波德萊爾與我國的“詩圣”杜甫作比較:杜甫念念不忘浪漫主義大詩人李白,但他自己卻以曲盡其妙的詩句描繪復雜矛盾的現實世界。也有人非議杜甫過于雕琢求工,這與鄙棄波德萊爾的“頹廢”殆無二致。現代詩人何其芳在只能戲作舊詩的時代也作過這樣的“自我批判”,“苦求精致近頹廢”。無論是“雕琢求工”,還是“精致”或“頹廢”,其實都要看它們的實質而分優劣、定棄取;如果徒有形式或無病呻吟,自然不足為訓,反之則應奉為圭臬。文學藝術的現實主義本質(或稱真實性法則)不可避免地與藝術表現手段和效果(或稱“美感法則”)緊密聯系在一起:沒有藝術性和美感效果的“真實”,不僅會玷污“現實主義”,尤為甚者,使文學藝術本身降格;當然,遠離“真實性”或事物本質的所謂“藝術”,效果與此相同。如果我們將“浪漫主義”理解為主要從主觀意向出發,更自由或更隨意地發揮作家的才能和技巧來表現世界的本質,那么,“現實主義”就可以認為是作家在這樣做之時表現得更自覺、更精確和更受客觀條件的限制。只有在一定的規范和限制之中,方顯出作家個人的才能和技巧精湛與否。現實主義作家由于更清醒地意識到客觀世界(包括語言媒介)對自己的約束性,因此要比浪漫主義作家更重視藝術的規范和技巧。波德萊爾的整個文學生涯和主要的創作實績都滲透著這種現實主義傾向,他與浪漫主義者的區別也僅在于此。
有人(如法國象征派詩人瓦雷里)很早已覺察出波德萊爾帶有“古典主義者”的意味,因為他“在自己的心頭帶著一位批評家,而且又把他和自己的工作聯系在一起”;這說明了他對“理性”和“思維”的重視,對“秩序”和“形式”的關心。(瓦雷里:《波德萊爾的位置》)情況確實如此。但是,波德萊爾不像一般古典主義者那樣墨守簡單或過時的祖宗成法。他熟睹“現代人”的靈魂,并創造了與之相適應的新的表現形式。從我們后人的角度來觀察,它們不僅補充了古典形式,而且增進了“古典美”。不過,現在許多人將此納入“現代主義”的混沌之中。20世紀的“現代派”大師T.S.艾略特早已認為“現代主義”文學就以“新古典主義”為基本的創作方法;但不少人也將與古典主義背道而馳的無理性的“達達主義”以及各種荒謬的創作手段當作“現代主義”的正宗,甚至將略為改頭換面的“浪漫主義”也算做“現代主義”。如此這般,不一而足。因此,這里不想隨大流稱波德萊爾為“現代主義”的開山祖師,而寧肯確切一些稱之為“將浪漫主義、象征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于一身的偉大詩人”。這樣稱呼并未抹殺他對現代思想和現代詩歌風格的深遠影響,而是排除了與他無干的或僅僅是某種附會的“現代主義”副產物。“現代主義”之所以如此龐雜,與這一名稱不無關系。永無止境的、令人目不暇接的“現代”產物,何種不可稱為“現代主義”的呢?
我們的稱呼與以往的貶稱以及現在大家習慣的“尊稱”均不相同。這并不意味著“翻案”。在文學藝術上無案可翻,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審美觀念對具體的審美對象作出這樣或那樣的審美判斷。旁人同意也好,不同意或加以補充修改也好,都不是輕易不容爭議的歷史裁決。我的上述看法主要根據本書正文所提供的材料,因此不妨作為這冊譯作的小序,以表譯者的觀感和態度。如果今后有誰能提供更多新鮮的、有說服力的資料,我們將重新校正自己對這位引人爭議不休的世界文化名人的看法。
陳圣生
1987年10月11日初稿
2010年4月15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