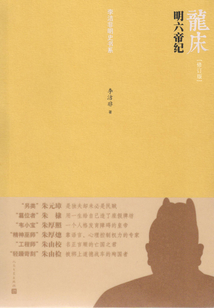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草莽之雄(1)
這個明朝締造者,以冷血和嚴重的暴力,把自己形象推向極度的黑暗。一提起他,人們油然想到“暴君”,他的名字也與嗜殺、酷刑、狠毒、野蠻緊緊綁在一起。就此言,他是極權體制推出的標準“獨夫”。然而,如果我們習慣性地以“獨夫民賊”相稱,卻發現有一半對不上號——他無疑是“獨夫”,卻并非“民賊”。這很少見,我們由此也格外注意起他的獨特性。
中華自三代以降,文明光燦,環列皆蠻昧未化民族,雖時有襲擾,以至國裂土分,但說到舉國淪亡的情形,卻還不曾有過。直到十三世紀,蒙古高原崛起一個民族,尚武剽悍,仗著馬肥人強,拉出一支前所未有的強大鐵騎,摧枯拉朽從東打到西,從北打到南,差不多征服了整個歐亞大陸。
全中國第一次真正地亡了。但那蒙古人,雖仗著騎兵厲害,武力之強自古所無,終究是草原上粗野少文、散漫任性的民族,以為不單可以馬上得天下,也可以馬上治天下,非但不向中原文明學習,以求洗心革面,卻讓自己的蠻昧習性一仍其舊,不足百年便告終結。蒙古人被趕回北方大漠,重新過上四處劫掠、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代之行天的,便是大明王朝。那開國的君上,喚做“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圣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偌長一串頭銜,除卻頭兩個字,剩下的皆系虛諛之辭,誰也記不住的,所以歷來大家都只管他叫“明太祖”。
說起這位太祖皇帝,那也真是迄來從無的一等人物,出于赤貧,十七歲那年父母繼歿,孤無所依,不得已竟入寺為僧混口飯吃,未久,寺院亦敗,他便只身一人“游食”四方——所謂“游食”,無非乞討為生。但偏偏這么一人,當著天下大亂之際,投身暴眾,由士卒而頭領,由頭領而元帥,最后遍滅群雄、逐斥元室、一統中華,成就二百數十年之基業。自古以來,舍漢高祖劉邦外,中國并無第二個起于平民的皇帝,但那劉邦,好歹曾身為亭長,謂之平民略嫌勉強,真正從底層“登天”的,上下五千年,唯有太祖元璋。
說鳳陽,道鳳陽
平常,從南山坡望去,曠野無際,野草萋萋。寬大的山坡幾乎一直很平緩地向北延伸著,只偶有起伏,間或點綴著幾株孤零零的樹。一條清亮的河流繞著山坡,靜靜流淌,陽光下就像條白綢帶。
此河名濠,小,長數十里。源有二,一自橫澗山,一自定遠城北,在濠州之南合流,蜿蜒東北而入淮水。小固小,卻非無來歷。很早以前,莊子常留連于此。濠水以澄澈出名,是“臨淵羨魚”的佳處,當年,莊子偕惠子同來賞魚,留下一段“子非魚”的巧辯典故。上千年過去了,平靜的濠水好像再沒有新奇故事發生,只是默淌。
至正[1]十二年,大旱令素常清亮的濠水全無往日風采,就像從少女紅唇一夜之間變成老婦槁唇;魚兒無影無蹤,河床隨處呈現網狀裂縫;少量幸存的河水,薄薄的,奄奄一息,在河中央最凹處反射出光來,幾乎看不出它在流動。
一條死水,猶如濠州的人心。
不過,此地人民對這情形倒也并不新鮮。七年前,一場更其兇烈的旱蝗之災,旬日之間奪走成千上萬條性命。那一年,單單是孤莊村朱五四老漢一家,五口人便死了三口,四月初六朱老漢頭一個撒手人寰,三天后,輪著大兒子重四斃命,又十日,朱家媽媽陳二娘丟下老二重六和老幺重八,也追著老伴和大兒子去了陰曹地府;可憐那重八年方十六,竟眼睜睜十來天的工夫連喪父母和長兄。好些年后,孤莊村父老說起此事,還都直搖頭嘆氣,直道:“慘哩……”
如今,當年人煙寥落、雞犬聲稀的景象,又在孤莊村重現。落日下,極目而眺,偌大的平野全然空曠,生生看不到一個人影,甚至不見鳥兒飛過,那份靜詳簡直是一種透著憂傷的美,可是久處其中,卻令人不免可怖。
就在南坡,一株老榆樹下,有一小土堆微微隆起,沒有什么特征,上面光禿禿地只長些荒草,而且經年風吹水刷,土包越來越平,眼看著就要流失了。但是繞著轉過來,猛然卻見一條大漢仰躺在土包旁,冷不丁嚇你一跳!那漢身長八尺,黝黑精瘦;穿一條污爛污爛的直綴,敞著胸懷,夕陽灑落處,肋骨歷歷可數;破帽兒遮臉,肚皮一起一伏——竟是睡著了。
前身即朱元璋充小沙彌之皇覺寺,洪武初遷至現址,賜名“大龍興寺”。
孝陵,位于南京鐘山。朱棣篡位遷都北京,其后諸帝皆葬北京十三陵,只剩下朱元璋孤零零在此。身后的冷清,最為形象地說明了朱元璋在皇權問題上自相矛盾所導致的失敗。
“八哥,醒醒,醒醒……”
漢子猛一驚,睜眼看時,是打小一處廝混的周家小三子。但見他背負布包,神色匆忙,似要出遠門的樣子。
“小三子,你這是要去哪兒?”
“說不得,八哥,出事了。那封書信被人知道了,想告發官家討賞哩。我尋思還是投湯二哥的好,咱一起走吧?”
漢子眼珠骨碌轉了轉:“真的么?”
“我還訛你不成?”周三兒頓足道。
漢子笑了:“兄弟,怎就改不掉你那急脾氣?要不,你先行一步,哥哥我隨后就來。”
“也罷。”周三兒拱手道,“八哥,那我就和湯二哥在濠州等著你。”
“一路珍重,兄弟。”漢子在周三兒肩頭用力拍了拍。
目送周家小三子漸行漸遠的身影,暮色下,漢子忽然感覺到一絲涼意。一群昏鴉飛了來,落在老榆樹上,“啊,啊啊”的叫聲送出,令本極遼曠的四野,更顯冷清。
漢子悲從心起,掉頭沖著小土堆翻身便拜:
“爹,娘!二老在世,教兒本分為人,兒原不想投湯二哥,如今村里人死的死,逃的逃,廟里和尚也散去大半,兒沒了著落……兒今二十有五,實不甘再像八年前那般游食為生……爹啊娘啊,兒當如何,替兒拿個主意吧!”
言畢,就兜內摸出一面小銅牌,那還是自己剛生下來時,吃不得奶,爹上廟里拜菩薩時請回來的護身符。銅牌一面刻著觀音像,漢子拿在手里,默想:“觀音像若沖上則去,沖下則留。”于是開口道:“爹娘在上,且助重八則個!”
銅牌拋起,落在土坡草間,撥開一看,觀音像沖上。再扔,如此;第三次又拋,仍如此。
漢子站起身,目光漸漸清澈,原本就有些兇悍的臉此時又蒙上了層剛毅之色。只見他頭也不回地大步走了,直走到西下的夕陽血似的慘紅里去……
——以上多系虛構,是當年讀吳晗《朱元璋傳》后,我在懷想明太祖朱元璋如何奮起于草莽之際,自己心里描畫出來的一幅“復原圖”。1978-1982年念大學期間,每年的寒暑假,我在合肥與上海之間這條鐵路線上來來回回要穿行四次;每一次,列車行經臨淮關-蚌埠這區間,我望著窗外的山川,腦中都止不住去浮想與朱元璋有關的舊事和畫面。
雖是虛構,但人物和大的情節皆有所本。其中,那個周家小三子,是周德興;湯二哥,就是湯和。這兩個人,還有徐達,都是朱元璋(小名重八)打小一起的玩伴兒,后俱為明朝開國元勛。至正十二年郭子興在濠州聚眾反,湯和先行投了郭軍,很快積功做到千戶,此時他捎信給朱元璋,催促也來入伙;元璋初意未決,求之于卦,才趕到濠州,由湯和介紹加入義軍。讀史至此,不免慨然:一座小小的孤莊村,蹇伏浩野,無憑無依,卻突如其來聚現了一個豪杰群體。歷史的脈絡,確非可以常理解釋者。
此草寇,非彼草寇
時勢造英雄,這話既對,也不對。很多時候,似乎具有必然趨向的時勢,最終卻并沒有造就英雄,只造就了偽英雄。這類偽英雄也曾一時叱咤風云,露出王者風范,但就在幾乎走上其命運巔峰的關頭,不堪轅軛,被最后一根稻草壓得轟然倒地——“大順帝”李自成、“天王”洪秀全,此之謂也。還有的時候,時勢貌似造就了英雄,然而不可一世的“英雄”卻辜負了時勢的造就,不可思議地敗給絕非為時勢所看好所鐘意的弱者、配角或二流人物,項羽之于劉邦如此,袁紹之于曹操如此,張士誠、陳友諒之于朱元璋亦如此。
張士誠,鹽販出身。元至正十三年起于泰州,至正十六年得據吳地,進而再得浙西,擁江南富庶之地,于是心滿意足,惟知自守。至正二十五年,陳友諒起大軍來取應天(南京),約士誠合而攻之。士誠竟以其“一畝三分田”為自足,不予呼應。其于元室同樣以茍且求存,降了反,反了又降,極盡討價還價之能事,終不脫小販本性。茍且至至正二十七年,業已擊敗陳友諒的朱元璋,騰出手收拾張士誠;是年九月,徐達破平江(蘇州),士誠自縊死。
陳友諒,漁夫出身。原為徐壽輝部下,至正二十年以陰謀發動兵變,挾壽輝,而自立漢王;不久,在采石磯(馬鞍山)以鐵撾擊殺徐壽輝。時諸強中,友諒廣有江西、湖廣之地,兵強馬壯,不可一世,驕橫萬分,銳意擴張,即興兵東犯。旌旗蔽日,舳艫擁江,順流揚威而至,志在必得,然而卻被朱元璋用誘敵深入之計,大敗于南京城外。兩年后,雙方再大戰于鄱陽湖;此番,友諒盡出其精銳之師——當時天下無出其右的巨型艦隊,“兵號六十萬,聯巨舟為陣,樓櫓高十余丈,綿亙數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朱元璋水軍極弱,雙方實力懸殊。但陳友諒一味恃強,朱元璋再次用計,以火攻大破陳氏巨型艦隊,戰局逆轉,八月,友諒中流矢斃命。
張、陳二人,一個當時最富,一個當時最強。以勢來論,元室衰微之際,他們誰都比朱元璋更有資格成就霸業,一統天下。但士誠其人,永遠只看得見眼前利益,一個地地道道的守財奴,本性如此,毫無辦法。陳友諒驕狠雄猜,心黑手辣,倒是貪得無厭之徒,怎奈量小氣狹、器局逼仄——僅從一件事上即可知其胸襟:鄱陽之戰,友諒勢蹙之際,居然“盡殺所獲將士”以泄忿,“而太祖則悉還所俘”——同樣也是本性如此,毫無辦法。
在兩個膀大氣粗的鄰居面前,朱元璋盡處下風,當初陳友諒搞擴張,先對朱元璋下手,多少也是捏軟柿子的意思。但是后來他肯定發現搞錯了人,至于鄱陽湖決戰他“矢貫其顱及睛而死”之際,只怕會感到平生最為后悔的一樁事,就是沒有弄清朱元璋是怎樣一個角色之前,即貿然對其出手。
而朱元璋,不管其他方面作何評價,我們得承認,他是古來“草寇”之另類。于是,脫穎而出,做成了古來“草寇”都想做而最后都做不成的事。其中,關鍵的關鍵,是朱元璋高度重視并解決好了知識分子問題。將領善戰、主公明睿,是打天下的保證,但不足以得天下。匹夫起事,先天不足在文化上。人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其實,政治也是戰爭的終點。沒有人為戰爭而戰爭,打仗的目的在政權,而政權雖靠戰爭贏得,卻無法靠打仗治理。從打天下到得天下,必須由知識分子隊伍建設來銜接。朱元璋最不可思議之處就是,以一個地道的泥腿子,而能深入理解“文治”的意義。
解縉談及此,說:
帝性神武明達……始渡江時,首兵群雄多淫湎肆傲,自夸為驕。帝獨克己下人,旁求賢士,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倦。[2]
《翦勝野聞》載: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后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開悟,豈非天生圣天子耶?”[3]
每克一地,朱元璋都不忘招賢求士。有名的一例,就是下徽州后召耆儒朱升問時政,而得到“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他在采石訪得儒士陶安,很急切地征詢政見。陶說:現今群雄并起,他們所欲都“不過子女玉帛”,建議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朱元璋大受啟發。[4]《明通鑒》也記有與儒士唐仲實的類似談話。胡大海打太平府時找到一個叫許瑗的儒士,派人送來見朱元璋,“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讀書人!’”[5]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的事業有了歷史性的轉折,標志是,這年三月,他成功地將劉基、宋濂、章溢和葉琛延入陣營。這四人聲望素著,才智、文章、學問,皆一時泰斗。他們連同早些時候在滁州加入的李善長,組成了超一流的智囊團。以這些人為中堅的知識精英,不單在戰爭中為朱元璋運籌帷幄,更從法律、政制、禮儀、財稅等諸多方面為未來明帝國設計一整套的秩序。明代的后世批評家回顧說:
漢高祖謂:“吾能用三杰[6],所以有天下。”……我明聿興,公侯爵賞數倍漢朝:李韓公[7]之勛烈無異蕭何,徐魏公[8]之將略逾于韓信,劉誠意[9]之智計埒于張良……我朝開國元功,視漢高尤有光矣,大業之成,豈偶然哉![10]
的確說到了點子上。
孟森先生論述明之立國,講了三條:第一,“匹夫起事,無憑藉威柄之嫌”;第二,“為民除暴,無預窺神器之意”;第三,“一切準古酌今,掃除更始”。這第三條就是講,明之立國,得益于文化上巨大成功,以大量制度創新,開啟歷史新階段——“清無制作,盡守明之制作”,“(清人)除武力別有根柢外,所必與明立異者,不過章服小節,其余國計民生,官方吏治,不過能師其萬歷以前之規模”[11]。僅以“黃冊”、“魚鱗冊”兩大制度創新,即可窺其一斑。“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12]由設“黃冊”,明初有了完全的人口普查,建起真正意義上的戶籍制。從社會,它解決了流移人口問題并解放了往昔在貴族和地主豪強強迫下為奴的人民;從經濟,它理順和保障了國家賦役的征調;從政治,它使集權統治更徹底,影響跨越數百年而至如今。“魚鱗冊”又稱魚鱗圖冊,是特別編定的全國土地總登記簿。明初決定對最基本生產資料——土地實行丈量和登記,“厲行檢查大小地主所隱匿的大量土地,以打擊豪強詭寄田畝、逃避課稅的行為……豪強地主被迫吐出他們過去大量隱匿的土地,就使朝廷掌握擔承稅糧義務的耕地面積大為增加”[13],孟森評論道:“明于開國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舉為之,魄力之偉大無過于此,經界由此正,產權由此定,奸巧無所用其影射之術,此即科學之行于民政者也。”[14]
《明史》說:
終明之世,右文左武。[15]
“右文”,就是優先重視文化建設和文臣,這是明代政治突出特色,朱元璋一開始即抱此旨:
(太祖)響意右文,諸勛臣不平。上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16]
洪武元年九月的《求賢詔》說:“朕惟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于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所守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沒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政,我得以濟民者,當不吾棄。”[17]過去教科書將朱元璋從農民起義首領變為皇帝,解釋為“變質”。這其實很對,朱元璋的確“變質”了,《求賢詔》就是“變質”的明證。
如果“不變質”,又如何?晚朱元璋二百來年,有那樣的例子,可為鏡鑒。
趙士錦是崇禎十年進士,在甲申之變中,羈劉宗敏營約二十日。脫身回到江南后,他把自己聞見寫成《甲申紀事》——劉宗敏身為大將,進城后惟知斂財,日夜拷掠百官,勒其銀兩,“有完銀多而反夾,完銀少而反不夾者;有已完銀而仍夾者,有不完銀而終不受刑者,識者以為前世之報焉。”“自十八日起,每日金銀酒器紬疋衣服輦載到劉宗敏所。予見其廳內段疋堆積如山,金銀兩處收貯,大牛車裝載衣服高與屋齊。”劉宗敏所為,李自成非不知,而竟無力轄制:
初七日,李自成至宗敏寓議事,見庭中三院,夾著幾百人,有垂斃者,不忍聽聞。問宗敏得銀若干,宗敏以數對。自成曰:“天象不吉,宋軍師言應省刑,此輩宜放之。”宗敏唯唯。每日早將已死者用竹筐抬出,每筐三兩人,以繩束之,至是五六日矣。
鳳陽古稱“濠”,以濠水得名。莊子常留連于此。偕惠子“臨淵羨魚”,留下一段“子非魚”的典故。
朱元璋的真容,很難從繪像上見到,都經過了美化。據說先后有兩位替他造像畫師,因偏于寫實而被殺。
錦衣衛創于朱元璋,一度逾于法外,后期“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咸徑法曹。終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獄”。
科舉為中國古代國家干部用人考試制度,對中國成熟的文官政治起到重大作用,但漸漸也成為束縛知識分子精神思想的工具。
按“階級斗爭”眼光,“苦大仇深”的劉宗敏,勝利后痛打劣紳、分其浮財,是勇于奪回屬于自己的勞動果實,他以對階級敵人的毫不手軟,證明自己不忘階級苦、血淚仇,亦即沒有“變質”。
反觀朱元璋,雖也“苦大仇深”,勝利后卻將階級愛憎拋到九霄云外,下《求賢詔》、搞什么禮賢下士,把壓迫自己的人奉為座上賓,與其沆瀣一氣,這不是忘本是什么?不是變質是什么?
苦皇帝
朱元璋既然黃袍加身,肯定發生了“變質”。然而,這種“變質”,為古往今來造反者所共想,如未實現,亦屬“非不欲,是不能”。始皇游會稽,車隊駛過,項羽躲在人叢里暗暗發狠:“彼可取而代也。”[18]這句話,陳友諒、張士誠、李自成、洪秀全腦海肯定都浮現過。問題是怎么變,往哪兒變,以及變成什么樣兒。史上不乏接近成功的造反者,最后不虎頭蛇尾的卻只有朱元璋。為什么?看看闖軍打下北京后的表現,或洪秀全在天京皇宮里做了些什么,大概不難明白。以那些也想“變質”卻不成功者為參照,我們發現,實際上朱元璋除了有所變,更有所不變。單論從造反者轉為統治者,他可謂搖身一變。但換個角度,看看在兩個身份中的表現,印象相反,朱元璋是他同類中變化最小、最少的一個。
野史有些故事,說他忌提舊事,一聽“禿”、“光”、“賊”這樣的字眼抑或哪怕是同音字,就不高興,就殺人。然而,也有記載顯示,他并不諱言貧寒出身和悲慘的少年經歷。濠州祖陵竣工后,詞臣奉撰《皇陵碑記》,朱元璋閱后很不滿意,稱“皆儒臣粉飾之文”,他攬鏡自觀,“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覺得以這種粉飾之文垂后,“恐不足為后世子孫戒”,決心親自提筆,“特述艱難”,如實記述自己的出身、家境和遭遇,“俾世代見之”——這就是洪武十一年的《御制皇陵碑》。
平常,他尤不吝于以其身世和人生體驗訓導諸皇子,使他們勿忘家本。做吳王時,一日,朱元璋率世子朱標祭祀山川,儀式結束,特地叫過朱標,指著身邊將士們說:“人情,貴則必驕。”“今將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庶諳勞逸,他日不致驕惰。”圜丘告成,朱元璋帶著朱標前去視察,歸途中,專門命隨從引導世子繞道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俟其歸,則召而誨之:現在,你知道農民多么辛勞了吧?
夫農勤四體,務五谷,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饑寒,方盡為上之道。
據說,為使諸子習于勤勞,不滋驕惰之性,曾命內侍特制草鞋分發給他們,并規定,只要出城走稍微遠一點的路,皇子們只能乘馬行三分之二路程,另外三分之一必須穿上草鞋步行。他定期打發諸子回老家謁祖陵,接受“革命傳統教育”,說:“使汝等于旁近郡縣,游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之所,訪求故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于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人一闊,臉就變,這似乎是經驗之談;所以,窮光蛋們揭竿而起之際每每要互相叮囑一句:“茍富貴,毋相忘!”實際上,往往忘性都比較大,不單自己患了遺忘癥,倘若別人來提醒,他還惱怒,以為羞辱。
到朱元璋這兒,終于破了一回例。他真的不曾忌其微賤之時,不因做了“萬歲”,而掩卻來歷出身。他曾在一份蠲免兩浙秋糧的詔書里徑稱:“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似乎對此身份甚感光榮,與臣下交談也不憚表露其“小農心態”,曾經說:“吾昔在軍中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饑餓的童年記憶,讓這位皇帝對糧食和農事有一種幾乎病態的敬畏。據說凡是空閑的土地,他都下令種上莊稼,而且還提出一種極其獨特的“種植理論”:“我于花木結實可食用者種之,無實者不用。”總之,不能用來填飽肚皮的,就無用。他曾頒旨嚴禁種糯,因為這種作物主要是用來造酒,而被視為“糜費”。平時在宮中跟太監宮女言“不離稼穡組紃”,后宮墻上門上,也到處畫著“耕織圖”。浙江金華出產一種香米,百姓“揀擇圓凈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年貢約三十石。朱元璋得知詳情后,下令中止此貢,改由內侍在宮苑內墾種數十畝,“計所入,亦足供用”。這辦法后來似乎還加以推廣了,以致宮中閑地都成了農田。某日退朝,朱元璋專門領著太子諸王去參觀他這一得意之作,指著菜地說:“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其實他借鑒魏武而發揚光大軍屯制,起因也是防止奪食于民;說:“兵食一出于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疲民力以供閑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
不過,這個“泥腿子”對農事的重視,似乎有點過頭。比如,有人建議開礦生財,被他訓斥一通,認為只要偏離農本,便是追逐奸利;司天監(掌天文歷法的機構)進獻一款元代水晶刻漏——中設二木偶,備極機巧,“能按時自擊鉦鼓”,或許是最早的自鳴鐘——也被朱元璋一通臭罵,說“廢萬機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而害有益也”。竟下令把它砸碎毀掉……看來,眼里只有糧食、莊稼和農活,并不總是好事。
一次,出游鐘山,回城時,從獨龍岡徒步一直到淳化門,才肯上馬。他感慨地對侍臣說:“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話鋒一轉,他問這些近臣: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所以他們才辛苦成這個樣子,你們這些當官的,心里曾經感念和體憫過農民嗎?接著,他講了一句讓人震驚的話:“且均為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為戒。”
“均為人耳”。并非朱元璋已有“平等思想”,而是“萬歲”之后未忘貧賤往昔,使他能夠將心比心、推己及人。
又某年隆冬,朱元璋視察城濠疏浚工地,見一民工光著身體,在渠水里摸索著什么,命人問之,原來是蠻橫的督工官員把他鋤子遠遠扔到水中,民工只好自己下河找尋。朱元璋聽說是這樣,馬上派人將民工叫上岸,另外發了一把鋤子給民工。他生氣地說:“農夫供役,手足皺裂,亦甚勞矣,尚忍加害乎?”令侍從將那個惡官抓來痛加杖責,一面氣猶未平,回頭對隨行的丞相說:“今日衣重(讀chónɡ)裘,體猶覺寒,況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隨即傳旨役民收工。
對朱元璋,人們談得較多是他屢興大獄、濫刑重典,我一度因此將他歸于“大暴君”行列。后從孟森先生《明清史講義》,讀到這樣一句話: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約束勛貴官吏極嚴,實未嘗濫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
一時振聾發聵。朱元璋有嗜殺之名,但過去只注意到殺人多,卻不曾留心所殺的主要是什么人。經孟森點撥,再去查證史著,果然。汗顏的同時,從中領悟到,讀史確不宜粗。
除了嗜殺,他還有一個嗜好:嗜儉。在中國,政治家節儉,往往是道學面孔的一部分,公開示人以儉,公眾視線之外,其實頗為侈費。朱元璋不是這樣,他的節儉,不是為“垂范天下”做做樣子,是窮慣了,是“積習難改”。
炎夏之日他在東閣臨朝,天氣太熱衣裳汗濕,幾次更衣,群臣發現這些衣服都是洗了再洗以致褪色的舊衣。南京宮室初建,負責官員將設計草圖呈見,朱元璋“見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理論是“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斲?”宮殿蓋得差不多了,照例應在梁壁施彩繪畫,還有人建議采用“瑞州文石”(貴重石材)鋪地,統統被他制止,而命儒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以及《大學衍義》等儒經,“書于壁間”。對于自己這一創意,他很得意,說:“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
洪武三年六月,天久不雨,朱元璋親率皇室全體人員到山川壇求雨,一律穿草鞋徒步而至,以草墊為席,露天而坐,白晝承受曝曬,夜晚衣不解帶即席臥于地;用餐由馬皇后率眾妃親手煮制,完全是粗糧做成的“昔日農家之食”,一連三日,才回鑾宮中。這種舉動,假使沒有從小吃苦的底子,縱然有誠心恐怕也頂不下來的。
在朱元璋,“不知奢侈”,未必是覺悟和境界較別的皇帝有多高,可能確因苦出身。打下浙西,朱元璋曾對降軍發表演講:“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潁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樂。”說得很實在。然而跟他出身相類者,畢竟以容易腐化為多,而且腐化的速度和程度往往也最驚人。所以對朱元璋的不腐化,我們還是得“有成分而不唯成分論”,更多看到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一面。太子和公主宮中重新裝飾,需一種叫“青綠”的涂料,工部奏請采辦,朱元璋堅決不答應,說在庫藏里搜羅搜羅,湊合著用就行了,“豈可以粉飾之故而重擾民乎?”一次,在奉天門附近他看見某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叫過來,問這身衣服花了多少錢,回答說“五百貫”,朱元璋聽罷大為惱火,斥道:農夫如何艱辛,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你游手好閑,不過仗著“父兄之庇”,如此驕奢,“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民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劉姥姥在大觀園里說過,賈府一頓飯花的錢,夠鄉下人過一年的。朱皇帝看到京城闊少的衣著,反應和換算方式竟與劉姥姥一般無二,也真是千古奇聞了。
這“劉姥姥的視角”,讓他有時會冒出對皇帝來說顯得古怪精靈的念頭。南京宮殿新成之際,朱元璋忽然把中書省大臣們找去,說多年戰爭令軍中許多兵士負傷致殘,失去工作能力,現在新宮建成,他打算在宮墻周圍的空地建上房屋,讓這些軍中致殘者居住,“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國家撥一定口糧,以這種方式把他們養起來。后來,他又專門降旨,指出所有戰場上犧牲者,其妻、子或老人一律由官方“月給衣糧賑贍之”,而老邁兵卒則“聽令于應天府近便居止……所給衣糧,悉如其舊”。洪武十九年,河南大饑,不少人家賣兒鬻女;朱元璋得到報告以后,不僅下令賑饑,而且決定所有被出賣的孩子一律由官府出資贖回。同年六月,他進而頒行兩項可能當時整個世界上都很少有的福利政策:一、所有年屆八十以上的窮人,官方“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年九十以上者,在此基礎上每人每年“加帛一匹,絮一斤”;二、“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歲給米六石”。他這樣闡釋他的政策:“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說起來,精神高度似乎并沒有超出儒家“民本”那一套,但實際做法是他的獨創。
晚年朱元璋,面對諸皇子,曾就自己是怎樣一個皇帝,親口做出如下自我鑒定:
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瞽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眾議,參決可否,惟善是從。若燕閑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茍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這份自我鑒定書,中間一段即“稽于眾議……惟善是從”云云,我們或有異議,但一頭一尾,則可說確無夸飾之處。在位三十一年,朱元璋不玩、不溺,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而回;白天所決事務,退朝后還要默坐審思,如感覺有不當者,雖中夜而不寐,必籌慮停當方肯就寢,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要說此人的為人,幾無一點閑情逸致,過去是苦孩子,當了皇帝也是個苦皇帝。
一朝權在手
然而世間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我們素日常見到看門人最珍視手中那點權力,也最善于把那點權力用到極致。我們也屢屢感到,權力越到底層,就看得越緊、用得越狠,絕不容人覬覦。這并不難解。對權力的過度珍惜,是與身處底層所得來和形成的更大的人身恐懼互為因果的。這種恐懼,令人一旦攫取了權力便會以近乎病態的方式捍衛之死守之。試想,當一個備受欺凌與屈辱的孤兒,一步登天成為皇帝的時候,能意味著什么?
有關中國古代帝權,之所以在明代——主要是通過朱元璋之手——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自會有他們種種理論和邏輯上的條分縷析,拿出種種所謂“必然”的論述來。對此,我這里不置一詞,只想說說個人因素起到的作用。
吳晗《朱元璋傳》講了朱元璋幼年和少年時的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朱元璋很小的時候:“替田主看牛放羊,最會出主意鬧著玩,別的同年紀甚至大幾歲的孩子都聽他使喚。最常玩的游戲是裝皇帝,你看,雖然光著腳,一身藍布短衣褲全是窟窿補丁,破爛不堪,他卻會把棕梠葉子撕成絲絲,扎在嘴上作胡須,找一塊破水車板頂在頭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讓孩子們一行行,一排排,必恭必敬,整整齊齊三跪九叩頭,同聲喊萬歲。”
第二個故事,講的是成為孤兒后的他,在皇覺寺中的遭遇:“(寺里)個個都是長輩,是主人,就數他小、賤,他得低聲下氣,成天賠笑臉侍候。就連打水煮飯的長工,也還比小行童高一頭,當他做二把手,支使著做這做那。這樣一來,元璋不單是高彬長老一家子的小廝,還帶著做全寺僧眾的雜役,根本就是長工、打雜了。事情多,閑報也就多,日子長了,塞滿一肚子冤枉氣,時刻要發作,卻使勁按住,為的是吃飯要緊……對活人發作不了,有氣無處出,只好對泥菩薩發作了。有一天,掃佛殿掃累了,掃到伽藍殿,已是滿肚子的氣,不留神絆著伽藍神的石座,跌了一大跤,氣忿之極,順手就用笤帚使勁打了伽藍神一頓。又一天,大殿上供的大紅蠟燭給老鼠啃壞了,長老數說了元璋一頓。元璋想伽藍神是管殿宇的,當看家菩薩的不管老鼠,卻害行童挨罵,新仇舊恨,越想越氣,向師兄討了管筆,在伽藍神背上寫了‘發配三千里’,罰菩薩到三千里外充軍。”
雖是兩個小故事,還是見出了朱元璋的個性和內心。一是他很有暴力傾向。二是他如果有怨氣,喜歡發泄也非發泄不可,對活人發作不了,就拿泥菩薩出氣。三是他那小小腦袋所想出的報復手段,居然已是充軍、流放這類方式。
看過朱元璋畫像[19]的人,恐怕很難忘記那張臉。《明史·本紀第一》形容是“姿貌雄杰,奇骨貫頂”。文人虛浮,丑怪駭人到了他們嘴里竟能轉變成這些詞。實際上,這張臉長得崎嶇不平,形狀活似一只長歪的山芋;黑而粗糙的皮膚散著幾粒麻子,額頭和太陽穴高高隆起,顴骨突出,大鼻、大耳、粗眉毛,兩睛鼓凸,發出冷酷的光;尤為奇崛的是他的下巴——從寬大有力的頜骨處開始向前突著,一再延伸,直到遠遠超出額頭之外,從側面看渾如一頭狠霸的大猩猩。這只罕見的下巴,再度提示了人來于動物的遙遠往事;它象征著健壯的咀嚼力和貪婪旺碩的食欲,令人聯想起獸界一切善于撕咬吞噬的兇猛捕食者。
同時不可忽視的是,這張“卡西莫多式”丑臉跟一個身為皇帝的人相結合,在心理上所必然引起的沖突。這并非出于無稽的相面學。據說先后有兩位替朱元璋造像的畫師,因為只知摹形繪影不解粉飾遮掩而掉了腦袋,直到第三個畫師,才仰體圣心,把他畫得慈祥仁愛。這是人之常情。對朱元璋來說,那崎嶇不平的相貌固然“雄杰”,但無疑也鐫刻著他卑低坎坷的出身、遭際,盡管貴為人君,歲月的無情雖可從宮庭畫師筆下抹去,卻無法從自己臉上和內心世界抹去。
前文提到孟森先生關于朱元璋“峻法”的評論,說他“約束勛貴官吏極嚴,實未嘗濫及平民”。這是孟先生的敏銳細膩之處。展開下文以前,我重申孟先生的這個觀點,再次強調不宜以“暴君”視朱元璋。暴君根本標志是虐世害民,只有與人民為敵者,才配此稱號。而朱元璋,不論在權力斗爭中多么殘忍,整體來說他不是禍害人民的皇帝,相反,歷來新朝新君喜歡掛在嘴上、口惠而實不至的“與民休息”,在朱元璋那里卻是其治政的切實出發點。洪武年間清丈土地,興修水利,獎勵農耕,減免賦稅,殺減貪風,改良吏治,老百姓都得利受惠。我覺得他尤其應被稱道的,是不好大喜功、不靡耗國力、不浪費民財,無意于什么雄才大略、豐功偉績、萬邦膜拜等虛榮。這些對中國那些所謂“有作為帝王”,從來是無法抵擋的誘惑,然而終洪武朝三十一年,在朱元璋的身上,我們絲毫未見這種自我膨脹,盡管作為“光復中華”的帝王,他似乎很有理由膨脹一番。他牢牢把握一點:不擾民、讓百姓安穩地生活。所以,當我們回味洪武時代,會驚訝于它非常平淡——沒有奇跡壯舉,沒有偉大工程,沒有征伐,沒有任何波瀾壯闊的事情。與許多開國君主相比,他簡直是過于安靜的皇帝。
但對官吏而言,朱元璋搞的真是不折不扣的酷政、暴政。可能中國哪個朝代,做官皆不曾像在洪武朝那樣提心吊膽。這位窮山惡水生養出來的貧民皇帝,把他那個階層的野性、狠勁充分發揮在吏治上,慘無人道地對待貪官污吏,剝皮、斷手、鉤腸、閹割……全是最駭人聽聞的酷刑,而且五花八門、種類繁多。另外我們還知道,幾乎整個古代,中國普通百姓是無權告官的,或者,凡告官者先打一頓殺威棒;然而洪武年間居然宣布,凡是貪贓害民之官,百姓人人皆可將其直接扭送京師。有時候我不禁懷疑,朱元璋如此嚴厲打壓官吏,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肅清吏治目的,又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瘋狂的階級報復”?因他的做法里頭,許多地方令人感到是非理性的、宣泄的,夾雜著強烈個人情緒,是恨,以及伴著毒意的快感。他不是心寬易忘的人,洪武十一年,當憶及父母雙亡、無地可葬的凄慘時刻時,他親筆描畫了使他深受傷害的一幕:“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這記憶,暗中怎樣左右著朱皇帝的心神,如何影響了他為政?
當然,還有比記憶和心理更重要的因素。
徐達,明開國武臣第一,有古大將之風。他的死也很蹊蹺,據說死于朱元璋賜膳之后。此當然不載于正史。
明建國功臣第一,明代制度制訂者,朱元璋曾將他比為漢之蕭何。七十七歲牽胡惟庸案,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