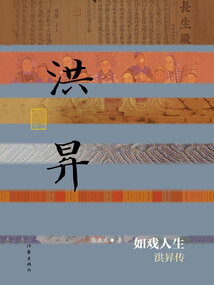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引子:在歷史的夾縫中
一
他孕育于一個王朝的末世,誕生于一個王朝的開端,歷史的后一頁已經掀開,而前一頁還沒有合上,一切仿佛已宿命般注定,當中國歷史又進入了一個劃時代的關口,這個人命定就是一個活在歷史夾縫中的人物。
洪昇,字昉思。如今“昇”字已被簡化,一個古人的名字已被今人篡改。昔人名字相輔,名與字是相互詮釋的,字與名又互為表里,因而稱作“表字”。洪昇之名,如《詩經·小雅》所云“如日之升”,洪昇之字昉思,昉,“日初明”,又可引申為起始、起源。在古人看來,一個人的名字絕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符號,而是命運與命理的象征,甚至是一個生命的全部寄寓。洪昇生于太陽初升、一日復始的辰時,正所謂“朝食”之時,一生下來就有飯吃。按說他還真是生逢其時,然而伴隨他的卻是改朝換代的腥風血雨,如《明史·劉宗周傳》:“兇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當國難當頭、危機四伏,對于那些奮戈而起的抗清志士,連等一餐“朝食”都來不及了。
洪昇的出生年月,在后世的考證中也存在時間錯位問題,如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年表》中將洪昇出生的時間定為順治十六年(1659),劉輝的《洪昇集》校箋中則定為順治十四年(1657),因而造成他《洪昇集》校箋的編年整體失誤。如今學術界已找到確證,洪昇生于清順治二年(1645)七月初一,此說已為學術界公認,再無爭議,也可謂注定。而接下來的歷史雖說已經注定,但在當時尚未塵埃落定。就說那一年該以哪個王朝的年號為正朔,還真是很難說。此前一年為明崇禎十七年(1644),農歷甲申年,這是中國歷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史稱“甲申之難”或“甲申國難”。是年正月,闖王李自成稱帝于西安,國號大順,年號永昌,隨后率大順軍攻陷京師,開進宣府,大明天子崇禎皇帝自經于煤山。天子崩殂,是為“天崩”。若李自成這位大順開國皇帝能在紫禁城的那把龍椅上坐穩江山,一六四五年當為大順永昌二年。然而,中國歷史的周期律在《春秋左氏傳》就已注定,“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隨著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天崩”之后又是“地裂”,李自成這個大順開國皇帝從“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到“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就像開了個歷史玩笑,一把龍椅又落在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的龍臀之下,大順永昌二年一變而為大清順治二年。但那個時年六七歲的小皇帝福臨又能否在這把龍椅上坐穩,無論對于清朝還是朱明,此時還是一個懸念。
那一年為農歷乙酉年,生肖屬雞,屬雞之人在民間也被喻為小鳳凰。看看詩鬼李賀那千古絕唱,“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這又與洪昇的名字不謀而合。屈原曾作楚辭《招魂》,在盛行巫鬼之風的楚地,相傳客死他鄉者的魂魄在迷茫中找不到歸途,其靈魂便成了漂泊在異鄉的迷魂,必須為其招魂:“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這《招魂》到底是誰所作,又是為誰招魂,眾說紛紜,一說是屈子懷沙之意已決,在客死他鄉之前乃自招其魂,一說為其門生宋玉所作,以招屈原之魂,抑或是為在秦國囚禁而死的楚懷王招魂。一句“朱明承夜兮”,仿佛千古讖言,預見了朱明王朝的覆沒,誠然,此朱明非彼朱明,乃是黑夜之后的紅日重放光明。這與當時的形勢卻也高度契合,當朱明社稷傾覆,清朝定鼎燕京,而江南猶存半壁江山,對于當時的江南士子,一如當年秦軍入侵的楚國,確實又到了救亡圖存的招魂時刻,而反清復明幾乎貫穿了一部兩百七十余年的清史。
盡管明崇禎帝已在國破家亡中自經于煤山,但國破山河在,一個王朝尚未在那棵歪脖子樹上吊死,一條龍脈還在江南延伸。這又得益于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所設置的二京制,北京為順天府,南京為應天府,合稱二京府,南京又稱留都,并與北京的明朝廷一樣設有六部等中央機構。當然,從職權而言,二京不可同日而語,北京那才是天子總攬朝綱的帝國中樞,而南京什么都不缺,就缺一個皇帝。當北京的明朝廷覆沒,崇禎皇帝殉國的噩耗傳到江南,留都南京的作用一下凸顯出來了,這邊既然擁有一套現成的中央機構,又有輾轉南下的明宗室及文武大臣,一個留都隨之就能像備胎一樣開始運轉了。他們擁立明神宗朱翊鈞之孫、福王朱由崧(又作朱由嵩)繼承朱明大統,先為監國,旋后登基,而新主登基,必改正朔,一六四四年還是崇禎的年號,一六四五年則改元弘光(弘光元年),史稱南明弘光政權。對于這個沿用大明國號、延續了朱明血統的南明王朝,正史一般不視為正統的王朝,而視之為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權,但在當時,對這個政權還真是不可低估,至少清王朝就絕對沒有低估,并視之為心腹之患。在南明建政之初,還擁有不亞于當年南宋的大半壁江山,而且打出繼承朱明大統、抵御異族入侵的旗號,一時間可謂人心所向,應者云集,何況在南明的旗下還有史可法、鄭成功等一干驍勇善戰的抗清名將,倘若弘光政權能按照史可法等人的意見,盡量讓“正人”占據要津,這個政權即便不能恢復中原,至少有可能再造一個類似于南宋的王朝,而這也正是清廷最擔心的。
然而,朱由崧一開始就對擁立有功的馬士英委以重任,拜為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而弘光政權由這樣一個“為人貪鄙無遠略,復引用大鋮,日事報復,招權罔利”的首輔大臣把持朝政,其“以迄于亡”的宿命已經注定。而另一奸詐之徒阮大鋮得其薦舉,被起用為兵部右侍郎,不久晉升為兵部尚書,弘光帝實際上已被這兩位權奸玩弄于股掌之間。如蔡東藩所云:“這位弘光皇帝,偏信馬士英,一切政務,全然不管,專在女色上用心。”當時,真正在苦苦支撐弘光政權的社稷之臣,則是原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弘光帝先拜其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后又加督師、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率師抗清。又如史可法所言:“在藩不忠不孝,恐難主天下。”由于弘光政權內部的權力紛爭、互相傾軋,又加之地方勢力乘勢崛起,攪得南明江山如一盤散沙。
二
順治二年(1645)三月,清攝政王多爾袞命豫親王多鐸率大軍南征,南明軍民掀起了對南下清兵的第一次抵抗。四月,清兵渡過淮河,攻打兵家必爭之地徐州。徐州總兵李成棟原本為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將領,此人一生反復,先是投降南明,官至總兵,此時又搖身一變降清,變成了清軍將領,引清兵南下,兵臨揚州城下。揚州地處長江與京杭大運河交匯處,素有“淮左名都”之稱,與拱衛南京的京口(今鎮江)隔江相望。若揚州失守,南京則危在旦夕。當清軍以紅衣大炮攻城,駐守揚州的南明兵部尚書、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在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情況下,率揚州軍民孤軍奮戰,戰至人盡矢絕,史可法被清軍俘獲。多鐸幾番勸降,史可法瞋目大呼:“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我頭可斷,而志不可屈!”史可法以不屈而死,時年四十三歲。多鐸為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五子,一生戰功彪炳,乾隆帝稱其為“開國諸王戰功之最”,但此人也以性情暴烈、嗜殺成性而為清“開國諸王之最”。他不但殘忍地殺害了史可法,對這座不屈的揚州城也實施了報復性的大屠殺,他縱兵屠城十日,被殺者數十萬(一說揚州百姓死難八十萬),史稱“揚州十日”。
隨著徐州、揚州相繼陷落,南明江淮防線已處于崩潰的狀態,清軍旋即橫渡長江,攻克鎮江,馬鞭直指南明帝都。眼看一座石頭城岌岌可危,弘光帝拋下一城擁戴他的百姓,溯江而上,逃奔蕪湖。農歷五月十五日,端午節后的第十天,清軍占領幾不設防的南京,一個短命的南明弘光朝廷便遽爾而亡,弘光元年轉眼變成滅亡之年。一切誠如史家之哀嘆,一個“狐鳴虎噬,紀綱倒持”的小朝廷,“卒不能保社稷云”。在占領南京后,清廷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平定江南捷音”,又于六月下令改南京為江南省,應天府為江寧府。但實際上,此時他們滅掉的還只是一個弘光小朝廷,南明政權還遠沒有到滅亡的時候,隨后又相繼建立了多個政權。與此同時,在清軍占據的北方各地,與南方抗清形勢呼應,山東、山西、陜西、甘肅義師紛起,一些此前降清的明朝將領也先后舉旗抗清,這讓天下士人看到了朱明王朝還有東山再起、卷土重來的可能。而南明這個沒多大出息又特別頑強的王朝,從北京明朝廷覆沒一直延續到清康熙元年(1662,南明永歷十六年),隨著南明永歷帝朱由榔與其子等被吳三桂處死于昆明,南明王朝才基本告亡,但永歷的年號一直被退守臺灣的鄭成功政權奉為正朔,直到永歷三十七年(1683)十二月,清軍占領臺灣,監國的寧靖王朱術桂自殺殉國,才標志著南明最后一個政權的覆滅。史載南明共傳四帝一監國(弘光帝、隆武帝、紹武帝、永歷帝、監國明魯王),享國十八年,一說甚至長達四十年,那就包含了奉永歷年號為正朔的臺灣鄭氏政權。它的存在,既是明朝的延續,也是清初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政權在存續期間一直被安南、日本、琉球、呂宋、占城諸國尊為中原正統政權,并派使者入貢,南明政權也一直繼承和延續了對這些附屬國的宗主權,為藩王登基頒發冊封詔書。而即便在它最終覆沒之后,反清復明,一直貫穿了清朝的全部歷史,幾乎所有的反抗都是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進行的。
清廷在以軍事手段打擊南明諸政權和反清義軍的同時,似乎覺察到了什么歷史玄機,于是,又開始施展更陰險的一招,就在順治二年(1645),清廷便下詔纂修《明史》。一個王朝的歷史,往往由下一個王朝來書寫,中國歷史就是這樣一代一代續寫的。而清廷在入關之初、立足未穩之際,便如此急切地纂修《明史》,就是為了提前宣告一個王朝已經滅亡,成為了歷史,不再承認南明政權存在,通過修史而建立起其入主中原的正統地位。此舉,誠如龔自珍所謂:“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順治二年(1645)為平年。在弘光朝廷覆沒后的閏六月,明唐王朱聿鍵于福州詔告天下,即皇帝位,建元隆武,史稱隆武帝。然而他的天下實在太小,號令不出八閩,事實上南明再無統一的中央機構,明宗室在各地文臣武將的擁戴下紛紛自立,先后有潞王朱常淓監國于杭州、益王朱慈炲監國于撫州、靖江王朱亨嘉監國于桂林,桂王朱由榔監國于肇慶,又無論是稱帝,還是宣布監國,對其地盤之外都沒有什么號召力,更無統一掌控的實力。此時南明已是諸侯割據,分崩離析,既無統一號令,也無像樣的軍隊,從隆武帝到各地監國也是徒有虛名,大抵是其擁戴者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當時,江南諸省兵荒馬亂,清軍在攻克南京后的短短幾個月間就占領了江南大半壁江山,南明政權雖大勢已去,但仍有一些南明軍隊與抗清義軍還在與清軍交戰,清軍打到哪里,當地人便紛紛自發抵抗。
六月,從錢塘江的潮汐聲中傳來了由遠而近的鐵蹄聲,清軍越過錢塘江,一座自古繁華的錢塘古城、人間天堂,眼看就要淪為清軍鐵蹄之下的地獄。時在杭州監國的潞王朱常淓一聽鐵蹄之聲,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不思抗清之策,一心只想投降。據史載,六月十三日,朱常淓“遣使迎降,并約滿人襲擊諸營”。這個潞王不僅是獻城投降,還約清軍襲擊駐防杭州的南明守軍,他不只是明朝宗室中投降清軍的第一人,恐怕也是明宗室中投降最徹底、行徑最可恥、最惡劣的第一人。然而,你說他投降叛國,有人卻振振有詞為他分辯,潞王開城門降清,乃是考慮到清軍一向有血腥屠城的習慣,若不投降,杭州生民就會像“揚州十日”一樣遭來屠城的滅頂之災,為此,潞王從杭州一城的百姓考慮,只得忍辱負重“遣使迎降”,此乃大義之舉、菩薩心腸,結果是保全了一座杭州城,也讓一城百姓免遭生靈涂炭。而杭人感恩,因此尊稱潞王為“潞佛”。歷來總有人為這種投降派找到歷史的情理邏輯,乍一看,此說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仔細一想,如果這就是投降的理由,一旦外族入侵、大敵當前,凡守土保境者皆可以此為借口,打開城門投降。而像潞王這樣向侵略者投降乃是大義之舉,那么像史可法那樣抵抗侵略者的反倒是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了,這就是從所謂情理邏輯推出一個荒誕的歷史邏輯,那歷史還有正義的底線嗎?
當時,很多江南士民都死死地堅守著一條正義的底線,如此前提及的劉宗周。宗周字起東,明崇禎年間曾任順天府尹、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職,他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學大師,開創了在中國思想史特別是儒學史上影響深遠的蕺山學派,清初大儒黃宗羲等就是這一學派的傳人。他以“慎獨”為學問的第一義,然而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他也走出書齋為南明中興出謀劃策。當他在“朝食”之時聽到潞王獻城投降的消息,“兇問已確”,絕望得大放悲聲,又云:“此予正命時也!”一個絕望的大儒,最終以絕食近二十天而逝。說來,洪昇還與劉宗周有間接的師承關系,洪昇后來的師執毛先舒曾師事劉宗周。劉宗周絕食而死后,后世有論者說,中華民族的命脈和中華文化的命脈都發生了危機,這一危機延續至今。
若不正視這一段歷史,就難以追尋那些夾在歷史縫隙里的個人命運,還有那一代漢族士人復雜而微妙的心理。而清廷對那一代漢族士人也采取了無所不在的強勢逼迫,清軍每攻占一地,一邊著手建立地方政權,一邊以鐵血手段逼迫漢民“剃發易服”,十天之內,江南人民一律剃頭。何止江南,連孔夫子的后裔也難逃此劫。如孔子六十二代孫孔聞謤上疏請求蓄發,疏曰:“臣家服制,歷三千余年未改,請準蓄發,以復先世衣冠。”多爾袞得疏大怒,立即下旨斥責:“剃發嚴旨,違者不赦。孔聞謤竟敢疏請蓄發,已犯不赦之條,本當從重治罪,但念其為孔圣人后裔免死革職,永不敘用。”清廷亦視孔子為圣人,但在剃發易服上絕無條件可講,沒有特殊照顧。在清廷看來,清人入主中原,一切必須首崇滿洲,而“剃發易服”則是其他民族歸順滿洲的標志,被清廷稱之為“剃發降我之民”。又據劉宗周的門生陳確在《告先府君文》所云:“去秋新令:不剃發者以違制論斬。令發后,吏诇不剃發者至軍門,朝至朝斬,夕至夕斬。”不能不說,清廷這一招既是絕殺,也是絕招,一場從腦袋到身體的改變,雖不足以讓漢民心悅誠服地接受其統治,但可以在精神上沉重打擊和摧垮漢民族尤其是漢族士人、士大夫的文化自信,又可以保持滿族不被人口占多數的漢族所同化。而這一帶有強烈民族征服性質的命令,對于漢民族確是最沉痛的打擊。一個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民族,打心眼里就對“夷狄”充滿了蔑視,在漢人眼中滿洲人也是茹毛飲血的野蠻人,蔑稱其為韃虜或韃子,他們又怎么甘心把自己變成韃虜、韃子那野蠻落后的形象呢?一時間,抗清浪潮風起云涌,而江南人民反抗“剃發易服”甚至比反抗清朝入侵還要激烈和頑強。此時已“剃發易服”的南明降臣錢謙益等向多鐸獻策曰:“吳下民風柔弱,飛檄可定,無須用兵。”然而,無論是降臣錢謙益,還是清軍南征統帥多鐸,都大大低估了江南士民反抗的意志。
當時,南直隸常州府江陰縣發出了這樣的告示:“豈意剃發一令,大拂人心,是以鄉城耆老,誓死不從。”自北京明朝廷覆沒后,江陰秀才許用每天都到文廟明倫堂叩拜明太祖朱元璋遺像,聞聽剃發令,他挺身疾呼:“頭可斷,發決不可剃!”一時間,江陰士民“奮袂而起”,推舉江陰典史閻應元為守城主將。典史掌一縣刑獄,此前曾有江盜船只百艘突襲江陰,閻應元橫刀立馬,振臂一呼:“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而此次守城,他又與陳明遇、馮厚敦等率十萬義民,面對二十四萬清軍鐵騎,兩百余門重炮,作殊死之戰,致使清軍連折“七王”“薛王”和“十王”等三王,還折損了十八位大將,清兵戰死共七萬五千人。從閏六月初一至中秋節,江陰義民困守孤城八十一天,史稱“江陰八十一日”,又稱乙酉守城戰。這是江陰士民創造的一個歷史奇跡。不僅是清軍低估了江陰百姓堅守抗清的意志,連清軍的紅衣大炮都低估了這座眾志成城的江陰古城。城破之日,閻應元被俘后拒不向清貝勒下跪,被刺穿脛骨,“血涌沸而仆”。乾隆年間,一位宋朝宗室后裔、詩人趙翼追懷這悲壯的堅守,對閻應元發出了這樣的贊嘆:“何哉節烈奇男子,乃出區區一典史。”除了以身殉國的閻應元,清軍對江陰百姓更是大開殺戒,“滿城殺盡,然后封刀”,而“義民無一降者,幸存者僅老幼五十三口”。江陰由此而被譽為“義城”。南明隆武皇帝聞之曰:“吾家子孫即遇此縣之人,雖三尺童子亦當憐而敬之。”而當清朝江山鞏固,清廷對這些殉國者亦予以旌表,后來乾隆帝追謚江陰抗清三公,閻應元謚“忠烈”,陳明遇謚“烈愍”,馮厚敦謚“節愍”。歷史還留下了閻應元在最后關頭所書的一副對聯:“八十日戴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誠如后世如是嘆惋:“有明之季,士林無羞惡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為得意;而封疆大帥,無不反戈內向。獨閻、陳二典史乃于一城見義。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至拱手獻人矣。”
從更遼闊的視域看,這種“誓死不從”的抗爭一直持續到南明王朝最終覆沒。
三
那么,當時杭州的情形又如何呢?據《仁和縣志》(轉引自章培恒《洪昇年譜》)載:“乙酉端陽日,群言藉藉,知大兵(清兵)已下金陵,弘光帝出走。至六月初旬,遣兵至浙,領兵者為貝勒王,為撫軍張存仁。先期,合城士民畏兵如虎,紛紛保抱,攜厥婦子,四鄉逃避。或渡江而東,或藏匿外縣之深山。流離辛苦,溽暑炎蒸,霍亂瘧痢,受病非一。而伏戎于莽,先遭荼毒者有之。大兵到日,在城居民閉戶不敢出窺。逾三日,令出,有所約法。居民乃稍稍安。然人情惶惑,每日數驚。當事皆望風解印綬去。錢塘令顧咸建初繳冊印,以保全士庶為心,授之以官,堅不受,斬之于白馬廟前,士民流涕。”
這當是逼近歷史真相的記載,其中提到了三個人物:一個是參加了江陰攻城和屠城的貝勒博洛,為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孫、清初理政三王之一。隨豫親王多鐸南下,順治三年(1646)任征南大將軍,率師駐守杭州。《清史稿》謂其“國初開創,櫛風沐雨,以百戰定天下,系諸王是庸”。一個是撫軍張存仁,遼陽人,原是明朝副將,后叛明降清,隸漢軍鑲藍旗。清軍入關前,他曾致信招降吳三桂。入關后,從征山西、河南、江南。順治二年(1645),張存仁隨貝勒博洛平定浙江,并擔任浙江總督。他上疏朝廷,“近有借口剃發,反順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處處勞大兵剿捕。竊思不勞兵之法,莫若速遣提學,開科取士,則讀書者有出仕之望,而從逆之念自息”。此外,他還提出了興辦學堂、減免賦稅等一系列主張,對安撫浙江、鞏固清廷對浙江的統治無疑有積極意義,清廷亦認為他的建議乃是安民急務,命各行省照此推行。但與此同時,他對反清勢力,包括那些不愿“剃發易服”者、“未盡馴服”者,絕不心慈手軟,亦如多鐸、博洛等清朝王公一樣大開殺戒,“以此伏法者不可數紀”。
另一個人物則是錢塘令顧咸建,字漢石,南直隸蘇州府昆山人,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授錢塘知縣。當清軍兵臨錢塘,潞王朱常淓、巡撫張秉貞皆降清。顧咸建在反復考慮后繳出縣印,“我不納印,累錢塘一縣百姓矣”!回到縣衙,即欲掛冠而去,有人告知貝勒王博洛:“錢塘令,潞王所與深謀者也。其人才望素著,且大得民心,宜亟用之;否則,亟殺之。”博洛一聽此言,旋即命快馬追上顧咸建。咸建自知不免一死,曰:“往而死,職也!”他衣冠整齊地去見博洛,博洛一見他就站起身,握著他的手,授之以官。咸建聲色甚厲:“愿早賜一死!”博洛不忍殺他,將他關押在獄中。咸建依然穿著一身整齊的明朝衣冠,端坐獄中,并書于案閱:“國不可負,親不可辱!吾文康公孫、汪夫子門人,若茍偷視息,所失多矣,如所學、所志何!”——所云“吾文康公孫”,咸建曾祖顧鼎臣為明弘治十八年(1505)狀元,屢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謚文康;所云“汪夫子門人”,咸建曾入汪喬年門下。汪喬年,字歲星,世稱汪夫子,浙江嚴州府遂安縣人,崇禎朝官至陜西總督。崇禎十五年(1642)二月,李自成部攻打襄城,汪喬年率師堅守城池,在城陷后自刎未遂而被俘。據《汪公忠烈祠墓記》:“左右喝令公跪,公大罵曰:‘吾朝廷大臣,奉命剿汝,恨不獲生咬汝肉。吾死當為厲鬼殺汝,以遂我報國之愿。’賊知不可屈,遂割公舌,擊公齒,猶以血噴賊,罵不絕口,隨遇害磔公尸。”咸建乃以此明志也。博洛見其寧死不屈,此人既不能為清朝所用,那還留著何用!顧咸建“乃與同縶者四人就刑朝天門”,那天是六月二十日,顧咸建被擁至鎮海樓,百姓男女遮道慟哭,一條路都走不通了。連劊子手都哭了,不忍加刑。咸建看著劊子手說:“我暴烈日下,渴甚,早一刻受一刻之賜!”劊子手揮淚斫之。清軍“以咸建及四人頭梟示鎮海樓上。百姓祭奠者日數千人,燒楮幣者如山積。十日夜,面猶如生。余首蠅蚋攢集,而咸建面無一蠅。觀者駭異,百姓哀號請命”。連博洛也嘖嘖贊嘆:“好官也!”命收葬之。
在歷史的夾縫中,每個人物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其各自的角色,而一個將要被命名為洪昇的胎兒,此時正在母腹里茁壯成長。倘若不是遭逢這兵荒馬亂的世道,他原本可以在那個“世代簪纓”“累葉清華”的鐘鳴鼎食之家靜靜地等待著降生。然而,他和一個民族的命運皆已注定,在經歷了天崩地裂的“甲申之難”后,中國命定還要經受血雨腥風的“乙酉之難”。清兵占領杭州,一座人間天堂已如世界末日一般。又如《仁和縣志》載:“當時上下不通,兵民未和,往往有意外虞……已而下剃頭之令,一時未盡馴服。以此伏法者不可數紀。”
歷史不可假設,但人心可以猜度,猜測洪起鮫此時的心境,作為一個“累葉清華”的世家子弟,從小深受孔孟之道、儒家思想之浸染,“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這是中國士子千古不易之信仰。洪起鮫雖說不是那種直接投身于抗清戰爭中的報國書生,但他不會輕易拋棄自己的信仰,他選擇的是攜家帶口東躲西藏,一是躲避戰亂,一是逃避“剃發易服”的劫數。當他們在驚恐慌亂的人群中奪路而逃時,清兵也正在追捕那些逃難者,一個聲音特別強大:“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
有的人已經被清兵抓住了,清兵使勁摁住他們的腦袋,把頭給剃了,而稍有掙扎便要付出慘痛的代價,那剃得像葫蘆瓢一樣的腦門上滿是血印子,辮子上沾滿了血跡。若敢反抗,“唰”的便是一刀。當一個讀書人的腦袋連同頭發被韃虜的快刀齊脖梗斬下,洪起鮫的眼睛一下就紅了。那何止是血濺三尺,血珠子飛濺出一丈來遠。洪起鮫眼看著躲避不及,被他夫人使勁一拽,一下便鉆進了亂哄哄的人堆里。當時,杭州城門口人山人海,誰都想要奪路而逃。一家人好半天才拼命鉆出來,當他們在滾滾人流中重新出現時,已經逃到了杭州的荒郊野嶺。眼下,洪昇還在他母親黃氏的肚子里孕育,這也是他的宿命,還在娘胎里就開始顛沛流離。看黃氏那突出的大肚子,很快就要生了,這也是她特別急切的原因,她必須趕緊找到一個生孩子的地方,而洪起鮫好像只關心后邊。他一邊跑一邊頻頻回首,看看有沒有清兵追上來,還要扭轉身子看自己的背后,但無論他怎么努力地扭轉身子,那背后的東西還是看不見。“呃,我背后有血沒有?”他問黃氏。這句話,他一路上已不知問過多少遍了。
當時杭州郊外的荊山就是他們的避難地,如今荊山翠谷已是杭州的一片別墅區,而當年還是荊棘叢生的荒茅野嶺,逃到這里已是山窮水盡,無路可逃了。又正值三伏天,江南的天氣潮濕悶熱,上有烈日暴曬,下有暑氣蒸騰,整個人就像在燒開鍋的蒸籠上蒸一樣。不要說一個養尊處優的書生受不了,想想一個即將臨盆的孕婦和她腹中的胎兒,該有多么難受。一個胎兒沒有胎死腹中,真是命大了,這個小生命也真是特別頑強。而在那條逃難的生死路上,一個丈夫,一個父親,眼看著夫人那突出的大肚子,又該怎樣焦急萬分——當務之急,就是趕緊找一個生孩子的地方。
那個結果已經注定,在一位偉大的劇作家注定要誕生的那個“赤日黃云”的早晨,一個受難的母親在一個費姓農婦家的茅棚中生下了一個亂世中的嬰兒。那破屋覆茅的房子,沒有一堵完整的墻壁,山中哀猿亂啼,洪昇落生的那張床是一塊粗糙的木門板,遮擋山風的門就是一副竹席。洪昇出生時,父母親想給他找一塊包裹身體的破布都找不到,而一個饑餓的母親也沒奶水喂他。他呱呱的啼哭聲,也讓父母親驚恐萬狀,當時,在那荒野的溪流聲中不時傳來清兵的金鼓聲,而在夜間的鬼火青青中甚至能看見清兵的獵獵飄舞的大旗。洪昇出生后,一家人在此山中躲藏了一個月,夜里稍有點風吹草動,一家人就如驚弓之鳥,抱起孩子便驚慌而逃,有時候一夜里就要在荒山野嶺中逃兩三回。這一個月,也不知一家人是怎么熬過來的,而洪昇的母親一輩子也忘不了。洪昇小時候,母親時常給他講起這血淚交織的一幕幕,想來也真是悲苦,錢塘洪氏子孫,原本是“門皆賜第,家有珥貂,三洪學士之世胄”,可洪昇竟然降生在這樣一戶農家里。如果不是洪母后來對洪昇“夙昔為余道其苦”,又如果不是洪昇以詩歌的方式把這一切呈現出來,這一幕幕幾乎不像是真的發生了。二十四年后,康熙八年(1669),洪昇已入讀北京國子監,在自己生日那天,他傷感地抬起眼睛仿佛默默地凝望著被陽光穿透了的江南,杭州,荊山,而母親講述的那一幕幕,又一下涌上了他的心頭,他的眼前,他的生日就是母親的受難日啊!一首《燕京客舍生日懷母作》,仿佛就在愛與受難中誕生:
母氏懷妊值亂離,夙昔為余道其苦:
一夜荒山幾度奔,哀猿亂啼月未午。
鬼火青青照大旗,溪風颯颯喧金鼓。
費家田婦留我居,破屋覆茅少完堵。
板扉作床席作門,赤日黃云梁上吐。
是時生汝啼呱呱,欲衣無裳食無乳。
亂余彌月還郡城,門卒持戈猛如虎。
見汝含笑思攫之,口不能言愴心腑。
……
此詩我只是截取了與洪昇誕生直接有關的一部分,還有一個開頭和下文,容后交代。我在此描述,實際上是對這首詩的復寫,我甚至覺得這首詩讓洪昇重新誕生了一次,讓后世得以洞察那歷史夾縫中的一幕。而在這一幕的背后還有更殘忍的一幕。說來也許是巧合,就在洪昇降生的那天,由于嘉定(今上海嘉定區)紳民對“剃發易服”誓死不從,明南京兵部主事侯峒曾等嘉定士紳率十三萬紳民起義反清,那個叛明降清的李成棟此時已任吳淞總兵,他火速率軍鎮壓,并連續三次下令對城中平民進行大屠殺,這是繼“揚州十日”之后發生的又一血腥殘暴的大屠殺,史稱“嘉定三屠”。從歷史的本質上說,這當然也是清軍犯下的罪孽,李成棟此時的身份已是清軍將領,他手下的兵馬也是清軍。然而對漢民族進行血腥鎮壓的劊子手,往往又是李成棟這種反復無常、喪心病狂的“貳臣”。不能不說,這次慘案對江南紳民產生了極大的震懾作用,也讓許多拒不從命者最終接受了那難以改變的命運,洪起鮫無疑是其中之一。
這首詩的末后四句,則交代了洪昇滿月回家時所遭遇的驚險一幕,一個生不逢時的嬰兒,在滿月后才得以隨同逃難的一家人回杭州城。在走近城門時,又發生了驚險的一幕,那守門的清兵手持寒光閃爍的金戈,一個個兇猛如虎,而剛剛滿月的洪昇還在天真無邪地笑著呢,那清兵一下盯上了他,他險些就被清兵給攫走了,“見汝含笑思攫之”。還好,有驚無險,清兵沒有攫走洪昇,否則,誰也不知洪昇會落入怎樣一種命運。有人說,在一個錯亂的時代,洪昇一生多舛的命運從此就注定了。不說注定,至少是從此開始了。對于洪昇這樣一個個體生命,這的確是一次宿命的誕生,而對于中國戲曲史乃至文學史,這又是一次偉大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