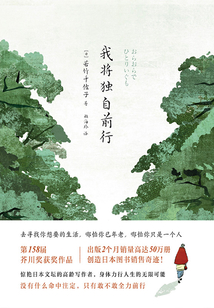
我將獨自前行
最新章節
書友吧 9評論第1章
哎呀,我這腦袋瓜兒出了啥問題?
這可咋辦,從今往后我這一個人,叫我咋辦?
咋辦咋辦?可不就該咋辦咋辦。
多大點事兒啊?有我在呢。你和我,到最后都拴一塊兒。
哎呀,你到底是誰啊?
那還用問啊?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啊。
桃子一個人坐那兒“咻咻”地啜茶,聽著一連串好像大壩決堤一樣奔騰而來的東北方言。這些聲音從她的身體里面不斷向外涌現。
除了大腦里傾瀉不止的對話聲,桃子背后還傳來輕微的聲音,窸窸窣窣地響動。
在這寂靜的房間里,即使是微小的聲音,聽上去也清晰得震耳。
這聲音從桃子的肩膀后面傳過來,離椅背不遠,正好從冰箱和碗柜中間那一帶發出,像超市塑料袋被撥弄著的聲響,聽著刺耳,令人不快。
窸窸窣窣,窸窸窣窣。
然而桃子毫不理會,還和著那聲音啜茶。
桃子不用回頭就知道聲音來源是什么——老鼠。
去年秋天,桃子養了16年的老狗告別了這個世界,從那以后,別說天花板上和地板下頭了,老鼠竟然與桃子在同一個生活平面上出沒起來,就像今天這樣,大白天的就出來了。雖說老鼠不至于大搖大擺,大概還保有一些對桃子的客氣,但依然聽得出來它對于發出聲音有著明確的信念。老鼠從屋子角落地板上的一個破洞進出,又是啃又是撓,發出各種聲音。雖說桃子不夠膽量放眼望向那洞口,但對于老鼠弄出來的聲音,聽著聽著竟習慣了。要知道,這屋子里除了桃子就沒有其他人,所以無論什么聲響都顯得寶貴。桃子對老鼠也曾十分厭煩,如今,比起那個,她更怕沒有任何聲音的屋子里那無邊的寂靜。
桃子捧著茶杯,在手里轉一圈,啜一口,感覺到交叉的手指被茶杯溫暖著,啜一口,再啜一口,百無聊賴地看了看自己的手,那一看就知道是久經勞作的手。童年時,桃子曾撫摩奶奶的手背,摩挲著,擰著,她那蓋在青筋突出的手背上的皮膚,皮實得驚人,揪著它拖起來老長,奶奶竟說不疼。那只骨節寬大的粗糙的手啊,此刻就在眼前。桃子沒想到會有這么一天,她不由得對著天花板發出了嘆息,目光散漫地將這一成不變的屋子看了一圈。
這是一間老屋子,一切都已老舊得仿佛經過了熬煮,呈焦糖色。
南面朝著小院,窗子是紙糊的,窗前,從左邊墻上到右邊墻上牽著一根晾衣繩子,上頭掛著半袖連衣裙和冬天的大衣,罩在衣裳外頭的洗衣店的塑料袋都沒拆掉,還有浴巾和看上去像是剛脫下就被隨便搭上去的裙子,拉鏈那里歪歪扭扭的。再往旁邊,掛著四串柿餅,再過去一點是綁著草繩的半邊兒鮭魚,在這沒風的屋里,不知是因懸掛位置不平衡,還是怎的,那鮭魚不停地晃悠。三月午后淺淺的陽光,穿過這些掛著的衣物照進屋里。
西面靠墻的是舊衣柜、佛龕、碗柜。碗柜的玻璃門裂了,用膠布粘著,那粘補的痕跡就像蜘蛛網。旁邊冰箱門上有貼紙的殘痕,一看就是孩子小時候粘上去的貼紙,后來想撕下,撕下了一半,另一半還殘留在冰箱上。
靠東墻擺著一張簡陋的行軍床,床頭有扇凸窗,窗臺上擱著一臺電視機,電線像纏頭布一樣裹在電視機上頭,旁邊是一塑料袋橘子,開過口的一升裝日本酒,插在空罐頭瓶里的筆、剪刀、糨糊,還有面挺大的鏡子。
傷痕累累的地板上堆積著舊書、舊雜志之類的東西。屋子北面是水池,旁邊堆著鍋碗瓢盆。現在桃子支著胳膊坐在四人用餐桌前,剛才她用胳膊掃開了桌面上的雜物,勉強開拓出了放茶壺、茶杯和日式煎餅的一小塊空間。別說桌面上其他部分都堆得如小山了,就連椅子,其他三把也都化身為堆雜貨的地方。
雖說雜亂,卻也營造出一種氛圍,可以說是混亂中自有秩序,也可以說是終極務實,總之衣、食、住三件事都能在這屋子里完成,相當實用主義。能否感受到這種氛圍就要看個人了。當然,這個家里并不只有這么一間屋子,旁邊還有一間可稱為客廳的地方,很久以前這里就變為了倉庫,所以這個家里的可用空間只有二樓的睡房和這間桃子的起居室,而且有時桃子覺得上二樓都嫌麻煩,三天里頭總有一天吧,她穿著膝蓋部分已磨出洞的運動衣套裝,喊著“穿啥睡覺不是睡?在哪兒睡覺不是睡?”就爬上了行軍床。
桃子仍舊在啜茶,背后的聲響如故。
咻咻,窸窸窣窣。
咻,窸窸窣窣。
咻咻窣窣。咻咻窣窣。
與此同時,桃子的大腦里——
“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
這些聲音內外夾攻,有時在碰撞,有時是和音,倒像一曲爵士樂了。這么說,倒不是因為桃子有多懂爵士,桃子對于音樂方面的事一竅不通,但對爵士卻情有獨鐘,或者說單方面認為爵士于己有恩。
桃子曾經很悲傷,雖然這悲傷是世間常有的一種悲傷,但于桃子而言卻是巨大的沖擊。那日那刻,就在桃子悲傷得雙肩抖動時,收音機里傳出爵士樂。桃子無法接受已經有歌詞的曲子,古典音樂則讓她的悲傷更深重。就在那悲傷中她聽到了爵士樂。至今她也不知那是誰的曲子以及叫什么名字,但是在因悲傷而撕扯欲裂的腦海里,那曲子仿佛在一下一下地敲擊。
緊緊包裹在身體里、大腦里的悲傷被敲得跳出來了。
桃子的手自然地動了起來,腳也在地板上踏起來,她扭動著腰肢,就像瘋了一樣晃動著身體。爵士的律動與桃子的扭動相呼應,成了毫無章法的桃子亂舞。可是桃子感受到了輕松。那是一個大雨天,從雨搭的縫隙間,光線直直地穿過紙窗透進來。桃子竭力晃動著身體,熱得呼吸困難。她一件一件脫去衣裳,在簇新的佛龕前,赤裸地舞動——桃子不會忘記那天。
在桃子的家鄉,一般不說“釋放出去”,而說“放出去”,“釋”聽上去有點文弱,“放”的發音讓人感受到意志和力量。那天,即使只是短暫的一刻,但桃子將悲傷“放出去”了。那天的爵士樂令桃子感恩。當時的桃子謹小慎微,若是如今,桃子會呵斥那時卑躬屈膝的自己。那天應該將收音機音量調得更大,那天應該將雨搭收起,在光天化日下大膽舞動。
可是啊。
如今聽到爵士樂,她的身體卻不會像那天一樣自然舞動起來,最多也就是捧著茶杯的左手食指略微抖動——可真不想將這也算在年齡的頭上啊。
而此刻她腦子里的話題并非爵士樂,那到底是在說些什么?
桃子腦子里亂亂的,她感覺自己似乎本來是要思考什么事兒的,可是想不起來。
桃子其實早已察覺自己的思緒會飛散。毫無脈絡的思緒忽而這邊、忽而那邊,根本把握不住。
“是因為年紀吧?哎呀,這可不好,可別什么都怨年紀。”
“那,該怨啥啊?有了,怨長年累月的主婦生活。”
“什么?長年累月一成不變的日子怎么就讓人思緒飛散了?”
漸漸地,桃子的心里出現了各種問答,體內各處也展開了忙不迭的有問有答。性別不詳、年齡不詳,就連用的語言也不一樣,更別提聲音了。如今桃子身體倒是不舞動了,或者說正因為身體不舞動,所以倒像是要填補這一空白似的,這陣子桃子心里的聲音越來越自在舒展。
有個一本正經的聲音在說:“主婦的家務活兒又細又雜,這也得干,那也得干。”
“那你倒是舉個例子啊?”這個聲音聽上去挺不耐煩。
“和一整天都在砍柴的與作(譯者注:《與作》是1978年日本歌手北島三郎演唱的歌曲,描述男人砍柴、女人織布的生活)可不一樣。”一個聲音說。
另一個聲音說:“這個例子夠過時的。”
“媳婦在家也織布來著。”
“那也不會像與作砍柴那樣一整天都在織布吧。要想著娃該哭了要喂奶了,要想著老婆婆可能又尿臟褲子得給換了,還要想著晚飯做啥菜。就這么雜七雜八啥都得干,那思緒紛亂飛散也是沒辦法的事兒。”
“你這么想啊,可我想的不一樣。”
“雖說千頭萬緒讓你腦子亂,可從年齡來說啊,現在可能是認真思考的最佳也是最后的機會了。還有幾年?維持現狀你還能活幾年?從現在起,凡事都要按照倒計時那樣來盤算了。”
“說得是說得是,是那么回事。啊,不是。”
各種聲音交叉來回。
“我想整明白這么多東北話是咋回事?”一個比其他嗓門都大的聲音說道。
桃子對這句話也很認同。她終于發現,在那雜亂無序紛至沓來的話題中,“東北話”才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桃子陷入沉思,為何如今突然要考慮“東北話”。自從滿24歲那年離開家鄉,已經過去了50年。無論是日常會話還是內心思考,桃子都用的是普通話。可是現在,濃濃東北味兒的話語在心里泛濫,甚至不知從何時起,想事兒也用起了東北話。晚上整點兒啥吃?我到底是誰?無論是吃喝拉撒的俗事還是形而上的疑問,這陣子用的全都是東北方言!或者說,在內心深處有人在對我說東北話,而且還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大堆人。我現在的思考,就靠這一大堆人的對話才得以維系。我都不知道那些想法能不能算是我的。它們千真萬確來自我的內心,說的人、聽的人都是我自己,可我總覺得我只是一層皮,“我”這一層皮包裹著的那些人到底是誰?我不禁問:“你是誰啊?你是怎么住到我心里的啊?”
哎呀,對了,這些“聲音”就像小腸里的絨毛,可以設想這樣的意境:我的心里被無數密密麻麻的絨毛覆蓋著,平時,它們那樣輕柔聽話,軟軟地搖曳,一旦要對我說什么的時候,那根絨毛就變得肥大、突起,然后開始發言。我好像挺煩惱的,又好像無所謂。我的心被我自個兒給篡奪了,好像也沒啥不可以。
桃子眼睛望向虛空,呵呵地笑了。又往肩膀后頭掃了一眼,感覺聽見了窸窸窣窣的聲音。
聽見這聲響,桃子忽然就忘記了剛才心中那來來回回的各種思緒,她的思考持續不了多久,就像母雞走了兩三步就轉身,內心的話題也總是千變萬化。它們來無影去無蹤,一個接著一個浮現又散去。就像現在,她已經在思考自己和老鼠之間的某種友愛關系了。“那時候可不是這樣”“那時候是啥時候”“那時候太多了”,心里有誰在不滿地發牢騷。
說實在話,過去的桃子別說對老鼠了,即使是見到蟑螂呀、小蟲子呀,她也總是狂呼亂叫地讓老公快來,那呼救聲令老公驚嚇不已。老公來了,桃子躲在和蟲子搏斗的老公后面,一臉崇拜地仰望著他。她一邊害怕,一邊卻又忍不住從指縫間看敵人被老公收拾的樣子,此情此景更令男人覺得有趣,特意將戰利品提到女人眼前。女人尖叫著逃跑,男人興致盎然地追,一邊搖晃著手里的蟲子,讓她快看。女人嬌嗔道:“不要啊,討厭。”——桃子也有過那樣的歲月。
斯人已去,良辰不再。當桃子知道怎么喊叫都沒用時,她擦干眼淚,自己卷起舊報紙,有時來不及卷報紙,就直接脫下拖鞋,用拖鞋使勁追打蟲子。一旦擊中,大喊快哉,發現自己也有野獸般的一面時,她還為此喜滋滋的。可不像現在,早就沒有那份斗志,很難說這都是因為老鼠發出的聲響。“我的心境到底有了啥變化?”立即有人轉換話題說:“那不用管,問題是你怎么又說東北話了?”這時,有個老婦人風格的絨毛出來了,她的聲音穩重沉靜,用一種苦口婆心的語氣說:“東北話,”頓了頓,又說,“東北話就是最深層的我自己。或者說,東北話就像吸管,將最深層的我自己吸上來。”
人的內心可不只有一層那么簡單,而是一層又一層疊加起來的。剛來到人世還是嬰兒時候看到的世界,是俺的第一層,后來,為了活下去,俺生成了各種各樣的層,一層又一層,可以說是被教會的,也可以說是被強行灌輸的,就像人們覺得很多事兒“非得這樣”“一定得那樣”。那些選擇,俺以為是自己做的選擇,其實呢,是被動的,被世界上那些堆積如山的約定俗成所要求,那些認知累積成了沉重的一大塊,就相當于地球的板塊似的。俺細細尋思,世間萬物都不是單獨存在的,一定有類似的模仿物。俺和地球也是宏偉的相似形啊。所以,俺心中的東北話板塊就是那最古老的一層,也可以說是沒人能進入的秘境里的原始風景。感覺深不可測吧?那倒也不至于,俺只要叫一聲“我說,俺在哪兒呢?”那原始風景就齊刷刷地凝結聚攏起來,東北話就冒了出來。那情形就像俺叫一聲“咦,我在哪里呀?”立刻就有一個精心打扮、神情矜持的我出現。這怎么說呢,就好像主語決定謂語,先選擇主語,接著就有那個階層的謂語以及思考方式出現。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挺可怕的,因為只要出現了東北話,“俺”就顯形了。可不是咋的?
“你說啥呢?”從旁邊那層突然發出聲音來。
你是周造嗎?哦,是俺家周造啊,老說啥來著?說“你總愛把簡單的事兒說得復雜,你這婆娘就愛瞎琢磨,我告訴你東北話它就是個鄉愁”。
你說得也有理,這陣子東北話老愛跑出來,俺也以為是懷舊之情,可是俺馬上就反應過來,事情哪有那么簡單啊,俺和東北話之間可不是那么尋常的關系,俺想來想去想到了老早。
桃子強烈意識到“東北話”這個概念時,還是個上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在那以前,桃子從未意識到第一人稱的發音是不同的。她一直和周圍人一樣說“俺”,毫無性別差異。上了小學,她才在教科書上發現男生女生的自我稱呼不一樣,有“我”,有“仆”(譯者注:日語中男孩自稱),那時桃子才感覺“俺”很鄉村味兒,說明確點就是土。桃子就想,那就用“我”吧,卻又不是那么簡單,因為一旦用了這樣的語言,就仿佛帶了點裝腔作勢,就好像變得不是自己了。魚刺卡在喉嚨里,吃一口白米飯就能吞下去;語言哽在心頭,卻無計可施,小桃子很為難。
如今想來,那正如一次“踏繪”(譯者注:德川家康時期,日本禁止基督教,下令所有教民踐踏耶穌畫像以示叛教),桃子感覺自己在接受考驗。桃子有對城市的憧憬,有對使用“我”的向往,然而如果真的使用了“我”,就好像一腳踢開了自己老家的空氣、清風、花草樹木以及和人們之間的聯系,這種背叛的感覺從腳踝那里攀緣上升,讓桃子感到不安。更要緊的是,如果對自己的稱呼都搖擺不定,俺以后會咋樣啊?俺就要變成吊兒郎當沒有定性的人了嗎?這種擔憂確曾在桃子小小的心靈里駐扎。
從那時起,東北話就成了桃子的心病。那種糾結的心情,就好像明明喜歡卻不能說喜歡,明明厭惡卻不能直接拒絕——就是那樣地擰巴。可是如果總這么糾結著,可就完全無法開口說話了,所以你就給這份糾結蓋上了一個蓋子,又跑到蓋子上頭穩坐著——這話是桃子內心的一個聲音,與此同時,各種聲音開始競相發出。
悠閑的聲音說:“這有什么呀?你人生都過了大半了,黃土都埋半截了,就把那些糾結、執念都放下吧。”
生氣的聲音說:“咋的?東北話招誰惹誰了?”
桃子心想,原來俺過得挺快樂啊。聽著心里頭各種說話聲,倒像是一頭扎進了娘兒們扎堆嘮嗑的曬谷場上,俺是孤單又不孤單,或者說處在這狀態就挺好。
這時,一個愛做總結發言的聲音出來了:“也許是為了排解獨居的無聊,大腦造出了自我安撫的防御機制哦。”
突然一個大嗓門來力壓群聲:“反正我看這就很正常,別磨嘰了。”
大腦里仿佛住著很多很多人,這算不算阿爾茨海默病的初期癥狀?分不清空想和現實,哪天腦子里的人都跑出來在現實生活中開口說話了那還了得?啊啊,太丟人了,腦子出了問題,以后一個人咋過下去?糟了糟了,這回咋辦?
管理著無數的絨毛突起的桃子,或者說直接連接著桃子身體的桃子,用桃子的話來說是一副臭皮囊的桃子,啊,太麻煩了,總之就是桃子本體,她的眼神飄忽,飄向了遠方。
真的呢,怎么辦?
一個女人在桃子心里從左往右跑過,往后梳攏的發髻扎得緊緊的,掖了塊手巾的衣襟扣得緊緊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那老婦人回過頭來,瞪著桃子問:“俺眼睛是睜開的吧?真的睜開的吧?”桃子忙問:“哎呀,奶奶,您咋現在來了?”
老婦人并不回答桃子,又接著問:“俺眼睛是睜開的吧?真的睜開的吧?”
桃子就像小時候那樣堅定地回答道:“嗯,是睜著的,是睜開著的。”
“是嗎?”老婦人嘆了口氣,一下子消失了。
奶奶又出來了!
無論是寫字還是拿筷子,基本上小時候所有的事都是一個人教給桃子的,那人就是令桃子懷念的親切的奶奶。奶奶做和服的手藝相當精湛,在桃子記憶中她總是在縫制和服,附近的和服店常常捧來上乘的和服料子,請她縫華麗昂貴的和服。做和服剩下的邊邊角角的衣料,奶奶做成沙包給桃子玩,奶奶做的沙包比誰家的都漂亮精致,在那一帶可有名了。
咦,那個沙包哪兒去了?桃子想站起身找,卻聽見一個聲音勸她:“我說,那是70年前的事兒啊,沙包早就無影無蹤了啊。”另一個充滿震驚的聲音:“什么?70年過去了?”于是她心里一片混亂。“是嗎?這么多年過去了啊。”“這日子可真快啊!”……穿越一片驚嘆光陰飛逝的呼聲,有一個聲音仿佛從縫隙中艱難地擠出來:“奶奶,奶奶好可憐啊。患白內障瞎了眼睛的奶奶,不相信自己看不見,總是瞪大了渾濁發白的眼睛,一遍遍問眼睛是睜開的嗎?因為問得太多,我回答的時候都不耐煩了。那時候我小,不懂得奶奶的心情,那生怕自己什么也做不了的心情是有多么凄惶絕望啊?現在我體會到奶奶的心境了,對未來充滿不安和恐懼的心境。也就是說,孤獨的人不僅僅是我啊,大家都一樣啊,天底下大多數事情都是循環重復的,奶奶和我,隔了70年的時光而同病相憐。”
俺不孤獨,俺不是一個人,桃子將這話念叨了幾回,然后在那上頭薄薄鋪上一層“既來之,則安之”的泰然達觀,安撫心神讓它們不要再眾說紛紜。
“話說,后來就不甩著拖鞋生氣了吧。”這是從別的絨毛突起處傳來的聲音,聽上去很年輕。話音剛落,一個頗有長老風采的聲音跑出來答:“俺現在知道了,活著就是件悲哀的事兒,虧得俺以前還以為只要努力就有辦法,只要努力就能開拓新的道路。就在這種信仰上頭,你和俺的生活才能平穩維持著。就算現在一片黑暗,只要忍耐過去就有未來啊,這種信仰,從那時起,就是從那時起……”
“那時是幾時?”
“那時,就是那時啊,就是俺最怕的事情發生的那時,俺就知道了,這世上有怎么都沒辦法、怎么都沒辦法的事兒。在這種事兒面前,怎樣的努力、怎樣的掙扎都沒用。當俺知道世上有怎樣努力也無可奈何的事情,就覺得時刻爭論輸贏的活法是多么可笑,無限搶占資源的活法是多么可笑,那些拼命使勁的活法是多么可笑,完全是將力氣用錯了地方。那時俺知道了人的弱小無助,知道了世界上有一面叫絕望的墻壁。懂得了這個道理,俺反倒感覺輕松了,而在那之前要如何為人處世,才是人要考慮的。一旦抵達,俺就好像成了另外一個自己。”
“那件事情之前和之后的我,完全不一樣了。我變得堅強。就好像已經挨過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波風浪,其他的小風浪已經不在話下,我只需要祈禱著,安心等待風浪過去。”
“說什么呢?簡直不知所云啊。”之前的年輕聲音狐疑地退下了。蒼老的聲音語重心長地繼續:“人啊,跟老鼠、跟蟑螂也沒啥大差別,還不都是東撞撞、西碰碰,得過且過,都是伙伴啊。是不?我可是發現了,其實大家伙兒都一樣啊。”
周圍傳來一句“別自個兒在那兒說教,能說點兒聽得懂的不?!”于是長老退了下去。
處于表層的桃子窺探著內心深處的各種聲音,表情復雜地“呵呵”笑了。
不知什么時候,從柿餅和浴巾之間透過來的微弱陽光漸漸退去,周圍已被薄薄的暮色籠罩。這種時段,桃子總是被一種似乎已經很熟悉但依然極具殺傷力的寂寞擊中。
桃子將茶杯里剩下的冷茶慢慢喝完。
“夜幕又降臨,帶來如煙往事。”桃子低低地哼了一句歌。世上還有誰比我更能深刻理解這句歌詞的含意?桃子又自言自語了一句。這是她十年如一日重復著的低語。
這時,突然從背后傳來像是“呼”或者“唉”的聲響。那不是以前常有的摩挲塑料袋之類的無機質的聲響,而是一種像人間氣息的聲音,是出聲,而不是響動。
桃子大吃一驚,她第一次有了想好好用眼睛看看聲音的“主人”的念頭。桌上有她擱置了兩天已經完全受潮而變得軟塌塌的咸米餅,因為一碰到假牙就痛,所以她放在一邊沒吃。桃子掰了一小塊米餅,沒回頭,朝著身后甩過去。
受潮的米餅落在地板上,靜默片刻,桃子計算著時間,在心里數著“一,二,三!”扭頭望去。看見了!哦不,好像看見了。灰中帶青色的后背到腹部,乃至細細的尾巴——確實仿佛從眼前掠過。
桃子看不真切,只一個勁兒擰著脖子往后看,這姿勢不行,得再轉過身去看看。桃子想調整坐姿轉過去看個真切,而此時她腦子里又涌現出很多很多人。不過,桃子覺得這根本不算啥了,她甚至覺得自己可能還能跟老鼠對話呢。這么想著,桃子干脆很有節奏地用雙手猛拍了一下大腿,打算借這股反彈力站起來轉過去,她預料中本該發出清脆的一聲“嘭”,入耳的卻是含混不清的一聲悶響,像受了潮。
桃子望過去,地板上只有散落的米餅,哪里有等著喂食的老鼠的蹤影。桃子呆呆站了會兒,為自己的孩子氣自嘲地笑了。沒有老鼠。她意識到如影隨形可相依偎的只有漸漸襲來的衰老。
啊,我是獨自一人啊,獨自一人好寂寞啊,這兩句話在桃子心中翻滾著。突然,一個勇猛的絨毛突起冒出來了,而且迭聲說:“俺說你啊,稍微不盯著你點兒就這德行,你這娘兒們,一轉眼就腦子停頓,把自個兒往酸溜溜的話里鉆。啥漸漸襲來的衰老,啥一個人好寂寞,那是你內心真這么感覺的,還是你用腦子設想出來的?”
“什么呀?討厭,胡說八道的煩死人了。”這是桃子本體和維護桃子的保守派絨毛突起。
“要對理所應當的事情保持懷疑,不被所謂的常識牽著走,不要畏難而逃,東北話為啥存在于你內心?是為了與本性本心連接啊,是呢是呢,啊啊天哪……”桃子終于忍無可忍,強行停止了思考。
“前寒武紀,古生代寒武紀、奧陶紀、志留紀、泥盆紀、石炭紀、二疊紀,中生代三疊紀、侏羅紀、白堊紀,新生代古近紀、新近紀,前寒武紀,古生代寒武紀……”
桃子屏住呼吸,面無表情,背誦地質年代名稱。
每當桃子遇到難以面對的情緒,比如痛苦難耐、萬分煎熬時,就這樣如同念咒一樣背誦它們,只為抑制住噴薄欲出的情感,渡過眼前的難關。
桃子只當從沒聽見那些無禮的絨毛突起的言論,昂然邁開了步子。
其實桃子非常喜歡閱讀關于地球46億年的歷史的書籍。自從在電視上看了部這類知識的紀錄片,她就徹底淪陷了。她將從這類科普節目里聽來的知識記在舊掛歷背面,還去圖書館查找書刊收集資料,鬧明白一點兒了,就在筆記本上工工整整地記筆記。剛才念的那段“咒文”就是那陣子的副產物。桃子從小就喜歡在紙上寫寫畫畫,只要在本子上寫著什么就能讓童年的桃子喜不自禁。從小時候起到如今成為老太婆,她一直喜歡書寫時的自己。桃子知道我們現在處于從260萬年前就延續的冰河時代的中間,知道從一萬年前起屬于比較溫暖的間冰期。說是“知道”,當然只是從字面上知道,對于目前地球究竟是怎樣的狀況無從想象。所以說到間冰期,桃子心里浮現的是梅花、桃花、櫻花、蒲公英一氣兒開放的春天,因為寒冷而僵硬瑟縮的肩頭一下子變得柔軟,輕松的春天,故鄉的春天呵。
雖說“間冰期”這樣的術語讓桃子想象的是故鄉的春天,但桃子也能在擁擠的電車里,在緊巴巴坐著的座位上,有意無意地展開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小字的筆記本,投入地研究地球的時代。
桃子慢慢走著,忠實地遵循在這個家中自然形成的“動線”,那是一條雖肉眼不可見,卻如同被又粗又黑的筆畫過那樣的、標準的移動路線。她順著這條線,穿過走廊,開門,上樓梯。樓梯盡頭是小小的轉角,一面是窗子,一面是墻,墻上掛著一張陳舊的掛歷,掛歷角落印著小字:1975年。那時候剛搬到這個家來,桃子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整天風風火火,日子滿是希望。那是桃子的花樣年華,是桃子的人生盛宴。
殘舊滄桑的掛歷上,印著千萬只火烈鳥,火烈鳥群眼看要從水邊凌空起飛。前面的那只火烈鳥已經飛起來,它的足跡還留在水里,留下清晰的波紋。緊隨著它,后面一排的火烈鳥跟著準備起飛,正在使勁劃水,而那之后還有無數的火烈鳥,形成壯觀的鳥群。剛看見這掛歷的時候,桃子曾想:如果自己是一只火烈鳥,大概是在鳥群的什么位置?在那遠看就像一片桃色的煙霧的鳥群的末尾,完全未發現頭鳥已起飛,還在悠閑地啄著水草,自己大概就是那樣吧。
現在桃子瞄了眼掛歷,然后將窗戶大大地打開。
伴隨著三月帶有料峭春寒的風,梅花的香味飄了進來。與桃子家隔了三戶的鄰居家,無人居住,但院子里有梅樹,今年梅花依舊開放。
“人面不知何處去,梅花依舊笑春風”,桃子對條件反射般地浮現在腦海里的古詩搖了搖頭,在窗邊托著下巴,視線飄向遠方。
從這里能眺望到桃子所在的城市,遠方田園盡頭有低矮的山脈,綿延在黃昏的暮色里。從星星點點的樹林和像樹林一樣聳立的高樓大廈間,能斷斷續續望得到高速公路。從那條高速公路一直往前行駛,按理說可以抵達桃子的故鄉。桃子有事沒事就愛眺望這風景,這一眺望竟然已經過去40年了。40年,說來簡單,開口輕輕就能說出來,啊,在這里住了40年了啊。桃子內心又出現此起彼伏、百感交集的聲音。
桃子的家,在郊外一個通常被稱作新興住宅區的地方。
穿越城市近郊的丘陵,那里設計得像棋盤一樣整整齊齊,梯田一樣一層層的房屋,看上去模樣都差不多。桃子的家不在最上頭,也不在最下頭,而是正好在丘陵的中間地帶。從家門口出去有個很陡的坡,從前坡下頭有一個超市。桃子年輕的時候,把兩個孩子分別放在自行車前后,順坡騎下去買菜,將裝滿菜的口袋一邊一個套在自行車龍頭兩旁,再一鼓作氣載著菜和孩子們騎著車上坡回家,回想起來跟耍雜技似的。
那時候的桃子可想過自己會老去?更別說可想象過自己會獨自老去?
“那時可真是啥都不懂啊。”絨毛突起發出感嘆之聲。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現在想來,“年輕”的同義詞就是“無知”啊。一切都要自己經歷過才會如夢初醒,幡然了悟,這么說來,“衰老”的同義詞是“經驗”,或者是“懂得”啊。
桃子總覺得“衰老”是接受失去,是忍耐寂寞,而此刻卻感受到些微的“希望”。“這不是挺快意的嗎?無論到多少歲,人們對于了解和懂得以前不懂的事兒都覺得快樂。”桃子的內心有個聲音在低語。伴隨著這低語,又一個聲音說:“那前頭還有啥不懂?還有啥?俺從今往后還能整明白點兒啥?要是整明白了俺能從這兒逃出去不?說實在話,俺有時都覺得活膩味了。”
桃子將絨毛突起們的喧囂與騷動置于腦后,凝神眺望高速公路后面那殘陽。
奶奶可能就在那兒吧,最近老是沒事兒跑出來的奶奶就在那兒吧,猶記得她用沙啞的嗓音教桃子見到長輩要敬禮。桃子坐姿不正,奶奶就拿根竹尺子插到桃子后背心,讓她看看自己坐得多歪斜。桃子要是做了沒禮貌的事兒,那根竹尺子就被奶奶用來打手心,竹尺子碰到手心時的瞬間,那涼涼的感覺,此刻回憶起,竟是親切極了。
桃子不由得挺直了背,正了正姿勢,朝著天空和遠山,輕輕說起話來。
“奶奶,俺在這兒呢,你的孫女在這兒看著晚上的天呢,俺活成這樣了,俺這樣行不行啊?”
“這是咋的了?”奶奶睜大了眼睛,定定地看著桃子,像從前那樣說話,“雖然不太好,可也不太糟,還行吧。”
桃子仿佛感覺到,準確說是仿佛聽到奶奶對她說話了,她立即被一種傷感包圍了。桃子有一種沖動,好想變成個四五歲的孩子,將臉埋進奶奶的大圍裙,嗷嗷地放聲大哭。奶奶的圍裙散發著太陽底下草席上頭晾曬的蘿卜干的甜味兒。桃子好想將臉埋進奶奶的大圍裙,可是桃子費力地忍住了這股沖動,要知道,桃子如今的歲數已經和那時的奶奶歲數一樣了。
桃子害臊地笑了。
就因為吃飽了撐的站在這兒眺望黃昏的天空,所以才東想西想的——桃子干脆利落地關上了玻璃窗,那瞬間,梅花的香氣好像軟軟地飄進了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