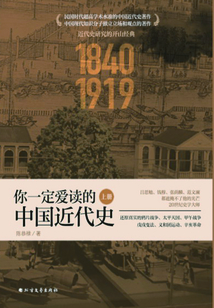
你一定愛讀的中國近代史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鴉片戰前之中國
中國據亞洲之東南部,其東部沿海六省,瀕臨渤海、黃海、東海,遙遙與日本及其屬地相對,其東五洋中最大之太平洋在焉。其在南部之廣東瀕臨南海。南部毗連安南(越南)、緬甸,其一現屬于法,一屬于英。其西南西藏,有喜馬拉雅山阻隔中國、印度陸路上之交通,西北新疆,北部蒙古,東北黑龍江、吉林與俄國領土接壤,奉天隔鴨綠江與朝鮮相峙。此中國邊疆之大概也。其強鄰有日、俄、英、法,四國之中,中日地位相近,中俄接壤長逾萬里,而英法以屬地關系,固不如日俄之密切。其在古代,疆域雖常變遷,而其地理上所受之影響頗為重要。其影響為何?曰:國內之農工商業,人民之生活情狀,以及交通國勢,多受地形、土壤、礦產、河道、氣候、洋流等之支配與影響。更就對外而言,古代航海術未精,船舶淺小,水手無犯風濤遠渡海洋之勇氣,沿海七省除海盜而外,別無侵擾之國,居民常能安居樂業。南部毗連熱帶半島,半島上之物產豐富,居民不必勤于工作,而食料衣服即綽然有余,懶惰不易奮發,不能大為害于鄰國。西南高山蜿蜒千里,立國于其地者缺少發展之機會,西羌、吐蕃力能跳梁于一隅而已。蒙古、滿洲地多曠野,氣候寒冷,土壤較瘠,人以游牧為生,耐勞受苦,體壯多力,善騎能射,茍有領袖將其團結,則戰斗力常強。是以我國歷史上之外患率多起于北方,匈奴之入寇,五胡之紛擾,遼金之壓迫,蒙古之侵略,滿族之入關,皆其明顯之證。迨航海術進步,機械學發達,海上交通,不唯無建筑之費用,且無修理之需要,反便于陸,亞歐之交通為之一變,而我國形勢隨之轉移。歐洲人乃自海上伸長勢力于東方,印度適在中國、歐洲之間,首當其沖,次及中國,固地理上之位置使之然也。
國內領土據今估計,凡四百余萬方英里,世界陸地約五千七百余萬方英里,亞洲一千五百萬方英里,中國面積約占全球十四分之一,亞洲四分之一。世界人口凡一億八萬萬,中國約逾四萬萬,殆占總數四分之一。就其分布而言,本部十八省共一百五十三萬方英里,人口據一九二三年郵局估計,凡四萬一千一百萬;滿洲三十六萬方英里,人口二千二百萬;蒙古一百三十六萬方英里,人口二百萬;新疆五十五萬方英里,人口二百五十萬;西藏四十六萬方英里,人口三百萬。十八省內,人口最密者,首推江蘇,每方英里八百人以上,甘肅人口最稀。面積人口之數目,皆非本于精確之丈量與調查,其價值不過使吾人略知分布之情狀而已。其在清代中葉,直省人口,視今殆無重大之不同,滿洲、內蒙古人口之激增,則始于清末領土視前削小,其詳見于后篇。人民耕種生活之情狀,百余年內,未有劇烈之改變。人口既以十八省為多,其地漢族之勢力最盛,漢族歷史上雜有苗、滿、蒙、回、藏五族之血胤,今日中國民族,乃合漢、苗、滿、蒙、回、藏六族而成,西人統稱之曰蒙古族,蓋蒙古成吉思汗之兵威震于歐洲,其子孫征服中國,以之代表黃種也。六大民族除纏回外,皆為黃種,其頭顱身體之構造,皮膚之顏色,發毛之黑直,多屬相類。其長矮不同之處,實無若何之重要,猶一族之子孫,尚或迥異也,證以見聞而益信,吾人漢族與滿人、回人同處一地,固難辨別其種族也。自其雜居以來,互通婚姻,血統上趨于同化。總之,六族之稱,本極牽強,今日殆為歷史過去之名辭,充量言之,只可代表居住一地之人,如浙人、蘇人、蒙古人之例,不得認為種族不同之民族也。漢族自黃河流域,逐漸移居于長江及西江流域。滿人隨清帝入關,分防國內要害,其根據地滿洲今為漢人居住之地。蒙古為蒙古族人游牧之場。回族以宗教之信仰,得有此名,其在西北者,多為突厥之后,又有雜居于內地及云南者。藏族游牧于青海、西藏、西康。苗族住于西南諸省之僻壤。六族中以漢人為多,其潛伏同化之力量尤大,然其久為土著民族,不敵游牧民族之強悍善戰,政治衰弱之時,則深受其蹂躪。十三世紀末葉,蒙古強盛,滅宋統治中國。其后朱元璋逐之,建國曰明,十七世紀,明室衰弱,滿洲愛新覺羅氏乘機入主中國,凡二百六十七年。茲略言之于下:
滿洲舊為東胡游牧之地,戰國時,燕王任用賢將卻之東北千余里,相傳其開拓遼河流域,漢武帝縣屬朝鮮半島,其后鮮卑遼金次第起于東北,皆所謂東胡族(即通古斯)也。明初太祖恢復遼河流域,成祖招撫黑龍江,然其設官治理,終與內地不同。遼河之西仍為女真舊部,女真部落而居,時人依其文化程度分為生熟,其人以游牧射獵為生,鍛煉成為強悍之身體,善于騎馬,一日之間,颶沒或數百里,所射之矢遠能殺人于百步之外。十六世紀末葉,建州部酋努爾哈赤善于用兵,合并諸部,兵勢漲旺,聲稱復仇,擾及明邊。明帝聚大軍分路攻之,并詔藩屬朝鮮葉赫出援,努爾哈赤次第敗之,盡取中國之邊藩,而明君臣尚無振作之氣,朝臣方努力于黨爭,互相詆訐,釀成宦官一網打盡之禍,言路妄發不負責任之評論,以致統兵大將,不得展其才能。由是努爾哈赤迭陷重鎮,盡降遼河以東之諸城,后攻山海關外之重鎮寧遠,不勝,負傷而死。一六二七年,其子皇太極(太宗)嗣位,先除內顧之憂,率兵問罪朝鮮,凱旋而歸,俄攻寧遠,無功,乃繞道西南,出內蒙古,大掠于中國北部。其時內蒙古諸部降服,獨察哈爾汗助明。皇太極攻之,收降其眾,聲勢大漲,改國號曰清,于是領土北界外興安嶺,東迄日本海,西至內蒙古,南臨長城,乃遣大軍深入中國腹地,終以未得山海關故,不敢據之。
方皇太極之侵擾中原也,值明懷宗在位,懷宗承熹宗之后,內亂外患交至,意欲和清,而以朝臣之堅持,難于獨行其志,乃練兵籌餉,增加田賦,以致貪官勒索,人民不堪其苦,危機四伏。陜西受禍較烈,其地初受官吏之虐政,后遇饑饉,人民無食,強者相聚為盜,政府應付,無堅決固定之政策,釀成燎原之禍。一六四三年,李自成進攻北京,懷宗自縊而死。明年,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因其愛妾之憤,乞師于清。時皇太極新死,其弟多爾袞擁立皇子福臨嗣位,親自輔政,改元順治,及得吳三桂書,率兵而往,大敗李自成軍,入據北京,命將進追流寇,平定黃河流域,旋取南方;明帝子孫之自立稱帝者,相繼敗沒,獨桂王據有云貴諸省,力圖恢復,后亦敗亡,中國復歸統一,而三藩尚擁重兵。一六七三年,康熙下詔撤藩,三藩先后叛亂,鄭成功之子經應之。康熙遣兵平之,俄降臺灣,由是國內無事,轉而經營東北,與俄國締結界約。會喀爾喀(即外蒙古)之西。準噶爾部崛興,其酋噶爾丹征服天山南北,領土包有科布多、青海及新疆(今名)一部分,且欲東并喀爾喀。值喀爾喀諸部內訌,噶爾丹來襲,諸部南請內附,清兵戰敗準部,收服外蒙古。噶爾丹死,其侄策妄善于用兵,乘機侵入西藏,清廷出兵敗之,留卒戍之,更征服青海,獨準部不服。及其酋死,乾隆出兵收取其地,天山南路諸城,后亦降服,其人信奉回教,故有回疆之稱。于是清之版圖,東北起自庫頁島,以外興安嶺為界,外蒙古毗連俄國西伯利亞,西北天山南北二路伸入中亞細亞,西藏南接印度,東方則臨海洋,臺灣諸島次第設官治理,琉球、朝鮮諸國按期朝貢,國內則開拓苗疆,改土歸流,其后大小金川之番人亦服。其領土之廣大,除元代而外,莫之與京,清代之極盛時期也。其領土可別為三,一曰行省,二曰屬地,三曰屬國。
滿人自關外入主中國,其原有之政府既簡且陋,不宜于廣大之中國,乃用明制,成立專制政府,皇帝為一國元首,統治全國,有無上之權威,其下有親王及內閣大學士佐之。大學士初為四人,佐理政事,擬詔命,整憲典,議大禮。十八世紀初葉,雍正分其職權,添設軍機處,其大臣無定額,多則九人,少則四人,由大學士尚書內詔委,掌管軍國大政,贊理機務,每日入朝,應對皇帝垂問,為最高之統治機關,其屬員章京佐之。庶政則歸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辦理,吏部考核功過,稽掌勛祿、蔭敘、封贈。戶部掌各省田賦,皇室經費,官吏廩祿,軍馕鹽課,鈔關雜稅,鼓鑄錢幣。禮部掌五禮兼領學校貢舉,藩國咨文。兵部厘治戎政,簡核軍實,兼管驛站。刑部掌折獄,審刑,簡核法律,讞定各省疑案。工部營修公共建筑,發給軍裝,修治河渠。六部組織,每部有尚書、左右侍郎,俱漢滿一人,共有六人,其屬員視政事而定,盛京設戶禮兵刑工五部,各有侍郎一人。都中衙門尚有都察院、翰林院、大理寺、宗人府、內務府、理藩院、通政司、詹事府等。都察院有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俱滿漢并用,下有六科給事中,十五道監察御史,其職守為核查官吏,敷陳治道,上為天子耳目,下達民隱。翰林院制誥文史,兼備顧問。大理寺平反重獄。三署及六部長官,亦稱九卿,參與朝議。宗人府掌皇族事務,內務府理皇室庶務,理藩院掌理藩屬爵祿朝會及控馭撫綏事宜。通政司、詹事府多為清閑衙門,以舊制設立者也。
地方官制頗為復雜,畿內順天府及滿洲之奉天府各有府尹、尹丞一人,直隸于中央政府。本部十八省之長官為總督、巡撫,其制殊不劃一,直隸、四川設有總督,但無巡撫,山東、山西、河南各有巡撫,但無總督,其余總督管轄二省或三省,省設巡撫。其職為考核屬官、治理民政、節制綠營等,凡省有總督巡撫者,奏折咨請,訓令屬官,多須會銜,嘗以意見不合,發生困難,尤以同住省城者為甚。其下有布政使、按察使佐之,布政使考察吏治,報于督撫,管理田賦,稽檢倉庾。按察使掌一省之刑名,澄清吏治,兼領驛傳。下有道員,掌核官吏,或管河糧鹽茶,或兼水利驛傳,或兼關務屯田。其下有府,府有知府,直隸州及直隸廳視府,設有同知,又其下有縣州廳,其官掌轄境內之政令、賦稅、訟獄、緝捕等,各有屬吏佐之,各鄉設有地保。其因重大事故,皇帝詔委欽差大臣,或將軍名稱,予以便宜行事之大權,余若河道總督、學政、鹽運使等官,或有職守,或無所事。十八省外,屬地若吉林、黑龍江、伊犁等,各設將軍。新疆、蒙古、西藏有參贊領隊理事辦事大臣。屬國則按期朝貢。軍隊分有旗兵、綠營、鄉勇,旗兵原為滿人、漢人、蒙古人之從軍入關者,分屬八旗,世受國恩,男子籍為兵士,大隊防守京師,或駐大城要害,由將軍或都統將之。綠營為各省招募之軍隊,維持地方治安,全國六十余萬,由提督、總兵統率,并受總督、巡撫之節制。及后旗兵、綠營不能戰爭,乃募鄉勇,戰則編之入伍,亂平則多解散歸農。
縱觀清代之官制,名雖根據于中央集權之政策,而以土地廣大,交通不便,監督不周,組織不密,地方官常有大權。皇帝身為滿人,初至中國,不通華語文字,不知其政治制度,勢必任用漢人,其心中固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思想,乃深信滿人,委為長官,借以監督漢人,子孫遵之,故軍機大臣多為滿人,六部尚書、侍郎名雖漢滿并用,而滿人掌握重權。統兵將帥,自三藩亂后,亦多滿人,太平天國亂起,始破舊例。地方官制基立于互相牽制之政策,造成極為復雜之組織,蓋以管官而非治民也。考其職權,多無明顯確定之規定,遇有困難,則互相推諉,利之所在,則相爭奪。實際言之,官署多為傳遞長官命令之機關,其弊則手續繁多,辦事遲慢,積久成為我國官署之普遍習慣。官吏出仕,八股考試為其正途,考取之士,思想才力梏痼已深,多無發展之余地,而人數眾多,任用無期,迨其年老,志衰力微,幸者始得重用。朝廷患其官于本省,得受家族親友之請托,例有回避,長官除一二例外,皆非地方之人,不知民情風俗,應興之建設,當去之弊端,甚者不通地方之言語,借重世襲之胥吏,唯求安然無事,敷衍塞責而已。康熙曾諭巡撫潘宗洛以不生事為貴,善于保持祿位之官吏,莫不奉為金科玉律也。官吏任期未有切實之保障,無論何時,朝廷均可罷免其職,或對調于他省,知縣為親民之官,其在一縣任期,亦有限制。
文武官之俸給,多本于明制,明代官吏之待遇頗為菲薄,清承其弊,世襲之王公歲俸較厚,百官則極貧苦。官吏原為公仆,有犧牲服務之義,不當視為職業鉆營,俸給不宜過于優厚,多增人民之擔負,亦不應過于菲薄也。適當之辦法,則宜酌量社會上之生活程度,平民所得之薪金,貨幣之購買力等,定其額數,足其一家之生活費用,庶可養成其廉潔而居官公正也。清帝入關初用明制,正俸而外,給予柴薪,俄將柴薪廢去,改定在京文武官之俸給。正從一品歲俸銀一百八十兩,正從二品一百五十五兩,正從三品一百三十兩,正從四品一百五兩,正從五品八十兩,正從六品六十兩,正從七品四十五兩,正從八品四十兩,正九品三十三兩,從九品三十一兩。漢員每人年給米十二石,滿員則數較多。在外之文官,按品給銀。武員則數大減,正一品九十余兩,從一品八十一兩,其品低者俸亦減少,所領之薪銀數亦無幾。外官均不給米,又無公費,乃賴額外之收入,或近于賄賂之饋遺;其征田賦也,有火耗陋規等名,京官亦有所得。雍正嗣位,改收火耗等項為國課,詔給京官俸米,每銀一兩給米一斛,另給恩俸,銀數一如正俸,六部尚書、侍郎,給予雙俸雙米。外省文官給與養廉,其數各省不同,總督自一萬至三萬兩,巡撫一萬兩左右。其他各官,今舉直隸之例略概其余,布政使九千兩,按察使八千兩,學政四千兩,道員兩千兩,首府兩千六百兩,余府兩千兩,同知七百至一千兩,通判六百至七百兩,知縣六百至一千兩百兩。官吏俸金視前略增,外官仍不足用,另立名目,浮收稅款,京官則多患貧。
官吏時為文人讀書力求之目標,會試有常科恩科,錄取之進士,多者三四百人,少者數十名,缺少人多。翰林院朝考重尚小楷律詩,其列高等者久始升用,外官以捐輸迭開之故,候補者多,茍非善于鉆營者,常難得缺,乃納賄權門,拜結師生同年,互通生氣,于是吏治大壞。一八一九(嘉慶二十四)年,疆臣陶澍奏稱吏治八弊:(一)勒接交代新官承認前任虧空,少者數千,多者數萬,告稟則上官有失察之咎,勢不敢為。(二)多攤捐款,名目有等補,幫助,貼賠,使費,每歲數百數千兩不等。(三)預備賞號,凡上司有事,或練兵,或巡邊,或公宴,均有賞金,上司收之作賞,吏役更索規費。(四)添辦供給,上司出入境時,有夫馬,有酒席,有站規,有門包。同城居者有輪月或包月之供給,一窗,一扉,一廚,一廁,皆取于附郭之州縣。(五)壓薦幕友,道府藩臬督撫所薦,不敢不受,有未見面而送束脩者,謂之食坐俸。(六)濫送長隨,上司薦之不得不受,更無所忌,乃外勾吏役,內通劣幕。(七)委員需索,一紙文書可辦之事,動輒派委數員調劑閑官,多所需索。(八)提省羈留,官進省后,轉委他人,一年半載之后,始令回任。陶澍所言偏于官吏之關系,可謂詳盡。清末御史曾再以之為言,蓋惡劣政治下難于避免之現狀也。其下胥吏多無俸給,迫而出于營私舞弊之途,以謀衣食,其熟于檔案者,善于取巧,勒索敲詐,無惡不作,而長官無如之何。相沿既久,人民之心理常以官吏之貪狠如狼似虎,事多解決于宗族,非不得已,決不稟報于官,人民之視政府存亡榮辱,不關于心。官吏之主要職司,則為維持治安,催征田賦,審判訟獄而已。
軍隊分八旗綠營已如上述,八旗就軍旗顏色而言,曰:正黃、鑲黃、正紅、鑲紅、正白、鑲白、正藍、鑲藍。中分滿軍旗、漢軍旗、蒙古旗。兵有定額,初約二十萬人。其駐京師者,前鋒親軍等每兵月餉四兩,驍騎銅匠等月餉三兩,歲均支米四十八斛。步軍領催月餉二兩,步兵一兩五錢,歲支米二十四斛,教養兵月給一兩五錢,但不給米。其家人不準另謀生計,男子皆有當兵之義務,然限于馬甲之定額,及后人口滋殖,一家三男,一人補甲,二人則無職業,全家唯恃餉米糊口,生活遂大困難。朝廷籌其生計,出款還其欠債,略增馬兵教養兵等,但以人數眾多,豢養究非辦法,終無補救于事。旗人自居內地以來,進為土著民族,所處之環境迥異于前,傳至子孫,改變舊俗。其優秀分子羨仰漢人之思想文藝,無知之徒樂于放縱聲色貨利之欲,乾隆用兵多用綠營,業已證明其喪失戰斗力矣。各省防軍初用綠旗以便識別,故稱綠營,全國凡六十四萬。其在京師巡捕者,馬兵月餉二兩,步兵一兩,米皆三斗。各省馬兵月餉二兩,戰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米亦三斗。其待遇不及八旗,缺額六七萬人,乾隆將其補足,后再裁減一萬余人,兵士各以衣食艱難,自謀生計,平日勢難操練,營中缺額之餉,皆為營官侵蝕,有事則臨時招募,平亂御侮則力不足,擾于民間則綽然有余。
政治上之積弊分言于上,其財政狀況,固吾人所當知者也,國庫收入,戶部例有報告,支出款項中有不可知者。收入以田賦為大宗,丁稅附之,丁稅分上中下三等,自一分至二兩不等,各省不同,康熙將其并入田賦計算,田賦乃為主要收入。每畝征銀自數厘至二錢不等,其最重者首為江浙,其地以南宋公田及明初張士誠之占據故也,清代因之。農民納稅年分二期,官吏征收者,一曰錢銀,二曰糧食,三曰草秣,一六五九(順治十六)年,征銀二千一百萬兩,糧六百四十萬石,一六八五(康熙二十四)年,二千四百萬兩,糧四百三十萬石,一七二四(雍正二)年,二千六百萬兩,糧四百七十萬石,一七六六(乾隆三十一)年,二千九百萬兩,糧八百三十萬石,草秣無足輕重。茲為明了當時國內之情狀。
《通考》所列田賦前三總數,與作者計算所得之和不同。各省款數,蓋有錯誤,如一六八五年,廣東田賦二百余萬萬兩,不免令人懷疑,其他原因,或催征不能足額也。《通考》記一六五九年,收入凡銀二一,五七九,九九七兩,一六八五年,二四,四四九,七二四兩,一七二四年,二六,三六二,五四一兩,一七六六年,則兩數相符,現無材料考證前數。表中所列之省名地名,中有異于后名者,吾人為明了歷史上十八省之成立,仍用舊名,甘肅、四川、廣西、云南、貴州諸省,收入數少之原因,或由于大殺之后,人口驟減,田地荒蕪,或由土司管理向不征稅,或因土壤磽瘠也。政府收入增加者,多由于荒地開墾升課,一省款數前后不同,則以豐歉,朝廷酌免田賦也。糧食種類不一,有米、麥、豆等,米則江蘇一省,定額逾三百萬石,南漕運京者凡四百萬石,初由運河北上,設官催督,費用出之于民,后河身淤高,運輸困難,運米一石入倉,曾用銀十八兩或二十兩,倉米出售,每石一兩。朝廷迄未改計,道光時,始改海道北上。其他收入,則以關稅鹽課為大宗,關稅分海關、常關兩種,海關以廣東為最旺。常關設于商業要區,一年收入約四百萬兩。鹽多出于沿海各省,由官督民煮曬,招商販賣于劃定之區域,征收稅銀,其區域廣大,而稅收最多者,首推淮鹽。內省銷售池鹽、井鹽,每年征稅約四五百萬兩,及私販增多,票引嘗不及額。余則牙稅、落地稅、茶課等均無重要。總之,乾隆中葉,國庫歲入凡四千萬兩,地方官之浮收,及其進貢物品,尚不與焉。支出以皇室經費、軍餉、政費為大宗。皇室經費有陵寢、祭祀、修繕、采辦、織造等名,用款從無定數,估計殆在五百萬兩以上。政費以養廉較多,朝中王公百官,每年俸銀一百萬兩左右,合計京外官七百余萬兩。兵餉約二千萬,驛站百萬有奇,兩數相抵,國庫尚有余款。乾隆經營新疆,歲支三百萬,募足綠營,增加賞恤,歲費二百萬。及嘉慶嗣位,收入略有增加,曾至四千三四百萬兩,無如內亂迭起,裁去之額兵,不過歲省四十萬,而黃河為害,修治南河增至三百萬,東河二百萬,其先修河,鄰近州縣,撥派民夫,乾隆中始全發帑,為數不過百余萬耳。宗祿亦以宗人繁衍,數大增加,由是財政漸趨于困難,尤以嘉慶末年為甚。
政府收入不敷支出,農民歲益窮苦,清初于大殺之后,田地有余,耕者安居樂業約有百年,人口大為增加。據《皇朝文獻通考》,一七一一(康熙五十)年直省人口二千四百余萬,一七四九(乾隆十四)年,增至一萬七千七百余萬,相去三十余年,增加七倍,一七八〇(乾隆四十五)年,增達二萬七千七百余萬,又據《皇朝續文獻通考》,一八一二(嘉慶十七)年,丁口凡三萬六千余萬。百年之內,人口增至十五倍,可謂速矣,一七一一年前,人口蓋已大增,不幸各省未有確報。其明年康熙詔定永不加賦,中云,“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人,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納錢糧。”人民初避丁稅,隱匿丁數,自此詔后,丁口報告,似宜較確,無如官吏視為無足輕重,不肯切實調查,其數雖可懷疑,然而人口激增,則可斷言。洪亮吉于時論之曰:
人未有不樂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后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田一頃,寬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人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各娶婦,即有八人,即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矣。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問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而玄焉,視高曾祖時,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為一戶者,至曾玄時不分至十戶不止。其間有戶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勢足以相敵。
洪亮吉之言本于深切之觀察,其所論增加之倍數,自今觀之,不免太速,而中國倫理觀念,及早婚習慣,皆足以促進人口之激增。及其增加之后,仍以農業為生,康熙永不加賦之詔中云:“人丁雖增,地畝并未加廣”,由是田地不敷分配。其時沿海島嶼,嚴禁人民往墾,其私往者,官焚其居,驅之回籍。一七八七(乾隆五十二)年諭稱浙江大小島仍循舊章,永遠封禁,凡請開墾者,從重治罪。滿洲、蒙古等地均禁漢人移居。據《皇朝文獻通考》,一六五九年,國內耕種田地,凡五萬四千九百萬畝,一七六六年,共七萬四千一百萬畝,相去百余年,開墾之地不足二萬萬畝,而人口增加,則在十倍以上。向者每人平均耕田二十余畝,今則二畝有奇,十人耕種一人所耕之地,每畝生產雖稍增加,固用力多而出產少,食料之困難可想,貧民益眾,衣食日難。
各省田畝表計算所得之和,大數同于《通考》,全國耕種之土地,殆多于此,蓋此報告就征稅之田而言,一省田畝以豐歉之不同,前后稍有出入,莊田、屯田、學田均未計入,直隸、四川等省之黑田尤多。據作者之估計,十九世紀中葉,全國耕種之田,殆有十萬萬畝左右,而人口激增至四萬萬,分配有限之土地,其何能足?尤以江、浙、魯、豫諸省為甚。張海珊以經世自期,頗留心于民生,其里濱近太湖,謂人浮于田,每家所耕不到五畝。一家五人,每人平均不足一畝,湖田原為植稻膏腴之地,生產力強,無如土地太少,收入有限,其生活可想。淮水以北,一家耕種十數畝地,貧苦之情狀殆猶過之。貧民潛往直隸、山西北部,為滿蒙地主佃戶。其近海者,冒禁耕種于島中,乾隆末年,諭稱山東海島有民二萬余名,浙江島嶼時亦有人潛往開墾,更有耕種于山地者,如浙民開山,長官禁之,其往皖南閑曠山問搭棚棲止者,道光飭官逐回其新至者。人民多以耕種為業,所出之粟,價無劇變,而民間通用之制錢日賤,清初每銀一兩易錢七八百文,繼則增至一千左右,至道光末年,兌至一千五六百文以上。人民納稅,出粟易錢,以錢易銀,于是所納之稅,名雖照舊,實則倍于往日,官民交困,農民之生計益難。朝臣未曾顧慮人口激增后之問題,其留意者,則八旗人丁也。清初中外駐防之禁旅二十萬有奇,清帝禁其營生,保護備至,無奈人口增加太速,而馬甲限于定額,旗人慣于奢侈,生計日蹙。雍正曾倡遷移旗丁于滿洲之議,惜未實行,及乾隆嗣位,御史舒赫德上奏旗丁移屯之計劃,戶部侍郎梁詩正亦言八旗屯種,乾隆遣壯丁三千余人開墾于松花江流域,而八旗子弟不便于邊外之生活,棄地還于北京。十九世紀初葉(嘉慶中),戶部報告旗丁五十萬有奇,合其家人,最少之估算,當逾二百萬人。朝廷曾許漢軍出為平民,無如其數無幾,無濟于事。于此生活困難之時,漢人勤苦耐勞,經營生產事業,滿人雖得政府之補助,尚不愿在關外開墾,而漢人則因生計之壓迫,違反禁令墾種田地,此固極少冒險之人。其在廣東、福建沿海之地,亦有經商傭工于海外者。然皆不能解決國內過剩人口之問題,其無職業者,遇是水旱疾疫,不能束手待斃,乃循一治一亂之慘殺故轍,亦可悲也已。
人口過剩隱伏禍亂之根,其起而叛亂者,秘密會社也。會社之初起,究不可考,漢代即有其亂,清帝以滿人入關,相傳遺民痛于明朝之滅亡,加入其中,意欲復明。斯說也,殆難憑信,兩廣總督徐廣縉曾奏三合會始于明代,明之中葉固有會黨擾亂也。清代主要之黨會可分為三,曰白蓮教,曰三合會(或作三點會),曰哥老會,其支派繁多,名稱復雜。三會之中,白蓮教為最早,二會與其相近之點頗多,或深受其影響。白蓮教之首領,初借勸人為善,醫治疾病為名,招收黨羽。其徒本多鄉間迷信極深之游民,及受所謂信條之后,忠于其黨,教主更借神怪不可思議之符咒,及天文預知之說,以堅固其信心。迨后黨徒眾多,遂起兵叛,政府禁之頗嚴,乃改名稱,秘密宣傳,迄今尚未絕滅。三合會、哥老會亦有迷信色彩,三合會盛于南方,其頭目有大哥、二哥、三哥、紅棍之稱,會員統稱草鞋。凡入會者舉行鄭重之典禮,名曰開堂,會規繁多,其不遵守者,即為背誓,五雷誅滅,所用之符號暗語,會外之人常不能解。哥老會盛于長江流域,組織目的近于三合會,其頭目之名稱,入會之形式,會中之暗語,皆無詳述之必要。凡此秘密會社之會員,注重義氣,會規諄諄然以患難相助為訓,地方之惡棍,迫于生計之無賴,往往加入其中。其人輕身好勇,練習拳棍,良民畏之。其雄霸于一方者,廣收徒弟,抗拒官吏,而官吏無如之何。其成立之要因,由于政府之腐敗,官吏監督之不嚴,無業者之眾多,與夫安寧之無保障也。魏源于《圣武記》中,記道光平瑤事云:“初楚粵邊郡奸民,為天地會,締黨歃約,橫行鄉曲,小剽掠,大擅殺,各有名號,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諾,吏不敢問。趙金龍起事,即戕殺會匪,故會匪不附,而郴桂兩粵奸民已所在蠢動,州縣借軍興團練,隨時禽治渠魁,又瑤平迅速,幸未生變。”瑤亂平于一八三二年,距洪秀全起兵十八年前,可見會黨勢力之一斑,嗣后國內擾亂,莫不與之有關。
十八世紀末葉,叛亂之原動力醞釀已久,心滿意足之乾隆,方以十全老人自慶,其禍亂之早發,促成于寵相和坤。初和坤專權,賄賂公行,吏治大壞,其私產或估其計不下八萬萬兩。同時,八旗綠營暮氣沉重,失其戰斗能力,攻取大小金川,糜餉之巨,勞師之久,數殺大臣,皆其明證。自乾隆讓位其子,其年為一七九六,迄于一八三九(道光十九)年,叛亂時起,其重要者凡四。一、白蓮教之亂——乾隆末年,白蓮教魁劉之協煽亂,事發而逃,湖北、四川諸省奉旨大索,胥役逐戶搜緝,多逞虐威。荊州、宜昌株連數千,富者破家,貧者瘐死,人民又以征苗攤籌軍費,失業問題,仇官思亂,湖北、四川、陜西之叛亂遂作,教徒脅民助之。官兵討賊,常殺良民,紀律廢弛,“所遇地方,受害甚于盜賊”,終不能平,后始利用鄉勇,采行堅壁清野之策,亂事漸定。一八一三(嘉慶十八)年,白蓮教余支天理教作亂,其教魁林文清賄通內監,會合黨徒潛襲宮廷,事敗就擒,余黨起兵于滑縣,不久即平,其支派迄未能絕。二、苗瑤之變——苗民自改土歸流以來,益退居于湖南、貴州僻遠之地,官吏待之甚虐,擾及閭寨,漢人侵居其地,苗民時思報復,至是起而作亂,大殺官吏漢人,迭陷重城,官軍討之,轉戰數年,會教亂方熾,改用敷衍之策,始得班師。一八三二(道光十二)年湖南之瑤作亂,瑤本戇鷙,居于五嶺,會匪欺其愚拙,勾結官吏搶劫牛谷,瑤民不堪其苦,其酋趙金龍率之作亂。其人矯捷善戰,朝廷聚大軍圍攻,多虐殺之。其時廣東之瑤亦叛,清兵往攻,瑤酋跪迎請降,殺之,瑤遂死戰,復招其出降,戰禍始已。三、回疆之叛——回疆自征服以來,朝廷委任滿員治之,長官以其路遠,恃而不恐,不善治之,而回人勇敢好斗,迭起叛亂,朝廷始乃慎重人選,終無效果。一八二五(道光五)年,長官勾結土官,搜括回民,甚且廣漁回女更番淫樂,回人憤怒,故酋之子張格爾乘勢起兵,恢復要城,朝廷遣大軍出塞,計誘殺之。復與浩罕捕兵,禁其互市。浩罕媾侵,清兵僅能保其壁壘,乃許之和,回人迄未心服,亂旋復起,幸即平定。四、海盜之騷擾——海盜初為沿海善于駕舟之游民,漢唐已有劫掠商賈之事,明代其勢益盛,至是仿造高大之洋船,中置利炮,漳人蔡牽統之,曾得安南人之助,黨羽日多,霸行海上,劫掠商船,勢大猖獗,而水師之船笨窳,不能御之。其在廣東者,為外船所敗,余黨擾于浙江。其巡撫阮元捐籌巨款,付交李長庚造大艦霆船,鑄炮配之,朝廷擢長庚為提督,蔡牽數次犯浙,均不得逞。長庚追盜,重傷而死,朝命裨將代之,追剿益力,阮元施用離間之計,由是蔡牽敗死,余黨降服。東南之海岸稍靖。以上數亂,聚國內精力財力,始能定之。
清至中葉,國勢漸衰,而對外之政策,本于傳統之思想,輕視外人,依然如故。其造成之原因至為復雜,統而言之,可別為三。一受地理上之影響,我國四鄰多為弱小國家,常來朝貢,其文化又不如我國,乃以天朝自尊,鄙外國為夷狄,而稱其人為番鬼。一為心理作用,人類之天性,以習見者為當然,久則生有擁護之心,茍往異鄉,其風俗習慣與之迥異將即感受不安,外人之種族容貌既不同于吾人,而言語飲食習慣風俗又各迥異,易于引起輕視厭惡之意,漸成普通之心理。一由于歷史上之遺傳,其說詳論于后。歷史上漢唐為中國強盛時代,版圖達于西域,中西交通便利,國際貿易發達。唐時外人居于境內,學術思想隨之傳入,中國吸收之后,發揚光大,成為文化燦爛時期,何近代固拒外人之深?古今何相去懸遠耶?問題頗關重要,茲分別言之于下。
我國天然環境,東南瀕海,古代海上貿易不甚發達,南方鄰國人民不善于營生,西南高山或無人跡,北部之曠大平原,人民稀少,沙漠適當其間,其北荒涼之西伯利亞,更無貿易之可言。對外貿易之途徑,西北較為便利。商人本于求利之心,涉萬里不辭其苦,陸路交通較為發達,其在漢時,小國臣服往來,尤形便利。其路程自我國內地前往陜西,深入甘肅,及抵敦煌,分有二道,一出天山南路,循戈壁沙漠之南而行,一出玉門關,自天山北路而行,繞道于戈壁之北,掠中亞細亞而南,商人之往來者,憩于和闐,以橐駝運輸,貨物萃集于其地。學者謂新疆為古代印度、波斯、希臘、中國文化接觸之所,其歷史上之名城,人民之生活,文化之程度,迥異于野蠻部落,商人自新疆西南而行,抵于波斯,復西行,入于小亞細亞,然后達于歐洲。水路自歐洲放船,出地中海,抵于埃及,然后易船渡紅海、阿拉伯海,抵于印度,船復東行,過馬六甲海峽,東至安南商港,自安南駛行,即至中國。海路自航海術進步,乘時季風前行,其便利遠過于陸路,漢以后之商人,多乘船至中國。
古書曾言昆侖,其說或為當時流行之傳說,或言其受外影響,無論如何,殆難認為追紀西北交通之路。公元前七世紀,秦穆公稱霸西戎,秦立國于今陜西中部,戎人多居于今甘肅,西域交通當有進步。西域本官書上含混之名稱,初指西方之地,當今甘肅、新疆,其后漢使通于大夏、安息、印度諸國,亦以此名稱之。朱士行之經錄稱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寶利房等十八人赍佛經來咸陽,始皇投之于獄。經錄相傳作于公元后三世紀,其說何所根據,今不可知。就年代而論,始皇與印度宣傳佛教之阿育王同時,阿育王曾遣高僧遠往各國宣傳佛教,高僧來之咸陽,有可能性。以上要為推論,今更有新證證明。安特生(J.G.Anderson)于河南、甘肅發掘遠古遺址,得有無數陶器,其花紋樣式,同于發現于小亞細亞者。其時期距今約六千年,據學者研究之結論,其地居民或自小亞細亞徙入,或受其影響,果爾,則六千年前,東西已有交通。周代興于西北,重視玉器,中國本部固無重要產玉之區,周歷初以七日紀日,同于外歷,均足以促人審思。及至末年,數學、天文視前大有進步,今據學者之研究,疑其深受外國之影響。秦始皇統一中國,銷兵器,鑄為金人十二,漢武帝討伐匈奴,得其重器,列休屠王之祭天金人于甘泉宮中,又得昆邪王之金人,知其燒香為祭。金人之為佛像,雖或近于猜想,而中國與亞洲西部及印度之有交通,實無疑問。武帝又謀夾擊匈奴,遣張騫西通大月氏,及抵大夏,見邛竹杖蜀布,詢之,知其來自中國,由印度販至大夏者。據此,西南亦有交通。后班超降服西域,遣其屬下甘英西通羅馬,至波斯灣而還。其時歐洲、中國尚無直接貿易,貨物均由安息商人轉運。
歐洲人深入亞洲腹地,始于馬其頓王亞歷山大之東征,初波斯西攻希臘,大敗而歸,雙方之仇恨深積。后馬其頓國崛興于希臘之北,降服南鄰城邦,其名王亞歷山大幼受希臘文化之影響,深表同情于希臘,具有雄心,欲征服世界,乃自小亞細亞追逐波王,侵入亞洲西部,公元前三二六年,逾越興都庫什山,抵于印度西北。會軍士思歸,不肯前進,始留戍兵而歸。斯役也,促進歐亞之交通,從軍之希臘人有留于印度西北者,建立小國,商人往來者尤多,販運貨物,中國絲遂傳入希臘。亞歷山大之師亞里士多德,西方之大哲也,其所著之書,中舉絲名,絲在古代為我國之特產,而亞里士多德能言其名,則其傳入歐洲殆無疑義,且進而為中歐交通之鐵證。及羅馬興起,貴族需用絲綢,價同黃金,商人謀自海上來華貿易,先是羅馬征服埃及,商人渡海至印度貿易。至是,船自印度東行,渡馬六甲海峽,泊于安南,其地遂為國際商業重要之地。公元后一六六年,我國史稱大秦安敦王遣使朝貢。其時值羅馬皇帝安敦勒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在位,使臣自安南遵陸路行,直達京都洛陽。其事未見于羅馬史,古代商人,固有冒充貢使者,其重要則證明羅馬商人之來中國耳。船向東北前行,即達中國海岸。二二六年,二八四年,皆有羅馬商人來至廣州之記錄。
據上所言之史跡,上古中歐當有交通,公元后三世紀,海上亦有貿易,亞歐往來遂有水陸二路。陸路商人結橐駝隊而行,逾越流沙,途中困苦,非言可喻;水路船舶運輸往來較易,商人乃多舍陸就水。后羅馬分東西二國,五世紀,西羅馬衰弱,野蠻部落侵入,歐洲之文化大受摧殘,地理上之知識喪失幾盡,歐亞之商業中衰。幸東羅馬維持其間,及穆罕默德創立回教,統一阿拉伯半島,同化野蠻土人,國勢驟強,阿拉伯人掌握東方貿易之權。中國時唐太宗在位,政治清明,境內安堵,待遇境內外人,大體上本于種族平等之原則,國際貿易頗發達于廣州、泉州,外人來至廣州者尤多。后唐室衰微,海盜漸多,流寇禍作。其首領黃巢所到之地,屠殺焚掠,無惡不作,及陷廣州,盡殺外人,商業始衰。北宋旋復舊觀,南宋軍餉無出,獎勵商業,海道轉盛。十三世紀,蒙古崛起于北方,其酋成吉思汗率其鐵騎出征,無不勝利,子孫乘其余威,跨有亞歐二洲,驛站之傳遞公文,橐駝隊之往來,海上之交通,均稱便利。蒙古人之待異族也,優于漢人、南人,教皇遣人東來,馬可·波羅仕于其朝。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東羅馬之首都君士坦丁堡,掌握歐亞交通之路,回商乃壟斷商業。
十五世紀,歐洲經濟狀況視前進步,東方物品之市場需要正殷,葡萄牙王子亨利(Prince Henry)獎勵航行,謀覓新路,以達印度,其勇于冒險之船長沿非洲海岸前進,一四八七年,抵于好望角,一四九七年,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率船繞道非洲,次年抵于印度,阿拉伯商人阻其貿易,然終販買貨物而歸。葡王得報,遣兵艦東渡,俄據印度西岸之良港歌那(Goa),以為根據之地,東取馬來半島之馬六甲。葡人復來中國,租借澳門,壟斷東方貿易凡有百年。荷蘭、英吉利商人起而與之競爭,荷蘭占據南洋群島,英吉利經營印度,法蘭西諸國商人繼之而至,東方葡萄牙之商業大衰。歐洲人東下之動機,始則求一航路直達東方,販運貨物以得厚利,航海家冒險事業之進行,常得國王之助,國王之政策,則欲收其發現之地,臣服土人,建立廣大之海外帝國也。其遠離祖國之水手,多為富于欲望之青年,對于土人無惡不作,及據其地,葡王委任官吏治之,天主教神父后隨之往。葡人初受回人之虐待,常有報復之心,強改土人之宗教,東方人民惡之。其販運回歐之貨,多屬貴族之奢侈物品,如中國之絲綢、瓷器、紡機,印度之寶石、美珠、顏料,南洋群島之豆蔻、丁香,其運來之物,以玻璃鐘表等為多。
綜觀中外交通之略史,吾人發生之感想,則為世界各國民族因其地理上之位置,歷史上之遺傳,社會上之需要,產生特殊文化,及與外國接觸,而始有所比較,發生異同,引起學者好奇研究之心理,常于有意無意之中,吸收外國之思想,模仿其制度,試以個人證之。個人生于社會之中,自少而壯,由壯而老,莫不深受家庭、社會環境之陶冶。其習慣行為思想言論之大部分,概為社會之產物,換言之,個人之在社會,以模仿為多,聚個人而成團體,合團體而成國家,由國家而成世界。世界文化之進步,一由于天才之創造,一賴模仿之能力。是故民族于世界上之占重要地位者,常于二者覘之。模仿之性質可別為二,其一于有意無意之中,自由模仿他國之長,以補本國之短,其一于困辱之后,始知墨守祖法之不利,迫而模仿他國之長。一八六〇(咸豐十)年前,我國所受外國之影響,多屬于前者,其后所受之影響,多屬于后者。其區別雖近于牽強,而目的則欲讀者之深思也。學術思想所以促進人類之幸福,不受國界之限制,我國文化于世界上之貢獻,吾人多能言之,而外國影響我國者,吾人亦當知之。茲略言之于下。
一、物產
物產以種子、土壤、氣候之關系,各地不同,其自外國傳入者,不知凡幾。據學者良芳(Berthold Laufer)所著之中國伊蘭(Sino-Iranica)一書,考證中國植物自伊蘭傳入者,不下數十種,如苜蓿、葡萄、石榴、胡麻、胡桃、胡荽、胡蒜、胡蔥、豌豆、菠菜、胡蘿卜、棗樹、黃瓜、西瓜、無花果、皂莢、鳳仙花、胡桐之類,歷時既久,中或改去胡字,今為吾人常見或日用之物,將信其原生長于國內矣。其傳入中國則始于西漢,張騫奉命西通西域,攜植物種子如苜蓿、葡萄而歸,后人以其開通西域,凡自西方傳入者,多附會于張騫。其信而有征者,則為苜蓿、葡萄,余多逐漸傳入,茲舉數例,說明于下。武帝得天馬于大苑,知其性嗜苜蓿,求取其實而歸。《史記》記葡萄亦于此時傳入,漸種植于北方,《唐書》記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于苑中種之。西瓜原為產于西域之瓜,夏時食之,可以止渴,其種亦得之于西方。梁(六世紀)陶弘景曾言寒瓜,其種類今不可知,五代史稱胡蟠居契丹(十世紀)始食西瓜,稱其破回紇得有此種。十一世紀,宋仁宗遣使航海買早稻萬石于占城,分授民種,其分種成熟正與江南之氣候相宜,農民胥受其賜。十六世紀,閩人得番薯種于外國,磽瘠之山地,皆可種植,木棉玉蜀黍亦自外國傳入。關于錦繡礦物藥石,亦有自波斯傳入者。其關系于民眾生活,至深且巨。
二、思想
戰國時中國之時間觀念、天文、算術等均有進步。法國著名之漢學家馬斯泊羅(H.Maspero)稱當時及漢代文學與印度、波斯相似,昆侖故事傳自印度;中國初無行星之名,至是始乃知之,其分一日為十二時,為巴比倫之制;墨子所論之幾何原理,同于埃及、希臘。其說今無傳入中國經過之明證,尚難指為中國確受其影響。《史記》中律歷志所言之律,盡同于希臘哲學家之言。外國學者之發明早于吾國,國內先無討論,一旦忽有若大之進步,頗足以促吾人之深思。其后中外交通益繁,佛教傳入,其始祖釋迦牟尼感于生老病死之痛苦,入山求道,了解人類痛苦之道,由于欲望,倡說八正道于世。其教初基于印度固有之因果輪回,免除痛苦之思想,而佛陀闡明倫理上之責任,及慈悲不殺之旨義,合知識情緒二者,成立宗教。佛教傳至印度西北,深受環境之影響,僧侶敬拜佛陀為天神,重視祈禱,由是傳入中國。后漢始譯佛經,自東晉至唐為其極盛時代,譯書既多,流傳益廣。南北朝時士大夫多與高僧往來,研究佛法,其以儒家自命而辟佛者,間接亦受其刺激。相傳梁武帝時達摩東渡,我國始有禪宗,其要旨則所謂“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也,識者近謂禪宗產于中國。無論如何,要與佛教有關。宋代道學家之主敬主靜,即佛教靜坐之變相。大儒陸九淵、王陽明等莫不吸收禪宗之思想。佛教傳入之后,方士受其刺激,效其組織,成立佛教變相之道教。佛教既入中國,后于名都大城,創立佛寺,其中佛像繁多,種類不一,見之警人身心,因而附會天堂地獄之說,隱喻獎善懲惡之意,又如輪回之哲學,說明吾人今生之享受,定于前生之功過,來生之享受,定于今生之行為。其說深入人心,往往于無意之中,約束人民,亦來自印度者也。回教、耶穌教傳入中國,亦有相當之地位。十七世紀,耶穌會教士輸入西方科學知識,固其明證。清代漢學大師戴震等精通數學,其考證之精核,或受科學方法之指導也。
三、文學
中外交通以來,文學受外影響,秦漢以前,固無論已。及佛教傳入,其經典梵文本也,漢人能讀者極少,漢末開始翻譯佛經,高僧以其文法構造之不同,字義思想之懸隔,襲用文學上之舊語,不免于附會失真,后乃創造新語。近據日人《佛教大辭典》所收入之新語,凡三萬五千,其少數成為我國文學中之習見語,如法界、果報、剎那等之類。漢譯之佛典文體,迥異于通行文字,其倒裝句法,解釋語法,形容詞句,及無韻詩歌,皆足以覘外來文學之色彩。譯者頗求其通俗,梁啟超稱之白話新文體,蓋有所見。宋代之白話文學受其影響,其最明顯者,則理學家之弟子效法禪宗之語體文而作語錄也。戲曲亦為文學作品之一,說者疑其曾受外國影響。許地山分析梵劇,謂歌舞樂在賓白之間,以及表演之角色,類近我國之雜劇,其相似之點,雖不足為曾受印度影響之明證,然而固為有力之建議。其他影響于文學者,尚有反切、四聲等,反切之法,合二字之音為一字,上必雙聲,發音相同,下為疊韻,收聲相葉。說者嘗謂反切由于天籟,不煩人造,殊不盡確,應劭《漢書》之注,孫炎《爾雅音義》之作,其法始乃大行。梁時慧皎所著之《高僧傳》中有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傳聲則三千有余。”要之,音韻學之始祖,皆在曹魏,適當佛教傳入之后,其受印度影響,殆無疑義。其可附帶說明于此者,則為字母。《隋書·經籍志》云:“自后漢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高僧傳》記謝靈運咨詢和尚慧睿經中諸字并眾音異旨,于是著《十四音訓敘》,條例梵漢,及唐失傳,高僧守溫因而整理來自西域之三十六字母,以為切韻。四音由音韻演進而成,沈約自稱為其所作,殆不足信。韻學與律詩關系密切,唐代律詩之盛,豈無因乎?
四、科學
科學之受外國影響者,秦漢已如上述。及唐武則天臨朝稱治,六八四年,頒行高僧根據印度歷法改訂之光宅歷。七二一年,玄宗詔僧一行再訂歷法,一行步推,依據印度成法。同時數學亦有進步,不幸書久佚亡,內容今不可知。元時領土初有中亞細亞,回人之天文學術傳入,郭守敬受其影響,造成負有盛名之儀器,明末耶穌會教士來華,其人精通天文、物理、數學、醫學,將其輸入中國,以為布教之機會,其最著名者,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利瑪竇習學中文,身穿華服,初傳教于廣東肇慶,后往來于南京、北京,上表進貢于明廷,后死于北京。學者從之游者,有徐光啟、李之藻等。其所著重要科學之書,有《幾何原本》《同文算指通篇》《西國記法》《勾股義》《測量法義》等,其所作之萬國輿圖,故將中國置于中央,迎合時人之心理。死后,頑固者目其教為邪教,政府放逐教士于澳門。其時滿洲崛興于東北,迭敗明兵,明廷以炮御之,復召教士工匠于澳門,鑄造大炮。湯若望等應詔入京,教士鑒于舊歷沿用已久,中多錯誤,得旨開創歷局,編纂歷書,兼造天文儀器。儀器種類頗多,以銅為之,精巧稱于一時,后清兵入關,幸賴多爾袞之保護,未盡損壞。未幾,清廷頒行教士編定之《時憲歷書》。及康熙親政,南懷仁奉詔,筑觀象臺,置新造之天文儀器于其上,后鑄重炮,以平三藩之亂。康熙詔其進講西學,扈從巡游,復命其考察各省之地勢,繪成地圖,歷三十年始成,名曰《皇輿全覽圖》。總之,耶穌會教士之影響于我國者至深且巨,數學,我國學者自受其指導,研究頗有心得,久已失傳之天元四元,復明于世,漢學大師且多精通數學。其所造之天文儀器,頗有美術上之價值,八國聯軍之役,德國取之而歸,大戰后復還我國。醫學傳入國內,新法牛痘拯救無數嬰孩,其法創于英人,一八〇三(嘉慶八)年西班牙人傳之于中國。
五、美術
美術之范圍頗廣,先秦美術作品之存于今者,多為金石。殷周彝器無制造人名,其花樣多同,無個人創作之表現。及至漢代,花樣之種類增多,其獸形類于外國之樣式,蓋自西北傳入者也。漢代石刻,內容或為神仙故事,或歷史人物,或為奇獸,要多粗淺,迨佛教傳入,乃深受希臘、印度一派之影響。初亞歷山大東征,留戍兵而歸,及其死后,其部將立國于西亞,希臘美術傳至亞洲,大夏、安息所鑄之錢幣,中印王像,其服裝同于希臘神像,及大乘佛法盛于印度西北,雕刻之佛像驟增,其裸體之狀態,肌肉之弛張,生氣勃勃,一如活人,模仿希臘之跡,顯然可見。其表現之意義,則為印度之思想,故有印度、希臘雕刻一派之稱,至是,隨同佛教傳入中國。近時斯坦因(Aurel Stein)等于新疆掘得之佛像,尤其明顯之證,古書稱高僧往印求經者,曾帶佛像回國。北魏大同(今名)龍門刻石,工程偉大,精細為國內希印雕刻之名作。塑像,唐代楊惠之負有盛名,其所塑之神像,神態弈然,其四尊羅漢尚存于蘇州甪直鎮。元代之建筑,頗受回人之影響,佛寺之建筑,塔則仿自印度,國內屋脊今皆斜下,亦受外國影響。繪畫秦漢殆無名家,畫家所用之毛筆,繪畫之材料等,均為中國產物,佛教對之,雖無重大之貢獻,要亦與之有關,或促進其發展,如供給畫家佛教上之人物,顧愷之于寺中作畫,衛協善畫神像等,皆其明例。梁武帝虔奉佛教,遣人至印度,習學壁畫,近時西北廢寺發現壁畫,其畫固自外國輸入者也。茲為便利之計,附言歌樂于此。漢代初以安息之獻,角觚戲興,西域樂器先后傳入中國者,有胡角、鳳首箜篌、琵琶、五弦笛等,并得樂工教習歌曲。隋煬帝定樂為九部,中多胡樂。唐興,《霓裳羽衣曲》由涼州節度使進獻。歌舞亦受外國之影響,如《舊唐書·音樂志》稱撥頭出自西域,胡人為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為此舞以象之也。自唐以來,音樂雖有變遷,而大部則仍相承,迄于今日。
以上列舉之事實,不過證明中國之文化,曾受外國之影響,歐洲近代文化則合埃及、希臘、希伯來、羅馬諸國之貢獻而成,原無足異。閉關自守之國,既無比較之可能,又無有力之刺激,進步往往困難,文化實無國界,歐洲思想,亦曾受我國之影響,如法國哲學家盧梭主張自然,則受我國老莊之影響,尤有進者,外國文化傳入之后,多受我國思想環境之影響,成為國內文化之一部分。其性質遂迥異于其在外國,吾人無須自餒也。同時,各國之政教,多基于歷史環境,于其傳入之前,當有深切之研究,詳論其利弊,外國之事物,未必皆有良好之結果,鴉片、煙草、楊梅毒瘡尤其明顯之例。鴉片之為害也,破壞道德、家庭幸福、經濟狀況、政治安寧,其種子自西北傳入,近代自海上運入,造成大禍,其事詳于后篇。煙草植于美洲,西班牙人移植于菲律賓島,閩人傳其種于福建,于是我國始有旱煙、水煙,最近卷煙傳入,漏卮甚巨,且有害于人生。楊梅毒瘡,說者言其初盛行于北美洲之南部,西班牙于發現新大陸后,占據其地,其遠離祖國前往之青年,多貪利無饜,放縱情欲,染得病菌,惡疾遂傳染于他地。我國之有此病者,始于廣東,其后漸及于他港商埠。三者之害,顯而易見,盡人所知,思想制度不善利用,其害或甚于此,盲從不辨是非之害,可不懼乎?總之,一國容納外人,國際上接觸之機會增多,發生比較之心,造成精確判斷之能力,天下之害,實多生于蒙蔽狹隘也。
古代中外之交通發達,何近代閉關而拒絕外人之甚耶?吾人就歷史上之背景而言,上古中國外患力足以制之,及五胡之亂,促進華夷互通婚姻之機會,隋唐曾去種族上之畛域,隋文帝、唐太宗之后皆為胡人,蕃將之立功于唐者,史不勝書。宋受外族之蹂躪,夷夏之觀念漸嚴,理學之發達,士大夫之胸襟益狹,終見滅于蒙古。蒙古人之入中國也,大肆屠殺,既平宋后,虐待漢人、南人,而又防其叛亂,禁南人攜帶兵器。其治中國也,唯知榨取于民,人民不堪其苦,加以喇嘛之橫暴,官吏之貪墨,貧民鋌而走險,相聚為盜。朱元璋力并群盜,驅逐蒙古人而北,為事頗易,斯見漢族之痛心疾首于蒙古人矣。其明顯之結果,對外引起仇外之心理,對內容忍皇帝威權之擴張,及明中葉,倭寇之禍大作,時人深信海上貿易,為其禍根,朝廷采用嚴監外人之政策,閉關思想,遂益發達。明亡士大夫抱有恢復之心,其種族之恨惡,往往見于著作,其入人之深,乃轉而以對歐洲人。歐洲人初至東方,不知中國之情狀,其政治家以為文化發達之古國,不惜卑辭厚幣求于中國。其遠渡之水手,多為富于野心之青年,類近海盜,無惡不作,反足以引起華人之惡感。其心目之中,以為外人嗜利無厭,心懷叵測,凡其要求概以惡意推度,自不研究其國中情狀。朝廷大臣堅信夷人恃茶葉、大黃為生,封艙為駕馭之秘法,遂益驕傲,荷蘭諸國且以藩屬自居,相沿既久,視為固然。吾人于言中外沖突之先,當略先知其來華之經過,及其貿易之情形。
初葡萄牙占據歌那,東取馬六甲。一五一六年,葡人附船抵于中國,明年(正德十二),葡船八只來粵,泊于上川島,遣船偕同使者前往廣州,葡船繼之至者,貪婪橫行,官吏捕之,不得,囚其使者,使者俄死于獄中。一五二二年,葡使復至上川島,明兵擊之,余眾逃往電白島,葡人心猶未已,航達福建、浙江,經商于泉州、福州、寧波。而寧波商業后頗發達,葡人強改華人宗教,誘拐婦女,長官討之,殺教徒一萬二千,內有葡人八百,泉州亦殺葡人,生者逃往電白,電白遂為商港。一五五七(嘉靖三十六)年葡人納賄粵官,得于半島澳門(今名),創立貨棧,曬干貨物,葡人始得經營澳門,歲納地租。中國對于澳門建筑城墻,限制交通,但仍認為領土之一部分,一八〇八年,英與法戰,遣艦保護澳門,兩廣總督吳熊光令其撤去,奏報朝廷,嘉慶責其防范不善,即令革職辦罪。其地訴訟歸于華官判決,犯罪之葡人由其官員交出;管理商業之權亦操于華官;如后廣州停止英國商業,而葡官亦奉命拒絕英人住于澳門也。葡人既得根據地于中國,壟斷遠東之商業,阻撓后至之歐商。其政府謀得權力,先后遣使臣來華,前三次未達北京,第四使臣得覲康熙,第五則朝雍正,第六則覲乾隆。使臣執禮甚恭,然終不得要領而歸。其后葡人之貿易衰微,而澳門仍為外人居留之所。
耶穌會于一五五二年成立,宣傳天主教于東方,葡人管之甚嚴,教皇派僧召集會議,議定章程,凡至中國者,須通華語文字。其人曾受良好教育,輸入科學知識,迎合人民之心理,利瑪竇謂上帝為天,許其教徒祭祀祖先,禮敬孔子,信者漸多。后守舊派杜米尼坑(Dominican)等教士來華,指摘其傳教方法,乃開會于廣州,共謀有所解決,而祭祖拜天為會中爭論之焦點,未有結果。舊派詆毀耶穌會于歐洲,報告教皇,葡人惡之,曾阻礙其工作,葡法大學傾向守舊,惡其思想之激進,耶穌會之敵增多。教皇改變態度,一七〇四年,派使攜帶教令來華,禁用天字及拜祖先,康熙根據耶穌會教士之報告,捕之送往澳門,教皇再派使者入京覲見康熙,請求管理教士,康熙不許,先曾遣使往謁教皇,杳無信息,疑其被殺,乃嚴待之,一七一三年,教皇解散耶穌會。其時江南有教堂百所,教徒達十萬人,他省亦盛,竟以教皇之禁令,發生阻礙。一七二三年,雍正嗣位,閩浙總督滿保奏請安置教士于澳門,改天主堂為公廨,上諭許之,天主教始衰。其原因則教士內訌,教皇妨礙耶穌會之傳教事業,雍正以教士干涉內政,而身信奉喇嘛教甚虔,故禁其傳教,及乾隆末年(十八世紀末葉),教亂迭起,天主教之禁令益嚴。一八五〇年,嘉慶嚴禁教士刻書,而神父傳教之熱忱,未為稍挫,仍有潛入內地者。基督教初以荷蘭之保護入于臺灣,及荷人被逐,教士亦去。一八〇七年,英國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粵,馬禮遜,基督教牧師也,譯成《新約》,刊行中英字典,我國遂有基督教。
方葡萄牙經營東方也,西班牙雇用之水手發現美洲,一五二一年,其臣麥哲倫繞行地球,發現菲律賓島,西人據之,后海盜林鳳(舊誤譯為李馬奔)率眾攻之,戰敗而逃。閩官遣艦偵之,抵于菲律賓島,次年,其長官遣教主二人為使,附艦渡閩,請求通商,使者無所得而返,再遣使者重申前請。中國許其貿易于廣州,然遭葡商之忌,無大發展。十七世紀,閩人經商于島中者日增,西班牙先后慘殺無辜之華人凡四萬余名。其南渡者不為稍止,西官乃限制華人六千住于島中,每人年納丁稅六元,其不改奉天主教者逐之,商業仍操于華人之手,西人用墨西哥銀幣買貨,墨幣由是流入中國。
荷蘭人繼二國東下,先是,荷蘭為西班牙之屬地,其人堅決果敢,信奉新教,不堪西班牙之虐待,叛而獨立,會西班牙、葡萄牙合并,嚴禁荷商販貨于葡京。荷船迫而東渡,一六〇四年,抵于廣州,以受葡人之阻撓,先后均無結果,改用兵船來攻澳門,不勝,逃之澎湖,更退據臺灣,一六六一年,鄭成功自廈門率軍二萬余人,渡海攻取臺灣,荷人大怒,遣船援助清兵攻陷廈門,而于臺灣則無如何。其后康熙征臺,詔荷蘭助戰,而荷艦失期,及至,臺灣已定。荷商既不得志于廣州,乃于福建要港賄賂長官,販運貨物,一七六二年,始設商館于廣州。其政府謀得商業上之權利,以為能得朝廷之許可,則廣東之困難立即解決,又以卑事日本幕府,得通商于長崎,遂迭遣使卑辭厚幣來至北京,遵朝見之慣例,行三跪九叩首之尊禮,惜皇帝未曾稍假顏色,允許其請也。結果清廷定其貢期,列為藩屬。
十六世紀末葉,英王致拉丁文書于中國皇帝,請求通商,不幸船破。其商人俄組織東印度公司,遣船駛往廣東,葡官鼓動粵官拒之,英船曾炮擊虎門,直駛黃埔貿易而去,其后至者,均不得貿易。會政府許其通商于臺灣、廈門,二地貿易頗形發達,后臺灣以降清而商業告終。一六八五(康熙二十四)年,朝令各口準許夷船互市,公司船俄至廣州,海關監督借端勒索,公司患之,遣船貿易于廈門、寧波,奈其長官非法需索甚于廣州,公司后設商館于廣州,并鞏固其地位于印度,在華貿易之額數占據第一,益欲改良商業之狀況。一七七八(乾隆四十三)年,英王遣使前往北京,中途船覆,杳無音信,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王遣大使馬爾加尼(George Macartney)來華。粵督以大班之稟報,奏其來祝萬壽。明年,船抵大沽,馬爾加尼自稱王使,華官頗禮敬之,遣船送往北京,中立大旗,書曰:“英使朝貢”。及抵北京,乾隆適在熱河,乃往覲見,大臣說其遵行三跪九叩首之禮,不得,乾隆許其以覲英王之禮朝見,待之頗厚。大使要求英國公使駐于北京,設立商館,中國開放寧波、天津,而于舟山、廣州附近,給予英商住留之地,改減船稅。原文并無傳教之要求,而乾隆詔書則言及之,蓋由于譯文之誤也。大使又說中國派遣公使駐于歐洲,清廷復文一一拒絕,遂無成功而歸。十九世紀初葉,英美交戰,英艦捕獲美船于澳門,粵官強令英商交出,爭執頗烈,后始讓步解決。英國欲因解困難之癥結,且謀商業上之利益,一八一六(嘉慶二十一)年,命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為大使東渡,及抵天津,長官說其叩頭,不許,旋至通州,即往圓明園,明日,至園,大臣強其覲見,大使謂其疲乏已極,而國書禮服未至,拒絕其請,朝臣說其回國,英使遂即日出京。初嘉慶欲其如禮覲見,諭稱不肯跪拜,即阻其入京。而大臣貿然同之至京,乃欲于困乏之余,而強其三跪九叩首也。大使之來,徒增二國之惡感耳。
歐洲關于中國之知識,多賴法國教士之報告,教士富于學識,本其見聞,發為文字,而使歐洲人稍知中國之狀況。法國在華之商業殊不發達,其王未曾遣使遠至北京,請求通商,一六六〇年,始有商船來華,一七二八年,設立商館,而貿易仍無進步。十九世紀之初,英法戰爭,法國海外之勢力遠非英比,其廣州領事(大班)館之旗升落不定,其他在粵貿易之商人,有美利堅、瑞典、普魯士等國。美國初為英國屬地,其需用之茶葉,由東印度公司轉運,獨立后,始謀直接貿易。一七八四年,美船抵于廣州,其商人無專利公司之限制,而船只較小,便于運輸,商業日益發達,在華之地位躍為第二。其余諸國均有商船來粵,惜其商業無足輕重,華官待之,多如英美商船。
水路通商略言于上,陸路與俄國交涉頗早。俄自蒙古人侵入以來,頗受中國之影響,及獨立后,經營西伯利亞,數遣使臣來至北京,中國殊輕視之。方清帝入主中國也,俄軍乘勢侵入黑龍江邊境,建筑雅克薩城,駐兵守之。會康熙于平三藩之后,出兵圍陷其城,毀之而歸,未幾,俄軍復至,清兵攻之。一六八九(康熙二十八)年,二國代表議和于尼布楚,締結條約,以外興安嶺為界,毀雅克薩城。二國邊吏不得容留逃入,嚴禁獵戶人等擅越國界,其有護照者始得貿易,違者各送本國治罪。約成之后,俄皇迭遣使臣來華要求改約,使臣遵守三跪九叩首禮,亦無結果。一七二七(雍正五)年,二國始訂恰克圖條約,初外蒙古與俄先有互市,及其臣服中國,疆界互市之問題,須協商于清廷。至是,雍正許俄議定疆界,成立恰克圖條約共十一條,明年,批準。條約規定邊界,互交罪人,遞送公文,及貿易往來。中國許俄建筑俄館于北京,教徒可學華文。會清用兵于準部,患俄助之,亦遣使臣入俄。二國自訂條約后,恰克圖之百貨云集,乃為漠北貿易之中心點,邊吏增訂互市章程。新疆自征服以來,邊界貿易亦有進步。一八〇五(嘉慶十)年,俄船二艘駛入廣州,關督延豐許其卸貨,朝廷嚴辦其罪,其心理則俄人于陸路上已有通商之權,不應再至廣州,販運貨物,而違反舊制也。
十七世紀,廣州、廈門、寧波皆有外船互市,稅收以廣州為輕,其貿易最為發達。一七〇二(康熙四十一)年,朝廷遣皇商來粵,壟斷國際貿易,其人非廣州之大商,外商惡其販賣遲延,粵商恨其專利,官吏嫉其奪去稅權,皇商乃許粵商貿易,其條件則每船納銀五千兩,其制后廢。商人羨其獲利之厚,趨之若鶩,互爭利益,俄自覺悟,成立公行,劃定物價,外商抗議于總督,謂將離港他往,總督飭命解散,商人旋復組織公行。政府防范商欠及其弊端,禁止商人私與外商貿易,更以廣州商業之發達,便利征稅及監督外人之計,一七五七(乾隆二十二)年,詔定互市限于廣州,公行遂有所恃,其會員驕奢日甚,破產者多,乃告解散,一七八二(乾隆四十七)年,欠債事起。其時民間借債月利低者二分,高者五分,外商運銀來粵借于商人,或博重利,或預訂貨,商人有無力償清者,官管行商益嚴。行商一稱洋商,其行曰洋行。據林則徐之奏文,嘉慶十八(一八一三)年,粵海關總督德慶奏準設總商綜理行務,嗣后承選新商須聯名保結,行商凡十三家,漸有倒歇,道光九(一八二九)年,存有怡和等七行。監督延隆準新商試辦一二年,由一二商人具保承充,十三行遂復。其品流始雜,欠債增多。一八三七(道光十七)年,粵督鄧廷楨會同關督奏復聯保舊制,其歇業者準其聯保承充,不添一商。行商設有公所,會商公共事務,對于政府負有管理外人之責任,對于外商有指導之義務。外商販來之鴉片、棉花,輸出之茶葉、絲綢,初皆由其轉賣,貨物之高低,供給之量數,由其操縱,并得抽貨價百分之三為其歸還欠款,或補償損失之費,不幸其款后歸官吏。
外船之駛往廣州也,先行商定稅金規禮,然后入港。清代關稅,一曰船鈔,一曰貨稅。船鈔根據船只之大小分為三等,其法測量船身之長寬,按其等級,以定其額數,貨稅頗輕。正稅而外,官吏規禮多至六十余種,雍正收之歸公,乃另立名目,勒索如故。其收入最豐者,首推海關監督,監督身為滿人,多為皇帝親臣,管理商業,征收稅銀,其品秩與督撫相等,不受其節制,先是外商不堪勒索之苛擾,則共同抗議,而以不至廣州為要挾,粵官斟酌情形,或去弊端,或拒其請,迨朝廷宣示廣州為互市商港,外商始失要挾,及行商成立,管理之法益備。外船來粵,先得澳門同知之許可,租屋于行商,及船泊于澳門,船主至其衙門,雇用領港通事買辦(買辦亦得于船入黃埔時雇用),船再駛往虎門,關督丈量船身,視其貨物,定其稅金規禮,船主如數與之,然后駛入黃埔。及船泊于碼頭,船主報告貨物于行商,由其介紹,或供給房屋、貨棧、仆人等。其販運貨物也,專向行商磋商,價值之高下,由其決定,外商茍以價太低廉,亦得拒絕出售,顧其遠至廣州,不愿再運貨物回國,而多尊重行商之意見也。運回之貨物,多為絲茶,法律規定每船載絲不得過于一百四十石,余多茶葉,其價亦由行商定之。外船之在黃埔也,期約三月,通事買辦皆得厚利,官吏胥役亦有贈遺。其不入港者,海關之稅額,官吏之規禮,均得減半,行商之傭錢,則為二千余兩。
廣州之外商無購地置產之權,其住宿辦公之商館,數凡十三,為行商之產業,蓋行商十三也。租金取價低廉,外商每于冬季入住,貨棧則在河南,亦為行商之產業。粵官之管理外人,也訂有條例,后益嚴厲。其要款如下:一、兵船不準駛入虎門泊于內江。二、番婦槍炮不準帶入商館。三、洋商不準私借夷款。四、夷商雇用華工不得過于定額。五、夷商不準乘轎。六、夷商不準劃船取樂,每逢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始得往游花園。七、夷商不準直接上稟長官,須由行商轉遞,并受其管理。八、夷商不準久居商館,販買之后,須即回國,或往澳門。規則中一、二、七三條,執行頗嚴,其禁兵船武器者,以防變起不測,而不易管理也。其禁婦女之入商館,一由于中外禮俗之不同,其時國內上中級社會之婦女,居于深閨,而外國男女同行,其服裝自華人觀之,則為妖艷,迄今民間尚有取種之說,一防外人久住不去也。其禁外人上稟,官吏稱為嚴肅政體,且為免除煩擾,便利行商管理之也,后以弊端叢生,始準夷商于城門遞稟。其禁外商久居廣州,外商去時,雇用工人看守商館,往來概須納費,其無住宅于澳門者,出納重賄,亦得私留住于商館。第三條嚴禁借債,而行商常以中外之利息不同,多借外款。四、五、六三條均為具文,商館雇用華工,官吏平日從不過問。坐轎之禁,本于輕視之觀念,雖曾發生爭執,然以外人不準行于市中,或自由出外,實無乘坐之必要。其往游花園,向不遵照定例,無事則劃船渡河,散步園中。綜觀管理章程,可稱瑣屑,其動機則官吏認“夷人犬羊之性”,不宜親近,發生事端,又患奸商之欺愚外人,乃借行商保護之也。
行商外商之買賣也,從未訂立合同,雙方均能履行言諾,其信實昭聞于世,相處亦頗和善,尤以伍紹榮誠實不欺,慷慨好施,見稱于外人。其得承充行商者,固須連保,亦當納銀,凡遇大荒河災,均須捐款。一八三一(道光十一)年,朝令歸還商欠,伍紹榮出銀一百十萬兩,一八四一年,英軍將攻廣州,將軍奕山議和,伍紹榮出銀一百萬兩,曾自謂其財產,共值二千六百萬兩。其款雖由經商之才能而得,亦賴專利制度之助,其不善經商而拖欠外債無力歸還者,亦復有之。其時國際貿易之普通言語,則為印度、葡萄牙、英吉利語言合成之洋涇浜話,通事習學其常用之話,全國無精通外國文字之人。商業雖受種種限制,然以實用科學之進步,世界交通趨于便利,年轉興盛。一七五一(乾隆十六)年,黃埔江中外船十八,英占半數,一七八九(乾隆五十四)年,增至八十六只,大多數屬于英商,美船次之。《達衷集》記一八三二年,英船有北上覓新港貿易者,及抵上海,其船主稱前來船七八只,現大船七八十只,買茶葉三千萬斤,湖絲幾百萬元。外船運來之貨,則為鴉片、洋布、羽毛、大呢、鐘表。自一八一八年至一八三三年,英美輸入之貨,價共四萬二百萬元,每年平均凡二千五百余萬元,中國之輸出者,價凡三萬六千八百萬元,每年二千三百萬元,稅收原定額銀四萬余兩,一七九九年,增至八十余萬兩,鴉片戰前,約銀一百七八十萬兩。官吏之規禮,則不可知。
官吏對于外商欲其遵守慣例,飭令行商通事負責辦理,除征收稅金規禮而外,其曾引起爭執者,則為法律問題。外人自通商以來,住于廣州,犯罪者殊少。期內間有華人毆殺外人,水手亦有醉酒滋事,或誤殺華人,或相仇殺者,初則概歸華官審判,按律治罪,外人亦無異言,后則力謀避免華官之干涉。其主因則中國法律初較外國為優,及后外國改良法律,而中國仍守舊法也。其尤發生困難者,常為誤會傷殺,不知誰為犯人,粵官責令船主、大班交出罪犯。其要求之理由,則共同負責之連坐法也。其法,子犯罪,父連坐,夫犯罪,妻連坐,兄犯罪,弟連坐,一家犯罪,四鄰連坐;甚者一人自殺于仇家之門,主人即犯嫌疑之罪。同時,官吏連坐亦嚴,殺人越貨之案發生,縣官負有責任,境內倘有匪亂大災,長官或受相當之處分。其對外人適用此法,乃當然之事。外人認為不公,事實上負責之人,往往難于負責,因其不知犯人之為誰何,而將其交出也。及起爭執,長官或許外人出金撫恤以作解決,或停止貿易以為恫嚇。外人住于中國,當守國內之法律,固無疑義。外人之辯護,則以官吏腐敗受賂,而判獄多不公平也。其尤難于解決者,則粵官飭令商人對于本國政府之行動負責也。英艦曾捕美船于澳門,粵官嚴令英商交出,英商則謂政府之行動不能負責,幾致決裂。其爭執雖或一時解決,然非適當之途徑也。
清廷之許外人通商,大臣謂其出于皇帝之天恩。乾隆于答英王喬治第三之詔書,自謂天朝之領土廣大,物產豐富,皇帝不愛珍物奇玩,無須外貨。其后俄船駛入廣州貿易,關督奉旨辦罪。朝廷以為俄人已得陸路通商之權,不應再沾天恩也。迨禁煙事起,自稱深悉外夷一切伎倆之林則徐猶曰:“從前來船每歲不及數十只,近年來至一百數十只之多。我大皇帝一視同仁,準爾貿易,爾才得沾此利,倘一封港,各國何利可圖?況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乃聽爾年年販運出洋,絕不靳惜,恩莫大焉。”此種思想足可代表普通心理。其時國內人口激增,生活艱難,教變迭起,禍亂時作,官吏之昏庸,軍隊之腐敗,莫不昭于耳目。而政府尚欲遵守祖法,閉關于交通發達之時代,自不可得。蓋自科學昌明以來,機械學有進步,輪船火車相繼發明,世界各國之關系因之日密,又值工業革命,資本家開辟市場之心益急,外船來粵之多則其明證。商業既日發達,事務劇增,交涉日繁,而政府輕視外國。嘉慶曾以英兵保護澳門,特降諭旨曰:“試思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賓,蕞爾夷邦,何得與中國并論!”又不許其公使駐京,廣州大班不得與長官直接交涉,乃無解決困難之途徑與方法,禍根遂伏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