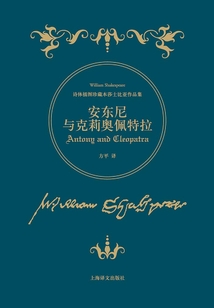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前言
《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這一氣勢雄偉、色彩濃艷的悲劇,大約寫成于1606年,正當莎士比亞的藝術才華達到巔峰狀態之時。早在十九世紀初,詩人柯勒律治就把它看做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外的第五個偉大的悲劇(是四大悲劇的“強大的對手”)[1]。全劇出場的人物共有三十四個,齊斯默說:“即使其中最低微的人物,出言吐語似乎亦滿帶詩情。”[2]赫茲列特說得更妙:“劇中人物在呼吸著,行動著,生活著,莎士比亞并不是在那兒設想他筆下的人物說什么話,做什么事,而是他一下子化身為人物,說他們該說的話,做他們該做的事。”[3]
至于活躍在舞臺中心的女主人公,更是受到評論家們的稱道。西松說:“哈姆萊特是莎士比亞所創造的男性中最偉大的角色,正像克莉奧佩特拉比起他筆下的其他女性,顯現出遠為高大的形象。”[4]克莫特說:“莎士比亞所創造的最偉大的女性形象,克莉奧佩特拉當之無愧。”[5]勃拉德萊把她列入哈姆萊特和福斯塔夫的行列[6],而我們知道,后二者代表了莎士比亞人物創造的最高成就,是兩個不朽的典型人物。
莎士比亞在一系列優秀的劇作中,提出了人文主義的新的人生觀、倫理觀和進步的理想。而這個悲劇中所表達的是非愛憎,可以看做是劇作家的人文主義思想的新的探索和發展。
戲劇一開始,埃及宮廷中就在議論著:他們的統帥這么地迷戀埃及女王太不成話啦,沒想到他甘愿充當風箱“去扇涼那吉卜賽騷娘兒們的欲火”!
這是十分尖刻的批評,這可說是群眾給他立下的口碑,也是群眾舉起的一面鏡子。安東尼還沒摟著他的情婦上場,我們先從這面鏡子中看到了他的不光彩的形象:
當今世界的三大臺柱之一,現在
卻變成給婊子玩弄的傻瓜了。
在藝術手法上,這個悲劇的這一特點很值得注意,人物性格的展開并不完全建立在主人公的自我表現上。在許多場合,我們是通過眾人的眼睛看到安東尼和埃及女王的。在埃及的宮廷中,在羅馬的政治世界中,大家都在議論這兩個中心人物,人人都發表他們的意見。有批評,有譏嘲,也有惋惜、贊美。結果,莎士比亞呈現給觀眾的是在不同視角下的、帶著不同主觀色彩的、獲得不同評價的安東尼和埃及女王。
這個戲劇中的眾多人物,就像樹立在安東尼和埃及女王前后左右的一面面鏡子。歐洲古代史上的這一對風流人物來到這個悲劇中,一舉一動,包括他們的愛情,都產生無數的投影:有重疊、有呼應、有沖突。最有意思的是在同一面鏡子中,最初反映的形象和后來反映的也前后不同,起了很大變化。這樣,人物的性格不斷地在我們眼前變化著、開展著,我們對于男女主人公的認識也不斷在深化。正因為這是多面體的、有深度的人物造型,所以很難對他倆作出一言以蔽之的全面評價。
現在,在他部下的這面鏡子中,聲勢煊赫的羅馬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黯然失色,毫無尊嚴可言。“給婊子玩弄的傻瓜”,這話多么刺耳!我們常說:“先入為主”,這第一個印象非常重要,而莎士比亞卻并不顧惜他的主人公,讓壞名聲走在他的前頭。安東尼的人格起點很低。
安東尼有雙重身份,既是位高權重的政治家,又是一個死心塌地的愛情的俘虜。兩者是相互沖突的。現在他竟然公開宣布:讓羅馬溶化在臺伯河里,準備和過去的政治家安東尼就此告別。“我的天地在這里”,他只想終老在溫柔鄉。無怪他的老部下看在眼里,十分痛心,嘆息道:“他不成其為安東尼了!”
他第二次出場,和羅馬使者邊走邊談,女王沒有在場,他頭腦多少清醒些。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安東尼也有他的內心矛盾——作為政治家的安東尼和作為情人的安東尼在他內心作斗爭。這是理智和感情的斗爭,這一回,理智占了上風,他有些醒悟了,向自己發出警告:
這牢固的埃及鐐銬我必須掙斷它,
再迷戀下去,就毀了我自己。
風云突變的軍事形勢,重新把安東尼推上了政治舞臺。安東尼憑著他的威信和才干,在跟敵對的軍事集團的談判中取得重大的勝利,把正在逼近羅馬的一場政治風暴消弭于無形。為了拉攏他,愷撒把妹妹嫁給他。在這個戲劇中,此時此際的安東尼來到了他政治生命中的頂峰,他再一次顯示出叱咤風云的英雄氣概。
萬萬想不到的是,正當他重振旗鼓,仿佛另有一番作為的時候,忽然從他心里冒出這么一段話:
我要回埃及去。盡管為了和解,
我締結了這門親事;可我的歡樂
卻是在東方啊!
重返埃及,他就此走上了一條下坡路,他的事業一落千丈。失敗、恥辱、滅亡,都在等待著他。
也并不僅僅是由于迷戀女色才導致他的海軍的覆沒。他的老部下、老戰士都懇切地向他提出:在海上和愷撒決戰是不利的。可是安東尼卻因為愷撒“在海上向我挑戰”不愿根據自己較強的陸軍實力制訂作戰方案,而輕率地選擇了對他不利的海上作戰。他死抱著傳統的軍人榮譽觀,把拒絕對方挑戰看做怯懦的行為,丟臉的事。反過來,安東尼曾經要求在陸地上跟愷撒一決雌雄,要求跟他單人決斗,愷撒卻因為這些挑戰對他不利而斷然拒絕。他只考慮怎樣在軍事行動中爭取有利的地位,絕不讓榮譽觀念來干擾他的制訂作戰計劃。
因此可以說,安東尼在海上的慘敗,不僅是迷戀女色的安東尼的失敗,也是只知道逞匹夫之勇、猛拼猛殺的舊一代軍人的失敗。在時勢造成的一代新人面前,作為軍事領袖的安東尼的局限性,完全暴露出來了。
在海上遭到毀滅性打擊之后,安東尼這個曾經“玩弄大半個世界于掌心”的巨人,他的政治生命可說已告結束了。本來統治著大半個世界的他,現在只有一個身份了:愛情的奴隸。埃及女王像一個闖了禍的小女孩,流著淚向安東尼討饒:“原諒我,原諒我吧!”安東尼這樣安慰她道:
別掉下一滴淚;你一串淚珠中的一滴
就抵得上我贏得而又失去的那一切。
給我一個吻吧。
現在,埃及女王的懷抱就是他最后的王國,他的生命意義全在其中了。可是強大無情的愷撒好像是可怕的命運,在粉碎了他的政治王國之后又毫不留情地要摧毀他的愛情王國了。他派出使者用花言巧語去拉攏埃及女王;恰好讓安東尼看到:埃及女王正伸手給使者親吻。這一強烈的刺激使他感到腳下的立足點在動搖;毀了他的小小的愛情王國就是毀了他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他那像怒獅般的咆哮是可怕的。傾盆大雨般的辱罵降落到了埃及女王的頭上,什么難聽的話都說出來了:當初他遇見她,她只是“過世的愷撒他盤子里的冷飯殘菜”罷了。
莎士比亞對于他筆下的主人公一點也不護短,甚至沒有一點顧惜;讓他在這場戲里出丑出個夠。當安東尼把什么臟話都罵出口時,他也是在自我譏諷,糟蹋自己的形象。拋棄了一個王國,只是為了一個“破鞋”,他自己臉上還有什么光彩呢?安東尼的形象一落千丈,墮落到這個地步,已經不能再墮落了。他的一生可說是失敗的一生,毫無意義的一生,因為他現在什么都不是了,連情人安東尼也不是了。
可是莎士比亞是一位心胸寬廣的人文主義劇作家。他不準備把安東尼一筆抹殺。安東尼曾經從羅馬派人給埃及女王送去一顆珍珠,致辭道:“那堅定的羅馬人向偉大的埃及女王獻上這一顆蚌殼里的珍寶。”
現在,把安東尼和埃及女王的一段史跡寫成一個驚心動魄的悲劇,就像一個采珠人——從外表粗糲的蚌殼里發現埋藏著晶瑩光澤的珍珠。這光澤的珍珠就是莎士比亞所發掘的人性美的象征。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從安東尼的政治王國的廢墟上站起來這么一個失敗了的但是富于人情味的政治家。莎士比亞按照他的認識,似乎要告訴我們:權勢——作威作福的政治權勢,和正常發展的“人性”是不能相容的。在莎士比亞的另一個悲劇《李爾王》里,李爾王這個專橫的暴君就是這樣,他是在喪失了他的統治地位,被趕出了宮廷,流落在民間之后,才恢復了“人性”,開始懂得了愛的意義。
一旦在政治舞臺上倒下之后,失勢的安東尼在對待他的部下和侍從時,顯示出他懂得了珍惜人和人之間的感情的交流,意識到他們和他是同樣具有人格的人,他和侍從們一一握手:“把你的手給我,你為人一向忠心耿耿——他也是——你——還有你——還有你。”他甚至流露出那樣一種思想,那是趾高氣揚的小愷撒絕對不可能在他侍從面前表達的:
我但愿自己能化身為這么多人,
而你們大伙兒,合而為一個安東尼;
那我就可以為你們盡點心力了,
就像你們曾經盡心侍候過我。[7]
主人和他的仆從們可以對調一下地位,主人也可以倒過來侍候他的仆從,這種帶有民主色彩的思想,安東尼過去是沒有的,更不用說小愷撒了——他總是奴隸主般把他的部下僅僅看做可以供他驅使的工具罷了。
在安東尼輕率地決定海戰之前,曾經有一個老兵規勸他不要在海上作戰;現在他再次出兵,決心阻擊敵人,又遇到了那個忠誠的老兵。安東尼一眼認出了他,跟他提起了前事:
只恨當初你和你那一身傷疤
不曾使我聽從你,在陸地上作戰!
一個主將能向他的兵士說出這么兩句話是很不尋常的,安東尼既表揚了老兵的忠誠、戰績(一身傷疤),又把部下當作戰友,在他面前承認自己的失誤,那說話的聲調中有著不容懷疑的誠懇。
表現得最有戲劇性的是他跟部下艾諾巴勃斯的關系。艾諾巴勃斯是安東尼的親信,他看到主子實在太不爭氣,懷著恨鋼成了鐵的絕望心情,背棄了安東尼,投奔到敵人的陣營去。安東尼聽到他的叛變,說了這樣一句話:“唉,我的命運叫忠心的漢子變了節!”
他完全理解艾諾巴勃斯出奔時的痛苦心情,沒有一句譴責的話,他還是用平時的眼光看待這“忠心的漢子”。他吩咐快把艾諾巴勃斯留下的錢財全都給他送去,還由他親筆簽名附信問候:“希望他今后再沒有理由要另換主人了。”
這句話里有這樣的意思:一個愧對自己部下的主將沒有權利要求部下的絕對忠誠。他把上下級看成一種相對的關系,并非絕對的關系。因此他要用溫暖友好的話去解除逃將的思想負擔。身敗名裂的統帥卻顯示出了一種寬宏的胸懷。
投奔到愷撒陣營的艾諾巴勃斯親眼看到了新舊兩個主子的不同——在人和人的關系上所表現出來的鮮明的對比。他后悔了。他決不愿意幫敵人去打安東尼,他要去找一條最污穢的泥溝了結自己的殘生。一直批評安東尼的艾諾巴勃斯,臨死的時候卻一聲聲呼喚著安東尼:“安東尼啊,你有多么的高貴,就越發顯得我這叛徒有多么丑惡!”
艾諾巴勃斯的死,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審視安東尼的形象。安東尼是一個徹底失敗的政治家,但是在這個失敗了的政治家后面卻站起了一個富有人性的人;他懂得了珍惜人和人之間感情上的交流,甚至把統帥和普通兵士的距離縮短成兩個戰友之間的關系。正是這一個政治上失去了權勢而人格上發出了光彩的安東尼,在我們的心目中站了起來,成為一個大悲劇中的主人公。
他在埃及女王的懷抱里閉上了眼。在安東尼的沉浮榮辱的一生中,本是交替出現著他的兩個身份;臨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這個曾經干下轟轟烈烈業績的羅馬統帥已拋棄一切,為了愛情死而無怨。愛情是他作出的人生的最后選擇。
埃及女王身上有許多缺點,莎士比亞看得非常清楚,也無意為她護短。但是一個藝術家的道德意識和體現他的審美意識的形象思維并不總是一回事;而一部作品的藝術性內涵也并不總是能完全納入道德化的思考范疇。為了賦予埃及女王這個妖艷的女性形象以不可抗拒的藝術魅力,莎士比亞可說使出了渾身解數,而并不問一下,在這樣一個不太體面的尤物身上傾注他的巨大的藝術才華是不是浪費。他喜愛他的埃及女王,可說是“愛而知其過”。他把他創造的這一個女人送到觀眾面前,要他的觀眾同樣感染到這種喜悅,為埃及女王而笑,為她而悲痛——你還沒來得及跟理性商量該不該喜歡她,先就給她的藝術形象迷住了。
前面說過,安東尼有雙重身份:政治家安東尼和作為情人的安東尼。埃及女王卻只容許他一個身份:永遠做她身邊的愛情的俘虜。她不僅把安東尼的妻子——在羅馬的富爾維雅看做她的情敵,就連政治家安東尼也被她看成了情敵。她用盡心計要安東尼在她的花天酒地的埃及宮廷里樂不思蜀,要安東尼為了她而把羅馬整個兒都忘了。
在成天追求歡樂的埃及宮廷里,忽然闖進了羅馬的使者,是告急而來。埃及女王立刻警惕起來,她決不容許羅馬的政治世界把她的安東尼從愛情王國里奪過去。她立刻加強她的“思想工作”,因此很有意思的是,他倆一上場,我們就聽到在進行著一次“愛情的拷問”——拷問安東尼對她到底忠誠到什么程度:
要是真算得上愛,告訴我,有多深。
可以量深淺的愛,未免太貧乏了吧。
我要立個界限,愛我能愛到多遠?
羅馬的使者可以拒絕接見,但是羅馬的嚴重局勢卻挾著一股極大的沖擊力量而來,不容許任意擋駕。安東尼的迷夢終于被驚破了。他下了決心:必須趕快回到羅馬的政治世界去。
他前來向她告別了。為了討得她的一聲“你去吧!”說了許多非走不可的理由;為了使她放心,又把妻子的情況告訴她:“富爾維雅死了。”丈夫提到妻子去世,竟然這么平淡,這么不動感情,只有那么一句話,應該讓埃及女王感到滿意了吧——她心里完全明白,那不近人情的冷淡,是因為安東尼的那顆心完全被她抓過去了。
安東尼說了一大堆話:羅馬的緊張的政治局面,緊急的軍事形勢,她明顯地表示不愛聽。羅馬這一個政治世界她一點也不了解,也一點不想了解;她讓安東尼嘮叨了半天,她一無反應;可是一聽說“富爾維雅死了”,那反應卻是十分敏捷,十分強烈。
她立即轉過身來,和安東尼臉對著臉。她第一件做的事,細細察看了對方的眼膛——果然是干干的,和干巴巴的語氣完全配得起來。這應該使她滿意了吧?不,她還不能放心,難道安東尼在內心深處連一絲一毫夫婦之情都沒有了嗎?當真被她埃及女王的濃艷的戀情榨干了嗎?會不會是安東尼在哄她呢?她故意裝出拒絕相信的神氣,試探一下:
盡管年齡改不掉我的癡癡癲癲,
倒是去掉了我的幼稚:聽什么,
就信什么。富爾維雅能死得了嗎?
安東尼的回答還是那么平淡、干脆:“她死了,我的女王,”而且交出羅馬的來信作證。她卻忽然貓哭耗子,假慈悲起來,故意責備安東尼不該那樣無情無義:
最沒良心的男人喲!
本該盛滿了
悲哀的淚珠的一雙水晶壺在哪里呢?
她是決不容許安東尼的眼眶里有一滴淚痕的,然而卻偏要為此而責備對方,故意把安東尼對妻子的無情扭曲為對她自己的無情。
現在我看清啦,看清啦,富爾維雅死了,
只落得這么個光景,將來我死了,
也無非這回事罷了。
不管安東尼一遍又一遍表白自己的心跡,總是不能博得她的滿意,稱許,她總是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受委屈的、聽信了花言巧語的可憐的癡心女子。在愛情的王國里,他倆分明不是處在平等的地位上,她是女王,有權要求她的臣子絕對忠誠,她只是責問:你貢獻給我的愛情就這么一點兒嗎?而她自己卻不必作出任何應諾。
安東尼在他難得清醒的時刻,也想要掙斷“這牢固的埃及鐐銬”;而女王怎么也不讓她的俘虜從她的掌握中掙脫出去,格外加強她的束縛。她施展出渾身解數,她把女性的一顆心、整個靈魂都投進去了。結果那柔韌而堅強的無形鐐銬在把對方鎖住的同時,把自己也緊緊捆綁住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主宰和她的俘虜,誰也別想擺脫誰。她的生命中少不了安東尼,就像安東尼舍不下這條“尼羅河的花蛇”。
一旦安東尼離開了埃及,剩下她獨自一人的時候,她頓時感到生命中出現了一大片空白。她像熱戀中的姑娘,沉浸在遠方的思念中。她和安東尼的關系開始轉變過來了。她不再高高在上了,受崇拜的不是她,而是她的英雄安東尼了。
埃及女王簡直是不可捉摸的。隨著劇情的發展,她每一次出場,都顯示出她不同的精神面貌、不同的情緒,有時在一場戲里,她的情緒也在不斷起伏變化。她尊貴、驕傲,像一只艷麗的孔雀;又是狡猾、柔媚,像狐貍、像貓咪、像花蛇。當她聽到安東尼在羅馬已和另外一個女人結了婚,她傾瀉在可憐的報訊者頭上的那一腔怒火是可怕的。她拳打腳踢,已忘了自己是個女王,已不像是一個女人,簡直是一頭受傷的母獅在大叫大吼!
在海戰前夕,她硬要替安東尼制訂作戰方案;雙方交戰,她非要親自上陣不可,結果招來了海軍的覆沒。安東尼的一世英名固然隨風而去了,女王的驕寵和自信也完全喪失了。她來到安東尼面前,只會低聲下氣地乞求寬恕。即使安東尼向她承認:“我這顆心是用纜繩縛在你的舵上,”她也還是只有一句話:“原諒我,原諒我吧!”再不敢分辯一句話。
匍匐在安東尼腳下,流著眼淚,知錯認罪、接受安東尼安慰的克莉奧佩特拉,和當初像愛神般接受崇拜的女王形象完全不一樣了。兩人之間的關系對調過來了。從此以后,對于安東尼,她過去那種賣弄風情、迷惑男性的小手段一齊收斂起來了。最后,她決心殉情的時候,喊出了:
丈夫,我來啦!但愿憑我這勇氣
表明我無愧于做妻子的名分。
這會兒,她體會到,在她自身內,正經歷著一個感情的升華和凈化的過程。現在她“從頭到腳,像大理石一般堅定”,“那變幻無常的月亮,再也不是主宰我的天體了”。這可以看做是她對于戲劇開頭人家批評她“婊子”、“吉卜賽人”的一個回答。
安東尼死在她的懷抱中之后,悲哀欲絕的女王可說洗盡鉛華,歸絢爛于平淡。她跟女王的地位、人間的富貴權勢告別,說道:
別叫我女王——不過是平凡的女人:
平凡的感情支配我,就像支配那
擠牛奶、干最骯臟的活兒的丫頭。
女王把她和安東尼二人間的愛情一下子擴大為千千萬萬的人們所共有的一種精神財富。人間最純潔、最可珍惜的感情就蘊藏在平凡的人們的日常感情中,為千千萬萬人所共有的愛情既是平凡的,又是偉大的。她和她的安東尼,憑著他們的愛情,不是作為特殊的大人物,而是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參加到千千萬萬人的行列中來了。這是愛情的升華,是感情的凈化。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里,她激情奔放,傾吐出對于安東尼的熱烈的愛情。她以迫不及待的心情歡迎死神的降臨。死,在她眼里并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被中斷了的愛情的延續。她急于去追隨先她而去的安東尼,在那里,他們那濃烈的愛情再不會受到任何干擾了。使人毛骨悚然的響尾蛇在她的眼里一點也不可怕。她死得那么從容。她把死看得那么美、那么富于詩意——毒蛇在咬她的胸口,她說是:
安靜,安靜些!你沒看見我那嬰兒
在我的胸口吃奶,讓它的奶娘
就這么睡去嗎?
她把生命和死亡的界線取消了,愛情卻和死亡連結在一起,她說是:“死神的一刺,就像情人輕輕地一掐,雖然疼,卻是好稱心適意。”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風流絕代的埃及女王仍然在表明:她是一個為愛情的歡樂而生、為愛情的歡樂而死的女人。她的語言是多么富于感情色彩,多么富于個性啊!她想到的不是去死,而只是去赴情人的約會,惟恐失去了屬于她名分的那重逢時的第一個吻。
女王像安然入睡般死去了,她的頭略微側了一下。她的侍女夏蜜安看到了,說道:“你的王冠歪了,讓我來替你戴正。”
這里是一個富于象征性的細節。全身盛裝、戴正了王冠的女王,就像彌補了過去的小節上的虧損似的,臨別人間,給人留下一個莊嚴、完美的印象。她的殉情具有一種在強大的惡勢力面前,弱者(一名聽憑擺布的女俘虜)挺身反抗,保衛自己的愛情的悲壯意味。她把自己的死看做對強權作斗爭,挫敗強者的手段。
在安東尼和埃及女王這一對情侶之后,小愷撒就是這個悲劇的第三號重要人物。以愷撒為代表的冷酷的羅馬政治世界,和縱情聲色、追求人生歡樂的埃及宮廷,在悲劇中構成了交替出現的兩個對立面。在愷撒這個政治家的身上體現了一種冷酷無情的處世原則。這是戲劇的第二個主題。整個戲劇是以“縱情”和“無情”這兩個主題交織而成的。
莎士比亞筆下的羅馬政治世界是一個骯臟的、充滿著政治陰謀的世界,那里只有爾虞我詐;為正直的政治家勃魯托斯所信奉的道德信念(見《居里厄斯·愷撒》)早已不存在了。我們且看“戰船設宴”這一場戲吧。曼那斯私下向龐貝獻策,趁宴席上酒酣耳熱之際,暗中砍斷船纜,把戰船駛到海心,殺了羅馬三雄,那么天下就屬于龐貝一個人了。這個計謀給龐貝駁回了,但并不是因為這事做不得(主人殺害賓客,違背傳統的道義精神),而是不該下手之前找他商量:
要是你背著我去下手;我事后會覺得
這一手干得真漂亮。可是現在我
不得不斥責這陰謀。[8]
古羅馬面臨著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龐貝叛亂了。安東尼不得不匆匆趕回羅馬,和愷撒、萊比多斯共同商討對策。這羅馬“三執政”中,安東尼是當時舉足輕重的第一號政治人物;愷撒則野心最大,城府最深,蓄意擠掉其他二人,好一人獨霸;但他又知道,在目前,光憑他一個,或者光憑他和萊比多斯兩個,是對付不了那緊急的局面的,必須借重安東尼的威信;出于眼前利益的需要,就得拉攏安東尼,于是在那唇槍舌劍的政治會談中,一個建筑在政治聯盟上的、毫無感情基礎的親事被提出來了。
在埃及宮廷里的人,充滿著七情六欲。他們只知道尋歡作樂,最后終于樂極生悲,自取滅亡,但是劇作家要我們看到,在那兒,人和人之間卻很少隔閡,他們個個都是有說有笑、有血有肉的人。
古埃及和古羅馬,在這個悲劇里,是奉行著不同生活原則的兩個世界。把這樣兩個世界衡量一下,我們也許可以理解了:安東尼趕回羅馬,正當他重整旗鼓、仿佛另有一番作為的時候,為什么忽然又一下子拋開了新婚的妻子,不顧利害得失,又溜回到尼羅河邊去找他的“小花蛇”呢?他本是堂堂的羅馬軍人,羅馬政治領袖,可是他在埃及宮廷受到的“情感教育”,潛移默化地把他這個羅馬人改造過來了,現在一旦重新跨進那個冷酷的政治世界,扮演一個戴著面具的角色太不好受了,他憋得慌。那種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也使他難以忍受。這時候,他忽然明白過來了,就像有一道亮光透射進他的心田,原來他的故鄉是在埃及,不是在羅馬!他不顧一切,渴望回到人的感情生活中去,他要松快地透一口氣。
如果說,安東尼和埃及女王縱情聲色是濫用了感情;那么對于小愷撒,人和人之間沒有感情可言,只是利用和被利用的關系。他利用“親愛的”妹妹去拉攏安東尼;利用安東尼的政治威信,把準備向羅馬進軍的龐貝穩住了,然后又利用萊比多斯,向龐貝宣戰;解決了龐貝,又翻過臉來把萊比多斯擠掉。在大大地擴張了勢力之后,就找個罪名,再來吃掉安東尼。
在這世界上再沒誰比埃及女王對愷撒更了解了。埃及女王是一個完全沉溺在感情生活中的女人,從她眼里看來,這種冷血動物簡直不成其為人。她用殉情來回答愷撒對于她別有用心的安撫。
在這個悲劇中,愷撒雖然取得最后勝利,他卻使我們不寒而栗,覺得這樣的人不值得羨慕。安東尼和埃及女王雖然是一場政治斗爭中的失敗者,可說是自取滅亡吧,他們身上的缺點是明顯的,但是我們的同情卻涌向他們!在安東尼自殺后,莎士比亞通過劇中人物說得好:“神啊,你把一些缺點給予我們,好使我們成為人。”[9]
這一對情人,雖然有缺點,他們是人,是有血有肉有情的人;是通過現實的教訓,有可能改正、提高的人。而愷撒不能說是真正的人,他只是冷血動物。
很難說愷撒的所作所為怎么樣傷風敗俗(他干下許多背信棄義的事,但是并沒有在舞臺上表現出來)。他幾乎可以被人當作一個正面人物看待。愷撒并不是理查三世那種大壞蛋,讓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反面人物;他倒是和托爾斯泰筆下的卡列寧,曹雪芹筆下的賈政,有更多的相似之處。劇作家不是從一般的倫理道德觀念去否定,而是更多地從審美觀念的角度暴露、批判愷撒的冷酷無情。這樣的批判意義也就更深一層。
歷史上的克莉奧佩特拉,從古代、中世紀到十七世紀,一直受到嚴肅的道義上的譴責,她始終被看做一個荒淫無恥的女人。可是到了莎士比亞筆下,埃及女王卻成為眾生所愛慕、贊美的對象了。女王儀態端莊、從容殉情后,悲劇結束在為她和安東尼升起的一片歌頌聲中。這位為情而生、為情而死的人間尤物已經超乎世俗的道德范疇了。盡管龐貝代表世俗觀念,把埃及女王看做一個淫婦:但愿她用“妖術”、“美貌”、“淫蕩”去迷住那個“酒色之徒”安東尼;可是緊接著,在下一場戲里,劇作家讓安東尼的部將用絢爛華麗的詩句描述她那令人目眩心搖的嬌艷、傾國傾城的風韻:
哪怕她在賣弄風情,
最神圣的祭司也要為她祝福呢。[10]
本來,荒淫無度只能是一種不道德;而老謀深算,在追權逐利的人眼里,才是一種值得贊美的德行;但是在這個悲劇里,這樣一條道德和不道德的界線隨著劇情的發展,逐漸淡化了,消失了。而另一條界線,從道德范疇向美學的領域延伸,卻被提出來了:有情和無情。情,區分了美和不美;因為在人文主義者眼里,為愛而激發的熱情,就像無煙的藍色火焰,是十分美麗的。
追求人生歡樂的埃及宮廷和冷酷的羅馬政治世界,在這個悲劇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杰出的人文主義劇作家仿佛要對人們說:無情最可怕,縱情勝無情。這其實也就是整個結構宏大的悲劇的主題思想。當然,今天的讀者要認識到,主題思想的重點是在前半句;肯定及時行樂的縱情,那只是在一定條件下的肯定,是有所保留的肯定;而批判卻是絕對的(在今天說來也還是有意義的):無情最可怕。
注釋:
[1]Coleridge:Essays and Lectures on Shakespeare (1930),p.97.
[2]D.Zesmer:Guide to Shakespeare(1976)p.364.
[3]W.Hazlitt: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s Plays,p.73.
[4]C.Sisson:“Shakespeare:the Complete Works”(1953), p.1125.
[5]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1974), p.1346.
[6]Bradley:“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1901),載Casebook Series,p.80.
[7]見第四幕第二景。
[8]見第二幕第七景。
[9]見第五幕第一景。
[10]見第二幕第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