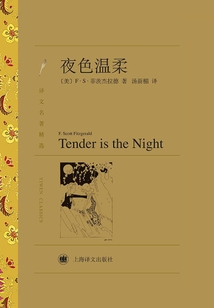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夜色溫柔》的創作與出版
馬修·J·布魯科里
創作
1932年夏
在“和平居”(La Paix),菲茨杰拉德聘用了他的第一位全職秘書,伊莎貝爾·歐文斯(Isabel Owens),給她每周工資12美元;以此,他準備對他的小說發起最后的進攻。歐文斯太太成了澤爾達(Zelda)的伙伴,斯科迪(Scottie)的代理母親,以及房子的管家。菲茨杰拉德放棄了梅拉爾基(Melarky)殺母和凱利(Kelly)船上生活的素材,新構想了一出發生在歐洲的故事情節,講的是一位美國精神科醫生,和一位富有的精神病人結了婚,這段婚姻把他給毀了。菲茨杰拉德無法完成小說的最初幾稿,這可歸咎于對殺母情節的素材缺乏堅持。1932年,他獲得了讓他感觸頗深的素材:澤爾達的精神崩潰和他自身狀況的惡化。他在繼續創作這部必須為他重振名聲的小說時,有一大籮筐的痛苦情緒可以利用。寫作《夜色溫柔》(Tender is the Night),成了他的一種嘗試,嘗試去理解自己是如何失去了一切曾經贏得的東西,一切想要得到的東西。
1932年8月,在他的《總賬》(Ledger)中,他記下:“小說的情節已經想好+結構已規劃,不會再長時間地擱淺了。”這個規劃包括16頁的故事匯編、人物速寫、表格,以及工作時間安排。
總體大綱
這部小說應達成以下目的:展現一個天生的理想家,一個被慣壞了的牧師,由于各種原因,屈服于中上層階級的理念,在登上社交界頂峰的過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和才華,開始酗酒,放浪形骸。背景之一是有閑階級在其最風光+最耀眼的時代,就像墨菲一家(Murphys)[1]。
主人公生于1891年,是像我自己這樣的一個男子,出生在一個由中上層資產階級落入小資產階級的家庭,但所受到的教育仍然花費不菲。他擁有一切天賦,在耶魯度過的歲月相當成功,但也不完全成功,卻還是得到了羅德獎學金,最后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取得學位+用一筆遺產出國到蘇黎世學習心理學。26歲時的他,前途似乎一片光明。然后他愛上了一位女病人,她由于年輕時的一樁事件,對于男性產生了一種奇異的殺人狂傾向。除此以外,她是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放蕩女。他“調整”了自己+她愛上了他,而他也回應了她的愛。
在戰爭中非現役服務了一年之后,他回來和她結婚+瘋狂地愛著她+為了將她完全治愈而全身心地投入。她出身于貴族家庭,父母一方來自美國,另一方來自歐洲,她年輕、神秘+可愛,是一種新的性格。他將她治愈了,方法是聲稱讓她達到一種穩定+他相信當下的秩序,而這種秩序其實他并不擁有,他事實上是一個相信共產主義的自由理想主義者,是一個叛逆的道德家。但他多年以來生活在恩惠當中+生活在資產階級中,把他給慣壞了,他結婚的時候,是個內心分裂的男人。在戰爭當中,他開始喝酒+婚后繼續偷偷地喝。照顧她的難度超乎他的想象,他內心越來越支離破碎,但外表一直保持著一副完美的容貌。
他在社交場合魅力四射,登峰造極,而內心卻變得墮落腐朽;就在這當口,他在里維埃拉和一位年輕女演員相遇,她愛上了他。對于這件事的一切后果,他盡量克制住自己不要害怕,而將他四分五裂的內心暫且拼合在一起的,也只有他外表的美好了。他也知道,他對她的愛,比不上自己曾經對妻子的愛。盡管如此,情感克制的效果就是,在他偷偷酗酒,過另外一種他自己的生活時,驅使著他去勾引他遇到的所有女人。對于這另一種生活,他的妻子并不知情,或者說至少他以為她不知情。他有一次離家,在羅馬和那位女演員在一起,他們的這場婚外的戀情令人失望,而且來得太晚,那次他還被警察毒打了一頓。回到家,他發現她并沒在休養,卻實施了一場謀殺,他懷著一腔厭惡,設法幫她掩蓋,而且成功了。然而,這卻向他表明,游戲結束了,他必須上演一出激烈的+深沉憂郁的舉動,來拯救她,因為他正在失去對她+他自己的控制。
他和一個非常強有力+魅力十足的男子有著點頭之交,認識一段時間以后,他現在故意要將他和他妻子帶到一起。當他內心懷著嫉妒和痛苦的時候,他發現這件事已經撮合成了,然后他離去,心里知道自己已經將她治愈了。他將疏于管教的兒子送去蘇俄,在那里接受教育,自己回到美國,做個庸醫。這樣他既在他的妻子身上實現了他的中產階級的感傷主義的想法,也在他的兒子身上達成了他的理想,+現在他自己就是一具軀殼,只要在舊有的秩序下活下去就行,別的什么都不要緊。
(更多大綱)
《酒鬼的假日》(The Drunkard’s Holiday,作者原來的書名)將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部展現英才崩潰歷程的小說。與《美與孽》(The Beautiful and Damned)不同的是,使他崩潰的不是懈怠,而是真正悲劇性的力量,例如理想主義者內心的沖突,以及周遭情境迫使他做出的妥協。
這部小說計劃寫成十萬字出頭,分14章,每章7 500字,第一和第二部分各5章,第三部分4章——將會有一章或等量內容由回顧構成。
·······················
狄克
男主人公生于1891年。小伙子身形壯實,相貌俊秀,也非常聰慧,博覽群書——事實上他才華橫溢,有著極其強大的個人魅力。這一切都從一開始就安排好了。他是具有無限潛力的超人,以中產階級的眼光,第一眼看他就是這樣。然而,他缺乏一種韌性——布朗庫西、萊熱和畢加索身上的那種粗獷,他全然沒有。他的外在特征,可以任意采用這些人的:杰羅德·墨菲、歐內斯特·海明威、本·菲尼、阿奇波爾德·麥克利什、查理·麥克阿瑟,以及我自己。然而,他看上去像我。
缺陷——例如急于擠入上流社會、飲酒、不顧一切地粘在一個女人身上、最后患上神經癥——都是逐步顯現的。
我們跟隨他從34歲到39歲的歷程。
狄克的實際年齡
1891年9月 出生
1908年9月 進入耶魯
1912年6月 20歲從耶魯畢業
1916年6月 從霍普金斯畢業。前往維也納(在那里8個月)
1917年6月 一年后,從事了其他工作,然后到了蘇黎世。26歲。
1918年6月 在蘇黎世取得學位。26歲。
1919年6月 回到蘇黎世。27歲。
1919年9月 結婚。28歲,之前拒絕了大學的神經學研究員席位,成為了診所的病理學家。或者他接受了?
1925年7月 5年又10個月的婚姻后,將近34歲。
故事開始
1929年7月 9年又10個月的婚姻后,將近38歲。
妮珂的年齡
總是在當年年份上減一。
1901年7月出生
之前求愛兩年半,自從她13歲時開始
災難 1917年6月 將近16歲
診所 1918年2月 17歲
10月中旬情況糟糕
停戰后情況較好
他于1919年4月或5月返回
她于1919年6月1日出院。將近18歲
1919年9月結婚。18歲
1920年8月孩子降生
1922年6月孩子降生
第二次復發,幾乎馬上就到了1922年10月,此后出現法國男人(或者是1923年夏天在結婚將近4年后出現的)
1925年7月故事開始時,她只有24歲
(一個孩子將近5歲(在胡安萊潘[Juan les Pins]時的斯科迪
另一個孩子3歲(在蘋丘[Pincio]時的斯科迪)
1929年7月故事結束時,她只有28歲
女主人公生于1901年。她很美,就像瑪琳·迪特里希那一類的演員,或者說更像諾拉·格雷戈——是有著琪琪·艾倫那樣一雙獨特眼睛的女孩子。她是美國人,有一點外國血統。15歲時被自己的父親強暴,是在很特殊的情況下——待定。她隨之崩潰,進了診所,16歲的她在那里遇到了比自己大十歲的年輕醫生,即男主人公。只有她對他的移情才能救她——當這不起作用時,她就會恢復殺人狂傾向,試圖殺死男人。她很純真,讀書很多,但沒有實際經驗,也沒有自己的方向,全靠他的給予。她是澤爾達的寫照——或者說,澤爾達的一個部分。
我們跟隨她從24歲到29歲的歷程。
對精神病這個素材的處理方法
(1)閱讀書籍,決定病例的大概類型
(2)準備一份囊括1916~1920年的診斷報告
(3)然后細看各個類別的素材,要復制的內容不要選太多
①E字母類目下選取
②F”””””
(這里不要用真實的材料)
③從其他類目下選取氣氛、精準度和素材,注意不要犯精神病學和醫學上的低級錯誤,但也不要炫技賣弄。只要用關系最不緊密的事實暗示就可以了。不要變得像醫生的故事。
必須避免福克納的態度,結尾不要變成小說化的卡夫艾賓(Krafft-Ebing)——最好是奧菲利婭和她的花朵。
對精神病這個素材的分類
A.描述
B.巴爾的摩
C.診所和剪報
D.舞會和初診
E.初入布蘭格林診所[2]——至1931年2月
F.佛雷爾(Forel)醫生(包括布洛伊勒[Bleuler]醫生的會診)
H.好萊塢
L.布蘭格林診所后期
M.我自己的信件和評論
R.羅塞林(Rosalind)和塞爾(Sayre)家族
S.斯奎爾醫生和日程安排
V.雜錄
這份規劃中還包括一張表格,將澤爾達和小說女主人公的病歷并列于一頁。
(335頁圖片說明:這是菲茨杰拉德列出的妮珂·沃倫和澤爾達·菲茨杰拉德的病歷對照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
女演員出生于1908年,她的演藝生涯與露易絲·莫蘭(Lois Moran)、瑪麗·海伊(Mary Hay)的相似——這就是說,她和大多數女演員不同,不僅僅是扮淑女,不單單是整天展現活力、健康和性感。與女主人公相比,她顯得臃腫,或者說將來會變得臃腫,而現在她年紀輕還看不出來。咪咪露普·維勒(Mimi-Lupe Velez)。
我們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她正處于演藝生涯最初的開端,已經拍了一部大片。
我們跟隨她從17歲到22歲的歷程。
這位朋友出生于1896年。他是一個狂放的人,長得像敦特(Tunte),也像會議室里那個皮膚黝黑的共產主義者。他有一半的意大利或法國血統,另一半是美國血統。他是個厭惡一切虛偽+借口的人(參考朗(Lung)那一類型,就像福斯·威爾遜[Foss Wilson])。他是那種能當部落族人或者共產主義者領導的人——一派貴族氣質,與資產階級毫不沾邊的國王。他為法國外籍軍團打了三年仗,然后一度操起畫筆,之后又去攻打摩洛哥北部里夫山的柏柏爾人。小說中他第一次出現,就是剛從那里回來,正尋找新的發泄途徑。他有錢,又有法國軍團的訓練——否則的話他一定會成為一個革命家。不論是做正事還是搞破壞,他都能干得不錯,但他的腦袋和男主人公比起來就差一些了。有點像珀西·佩恩(Percy Pyne),也有點像丹尼·霍頓(Denny Holden)。
我們看到的是28歲到33歲期間的他。
在重新規劃小說的時候,菲茨杰拉德從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紀錄片式的材料組織方式中獲得指引。馬修·約瑟夫遜(Matthew Josephson)的《左拉和他的時代》(Zola and His Time)(1928)一書中對此有描述。(《夜色溫柔》出版時,菲茨杰拉德寄給了約瑟夫遜一本,書上題有這段話:“若不是‘左拉’極佳的組織手法+你將其再現,這本書永遠不可能上架。”)在寫作這部小說的過程中,菲茨杰拉德脫離了最初的規劃;例如,妮珂在書中并沒有殺人傾向。這份規劃表明,從1932年最終確定情節開始,這部小說就不是對真實生活的直接轉錄。角色都是復合體。妮珂是“澤爾達的寫照——或者說,澤爾達的一個部分”,再復合上一個虛構的角色和虛構的故事。沒有證據表明澤爾達曾遭到亂倫的侵犯。
小說的手稿已經有了暫定的題目,叫做“酒鬼的假日”(這曾是菲茨杰拉德1919年計劃寫的一本小說的標題)。這份手稿所展現的是,菲茨杰拉德雖在挽回早先幾稿的精華部分,但1932年夏天的這本書是一部新的作品,綜合了他旅居海外時遇見的許多人和事。澤爾達的精神病——轉移到了妮珂·戴弗身上——是起到催化作用的經歷;但小說的主題寫菲茨杰拉德如何荒廢自己才華,這是由理查德·戴弗醫生的職業生涯來表現的,他代表著菲茨杰拉德的自我判斷和自我批判。塑造戴弗這個角色是相當復雜的,因為菲茨杰拉德同時將自憐和自卑注入了他。“戴弗”(意思是潛水者)這個名字,揭示了菲茨杰拉德對男主人公,以及對他自己的復雜而矛盾的感受。狄克·戴弗當然從前途無量墮入了身敗名裂,但他的全名在俗語中也有“吸雞巴的家伙”之意。戴弗之所以墮落,是因為他受到的不良影響,更是因為他自身就容易受這種影響。一言以蔽之,他是被有錢人給毀了;但令他崩潰的真正根源是他需要被人愛,被人仰慕,這驅使著他恣意揮霍自己的情感資本。戴弗醫生治好了他的病人兼妻子,卻犧牲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菲茨杰拉德在小說中治好了澤爾達的不治之癥,他這樣做,可能是試圖寬恕自己,減輕自己因為妻子的瘋病而感到的內疚——同時也是在懲罰自己的揮霍浪蕩。
《夜色溫柔》的題詞——“獻給/杰羅德和薩拉/快樂永在”——讓人一不留心就假定戴弗一家是墨菲一家的翻版。仔細一查,就發現這種假定不能成立。在包含殺母情節的版本中,派普(Piper)一家(洛爾拜克[Roreback]一家)的模板是墨菲一家,但在菲茨杰拉德的寫作和重寫過程中,他逐漸脫離了墨菲一家。墨菲一家在社交場合的特點和背景細節,遷移到了戴弗一家人身上;然而戴弗一家是虛構的——或者說是合成的——角色,比起和墨菲一家,他們和菲茨杰拉德一家更相近。菲茨杰拉德的“總體規劃”表明,即便是在最初階段,戴弗一家也并不是對墨菲一家的直接轉錄。狄克的外在特點是由墨菲、海明威、菲尼、麥克利什、麥克阿瑟和菲茨杰拉德組合而成的。約翰·奧哈拉(John O’Hara)后來告訴杰羅德·墨菲:“斯科特寫的是人生,不是各人的生活。這里有一部分原因是斯科特總是在寫人生。遲早,他筆下的角色都會成為菲茨杰拉德世界里的菲茨杰拉德角色……當然,他一路走過,就和真正的墨菲一家相距更遠了,更不相像了。狄克·戴弗最后成了十足的菲茨杰拉德……”
除了《人間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菲茨杰拉德從來沒有寫過一部直接取材于真人真事的小說(roman à clef)。然而,他的確一直從真實生活中萃取他的一些人物——有時候寫得和真人很接近。艾貝·諾思的原型明顯是林·拉德納(Ring Lardner),與查爾斯·邁克阿瑟也有一分相似,但他的生活經歷是虛構的。湯米·巴爾班是五個人的合體——愛德華·約占(Edouard Jozan)、馬里奧·布拉吉奧提(Mario Braggiotti)、湯米·希區柯克(Tommy Hitchcock)、珀西·佩恩和丹尼·霍頓。雖然菲茨杰拉德沒有將海明威指定為巴爾班的原型之一,但兩者明顯有聯系:巴爾班篡奪了戴弗在里維埃拉的王國,就好比海明威的文學名聲蓋過了菲茨杰拉德。巴比·沃倫的原型是薩拉·墨菲的妹妹霍伊特(Hoyt),但她的名字用在了露絲瑪麗·霍伊特身上。
在《夜色溫柔》中,露絲瑪麗是體現菲茨杰拉德角色創作手法的最佳例子,她是由虛構的弗朗西斯·梅拉爾基(Francis Melarky)和女演員露易絲·莫蘭兩者合并演化而來的。露絲瑪麗·霍伊特和露易絲·莫蘭相似,而在她身上發生的一些事情是從梅拉爾基草稿中挽回的。在創作過程中,菲茨杰拉德將早先版本中的主角,轉變成了最終出版的這部小說中的觀察者、反襯者的角色;但在整本小說中,露絲瑪麗的敘述視角并非保持不變。在梅拉爾基版本中,菲茨杰拉德嘗試采用了部分參與故事的敘述者(partially-involved narrator)這一手法,但又放棄了——原因大概是《夜色溫柔》的故事范圍太廣,一個角色無法全部觀察。
早先草稿中的材料并非直接轉用于戴弗版本。對挽回的內容,菲茨杰拉德進行修改或重寫,而且他也為新角色寫了新的材料。直到艾貝在第一卷第19章中離開巴黎,“酒鬼的假日”是以梅拉爾基的材料為基礎的,而小說的其余部分都是新寫的——除了對于狄克在羅馬被打一事的敘述,這部分原先計劃作為殺母情節的引子。這部小說是歷經多道草稿才最終完成的。寫作時,菲茨杰拉德一貫用的是鉛筆和無行線的法律文件紙。[3]他的秘書歐文斯將寫成的章節打字成稿,一份原稿(預留三倍行距以便修改)加上兩份復制稿。菲茨杰拉德在原稿以及單份或雙份復制稿上進行修改。然后最佳的修改版本將被重新打字,修改過程還會繼續。在每一個階段,菲茨杰拉德都會對文字進行修改潤色,使句子變得緊湊,并更換用詞。歐文斯回憶道:“他清醒的時候,工作狀態很不錯,非常順利。他很自覺,一般連續寫作兩個小時,然后停下,稍后回來再繼續。他喝酒的時候,就坐不定了,會從他的辦公室里走進走出。”
“酒鬼的假日”將在《斯科里布納雜志》(Scribner's Magazine)上連載,完整的打字稿是一份700多頁厚的雙倍行距稿件。菲茨杰拉德在打字原稿上作了修改(將其重命名為《戴弗醫生的假日:一部羅曼史》[Dr. Diver's Holiday:A Romance]),然后又修改了復制稿(重命名為《夜色溫柔:一部羅曼史》[Tender Is the Night:A Romance])。副標題“一部羅曼史”表明,菲茨杰拉德認為這本書脫離了虛構文學的現實主義或小說特有的模式。(我們不知道菲茨杰拉德是否熟悉霍桑[Hawthorne]對于為何將《有七個尖頂閣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定義為羅曼史的解釋,但是菲茨杰拉德在這里采用這個說法,和霍桑的用法是一致的,用來指稱一種形式或技巧,它賦予自身“一種權利,在很大程度上,能將{人心}放置在作者選擇或創造的情境下,以展現其真相。作者如果認為需要,也可以操控他的氣氛媒介,調節光線明暗,深化并充實畫面的陰影層次。”)菲茨杰拉德后來向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將其描述為“我信仰的證明”,《末代大亨的情緣》(The Love of the Last Tycoon)也會有“一部羅曼史”的副標題。
雖然“戴弗醫生的假日”對于“酒鬼的假日”而言是一種改進,但菲茨杰拉德擔心這個題目會讓讀者以為故事是關于醫生的。《夜色溫柔》取自濟慈(Keats)的“夜鶯頌”(“Ode to a Nightingale”,菲茨杰拉德稱自己每讀一遍,必哭一次),這個題目讓菲茨杰拉德感到滿意;但需要說服帕金斯([Maxwell]Perkins)和《斯科里布納雜志》的一些人,因為這個題目不“好賣”,給不了買家關于作品內容的提示,菲茨杰拉德也曾考慮過一個中性的題目“理查德·戴弗”。《夜色溫柔》及其引語(“我已經和你在一起!夜色那么溫柔……/……不過這里卻沒有別的亮光,/除了有一線天光被習習和風吹過/灰暗的綠蔭與迂回曲折的苔徑。”)喚起了那種彌漫在菲茨杰拉德的羅曼史中的失望情緒。濟慈的詩所表達的是試圖逃脫痛苦的現實,結果又重回不幸。這首詩的最后幾行表達了狄克·戴弗在小說結尾處悵然若失的心境:“這是個幻覺,還是夢寐?/那歌聲去了:——我是睡?是醒?”
出版
1934年4月
《夜色溫柔》的開場是1925年夏天的里維埃拉。年輕女演員露絲瑪麗·霍伊特在那里遇到了一對極有魅力的美國夫婦,迪克和妮珂·戴弗。戴弗家的交際圈內有一位酒鬼作曲家,艾貝·諾思;還有湯米·巴爾班,美籍的法國雇傭兵,此人愛上了妮珂。露絲瑪麗則為迪克所傾倒。一段倒敘道出了原委,迪克和妮珂·沃倫結婚時,是一位年輕有為的精神科醫生。妮珂是一位富裕的精神病人,曾被自己的父親強暴。作為她的丈夫和醫生,迪克越發感覺難以堅持自己的專業觀點,疏忽了研究工作,妻子的財富也同時助長了他奢侈的生活作風。用沃倫家的錢,他成了瑞士一家診所的合伙人,但最后被迫離開,原因是他對工作已經不再專心投入——酗酒就是體現。在一趟羅馬之行中,他與露絲瑪麗圓滿了兩人的關系,后因酒后爭斗而被警察毆打。1929年,戴弗一家重返里維埃拉,迪克酗酒更兇了,而妮珂也離他而去,投奔了湯米·巴爾班。迪克試圖在美國重操舊業,但最終成了一個碌碌無聞的小鎮醫生,湮沒在人海中。
在記敘迪克·戴弗走向沒落的過程中,菲茨杰拉德也在試圖解釋自己從1925年開始的意志消沉。他認識到,造成兩個人這種情況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對性格的一種浪漫觀念。迪克“他常常想他要做個好人,和善、勇敢、睿智,可是這一切很難。要是可行的話,他也要為人所愛。”[4](第二部第4章最后一段)迪克的敏感神經在他遇見妮珂之前就已經有了——就如同在遇見澤爾達之前,菲茨杰拉德的性格就已經形成了。做出和尼科爾結婚這一決定,并不是因為沃倫家的錢,然而她的錢最終卻消磨了他對工作的專注。他娶她是出于他需要有人對他有所求,需要有人派他用處。但迪克的慷慨并非毫無私心,因為他需要那種由他激發的“情感的狂歡”。(第一部第6章中間)他對露絲瑪麗的迷戀清晰地指明,在小說開場時,他惡化的進程已經相當深入了。他引人愛慕,其代價便是不斷耗費他的精力,而勤奮的男人本該把這能量留給工作。妮珂的力量不斷上升,而他卻是在走下坡路,當上升下降兩條曲線交匯時,迪克做出了職業決定,讓他的病人兼妻子“出院”。妮珂已經準備好了分手,但迪克迫使她宣告她的獨立:“病案真正結束。戴弗醫生終于自由了。”[5](第三部第9章最后一句)迪克·戴弗的惡化看得讓人心里很不好受,因為他是被他性格中那些原本或許可以使他成為偉人的元素給毀了。他的雄心壯志逐漸萎縮成了“致命的愉悅感”。
這部小說從1934年1月開始連載在四期《斯科里布納雜志》上,1月雜志封面便是菲茨杰拉德的肖像。愛德華·申頓(Edward Shenton)為雜志所作的鋼筆畫插圖尤為成功,于是在出版成冊的書中保留了下來。連載共有12個篇幅較長的章節,這也正是菲茨杰拉德1932年的計劃。(書分成了三卷,共61章。)在雜志第一期中,刊載的是正式出版后的小說第一卷前18章——直到艾貝·諾思離開巴黎。2月的雜志刊出了第一卷的其余部分,還刊出了第二卷倒敘部分的前9章——直到迪克決定和妮珂結婚。3月刊中,倒敘部分連載完畢,第二卷以迪克在羅馬挨打結束。4月刊則是完整的第三卷。
菲茨杰拉德和斯科里布納出版社都期待著連載能引起人們關注,從而為書促銷,但實際上連載可能有損于《夜色溫柔》最初獲得的反響。兩期連載之間的30天時間使得小說的結構——包括時間先后順序的斷裂,以及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間敘述視角的轉換——變得模糊不清。菲茨杰拉德懷疑有一些評論家是看了連載以后才做的評論,所以力勸他的朋友們重讀小說的全本。出版日期前一個月,他寫信給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作者試圖為作品的部分失敗辯解,必定是荒唐可笑的——但我真的希望你,還有其他人,都能讀到全書,而不是雜志版本,那個版本有些地方是匆忙拼湊起來的。比如后半部分的外觀,現在已經精致得多了。”菲茨杰拉德在送給多羅茜·帕克(Dorothy Parker)的書中題道:“這比雜志更好。”連載版本中有六個小場景在書中刪去了。(書中刪去的場景包括:兩組描寫艾貝·諾思在里茲酒吧中的場景[第一卷];迪克在因斯布魯克和一個女人牽扯在一起[第二卷];以及迪克從父親葬禮坐船返回歐洲途中的三組場景[第二卷]。在連載之前,菲茨杰拉德從第三卷的打字稿中,刪去了關于湯米和妮珂在里維埃拉去看一伙美國歹徒幫的敘述。)唯獨在書中恢復的段落是雜志中不能刊載的涉性內容——主要是擴充敘述沃倫如何坦白自己與妮珂的亂倫關系。
菲茨杰拉德于1934年1月和2月前往斯科里布納出版社,修改校樣。他與約翰·奧哈拉和多蘿西·帕克在紐約共處了一段時間。奧哈拉當時正在完成他的第一部小說《相約薩馬拉》(Appointment in Samarra),他很感激菲茨杰拉德的鼓勵。(《相約薩馬拉》于1934年8月出版時,菲茨杰拉德的一句話用在了廣告中:“約翰·奧哈拉的小說證明了自從大戰以來美國作家正在大踏步地前進。”)菲茨杰拉德主動借錢給他,但奧哈拉婉拒了,因為他知道菲茨杰拉德手頭并不寬裕。
斯科里布納的編輯約翰·豪爾·惠洛克(John Hall Wheelock)后來說,與他共事過的作者中,唯獨菲茨杰拉德一人,喝醉了酒,還能把文字修改得更好。菲茨杰拉德一道又一道的廣泛修改校正,給校對工作增加了難度。出版成冊的書中有幾十處拼寫錯誤,也有時間順序上的不一致,使得迪克·戴弗走向沒落的過程變得模糊含混了。錯在作者,但斯克里布納出版社本可以仔細編輯,提醒他注意這個問題。
1934年2月12日,澤爾達從蒙哥馬利搬到巴爾的摩整整兩年后,又進了菲普斯診所(Phipps clinic)。她沒有好轉的跡象,菲茨杰拉德便將她轉往紐約州比肯的克雷格療養院(Craig House)。這是一家度假村式的療養院,每周最低收費175美元。澤爾達被禁止寫作,于是在1933年和1934年主攻繪畫。菲茨杰拉德與在巴黎時的朋友嘉瑞·羅斯(Cary Ross)一起為她安排了一場畫展。雖然畫展意在鼓舞澤爾達的志氣,但她卻覺得菲茨杰拉德占了上風,于是不愿積極參與。畫展于3月29日至4月30日期間在羅斯的畫廊進行,在阿爾岡昆酒店(Algonquin Hotel)還舉行了一場規模較小的聯合展覽,展出的是澤爾達的畫作和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的馬利翁·海因斯(Marion Hines)博士的攝影作品。澤爾達的畫展和《夜色溫柔》的出版正好重疊,菲茨杰拉德這樣做,可能是試圖對之前迫使她放棄她的小說創作而做出補償。畫展目錄冊上有一段雋語:PARFOIS LA FOLIE EST LA SAGESSE[6],目錄列出了澤爾達創作的13幅彩繪和15幅素描。畫家生平簡介中寫道:“她的作品是想象力和詩意的結晶,這些特質使她在大戰結束后的日子里幾乎成了傳奇式的人物,而她和她的丈夫則成了爵士時代年輕美國的象征。”她的畫作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兩幅菲茨杰拉德的肖像:一幅題為“短號手”(The Cornet Player)(由多蘿西·帕克購得),另一幅題為“樹叢中的肖像”(Portraits in Thorns)(未出售)。兩幅肖像畫現在都下落不明。(澤爾達的一些畫作放在位于蒙哥馬利的一個棚中,在她死后,這個棚起火焚毀了她的畫。在二戰期間,她將自己的其他的畫作捐給了軍中的士兵當畫布使用,于是上面又覆蓋了其他人的畫。)
澤爾達的畫展開展時,她被允許暫離克雷格療養院。畫展的反響令人失望,全部收入只有328.75美元。《時代》(Time)雜志在評論這次“追求名望的最新嘗試”時寫道:“出自才華橫溢而性格內向的畫家筆下,這些作品畫面生動、具有強烈的節奏感。人物的腿和腳被放大,讓人聯想起她兒時跳芭蕾的那段略帶粉色的時光——這個小技巧她可能是從畢加索那里學來的。在表現一場達特茅斯橄欖球賽的一幅印象作品中,體育場被畫成戲院大門的樣子,球員就像是舞蹈演員。《中國劇院》(Chinese Theatre)展現的是一大團糾結的雜技演員,背景則看得出是觀眾。還有兩幅印象作品是她丈夫的肖像,以及一幅翠綠色的、邊框用擺成幾何形狀的電話線點綴的《鄉間春意》(Spring in the Country)。”澤爾達告訴《時代》雜志記者,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自食其力,但這場爭取獨立的嘗試失敗了。
關于寫作素材的爭吵令菲茨杰拉德一家十分不快,所以澤爾達直到《夜色溫柔》連載時才開始讀這部小說。就小說開始連載,她向菲茨杰拉德表示祝賀,并于4月從克雷格療養院給他寫了一封信:
這本書相當宏大。詩意的散文語言具有力量,使得振奮的情感一直延續,而角色面對著比他們所詮釋的人生更為強大的力量,只得屈從,這都非常感人。目睹一個人原本對其個人意志深信不疑,而最終屈服于無常世事的安排,讓人潸然淚下。這就是一本好書的目的所在,而你寫的正是這樣一本好書——那些面對自己顯得無助的人們,那優美的散文語言,顯而易見,對于這兩種表達的信念是堅定的。這是一部誠懇、質量上乘的書,是一份首創的文學貢獻,將在今后數年內成為作家們的關切。
在克雷格療養院,澤爾達并沒有好轉。1934年5月19日,她因緊張型精神分裂癥被送往“謝博德與伊諾克·普拉提”醫院(Sheppard and Enoch Pratt Hospital)入院治療。此時,菲茨杰拉德已經接受了澤爾達將不可能痊愈、他們將再也無法繼續共同生活的現實。在他的《筆記本》(Notebooks)中,他這樣寫道:“我再抱希望的力量,留在了那些通往澤爾達的療養院的小路上。”
(曹小川 譯)
注釋:
[1] 指的是杰羅德和薩拉·墨菲(Gerald and Sara Murphy),是旅居法國南部的美國富人,作者的朋友。
[2] 布蘭格林(Prangrins)診所位于瑞士尼翁(Nyon),澤爾達曾在此接受治療,后文提到的兩位醫生都曾為她診療。
[3] 法律文件紙(legal-size)是美國常用的一種紙張規格,大小是215.9 mm× 355.6 mm。
[4] 第168頁。
[5] 第382頁。
[6] 法語,意為“有時,瘋狂正是智慧”。